作者:王 澎
摘 要:
《纲鉴易知录》是明清纲鉴类史著的代表作。吴乘权强调读史之法,务求简易,采取繁简调和、简明易知、便蒙为基的编辑策略,令纲鉴类史著走向普及化与精湛化。伴随《纲鉴易知录》的流行,不仅出现购、借、赠、钞、让、藏等丰富多样的流通形式,该书也多被阅读引征、私塾所用,是贯通清代私塾教育至科举考场的重要历史教材。至近代,《纲鉴易知录》作为概念符号和史学资源被反复提及与运用,成为在新史学中不断发挥效用的旧史学因子,呈现断之不离、舍而难弃的现象,反映了近代历史教育古今交错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吴乘权 《纲鉴易知录》 纲鉴类史著 历史教育
《纲鉴易知录》(以下简称《易知录》)作为超越同类纲鉴类史书水平的典范之作,深度参与清代历史教育和近代史学更替及教育变革。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视作研习古代历史的“入门书”。然而受其普及性史书性质影响,《易知录》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历史书籍”,长期未得学界重视。实际上,吴乘权“欲求一读史之法”,试图为后世读史者提供最为简明易知的史学读本,这也令该书成为难以替代的基础教材。本文拟对《易知录》开展专门考察,探究其文本的知识构成,分析其撰述策略和旨趣,从而揭示《易知录》何以成为历经新旧史学更替,却始终发挥着历史教育功用的经典史著。
1
“欲求一读史之法”
吴乘权(1655~1719),字楚材,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平生兼具幕僚与塾师双重身份,曾任福建巡抚吴兴祚、闽浙总督范时崇的幕僚;也曾为塾师,课徒授业。康熙四十四年(1705),友人周之炯、周之灿“携其手辑《纲目全编》以示予读史之法”,三人理念相合,抄撮编辑而成《易知录》。同时,吴氏据友人朱国标《明纪钞略》续辑而成《明鉴易知录》,并付之梓,康熙五十年(1711)由尺木堂刊行。
《易知录》为纲鉴类通史著述,全书自三皇五帝至元顺帝计92卷,明纪15卷,共107卷,约180万字。该书主体部分源自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周威烈王以前史事按吴乘权所言,“然金氏有《前编》,尊之为纲,而目则变而云纪”。,且学界一般认为该书上古史纪辑录自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与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但比对文本可知,该书并非直取上述著作,以《王凤洲纲鉴会纂》为核心的纲鉴类史著才是编辑《易知录》所依赖的基础文本。《易知录》与《王凤洲纲鉴会纂》(以下简称《会纂》)、叶沄《纲鉴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内容高度重合,是继承发展以《会纂》文本为核心的前人纲鉴类史著成果而来。其中,周威烈王以前的上古史部分是抄撮众书而成,多采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质言之,前代纲鉴类史著是《易知录》的核心知识来源,是书基于此实现知识再生产。
《易知录》参考著作丰富,有近百部之多,其中对宋元明纲鉴类史著多所引证。书中宋以前多采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与刘友益《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以小注“发明”“书法”形式列于纲目正文后,宋以后则以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与周静轩《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为“广义”“发明”。对陈極《资治通鉴续编》、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丁南湖《通鉴节要》、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等书也多有参考。此外,是著对正史、诸子百家等著述也多有参引,有数十本之多。除删繁编辑前人“纲鉴”类史著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外,该书对涉及的典故句读、舆地沿革、字画音声多详加辨注,其中追加“注音”说明就有三百余条,足见吴氏等人编辑之用心。
就是书反映的史学思想来看,吴乘权推重经史,重视义理。全书围绕“五经”反复注释,常于“纲”“目”正文后以小字征引经文内容,“注音”之中也不乏征引说明。各史书记述和史家评论同样是吴乘权关注的重点内容,相较于其他纲鉴的杂采诸说,《易知录》多援引司马光、胡寅等史家论述。同时,多于“纲”“目”之中强调义例、笔法,“书法”“发明”“广义”不落其后,并在“注音”中多加探讨。如“杨广弑君”条,《易知录》引尹起莘评论来强调《资治通鉴纲目》“正名定罪”的笔法意义,并补注“许世子止弑其君”事,最终得出“除恶于微之意”的解释,以此凸显义理。同时,注重正统,规范统系。吴乘权对于政权的僭伪与正统自有判断取舍。以晋为例,《会纂》将晋并入“后汉纪”视为僭伪,《易知录》虽也尊蜀汉正统,但“后汉纪”仅附魏、吴。同时舍弃纲鉴常载的“吕秦牛晋”之说,不取司马睿为小吏牛金之子的说法。归根结底,吴乘权是为强调史法,以求引导。他具有明确的历史教育意识,认为史学教材的价值在于对学生“引导”有方。因此,他指明编辑《易知录》是为“欲求一读史之法”。“纂辑家就简删烦,名手错出,而微言奥旨,字义典实,略焉弗详。”他眼见“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亟欲申明“读史之法”,以求“引导”有方,便于历史教育,并最终实践在《易知录》的编辑中。
细究《易知录》的编纂工作,吴乘权以“欲求一读史之法”为编纂理念,以“宁简毋详”“宁陋毋雅”为编纂宗旨。务求繁简适宜、通俗了然,以致“易知”。基于此,吴氏采取如下几种策略进行文本编纂。
第一,继承优化,繁简调和。《易知录》继承以《会纂》为核心的纲鉴文本,对纲鉴模组和文本内容多加编辑取舍,形成一繁简适宜的史学文本。纲鉴的常见模组主要包括:历代先儒表、世系统系图表、纲目正文、潘荣《通鉴总论》、眉批、帝评、诸家注释评论、“《历年图》曰”、各朝总论(其中多引顾充《历朝总论》)、历朝歌诀等。《易知录》在保留历代先儒表、眉批、帝评、诸家注释评论这些基本模块的同时,精简优化。其中以诸家评论的择选最为突出。如两汉帝纪部分,《会纂》共引评论860条,《易知录》直接减选至177条。而与《易知录》同时期的以精简为诉求的《会编》,两汉部分仍择采评论230条,较《易知录》为多。《易知录》虽注重征引通鉴类著述的内容和评论,但也是达意即止。不再如明人纲鉴,追求名人效应,反复引述名士时贤评论,避免了征引琐碎的弊端。至于直接服务科举的眉批,《易知录》也及时做出精简和调整。《会纂》列眉批2001条,《易知录》只有606条。为因应科举,《会纂》列出“问沛公见羽鸿门与项羽不渡乌江得失何如”“拟汉春和赈贷诏”之类问答试题。因清代科举偏重首场,《易知录》及时调整,仅列简要标题,不再具体列出专门服务于第二、三场的拟题与史问。上述有关项羽的问题就直接简化为“沛公谢羽鸿门”。
同时,《易知录》优化纲鉴文本内容及注释,调和繁简。如“盘庚帝纪”的记述,《易知录》删去《会纂》纲目正文后的“苏氏曰”“胡宏《大纪》论曰”“王世贞曰”三条评论,并简化正文记述。又如“卧薪尝胆”相关记述,《会纂》为:“吴王许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易知录》直接优化为:“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至于注释,《易知录》在精简的同时,增补优化,增加六经注解,规范地理。《易知录》将《会纂》“苑台”注60字的内容,精简成“南距朝歌,北距邯郸,皆为离宫别馆”一句。将《会纂》并不确定的仲丁所迁之“嚣”地,明确注解道:“敖,今河南开封府河阴县。是时亳都有河决之患,故迁于嚣。”此外,书中凡逢六经典故及相关内容便出注明释,共有二百余处,可谓详尽。
第二,首尾贯通,简明易知。吴乘权为求“易知”,在统系、文本内容及注释方面颇下功夫。
首先,吴氏梳理出清晰简约的通史架构与继承统系,贯通古今。上古史因不易考证,往往记述驳杂,不成一简明统系。《易知录》厘清古史脉络,拨冗存信,较前人纲鉴记述为优,其对“五帝纪”的处理即是如此。《会纂》“五帝纪”载伏羲氏至帝舜三十位帝王事,与其他纲鉴大抵相同,甚至有所增补。《新刻世史类编》依托《会纂》记述,补入《荒史》内容,扩充至“太嗥史”“炎帝史”“黄帝七主史”三史三十一位帝王。《会编》对“五帝纪”虽有缩减,仍载十五位帝王。《易知录》将“五帝纪”帝王减省至八位,历史线索明晰,统系清楚明确。并舍弃纲鉴惯引的陈定宇、丁南湖、周静轩评论,增引“渭上南轩曰”凸显其择取的合理性。其称女娲至无怀十五世帝王,“多无稽不经之语,故姑阙之”。
其次,文本呈现与注释皆以明确易知为首要,应注尽注。为此,吴乘权指出《易知录》尽力做到以下六点:典故详明、舆图直指、别加黑圈、细分句读、校正字画、辨别音声。不同于以往纲鉴通常只择重点而注的特点,《易知录》“必指出为某经、传、子、史之某篇某章”,以图确然分晓。且对职官典制、人物事件、器物书目、专有名词乃至民俗节日等都详加注解,诉求易知。职官典制,其对“客卿”“啬夫”“录尚书事”“两税法”等条皆有详细注解。人物事件,如“赤松子”后《会纂》注“古仙人号也”而《易知录》直写“古仙人”,简洁明了;又如“孔子七十二弟子”条,《会纂》《会编》皆未出注,《易知录》则列出全部姓名,即阅即知。器物方面,器皿、动物、货币、宫殿等都注明特征属性,形象生动。对于“天家”“两京”“四辅”“浮图”这类专有名词,也会别加注解,年号更是随时注出。而节日如“寒食”等,都有繁简两种注法,随正文需要即时出现。至于字画音声更是该书特意注解之处,全书对异体字、通假字、难读字、需解字随时标出读音、字义和“平上去入”四调。如“劝光内其女入宫”,以小字标出“内”的“纳”音;“蝗出为灾,灾弥”,小字解“弥”为“米,息也,幸也”;“卒”字则小字标出其相通的“猝”字等,不胜枚举。统观之,《易知录》全书字画音声厘正标清,典故简洁详明如此,纲鉴类史著中少有更胜《易知录》的。
最后,对相关注释采用重复标注和“见前见后法”,反复提醒读者,以便有效“引导”,阅即“易知”。吴乘权深知“易知”的关键在于重复,反复注明既可让连续阅读者得以熟悉和温习,也会令随手翻阅或任取一卷阅读之人,对书中所涉字画音声、典故地理皆了然于胸,片纸即有所得。受传统纲鉴卷帙烦冗的影响,读者阅读文本及注解时多前阅而后忘,故有“既成童,经义通;秀才半,纲鉴乱”的说法。《易知录》同样面临“观前固昧后,观后亦遗前”的问题。有鉴于此,吴乘权充分运用“见前见后法”,令注解“复出则见”,极大消弭阅读障碍与卷帙不同所带来的文本断裂感。“则全部神理,首尾贯穿”,“更觉通体精神”。此法在全书主要有两种运用方式:一是直接用数百次的“见卷”“见上”等标出,勾连索骥,不断提醒读者;二是对字画音声、典故地理不断重复标注,令每篇注解如新,从而满足随时抽取阅读皆无所不知。通过如此反复地标注提示,“易知”且便于“引导”的诉求与理念自然贯彻实现。
第三,便蒙为基,雅俗咸赏。《易知录》与以《会纂》为代表的纲鉴类史著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以士子举业为根本,而前者以教授蒙童为核心,《易知录》有着更强的便蒙针对性。这也是吴乘权舍弃纲鉴向来标榜的名家评注的主要原因。“徒沾沾于句栉字比,审音训义之末”,即为“藏之家塾,以课弟子”,并非客套之辞。《易知录》也直接被视作“村蒙书”。一般的纲鉴类史著或也言及为童蒙所用,单就提供名家评说、举业所需拟问策题甚至展现史学见地而言,制举所用才是书坊制作出版此类书籍的主要原因。例如言称“世史便蒙”的《新刻世史类编》就是举业用书,而纲鉴更被视作应举的主要“途径”。
《易知录》继承优化前人纲鉴文本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纲鉴类史著的阅读门槛,将纲鉴真正落实到童蒙用书的专业水准,并获得巨大成功,从而产生深远影响,这是纲鉴类史著此前未曾实现的。“便蒙”的关键是如何将童蒙不晓的士人常识为之说清注明。满足此点则自然“易知”,粗识文墨者与底层文人阅读起来也无障碍,真正做到雅俗咸赏。同时,对于下层士人和普通读者而言,一本简明易知、雅俗咸赏的纲鉴,也打破了以《会纂》为代表的纲鉴类史著集中服务科举士子的知识壁垒。故而巡抚吴存礼大赞该书“繁简适宜,雅俗咸赏”,“信手拈一卷细阅之,无义不抉,无书不罗”,“名曰易知,良不诬也”。更有甚者,咸丰末年的女伶胖巧玲喜阅《易知录》,以致“常不离手”。
以下几例则生动诠释了吴乘权以便蒙为基的编辑实践。《易知录》考虑到孩童基础,对于“孙仲谋”“刘玄德”之类称谓,都会在旁加标小字“孙权”“刘备”,“老庄”这样的简称也会小字注明“老子庄子”。又如项羽斩宋义事,其中“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不听从也,羊愈牵愈不进),贪如狼(狼性贪),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一句,《会纂》《新刻世史类编》《了凡纲鉴补》诸书皆无,《会编》有此句却无小字注解。《易知录》择选此句并注明羊、狼习性,教知童蒙之意明显,也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此外,全书凡涉“六经”相关内容皆明确标出,童幼对于经典并不熟知,故处处令其明确知晓,从而关联平日所学经书,为其熟稔制举打下基础。即如元人郑镇孙所强调的,“辞之涉经若史也,幼学未知读也,此纂注不可不作也”,“为小学之基也”。
综上,吴乘权以“宁简毋详”“宁陋毋雅”的编纂宗旨和“欲求一读史之法”的编纂理念,务求《易知录》简明易知,从而呈现出“简”“明”“俗”的关键特征。纲鉴类史著发展至清代愈趋精简,此点与以《会纂》为代表的明代纲鉴类史著追求荟萃名家注解和评点的编纂理念明显反背。《易知录》是“明朝以来’纲鉴’类史籍长足发展的硕果”,也是清代普及性史书“走向精湛化的代表作”。一方面,纲鉴类史著虽始终是历史知识市场化的产物,但市场需求、编纂理念的变化革新,令纲鉴类史著在清代显现出新的态势与面貌。清代科举考试对历史知识需求的贬损与不重视,既促成简易纲鉴史著—《易知录》的产生,也让以便蒙易知为特点的《易知录》能够满足举子应试需要,得以流行。另一方面,纲鉴类史著产生之初即以诸史浩繁为由,诉求纂成一部内容简约、义例清楚的纲目体通史。但随着纲鉴的发展,名家评点、诸家注解堆叠其上,反成明代纲鉴类史著的典型特征之一,与求简的纲鉴编纂初衷背道而驰。“纲、目愈备,合而读之,卷帙繁重,莫得其要领。”冯梦龙编纂《纲鉴统一》意在“删繁去冗,务极简要”,却仍不舍诸家评注、页眉题解且多有按语。故叶沄言道:“惜明代所纂小鉴,多坊间倩庸手裁削、假托巨公以行世。每繁简失宜,承接疏谬,百余年来无正之者。”《易知录》的出现,意味着纲鉴类史著从以纲目为体例,不断融会承载通鉴知识,取径广收辑览的“会纂”“会编”编纂方式,重新走回力求纲举目张、务以简约的文本呈现道路。该书的成功,也让纲鉴知识在清代实现下沉,并最终令《易知录》在明清纲鉴类史著谱系中别具地位。
2
“几于家有其书”
《易知录》自康熙五十年刊后,印行不断,流行甚广。以致“家弦户诵”,“坊间盛行,几于家有其书”。随着《易知录》的流行,购、借、赠、钞、让、藏等丰富多样的书籍流通形式见证着该书的传播。王韬的日记中就有《易知录》的购书记录,藏刻书家刘承干也购得过此书的坊刻本。晚清学者谭献、蒋维乔都曾跟同学借此书来阅读。《易知录》作为赠书也参与到清代文人的交际中。晚清学者莫友芝多以赠书交谊,他于同治元年购得此书并赠给友人程月波。《易知录》在流通过程中也出现有节钞本,清人黄谦就依据《易知录》辑出六卷本的《纲鉴易知录摘钞》。此外,该书在传播过程中亦有转让的情况,《天声报》上就曾刊有出让大众书局版《易知录》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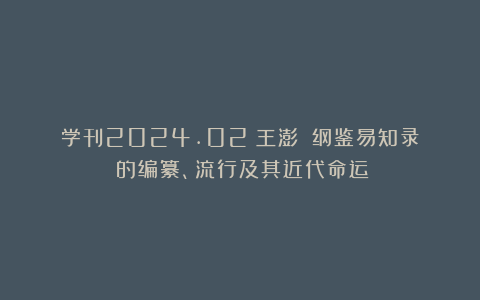
至于该书的藏用则存在官方与私人两种情况。一方面,《易知录》曾作官学和地方书院藏书。道光二年泌阳县教谕贾鹿洞、训导窦豹变查明存册,“颁学现存书籍”中有《易知录》32本。甘肃皋兰县下五泉书院的“存贮书目”中有“《纲鉴易知录》一部六套计四十六本”,为书目中唯一的纲鉴类史著,更说明该书此时已流通西北;济南泺源书院亦存《易知录》49本,且无其他纲鉴。《易知录》也被清代藏书楼所藏。淮阳县图书馆前身为设置于崇经义塾内的藏书楼,其近代转型为图书馆后,还藏有《易知录》16册。另一方面,《易知录》颇被私家收藏。晚清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就藏有该书,并录入《八千卷楼书目》。另据民国《威县志》所载,威县城内贾家街尚希颢筱酉山房藏《易知录》20卷,骆家街王以锷楚碧堂藏107卷,曹家营李光滨藏112卷。可知清时私家收藏《易知录》更当不输。
《易知录》制售上始终保有的较低价格与科场实用功能,令其在市场流通中占据优势。价格方面,以晚清为例,《易知录》大多定价1元至2元,精刻铜板最高也只售4.5元。而刻本《御批通鉴辑览》“价格很贵”“非银圆一二十元不能买到”,铅印本《通鉴辑览》定价2元左右,仍高于《易知录》。实用方面,《易知录》除私塾蒙授外,主要被科举士子作为场屋试料使用。体积便携、随时查阅是为刚需,《易知录》在此方面可谓做到了极致。南怀瑾回忆他十三岁时所读的《易知录》,即是此种“每个字只有零点二公分大”“方便携带”的科考便携本。清末上海乐善堂出售的精刻铜板《易知录》亦称“字画明晰,装订精雅,尤便舟车携带”,为“文场必备”。
《易知录》流行的背后,是其文本及所携历史知识的持续传播与渗透,并不断地被阅读与接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知录》成为后世纂修地方志的重要参考与引征依据,特别是确定地理和修订记述两方面。就前者而言,《易知录》所注地理地名多被方志采用。道光《榆林府志》界定榆林地方、同治《霍邱县志》确定霍邱义城、民国《兴城县志》区分首山与马首山,皆依据并引用《易知录》。就后者而言,原有的方志记述在地方志的修订过程中也会依《易知录》加以订正。道光《建阳县志》多次依据《易知录》订正旧志内容。有关南唐林仁峰的记述,新志“考《纲鉴易知录》”,认为“旧志仁肇密陈云云之上有’会李重进以扬州叛’八字”记述有误,“今参《纲鉴易知录》订正”。对于谢枋得死后《易知录》所载“其子定之护骸骨归葬信州”事,则予以保留。道光《略阳县志》修撰时亦比对《易知录》与旧志记述,从而修正“《纲鉴易知录》注歙所袭之略阳”事。此外,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光绪《安国县新志》、光绪《昌平外志》等方志都对《易知录》有所参考。
第二,《易知录》在清代长期被选作私塾教本和举业用书。该书是村学究眼中“顶好的史书”,“做策论的料子”。严复甚至视《易知录》为制举史书的代名词,称“《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具体来看,地方塾师开展历史教育多以此书为基础教材与知识资源,其中浙江塾师赵钧与林骏对《易知录》的校读与授学最具代表性。道咸年间,历任瑞安、上韩等地塾师的赵钧在日记中有点阅《易知录》的记录。赵氏得精刻小板《易知录》,珍视异常。因“内有缺幅”,故“手自抄补”,且校毕后叮嘱曰:“凡我子孙,当加意珍惜。”赵钧从道光六年十一月开始校阅《易知录》,持续到道光七年五月,至第十一本。此后中断至道光二十八年,方才重拾点阅,及至年底结束。日记不乏赵氏对该书的点勘、摘录和评论,借此可以了解其点阅过程和阅读体验。如赵钧八月廿一日读到《易知录》四十一至四十三卷中献鸟及唐太宗臂鹞之事,评论道:“禽鸟之好,明主尚然,况昏庸乎?况更有动人甚于珍禽奇兽者。”十一月廿一日点校时,赵钧更是针对君臣国势洋洋洒洒评论近百字,议论君心明暗对于国家的影响与为官之人品格,最终感慨:“品苟污下,虽贵为公侯,贵为将相,一旦身死,究与草木何异?”赵钩点校时也会在卷上标记,点校毕将标记处“逐卷摘出”,且所摘皆“记明某卷”,“以便覆对”,“中间尚有疑字,用小∠记在上方横界处,须再觅善本正之”。赵氏点校完《易知录》后仍多次阅读。其校毕次年还多次阅书并发议论,主要愤慨于两宋之交事,叹息“君臣上下,愦愦何如”,并在最后一条记录中叮嘱子孙“加意珍惜”此书,足见其对该书的喜爱程度。
清末温州塾师林骏在日记中同样留有点阅和教授《易知录》的记录。林骏自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始至次年四月,持续点读该书,多达50日次。据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在馆,与门人说《纲鉴易知录》”,这也是该日记最早提及《易知录》之处。《易知录》的讲解是其教授该书的重要环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夕、二月廿七日夕,皆与诸生讲解此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的讲授记录最为详细,该日林骏为其学生孙延曙讲授《易知录》南宋纪内容,论及“罢岳飞,奉朝请节”之事,详释朝请制度及历来说法。林氏援引《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纲目》诸书释“朝请”,并论古及今曰:“桧欲夺飞兵权,成己合议之谋,使居闲官,不与朝议,亦明升暗降之例也。今之大僚致仕闲居,只受朝廷钦赐,或遇恩加衔,附片奏谢,或以乃祖勋劳,荫其孙子,使彼他日长成引见,正此类也。”可见其讲解之细致。
第三,《易知录》是清代文人、官员以及近代读书人少时阅读的重要书目。清人张星徽、周广业都曾见阅该书。张氏辑录《历代名吏录》多次引征《易知录》。周氏论及张居正事,引用《易知录》所记来证明张居正彼时的权势,称“居正卒,余威尚在”。晚清官员延昌在其所著官箴书《知府须知》中,录有光绪五年他选补浔州府时备带的书籍,其中史书所见仅有《易知录》和郑元庆《廿一史约编》。且其后所列“府考应用各书”中并无史书,或满足一个知府的基本历史知识需要。又因延昌认为浔州“书坊既少,书目不全且纸板过劣,其势必须由京多带”,故《易知录》所带多达八套,远高于其他书籍携带数量,也可知该书在延昌眼中的重要程度。而延昌所撰《知府须知》在晚清发行量大,于外放府县官员中颇具影响,反映了晚清一般基层官员的读书情况。署理崇义知县的周长森也曾在一年半的代理任期中阅读《易知录》。此外,近代读书人多数在童蒙或少年阶段阅读过《易知录》,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范文澜、吕思勉等都曾习读该书。
3
“一切知识之根源”
近代历史教育存在两股力量的博弈,一是以纲鉴为代表的旧教材与新式历史教科书之间的优劣竞逐,二是新教育、新史学与旧教育、旧史学之间的代谢和角力。然而在此博弈过程中,《易知录》这种内容简要且便于教学的旧教材,凭借其自身优势,在新旧教材更迭之中寻得了生存空间。即使到了1933年,时人指出鉴略之类教材“逐渐少见,甚至于绝迹了”,却仍称赞《易知录》是“一部比较精要的好书”。及至20世纪40年代,李季谷还认为必须阅读《易知录》诸书,“以作一切知识之根源”。时人也将知晓《易知录》作为读书人的标志,称“知道《纲鉴易知录》,无疑地是个知识分子”。那么,《易知录》何以历经近代以来科举的改废与新式教科书及历史教育的冲击,成为在新旧史学与历史教育中通行的历史教材与史学资源?值得详加考察。
《易知录》在清末教育变革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戊戌变法提倡义论,安阳知县叶济命士子注重实学,即以《易知录》诸书奖励学子。此后,科举改试史论带动史书风行,更令该书成为士子热购和学习的重点书籍。时人指出家塾教育中“如廿二史不能全阅”,则阅《易知录》诸书。童生报考史论,带的则是《易知录》之类翻查作答。商务印书馆出品的《易知录》采新法印刷且体小价低,更是大受读书人欢迎。而且被地方书院购得,以供生童之考。及至学堂变革,《易知录》作为教本和必读书仍被广泛使用。1901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筹办济南大学堂,就将《易知录》定为蒙养学堂的历史教本。1902年,皮锡瑞到小学堂更革书单,“出示买书、读书之法”,明列《易知录》。1904年,《四川官报》所录公牍中有人指出将《易知录》作为高小的习史教材,“以《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两编为之讲授,殊不为繁”,认为较顾锡畴《纲鉴正史约》、袁黄《了凡纲鉴》更优。
此后清廷废除科举,伴随新学制的不断颁行,对新式教科书的呼声日盛,作为旧教材代表的《易知录》也当被淘汰。实际却是《易知录》无论作为教科书,还是提供历史知识的重要资源,在近代从未离场,反而呈现出断之不离、舍而难弃的矛盾局面。
其一,优质历史教科书的长期匮乏,导致作为旧教材代表的《易知录》始终被提及与使用。一方面,《易知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点且不合于新式教科,这促使新教材的产生。《易知录》虽是“销行普遍”的纲鉴,但存在“详于纪言而忽于纪事”等问题,“今则全体落伍且有毒素”。《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诸书“不宜于教科”,已有一定的共识。即使女学,也诉求勿使《易知录》作为史学概要书,认为“《纲鉴易知录》《七种纪事本末》之类,不适今用”。正如齐思和所总结的,“旧式的课本像《十七史详节》《纲鉴易知录》之类,早已不合时代的需要,于是新著的通史便应运而起了”。另一方面,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优质历史教科书的长期匮乏,致使“不宜于教科”的《易知录》一直存在使用空间。清末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日本中国史、东洋史教材的引进虽令教科书渐次迭代,但学堂始终拿不出像样的教本也是实情,“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正因如此,《易知录》虽然被人“看得最浅陋”,仍好过“比《易知录》更加浅陋”的日人那珂通世所著《中国通史》。林獬不满于《易知录》,却也认为“小孩子读的史书,如今却没有一部好的”。1904年崇实书局再版的《续中国通史》一书,虽署日人山峰畯藏著、中国汉阳青年编,实则是书坊节抄《易知录》而成。这足见当时教科书市场的混乱,却也说明《易知录》仍是被充分利用的教本资源。1909年,在有关修改学部奏定章程的诸多讨论及建言中,还有人提议“小学中学除读经外,仅宜授以《纲鉴易知录》《古诗源》等书”。江苏省视学侯鸿鉴上书彼时江苏各县历史教科书选用的乱象,同样发现《易知录》还被用以训蒙,“《纲鉴易知录》为历史课本,以及各种支离罕见之杂书,且用为训蒙之用者矣”。
至民国时,相关情况并未好转。杨昌济认为,“单看学校用之历史教科书,难于得历史之观念”,最后只得推荐学生阅读《易知录》。同时也有人直接表达对辛亥革命后教科书编纂的失望,指出学者或学生只能多依靠《易知录》。“清退位六年以来史书修辑未竣,而坊间竞行新体历史暂充教科,未足厌学者研究之望,同人悯焉。因查旧日学界所奉为圭臬者,惟《纲鉴易知录》一书最为简当切用便于记忆,受书之子几于人手一编,其效用无俟赘述。”此外,钱玄同也强烈表达他对当时历史教科书的不满,认为新式教科书还不如以《易知录》为代表的旧教材。他说:“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国语和历史读本,一言以蔽之曰,都是对于低能儿的教材而已……老实说吧,我是曾经做过八股的人,什么《左传》《史记》《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都曾翻过的,看了那些教科书中简短的叙述,也还要摸不着头脑ㄋㄝ!”柳诒徵不满于当时历史教科书的记叙空洞,批评它们虽有纲领却内容不详,“教科书都是鱼网式的。虽则能有纲有领,但是中间尽是空穴”,最后直接指出学习历史需看《易知录》,“所以我们研究历史,最好还是看《纪事本末》、《通鉴》、《易知录》等,较为有用。能够得看他的一切经过情形,方不至有所误会”。
其二,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历史教育的长期不振,令《易知录》作为历史知识的奠基作与补充源被反复地追忆和需要。20世纪20~40年代,时人对当时中小学乃至大学历史教育的批评甚多,“历史教育之失败已成为时人普遍的共识”。晚清受八股制艺影响,一些学子疏于史学,仅读过《易知录》便可称“嗜古”,获讥“与没字碑无以异”。此后这一情况未见好转,反而恶化。1924年的《晨报副镌》上有人说他看过《易知录》,故“在高小同班里面,历史一科自然就是占优胜的了”。章太炎在1933年批评当时历史教育的浅显与不受重视,指出“因之历史一科,黄舍中视为无足重轻,所讲者不过一鳞半爪”,因此“在昔《纲鉴易知录》,学者鄙为兔园手册子,今则能读者已为通人”。彼时章氏所能想到的历史读本还是《易知录》,也足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与典型性。范文澜在1935年批评当时学生所学都是“一些破碎的历史知识”,他认为“《纲鉴易知录》实在不是陋书”,并将其作为“一般人必须读的旧书”。
待到40年代,历史知识的匮乏与历史教育的不振则更为严重。“青年学子,终年兀兀于英文理化,至历史一科,降为附庸,视为无足重轻,于是历史成绩,每况愈下,对于本国历史,忽略尤甚。”以致钱穆直言彼时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李季谷由此提出的根本补救之道是,“亦必浏览《纲鉴易知录》及《读通鉴论》数书,以作一切知识之根源”,以此打下历史基础。不少学者也将《易知录》作为最低限度的历史读本,希望时人阅读,以便补足基础历史教育的缺失。邹韬奋根据陆费逵所拟之“最低限度当读之国学书”,将《易知录》与《史记》并列,作为史部仅有的两部书来推荐。更有人认为,“凡欲建功立业,最低限度,也得念完一部《纲鉴易知录》”。1941年《申报》发表的《历史的研究法》一文,还将《易知录》列为普通初学者的必读书,与夏曾佑、陈恭禄等人编写的新式教科书并列。
其三,《易知录》是近代读书人经常运用的史学概念、知识资源乃至历史材料,该书早已深入人心。有文章将《易知录》比喻为“明星”,以作“历史”的代名词,其曰:“我所恃者亦只一颗给予光明之星耳,—星非他,即一部《纲鉴易知录》是也”。也有人将《易知录》与最基本的历史教材与历史认识画等号,“我们就把我们的历史——即如最普通的历史课本或《纲鉴易知录》翻开”。抗战时,有人回忆起在学校阅读《易知录》所见的明亡史事,认为明遗民“最足矜式”,从而呼唤“培养正气”,坚定抗战。同时,不少近代史家早年间通过阅读《易知录》打下知识基础,甚至还因此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萧公权幼年时,老师何笃贞不让他阅读《史记》《汉书》等史学要籍,“而让我们去细看吴乘权根据朱熹《通鉴纲目》所编的《纲鉴易知录》”,萧氏对此极为肯定并认为“后来受用不尽”。姚名达10岁时从父亲处得到一部铅印小字本《易知录》,他再三精读并称:“我研究史学的兴趣和基础,也在那看《纲鉴易知录》时便已奠定了。”杨向奎指出其“史学基础是在幼年家塾中培植成的”,他曾阅读《易知录》,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历史发生兴趣”。
此外,《易知录》是史家常见的史学资源与研究史料。顾颉刚论辩《尚书·金滕》篇,指出传统周公形象的认知来源便是《易知录》等书。“我们通常从《纲鉴易知录》等书中得来的周公的印象,总以为是一位极漂亮,极重实际的政治家。那知读了此篇,竟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而皮锡瑞对上古帝王统系的质疑也是源于《易知录》诸书,“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首所列帝王之年,皆本邵子意推,遂成铁案。唐尧以上,或本于皇甫谧,其不可信,一也。”可知《易知录》所载规整的历史体系及上古史实的阅读传播,一定程度促进了疑古思潮的产生。“社会史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也不乏阅读和使用《易知录》。“社会史派”就曾援引《易知录》内容作为史料,齐思和对此批评道:“他们的理论有时很是奇怪,而他们所找的材料又很不完备,有的甚至止从《通鉴辑览》、马鼎《绎史》,甚或《纲鉴易知录》、《辞源》之类书籍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在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眼中,《易知录》实际颇具史料与史学价值。吕振羽在谈及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时,就将《易知录》列为“史料”一类,并视此书为基础的历史知识。范文澜在强调治史的客观性时,也以《易知录》作为最基本的史料及历史认识来源进行举例:“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也不能凭臆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合自己主观的志愿。如果这样做,关于古代史,最起码的《纲鉴易知录》就会不答应。”
总之,虽然近代以来《易知录》一直被认为“不适”“不宜”新式历史教育,但在新旧历史教育转型的青黄不接之际,《易知录》因其简易便读的文本特性,连同晚清乃至近代读书人自身的阅读和教育经历,令该书成为不断被提及、阅读和利用的教材、史著乃至史料。由此,《易知录》反而成为新史学中的旧史学、新教育中的旧因子,在新旧史学与教育的更替间藕断丝连、寓旧于新,以致断之不离、舍而难弃,最终变作新史学与新式历史教育的特殊补充与知识资源。
4
结语
一直以来,纲鉴类史著被统一视作举业用书或“兔园册子”,基本只以其服务对象士子与童蒙来进行简单划分。此举忽略了纲鉴类史著自身的发展轨迹与单一纲鉴的文本特性。不同时期乃至不同编纂宗旨的纲鉴文本实际存在差异,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也有所不同。钟鸣旦就提醒学界应当注意纲鉴类史著自身的知识谱系与发展脉络。《易知录》秉持“欲求一读史之法”的编纂理念,与“宁简毋详”“宁陋毋雅”的编纂原则,继承发展前人纲鉴类史著,使之直达底层文人与童蒙群体。该书借助其高流通的文本属性,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纲鉴类史著的普及性价值。这既是纲鉴类史著发展到清代趋向普及化、精湛化的产物,也是其回应举业市场与受众需要的结果。此过程生动地展现出一部纲鉴基于纲鉴类史著体系实现知识再生产,并最终创造自身的史学价值。
归根结底,《易知录》的成书、流布及影响,反映了一部纲鉴如何从纲鉴类史著谱系中脱颖而出,建构出流动的、具有文化和精神意义的“中层”乃至“底层书籍世界”。由此,《易知录》参与建构多数近代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世界,凭借其文本特性与广泛的学人受众,成为新史学中反复被提及与运用的史学资源和概念符号,补充了近代的历史教科书不能满足历史知识需要的缺口。该书虽然是旧史学的代表,是新史学和新式历史教育批判与扬弃的对象,但也成为新史学的知识资源。新旧史学的更替和裁汰并非一蹴而就,以《易知录》为代表的旧史学因子,仍在新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呈现断之不离、舍而难弃的现象,揭示了近代历史教育的古今交错之面相。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下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刘嘉诚
排版:杨昌泓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