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诗人徐志摩死于空难,震惊了整个文坛。
那年他不过三十四岁,风华正茂,却陨落于济南山间的迷雾中。
随着他的离去,爱恨旋涡也在不同的人心中翻滚,张幼仪的冷静、陆小曼的否认、老父亲徐申如的沉痛。
一段段隐秘的情感被掀开,一笔笔不为人知的供养也浮出水面。
为何陆小曼能在丈夫去世后,仍享受长达十八年的经济支持?是谁在悄无声息地供养她?
徐家媳妇
1931年11月的一天,张幼仪在云裳衣店里亲自翻阅新到的布料样本,一边还惦记着那几件赶工的男式衬衫——是徐志摩特意来催的。
这个前夫如今已不再属于她,却仍像老朋友一样,偶尔出现在她生活的缝隙里。
谁也没有想到,之前那一场平常的见面,竟是诀别。
张幼仪正在休息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张幼仪从浅眠中惊醒。
她披上披肩开门,一位穿着邮差制服的年轻人神色凝重地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封电报。
“徐先生出事了,飞机坠毁,遗体在济南。”
她愣了片刻,几乎不敢相信,她的手在发抖,几秒之后,那封还未展开的电报终于落入她掌中。
信差犹豫着开口:“陆太太……她不肯收电报,说这不是真的,拒绝认尸。”
一句话比电报更具冲击力。
在她看来,无论如何,陆小曼是徐志摩合法的妻子,是应当担起责任去收拾这场人间残局的人。
可现在,陆小曼却像是一个逃兵,扔下战场,避之不及。
那一天,张幼仪在屋中踱步整整一圈又一圈,最终,她定下心来,拿起纸笔,开始为“后事”做准备。
她知道,此刻自己必须出面。
不是以徐志摩的前妻身份,而是以“徐家寄女”的名义,替这个破碎的家庭做一回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照顾徐家的颜面,她安排了十三岁的阿欢——徐志摩与她的长子,以“长子”的名义前往认领遗体。
海格路125号的大宅,只剩她和徐志摩的老父亲徐申如两人。
她不敢贸然告知老爷子噩耗。
才过了几个月,徐家老太太也刚离世,老人两鬓斑白,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用委婉的语气,慢慢铺陈这个事实,直到第四天清晨,才终于低声哭着告诉他:“没救了,他走了。”
老人愣住,良久才喃喃:“那就算了吧,去了就算了吧。”
随后,他亲手写下一副挽联,字字带血:“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这一切,陆小曼全未参与,她的沉默,她的逃避,像一块冰冷的石子投进了这潭哀痛之水。
不是没有人去请她,不是没人希望她站出来,哪怕只是一句哀悼,一个眼神。
但她拒绝了,固执地坚信这噩耗不过是谣言,是一场闹剧。
直到徐志摩的棺木运回上海,直到公祭开始,她才姗姗来迟,表达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要求”。
最后的公祭
飞机坠毁的噩耗传来时,中国航空公司派人赶赴现场,撬开残骸寻找机体编号与乘客遗物,却发现那具孤零零的焦尸早已面目不辨。
棺木临时在济南城边封装,在几近战火洗礼的环境下等待合适时机运回上海。
张幼仪接到电报时,刚送完儿子阿欢返校,疲惫未消,心又悬起——徐志摩的棺木终于能回来了。
她立即协调场地,安排安置,甚至连灵堂的布置细节都亲自过问。
尽管不是她的责任,但她知道,她若不管,就再无人会为他张罗这些。
徐志摩的遗体是由中国银行租借的一节火车车厢运送的,车厢四周围上帷幔,门窗紧闭,棺木上贴着封条,以防途中的颠簸震动了那具早已破碎的遗体。
棺木到达上海当天,灵堂设在中国银行礼堂里,一派肃穆。
灵柩静静地摆放在堂中,张幼仪穿着一袭黑色旗袍,站在礼堂门口,一边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一边留意着现场布置是否得当。
她没想过会出现在这场公祭中,直到有人打来电话:
“你必须来,陆小曼提出要换棺材和寿衣,没人能压得住她。”
张幼仪应邀进入灵堂时,现场已传来些许窃窃私语,灵柩前方摆着徐志摩的遗像。
没等她开口,一位中间人低声告知:
“陆太太刚刚来过,看到这副传统棺材很不满意,还说要把寿衣换成西装。”
语气里夹杂着几分无奈和隐隐的不解。
张幼仪愣了一瞬,随即冷静下来,沉声回应:
“现在还能折腾什么?”她目光扫过现场,仿佛不是在看一口棺材,而是在看一段被无数人误解和粉饰的“浪漫爱情”。
中间人劝她稍微考虑下:
“陆太太说他喜欢穿西装,这样比较符合志摩生前的气质。”
张幼仪皱了眉,语气并未抬高:
“我不懂,难道他死了也要’风度翩翩’?人在中国,死也该有点中国人的体面。西装?再换回礼帽、皮鞋,是想送他去赴宴吗?”
她转身,环顾一圈,轻声而坚定地说:
“不要再动他了,他走的时候已经够辛苦,别再把他拖进这种荒唐的折腾里。”
言罢,她留下一句话:“你只需告诉陆小曼,这是我说的。”
那天之后,没有人再动过棺木,也没人再提换寿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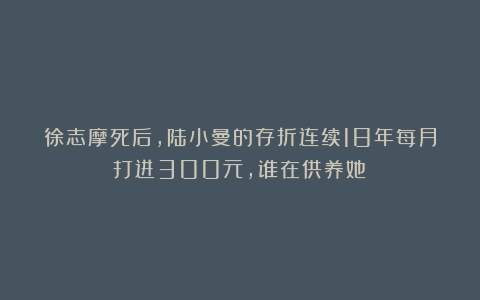
张幼仪知道,陆小曼不是没有情绪,只是,她对处理死亡这件事,从未认真考虑过别人感受。
陆小曼没有出席正式的悼词环节,只是站在礼堂后侧,戴着黑纱,神情落寞。
张幼仪远远地望了她一眼,这个女人也许只是太过脆弱,脆弱到无法面对死亡带来的真实冲击。
从那天起,她们二人之间,再无交集。
公祭结束,灵柩被运往指定墓地入葬。
张幼仪最后回望那张遗像,那个她年轻时曾深爱、后来又决然放手的男人,终于彻底从人世间告别了。
从奢入俭
徐志摩离世之后,陆小曼的世界仿佛被一夜抽空。
她不是不知道生活的重量,只是过去太久有人替她扛着,所以当这道支柱轰然倒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先去应对哪一部分的崩塌。
她的生活,是从细节开始坍塌的。
往日那幢老洋房里,香水、旗袍、缎带、摆设、画作,处处透露着精致与华丽。晨起有人送茶,夜里有人备鸦片。
她习惯了这样的节奏,也习惯了那种“才女交际花”的社交世界。
徐志摩在的时候,她不需思考明日的支出、哪笔账是否对得上,只需安心吟诗作画,偶尔病一场,也有人为她四处求医问药。
可如今,那口钱井被封死,世界顿时变得沉寂又冷硬。
最先断掉的,是鸦片。
这并非她主动选择的戒断,而是无力继续。
即便她再怎样精打细算,也无法维持每日的阿芙蓉供应。
身体是诚实的,很快,她开始发抖、头疼、冒冷汗,每到夜深时,蜷缩在床角,像条无处可去的猫,她恨这种状态,却又无力摆脱。
为了维持生活,她不得不向外人求助。
曾经那些在她面前阿谀奉承的文人雅士,一个个脚步疏远,鲜少有人再登门寒暄。
她开始向朋友写信借钱,有时是几块,有时是几十块,更让她难堪的是,部分信石沉大海,另一些,则附带冷言冷语:“陆太太不该如此败光志摩先生的余荫。”
事实上,在徐志摩活着的那些年,早已有迹可循。
他作为大学教授,收入不低,兼职稿费也算丰厚,可这都敌不过陆小曼的花销——更何况,她始终不肯离开上海,而他却得在北平任教、奔波两地。
那是一段疲惫的婚姻生活,他飞来飞去的机票,多数是自掏腰包,即使偶尔搭上中国航空的“免费乘机券”,也要靠自己写文章换得。
他甚至干起了“带人看房”的活儿,为的是从上海某些洋房中抽取介绍佣金。
若说文人风骨不堪世俗,那徐志摩显然早已打破了浪漫幻想,他在为爱奔走,也在为生活屈膝。
即使如此,他仍旧供养着陆小曼。
陆小曼偶尔也会心软,写信劝他别太辛苦,可转身便要购入新画布、添置香水,那些贵重物什,是她习惯中的一部分,不愿剥离。
而这一切,在徐申如眼中,早已是无数次压抑的怒火。
这个白发人曾在儿子娶了陆小曼之后,尝试过与她相处。
他会为他们做饭,买菜,甚至亲自清扫庭院,可他始终是外人,哪怕是徐志摩的父亲,也无法融入那个充满香烟与鸦片的空间。
最令他无法原谅的,是某次他亲眼看到陆小曼邀请一位名叫翁瑞午的男子进屋,堂而皇之地在卧室内共吸鸦片。
他没有当场发作,只是第二天悄然收拾行李,搬回前儿媳张幼仪的屋檐下。
那之后,他再也没踏进那个家一步。
三百元背后
徐志摩死后不久,徐申如便悄然做了一个决定——那张写有陆小曼名字的银行存折,将继续每月定期入账三百元。
这笔钱,原是他在儿子尚在时,勉强同意拨出的生活补贴,曾几次因陆小曼的挥霍被他心生不满,却始终未曾真正中断。
当儿子骤然离世、家庭轰然倒塌,他却选择将这笔钱保留下来,甚至更为稳妥地处理转账,只为了“眼不见,心不烦”。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沉默的追悼方式。
徐申如并非看不清陆小曼的种种行为,他早在两人婚后的日常中就感受到这位新儿媳的张扬与不驯。
她不谙人情世故,却又高傲执拗;她待人疏淡,却又沉溺社交圈的喧闹;她拒绝工作,却挥金如土;更要命的是,她染上了阿芙蓉。
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让长辈安心的“家中主妇”?
可即便如此,当徐志摩的棺木封入黄土、家中再无这位独子的身影时,徐申如心中的执念也慢慢变成了责任。
他不再为陆小曼的过错争论、不再分析她与儿子的婚姻究竟谁对谁错。
他只认定一点:这是志摩的妻子,是他未能照顾终老的人。儿子未尽的义务,作为父亲的自己要替他继续承担。
那时的上海动荡不安,抗战的阴影已渐渐蔓延到城市每一个角落,连银行也屡屡搬迁改址,但徐申如的“供养行动”从未间断。
1944年,徐申如辞世,这位曾在风雨动荡中支撑着大家族的老父亲,最终也闭上了眼睛。
可等遗产清理完毕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陆小曼的那张存折,依旧安然无恙,仍在正常运作。
钱从哪里来?
答案,在张幼仪手中。
她没有声张,只是低调地接过了徐申如的“职责”。
外人不懂,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补偿?是责任?还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缠?
她想了许久,在晚年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
这份供养,或许不是对陆小曼,而是对徐志摩的一次长久告别。
直到她离开大陆,供养才真正终止。
陆小曼终老时身边无儿无女,亦无伴侣,那三百元却延续了整整十八年。
一笔不间断的钱,藏着两代徐家人不言而喻的情义、矛盾与悲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延续,一个前妻对往昔爱情的体谅。
也许,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那些年的供养,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段破碎情感的安置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