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历史的起点:《史记》
中的时间设置及其意义
摘 要:《史记》里的宏观时间结构主要表现在三个秦朝以前的年表中。在年表里,司马迁将西周的历史以共和元年为界裁为两截:一截入《三代世表》,未予编年;一截入《十二诸侯年表》,开始纪年,并与汉元年建立了岁岁相接的年代关联。共和元年是他刻意选择的“历史起点”。这一年之前是周衰前的“古代史”,而之后则是周衰至汉兴的“近代史”。《史记》是以“汉兴”为题眼,以“近代史”为主的历史。其时间设置因此具有指示周汉相继的象征意义。《史记》中的象征性理解历史的方式源自《左传》,从《左传》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叙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事件的指示意义。清华简《系年》的出现说明此种类型的历史写作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与《春秋》和《左传》相比,《史记》赋予了时间以独特的叙事功能,让时间具有了展现历史演变的意义。
关键词:史记;历史的起止;象征性时间;共和元年
阅 读 导 引
一、《史记》中的宏观时间框架
二、《史记》时间设置的象征性
三、《史记》历史观念的渊源
四、《史记》年表的叙事功能
结 语
《史记》将长时段、大空间内的人和事笼括起来,形成一种相对全面的对过去的理解和叙述。司马氏父子的撰述,有自己的取材标准,即《伯夷列传》所说的“考信于六艺”。通览全书,以特定标准选录的古籍文献,是《史记》汉初以前历史的主要建筑材料。部分文献材料可以与传世文献或唐宋类书所存录的古文献相对勘。《史记》对古文献的转录是一种变相的文献收藏,很多重要的古书虽然散佚,但却因《史记》的裁取而间接流传了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难确定《史记》汉以前的历史哪些记载是转录,哪些记载是自撰。于是,利用其具体文句、篇章来理解或辨析司马氏父子的观念和思想,在学术上就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史记》的整体架构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同的设想,但它属于司马氏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不必纠缠于其文本中的细枝末节,而是登上山顶,俯瞰其山势走向,近观其写作的布局结构,远观其写作方式的观念渊源。司马氏父子的表层叙事之下,还赋予时间和事件以象征意义,体现了他们对历史变迁的结构性理解。这种将回溯过去变成理解历史内在发展的写作方式,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大方向。特别是《史记》纪年起点和终点的选择,别具深意。《史记》以共和元年和太初元年为起止确立了以年纪事的边界,司马氏父子据此划定了以周汉相继为基本轮廓的主体结构。本文尝试从写作的视角来理解《史记》的叙事,追溯《史记》这种书写和理解历史的方式的起源,并特别关注时间在《史记》叙事中的功能和意义。
一、《史记》中的
宏观时间框架
《史记》虽然以《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前后相次,作为其历史大厦的柱石,但《史记》里的宏观时间结构却并不以王朝更迭为界。太史公的历史分期主要体现在三个秦朝以前的表中,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其中《三代世表》没有纪年,是按照世系来编的表。《十二诸侯年表》则有了详细的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前841),止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是一个365年的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序》称此表“自共和讫孔子”。《六国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6),结束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共270年。公元前206年即汉之元年。通过年表的时间分割,司马迁将汉代以前的历史分作三个主要时段:
(一)黄帝至共和元年;
(二)共和元年至周敬王四十三年;
(三)周元王元年至秦二世三年。
《史记·六国年表》末页,
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
在这个历史分期里,周之后是汉,秦朝的历史编入了《六国年表》,并没有在《史记》的宏观时间框架里获得独立的位置。在时间上最具意义的是共和元年,这是《史记》以年纪事的起点,此前的历史司马迁本可赋予编年,因为不论从世系书,还是从谱牒、历书等文献中,司马迁都可将纪年上溯至周初或更早。如在《周本纪》里,武王时代有时间记录,但成王至穆王时代则主要使用了《尚书》类文献,没有用世系、谍谱类文献。穆王至厉王三十四年,《周本纪》采用了类似于《国语》的文献。厉王三十七年,便是共和元年了。这种时间设置与《十二诸侯年表》相似。其原因除了文献材料的限制和其考信于六艺的取材标准外,还应该有写作的深意在。毕竟《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至鲁隐公元年的一百多年几乎是空白的表格,各国的纪年材料也非常稀缺,共和元年之后的一百多年和共和元年之前的一百多年,文献材料的稀缺没有明显的区别。为何司马迁偏偏选择了共和元年呢?且对司马迁来说,可信的纪年并非始于共和元年。“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然“周以来乃颇可著”,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云云,说明至少周厉王之前是有清晰的年历的。如《鲁周公世家》伯禽之后每一位鲁公都有在位年数,据此很容易将伯禽卒年推定在公元前998年。除了鲁国之外,依据诸本纪和世家中的记载,周和各诸侯国自共和元年可以上溯的时间分别是:周37年,秦16年,曹23年,陈12年,卫25年,宋17年,晋17年,楚6年,即秦、曹、陈、卫、宋、晋、楚等国均标出了与共和元年相对应的本国纪年,这或是他说“周以来乃颇可著”的原因。在年表里,他将西周的历史以共和元年为界,分为两截,上截纳入《三代世表》,下截则入《十二诸侯年表》。不仅《三代世表》中的周代历史没有纪年,《周本纪》中周厉王之前的王,除了周穆王,其他周王都没有清晰的在位年数。
年表里的共和元年是周室衰落,诸侯兴起的起点。因秦未被纳入其王朝更迭的大结构中,周衰之后的王朝时代便是汉了,共和元年也是汉兴的遥远起点。故《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起点是周之衰,而终点则是汉之兴。这两个表是有年可纪的历史,可以一年年地回溯,发现“汉兴”前史。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首页,
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
《史记》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时间基点是太初元年,这一年的意义和共和元年非常相似,也代表了一个大的时间分界,是《史记》中“历史”的终点。《太史公自序》说太初元年“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注释“诸神受纪”一句为:“告于百神,与天下更始,著纪于是。”可以说,太初元年对于汉武帝时代的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因此,它不仅是《史记》叙事的终点,也定义了《史记》的性质:《史记》叙述的是旧时代的历史。
故《史记》里的时间已经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线索,而成为《史记》呈现其意义的工具之一。共和元年和太初元年是《史记》时间结构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如果仅将其视作普通的一年,恐怕就无法整体上理解《史记》所蕴藏的意义。事实上,读者确实很容易忽视这两个年份在《史记》叙事,特别是其时间架构中的价值。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感知和司马迁时代并不完全一样。今人已经被公元年代框架所训化,习惯地默认公元年代是自然存在的时间刻度。丹尼斯·费尼(Denis Feeney)在《凯撒的日历:古代的时间和历史的起点》一书中,就特别讨论了公元纪年对当代人的潜在影响:“我们纪年系统的便捷和看似自然的特性,使我们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它所产生的所有日期本身最终都是同步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以公元前、后为时间轴来构建连贯历史年表的工作,已经被我们所有人彻底吸收并自然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忘记了我们的前辈们自文艺复兴以来做了多少同步工作,才能让我们能够说出’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这样的话。这一驯化工程在便利性和可转移性方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但这也是古代研究者应该经常进行的一项陌生化工作,因为当用看似科学的统一编排——儒略历和公元前、后纪年系统——来掩盖不一致的古代数据时,我们所失去的历史知识与我们所获得的便利性一样多。”公元纪年是我们现在用以理解历史的时间轴。欧洲大约在16世纪中期开始逐渐使用这种纪年方式,而我国则更晚,要到新中国的建立,至今不过七十多年。然而,公元纪年已几乎成为我们潜在的、无意识的,甚至是绝对化历史时间认知方式。中国学者面对的年代问题和费尼所讨论的希腊、罗马年代问题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们却共同处于公元年代的时间意识之中。如果我们也像费尼一样,将《春秋》《左传》《史记》,乃至《诗经》《尚书》《国语》中的时间重新陌生化,摆脱对公元纪年的依赖,或许会发现那些古代文献中被隐没的意义。
Denis Feeney,Caesar’s Calendar:Ancient Time and the Beginnings of History书影
国人暴动,厉王出奔,被《史记》认为是周王朝国运的转折,自此之后周王朝不可逆转地进入了衰落的过程。因其重大的转折意义,共和元年成为叙事的标记点。我们之所以要把古代的纪年,如汉武帝建元元年括注出公元年代,就是为了将这一古代的时间转化为现在的时间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标识古代不同事件之间的年代关系,以及这些事件和今天的距离。共和元年的功能和公元元年很相似,它至少是汉代的读者判断一个年代具体位置的锚点。只有将想象和描述依附于某个标志性的事件,时间序列才可能展开。马克·吐温(Mark Twain)借用南北战争在美国南方人回忆中的功能,巧妙地说明了锚点事件对于构建时间序列的价值:“战争就像其他地方的公元一样:他们都是从战争开始的。你整天都能听到有人把事情’说’成……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或者是在战争之前发生的;或者是在战争之后发生的;或者是在战争之前或之后大约两年、五年或十年发生的。”其实这种类似于南北战争的时间标志事件我们也常用,比如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等等。在《史记》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锚点事件,比如齐桓公葵丘之会,晋楚城濮之战,孔子相鲁等,它们在《史记》中都有校准时间的作用,但唯有共和元年具有建立时间标尺的功能。这个年份是《史记》构造的前汉代史的起点,也是《史记》时间轴的起点,这一年之后的历史都可以被纳入一个以王朝年代为中心的时间序列,不同诸侯国间参差的年代也得到了一个参照系。
Paul J. Kosmin,Time and Its Adversaries in the Seleucid Empire书影
二、《史记》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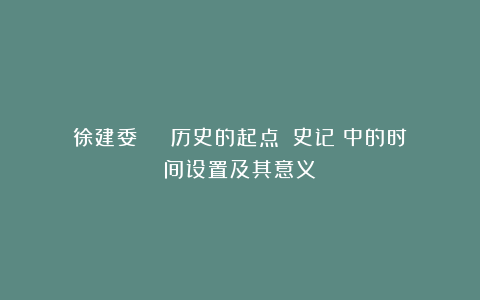
设置的象征性
理解《史记》中时间的叙事意义,还需从《史记》写作构想及其起止的改动来切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借与壶遂辩论,详细解释了他们父子的著作理想。他引述了父亲司马谈的话:“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谈的理想是续写《春秋》,这才引来壶遂的问难。汉武帝时期,制度和礼仪的更新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和期待,很多读书人也希望能够出现与汉王朝相匹配的新经典。在汉代人的认识里,孔子以来推崇的六艺是周的经典,汉代亦应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与六艺合为七艺。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里就有“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的说法。司马相如所说的《春秋》,指的是新《春秋》。司马氏父子所谓的“继《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写一部经传并行的、综合六艺体系的新《春秋》。这与司马相如的期待是一样的。司马谈临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为新时代著史之意更是十分清晰明白。这是著汉典以效周典,是有象征性的。
与模拟《春秋》相关,《史记》起止年代的变化也体现出了其时间设定的象征意义。这个问题源自《太史公自序》里的矛盾:
1.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2.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我们在《太史公自序》里看到了两个《史记》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一个是从尧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即所谓“麟止”,前122),一个是从黄帝到太初元年(前104)。吕思勉在其读史札记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判断《史记》原本的本纪开始于尧,而非黄帝。黄帝、颛顼、帝喾的传记乃是后人根据《五帝德》补入。尧至麟止、黄帝至太初两种起止都与汉武帝时代的象征性大事有关,由此顾颉刚认为这两个起止并非后人缀补,而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先后持有的不同写作计划,元狩元年十月(公元前123年年末)获白麟,汉武帝命作《白麟之歌》,这时司马谈是太史公。《史记》起于尧,终于获麟的写作计划,应该是他拟定的。从尧到“麟止”,是一个整体上模仿《五经》的起止计划,这正与其写作构想一致。《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中所记录的历史中,尧舜时代是最早的,见于《尚书·尧典》,而最晚的记录则是《春秋》中的“西狩获麟”。麟是太平时代的符瑞,是西汉时代的常识,《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这里所说的符瑞,无疑就是元狩元年所获的“白麟”。《史记·封禅书》载元朔六年(前123):“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袛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故知汉武帝元朔六年,捕获一头白鹿,以为瑞应。元狩元年又猎得一头一角兽,不是白色。有司附会为麟,武帝顺水推舟昭示天下,暗示上帝赐麟,可见最初所谓获麟,并不是白麟。汉王朝随后将先后两次猎获的白鹿和一角兽合并命名为“白麟”,当然是要和《春秋》的记载联系起来,向天下宣布太平时代和真正王者的到来。这件事不仅是《史记》最初计划中的终点,也是触发司马谈产生著书想法的起点。受到王朝和天子如此重视的白麟,以及官方命名上的有意附会,或许给了司马谈灵感,让他开始意识到要写一部新的《春秋》。将“麟止”作为《史记》的终点,正是“继《春秋》”的最佳方式。
司马迁元封三年开始续写后不久,西汉王朝就迎来了另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太初改历。历法是上古时代人们统合时间、空间以及人类社会各种礼仪、制度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沟通天人的工具。历法的改变意味着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制度礼仪都要发生变化,因此,太初元年的改历,是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时刻。而且司马迁也是太初改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汉武帝元封七年的冬至日,与时间循环相关的天文标记和历表都回到了历法意义上的原点,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正好是黄帝时代历日的回归。这是更新历法的最佳时机。太初元年历法的更新,意味着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和新的历史的开始。太初即为宏大的开端,“一种全新统一的世界秩序自此开幕,同时这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太初’宇宙的新生”。在太初元年之后的司马迁,很自然的会将记录过去的终点选在太初元年。这样一来,他就改变了父亲的写作计划,作为起点的尧的时代就与作为终点的太初元年不相匹配了。司马迁需要确定新的起点。太初改历要复现的黄帝时代,自然成了他的选择。至此,《史记》写作的起止年代得以确定。
故《史记》和《春秋》《左传》不一样,它里面的时间起点不是自然的起点,而是人为的起点。共和元年以后的时间有计数的功能,从这个点开始,时间按照以年为单位的刻度,一格格地走到了汉武帝时代。所以能够与汉武帝时代建立年代联系的是共和元年,而非黄帝时代。共和元年不仅是王道衰微,诸侯力政的开始,也是汉之兴的计数时间的起点,是一个推动叙事进程的能动的时间。
这种推动历史叙事的时间性表述,在《周本纪》里表现为对王朝的“周衰”的反复提示。“幽厉之后”几乎成为了《史记》早期历史讲述的惯用语。在一部分“太史公曰”或序言之中,司马迁(或司马谈)也会明确勾勒出其主线,“周衰”至“汉兴”就是一种最常见的修辞和叙事逻辑。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史记》的叙事里,周汉相继是其大框架,黄帝乃至殷商的历史,并不是其重心所在,起到的是入话或楔子的功能。黄帝时代虽是《史记》客观意义的时间起点,但更像一个静止的历史背景。通览《史记》,会发现黄帝只在三篇文献里占有重要的位置:《五帝本纪》《历书》和《封禅书》。夏、商、周、秦、楚等虽在世系上均可上溯至黄帝,但《史记》诸本纪及世家的世系,却并不以黄帝为起点,而是将帝喾或颛顼作为诸民族的先祖。《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临终叙述写作缘起,以周公、孔子为先贤,取法于周的观念是很明显的。《史记》重心是仿效周公、孔子,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著史文。在司马氏父子看来,周公所述为周王朝奠基时代的文武之德,孔子则面对幽厉以来的世道衰微而修旧起废,他们分别对应着周兴和周衰。司马氏父子面对的是“汉兴,海内一统”的局面,故“汉兴”二字才是《史记》的题眼。
《史记》不论是止于元狩元年,还是太初元年,都是一座在汉武帝时代用文字筑成的纪念碑。它是一部在文本之下潜藏有象征意义的著作。其象征意义的设置,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时间的剪裁来实现的。
三、《史记》历史观念的渊源
《史记》时间设置的象征性,最早可以在《左传》和《国语》看到。《左传》最后以“悼之四年”(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章结尾,内容是智伯伐郑,与赵襄子交恶之事。随后又记“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韩、魏与赵氏谋杀智伯,已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国语》的叙事,正是结束于鲁悼公十四年智伯之亡。马王堆《春秋事语》也是结束于鲁悼公十四年智伯之亡。《左传》《国语》和《春秋事语》的结尾都指向了智伯之亡。黄震《黄氏日抄》引苏辙、吕祖谦说云:“苏氏曰:自隐以来,诸侯始专,而五霸之形成。获麟之岁,田常弑简公专齐,后二十八年韩、赵、魏灭智伯分晋,而战国之形成。左氏传《春秋》止于智伯之亡。东莱吕氏云:《左传》终此,温公《通鉴》始此。《通鉴》继《左氏传》而作也。”即智伯之亡是三家分晋的起点,预示着战国时代的来临。《资治通鉴》开始于智伯之亡,有相继之意。张溥对《左传》终智伯的解释也很值得参考:“一以示兴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晋阳之守,赵以仁兴。决水之祸,知以骄灭,此兴亡之戒也。晋分则秦强,秦强则周亡。此周、秦之端也。”智伯亡后,三家分晋,秦由此而逐渐强大,这是很有解释力的分析。
《左传》《国语》和《春秋事语》共享了一种历史认知,应该不是偶然的。清华简《系年》的出现,为我们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线索。《系年》是一篇完整的文献,由23章文字组成,各章大体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并相互独立,但明显有一条叙事的主线。李学勤有简洁的介绍:“《竹书纪年》的记事始于夏代(或说五帝),《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李零也说“此书涉及国家很多,但不像《国语》那样分国叙事,而是有一条主线。它讲西周衰亡,是为了引出东周各大国的崛起”。即《系年》中,讲述西周历史,特别是其衰亡的历史,是为了理解东周大国的崛起。这是一种寻因的历史观,和《左传》惊人地相似。《左传》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公元前350年之前,与《系年》的抄写年代非常接近。二者如此接近的历史认识,很难让人认为这仅是巧合。
与《左传》《国语》《春秋事语》结束于智伯之亡不同,《系年》记事结束于楚悼王五年(前397)。《系年》第二十三章出现了楚悼王的谥号,多数学者判断《系年》书于竹简的时间在公元前381年之后。但这应该是《系年》抄写的年代,而非文本写作的年代。今日所见楚简《系年》,应该是文本写成后,又在公元前381年以后被抄写复制的一个文本。原因除了其记事止于公元前397年外,还和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章提到的六位没有谥号的国君有关。尤锐(Yuri Pines)对此已有考订:
我们可以确认《系年》的编纂是公元前381年以后的事情,因为《系年》第23章第127简记载了楚悼哲王/悼王是在公元前381年。章22—23所提的六国国君在位年代如下:晋公止是晋烈公(约前415—前389年在位);齐侯贷是齐康公(约前404—前391年在位,去世于前379年);鲁侯显是鲁穆公(约前410—前377年在位);卫侯虔是卫慎公(约前414—前383年在位);宋公田是宋休公(约前403-前385年在位);郑伯骀是郑繻公(约前422—前396年在位)。……其中四位国君比楚悼王去世得早,《系年》编纂者肯定知道他们的谥号。而不知道这些国君谥号的人应该是公元前4世纪初的楚国的史官。
尤锐已经判断出《系年》的写作在公元前4世纪初。我们还可以根据国君的在位年推断出这一章具体的写作年代区间。国君即位之前不可能被称为某公、某侯,下葬后则有谥号。所以最晚即位者和最早离世者之间的时间,就应该是《系年》文本写成的年代。上述《系年》所记无谥号的国君中,最晚即位者为宋休公,最早离世者为郑公。故《系年》的出现,应该在宋休公即位之后,郑公离世之前,即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96年之间。因其记事正好结束于公元前397年,所以可判断《系年》的文本完成于公元前397或公元前396年。
《左传》和《国语》的主体部分,大约也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加之《系年》和《左传》《国语》在历史观念和记事上的一致性,说明这种关注周室衰落和诸侯兴起的历史认识和写作,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此前强盛了三百年的晋迅速让位于三家。从《左传》《国语》《春秋事语》和《系年》所持有的解释方向和历史观念判断,理解三晋列为诸侯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动,是这类历史著作出现的主要动因之一。这时的新兴诸侯也需要建立自身历史的合法性,那么从周衰开始追述历史,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清华简《系年》叙事简略,但其理解历史的模式与《左传》非常一致,偶然性事件造成的历史发展方向的变化,是其着重记录的内容。很多学者认为《系年》接近于纪事本末体,正是这个原因。这也说明《左传》式的叙事模式并不是其首创,而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一种理解方式。
可以说,公元前400年左右出现了一次历史写作与编纂的热潮,从西汉文献看,战国末年至西汉时代文献中的历史材料或历史故事,大多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不仅如此,那时的历史写作,还共享了同样的历史观念,并一直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
四、《史记》年表的叙事功能
相比于《左传》《国语》或《系年》,以理解盛衰为追求的历史写作在《史记》里更加成熟,并赋予时间新的叙事功能。在处理历史上的时间时,《史记》写作遇到的最大困难应是协调和统一不同的记事和时间系统。这也很可能是司马迁没有采用共和元年之前纪年材料的原因之一,时代越早,各类纪时材料之间的协调难度就会越大。直到司马迁可以使用《春秋》和《左传》时,他对时间的协调才变得容易起来。
孔子编纂《春秋》,已经以鲁公的年世为轴,在协调诸侯间互异的纪年体系了,其做法是将诸侯之事放入鲁国的时间系统里,形成以鲁国纪年为框架的叙事体系,如刘知几《史通》所言,这种做法应该是《史记》本纪的源头。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受到丹尼斯·费尼的启发,在他为《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所写的第18章《历史学与帝国》中特别讨论了周秦时期编年史中的时间同步工作。并特别分析了《左传》《竹书纪年》和睡虎地《编年记》。这几部著作的时间同步工作还仅限于线性的叙事,《史记》年表则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同步做法:将不同的时间线平面化和视觉化。共和元年以来,以周王年代为纲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协调和同步各国历史的功能尤为突出,让不同地区的事件统一到一个时间框架之内。《左传》中诸侯国之间的历法和时间计算并不相同,如何将不同时间线中的事件同步到一个时间序列里,对任何人来说都颇具挑战。周代主要以天子和诸侯在位年来纪年,但不论是周王朝还是各诸侯国时常会发生政变,并造成非正常的君位更迭,即位的新君一般会直接开始改元纪年,而通过正常途径即位的国君,大多会隔年改元。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历法也存在差异,在观象授时阶段,有的国家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有的则以正月;同一国家,如鲁国,前一年还是以十一月为岁首,下一年却有可能调整为十二月。所以不同诸侯国之间的年代对应会有很大参差,且没有规律可言。夏历十一月,在春秋时代的鲁国有时候已经是新的一年了,但晋国却还在旧年;而有的年份,鲁国有和晋国有共同的岁首和岁末。鲁国年初发生的事,对于晋国来说,有时是年末,有时又在年初。当一件发生于夏历十月以后的事出现时,不同诸侯国史官的记录年代就很难协调。在《十二诸侯年表》和本纪、世家之间,以及年表中不同诸侯国之间,存在非常多的一年或两年的年代差,就是这一难题的反映。
战国以前,解决因地区差异造成的时间和事件的不同步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锚点。《左传》中保存有这种同步各类事件的痕迹,如“会于沙随之岁”“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之岁”“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蔡侯般弑其君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等以同年重要事件为标尺的纪年方式,也有“杞桓公卒之月”“齐师还自燕之月”等以某月的发生的大事为锚点的方式。出土的楚简里,以标志事件作为时间标尺记事颇为常见。但是当遵循王公纪年传统的史书和标志事件纪年相遇时,年初/年末或隔年/不隔年等问题就会特别凸显出来。因此这种协调时间的图表并不好制作。考虑到这些,《史记》东周年表的制作更显得意义非凡。
在汉武帝时代,存在多种类型的以时间为线索的文献,如世、谱和历等。世系一类的文献在战国秦汉间颇为流行。司马迁于《史记·三代世表序》说有《谍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有《春秋历》《谱牒》,足见年表的绘制主要依据历和牒两类文献。所谓“牒”,即“谍”,也就是“世”。《汉书·艺文志》有“《世本》十五篇”,历谱十八家中也有“《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这里的“世”和《史记》中的“谍”或“牒”所指相同,乃是一种书于牍板的世系类文献。《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讲教育太子时,有:“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可见世载录先王世系,并兼有警示和劝诫的功能。那么世应该有简短的大事记录。2002年和2004年,湖北荆州印台60号汉墓和荆州松柏1号汉墓都出土了题为“葉书”的文献,李零、陈伟、陈侃理等学者皆有研究。松柏1号汉墓的“葉书”以在位年为主,但也在“吕太后八年死”之后,记“其七年,发卒击南越尉它;八年死,赐户爵各一级”。陈伟、陈侃理均判断“世”之书,即“葉书”,也即“牒书”,最初写于牍板(即牒)上。
不论是松柏1号汉墓的“葉书”,还是秦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大事记,都是单线的记录,并没有《史记》年表的那种复线的网格布局。复线布局的世系,应该是谱。《史记索隐》引刘杳说曰:“《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放《周谱》,谱起周代。”《周谱》的旁行斜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式并不好判断,但大体就是《三代世表》的样式,已经是复线的世系了。但《三代世表》本质上是一种树状图谱,是基于宗族血缘世系的系统,并非以年为刻度的表格式时间图谱。
表格式时间图谱很可能是司马迁融合历表和世系书为一的创造。这种类型的年表具备了历史叙事的功能。《太史公自序》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就有综合《春秋》和谱、牒的意思。东周的两个年表相当于将东周史平面化和视觉化,并为这个阶段的历史建立了一个时间刻度或坐标轴,将原本相对的时间,变成了绝对的时间。整体看,这些年表是网状的,每一格记事都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因果的关联性。年表让时间变得可视,不同诸侯国的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关系也清晰可见。即每一格记事的意义是由整个时空之网赋予的,它同时又是这张网的一部分。年表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能力,让时间在可视的空间中流动。用几何空间结构来记录历史时间和事件,让其变得更加可以理解。故不仅历史叙事的起止设定,《史记》的年表同样让时间获得了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功能。特别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几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叙事模式。
这一形式的历史与公元4世纪出现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编年史》极为相似,二者结构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十二诸侯年表》的时间序列是自右往左,而《编年史》的则是自上而下。这与二者所使用的抄写材料和书籍的形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史记》的年表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刘知几《史通·表历》篇甚至认为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年表,其他类型的年表都无必要,《史记》列表“成其烦费”,“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并不会看表。他甚至批评《汉书》《东观汉记》在体例上完全没有必要列年表。但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出现以后,却特别受欢迎,“尤西比乌斯年表的近代版本,跻身于最早的印刷书籍之列;在任何一位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学者的藏书中,《编年史》也是最重要的必备参考书之一”。中国史书中年表受到冷落,可能与纪传的发达有关。刘知几的批评从另一角度看,是《史记》所建立的年代框架已经被后世的文人完全接受,甚至成为默认的古代历史结构。而最初建构这个理解结构的年表,反而不那么必需了。
尤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约339)
《史记》采用线性的时间架构,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武帝时代,这一选择却具非凡价值。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时,正是汉武帝封禅泰山至太初改历期间。据郭津嵩的研究,此时汉武帝已经被公孙卿说服,采纳了循环式时间观念,将汉武帝时代视作黄帝时代的回归或复现,这是一种颇具神圣性的时间观念,也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在太初改历时,上元以来的年数是十分清晰的,即4617年,《史记》完全可以按照这一时间框架,画出一个循环式的年表。然而,《史记》没有将这种神圣性的循环时间纳入叙事系统,而是坚持使用战国以来六艺解释体系中的世俗时间观念,将周衰作为汉兴的起点。司马迁自述其取材标准是“考信于六艺”,六艺经典里,《尚书》《诗经》《春秋》乃至其传记,都是世俗的、线性的时间,即便是他写《五帝本纪》参阅的《五帝德》和《帝系》,也都是客观的线性的世系,与武帝信仰的循环式神圣时间观念并不兼容。《史记》本拟六艺,采用六艺的时间模式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在将黄帝和太初设为起止之后,司马迁仍然没有将太初改历背后所存在的时间观念明确书写下来,显现了他的某种坚持。《史记》《汉书》之后,官方著述便以史书为主,《史》《汉》塑造了后世史书的书写模式,它们中的时间结构和观念也自然被延续了下来,线性的和世俗的时间成为传统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感知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文化的品格。这也许是《史记》时间框架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从周衰到汉兴并不构成因果的链条,而是天下世界由混乱到统一和兴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神圣的力量推动的,也不是伟大过去的复现,而是文明的自然进程,是从一个盛世向另一个盛世的过渡,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推动的历史。这种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之于人的倾向,虽然源自《春秋》《左传》,却因本纪、世家、列传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史书体例而得以强化。这是司马迁对历史的理解,更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代的理解。周衰至汉兴的这段线性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太初元年以前旧时代的纪念碑,也是一座象征新旧时代更替的界碑。
结 语
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列为诸侯,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已然瓦解,历史出现了大的变化。不论是诸侯还是士人,都需要理解这种历史的变化。《左传》《国语》类的史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集中编纂,《系年》是这一类史料最早被系统化的代表之一。他们理解历史的方式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史记》在叙事中,特别重视“周衰”这一起点,这一认识和《左传》《国语》相似,只不过《左》《国》是将周衰视作战国时代的缘起,而《史记》则是将其视作汉代历史的远源,并特别选择了共和元年作为周衰的起点。这是其“近代史”的开端;共和元年以前,则是其“古代史”。《史记》先秦历史的年代框架虽然参照了《尚书》和《春秋》,但却特别重视周厉王以来的“近代史”,目的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推究汉兴的缘起。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古代史”非司马迁所重,它并不属于理解汉兴的主要环节,故《史记》中的古史主要以《诗》《书》中的材料为主,并不关心其是否具有清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至太初元年只有738年,在《史记》所囊括的时间序列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构成了周衰至汉兴的完整过程。这种截断历谱,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做法,让时间也成为被剪裁的对象,不再是天然存在的外在历史框架,具有了构造历史过程和赋予事件以历史意义的价值,对后世的时间观念有奠基意义。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