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65号,坐北朝南,位于园子的西半部,在几株大树环抱下,一条小路通向它的正门。四周没有绿篱围着,草地宽敞。后面与66号为邻,前面与64号为邻。上图中远处的那排白墙红窗棂的平房,正是后来加盖的燕南园50号。
我从小就对这栋楼很好奇,因为它和我家住的燕东园40号一模一样,在燕东园这样带有较大顶楼的一层别墅小楼还有四座,但在燕南园只有独一无二的65号。
我也一直对65号的住户充满好奇,究竟有哪些人家曾经生活在和我家一样的居住空间环境里。寻找这份名单时曾遇到一个难题,后来随着考证“吴文藻、谢婉莹所住的60号究竟是否现在的66号”迎刃而解,原来现在的65号,在燕南园1945年以前的门牌编号是61号。查找1926—1937年度“燕京大学教职员通讯地址”,我发现从1930年至1937年在这里住的是梅贻宝、倪逢吉夫妇。
前文讲过,燕园曾流传一段佳话:“燕京的三位小姐,招来清华的三位女婿。”说的是清华大学送出留美的三位高材生 ,与三位留美的燕京大学女生结为夫妻,学成归国后统统“入赘”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为首的校方,采取了与现在高校类似的引进人才政策,为他们三对夫妇提供了优厚的薪酬还有最好的住房。当时最好的住房就在燕南园、燕东园,而燕东园先建好,不少楼已经住满了,燕南园还在分批建设中,因此他们先后搬入燕南园,李汝祺、江先群住进62号(现在的64号)、梅贻宝、倪逢吉住进61号(现在的65号),吴文藻、谢婉莹住进60号(现在的66号)。
梅贻宝、倪逢吉夫妇服务燕京大学20年,是创建燕大的“老臣”之一,梅贻宝还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校长(1942—1946)。1949年5月他们从上海离开大陆移居美国,从此在中国内陆的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消失了。
建筑物作为物质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能帮助你与历史人物建立对话和联系。面对燕南园65号别墅小楼,我来尝试打捞湮没已久的梅贻宝、倪逢吉夫妇。
一
梅贻宝(1900—1997)
梅贻宝1900年生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15年与梁实秋、顾毓琇同期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有梁实秋的文章为证:“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云、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1923年他与梁实秋、顾毓琇、梁思成、吴文藻等同船赴美。他插班进入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欧柏林学院,一年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系。1927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在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响与指导下,梅贻宝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墨子:一位被人忽视却与孔子匹敌的对手》(《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主要内容是通过中西比较视角,重新评价墨子的哲学地位,论证墨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对手”,更是中国伦理与政治哲学中极具原创性的代表人物;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革精神和功利主义色彩;与孔子的“仁爱”思想对比,墨子的“兼爱”更具普遍性与平等性。这篇论文是早期系统向西方介绍墨子的英文研究之一;后被扩展为1929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墨子的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梅贻宝当选中国学生会干事,工作中与担任中国学生会会长的倪逢吉相识。这位清秀干练的江浙女子,当时在哥大颇负盛名的社会学系修读硕士。两位优秀的学子互相吸引,两颗年轻的心在异国他乡慢慢靠近。
倪逢吉(1902—2001)
倪逢吉1902年生人。1920年她进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习。一年后,通过严格的选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专为女生设立的庚款留美名额。此名额开始于1914年,每隔一年录取10人左右,后因经费紧张减少为5人,至1927年止,仅招收了7批共计53人。倪逢吉就是清华大学1921年选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她赴美后,先入金陵女子大学的“姐妹校”史密斯学院,后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1925年,倪逢吉硕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地位之变迁》。同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伯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密大校友巴伯先生专为亚洲女性留学美国所设立的。
1926年,倪逢吉比梅贻宝先行回国,在母校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一年,教授历史学、社会学;第二年北上,开始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并被推举为燕大董事会中的女教员代表董事。她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多,她呼吁女性以实际行动求得自身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更呼吁社会解开施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锁,倡导“男女道德标准当求同一,女子讲贞操节义,稍一失常即为一般人所不齿,男子则酒地花天不以为羞,这样畸形的道德标准日后力求取消”。
燕大社会学系在介绍当年都有哪些名师曾先后任课或兼课时,开出一长串名单:陈翰笙、吴文藻、张鸿钧、严景耀、雷洁琼、杨开道,言心哲、陶孟和、冯友兰、赵紫宸、倪逢吉、赵承信、李安宅、关瑞梧、陶希圣等,倪逢吉跻身其中。
1928年,梅贻宝学成归国。他在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还到哈佛大学、德国科隆大学进修过,并游历了西欧诸国。在北平火车站迎接梅贻宝的,是等待了将近两年的倪逢吉,梅贻宝随即把倪逢吉介绍给了家人。利用夏天的假期,倪逢吉带着梅贻宝回了趟浙江,得到了家中父母的认可。这一年,燕京大学的注册课主任正好出缺,梅贻宝应聘就职。
“我同逢吉于1928年订婚,1929年结婚。新郎长袍马褂,新娘则凤冠霞帔,花轿迎入礼堂。盖殊不欲采用西洋婚礼服装也。未料竟成花边新闻,轰动一时。上海图画月刊登载婚礼照片甚多。可惜多年流离迁徙,全都失散无存。”梅贻宝在自传中说。
1929年第38期《良友》画报“结婚留影”专栏
找到了1929年第38期《良友》画报,在“结婚留影”一栏,刊登了两对新人的新婚照,左边是吴文藻谢婉莹的西式婚礼,右边是梅贻宝倪逢吉的中式婚礼,相映成趣,令人莞尔一笑。
梅贻宝夫妇婚后搬入燕南园65号。1931年生祖骥,1933年生祖麟。梅贻宝担任注册课主任,教务处主任。在燕大读过书的学生,差不多都认识这位儒雅清秀的梅先生。他曾担任过几年招生委员会主席,与报考新生打过一阵子交道,开学后则为入学新生开一门思想方法课程,同时常年教授一两门哲学课。“师生间较多认识往来,庶几近乎教育理想”。
梅贻琦(1889—1962)
1931年末,梅贻宝的胞兄梅贻琦从华盛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调回,就职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春天,梅贻琦夫妇携五个子女搬进了清华园头号官邸甲所。
梅家五兄弟中,梅贻琦居长,梅贻宝居末,两人相差11岁。庚子之乱,梅家避乱逃亡,回来后发现所有家业已被洗劫一空。梅家诸子女原来每人都有一位奶妈,到了庚子年出生的梅贻宝,没钱聘奶妈了,母亲又奶水不足,只好佐以糕饼喂养。那糕饼就是米面粉搅拌放一点儿糖。每天抱着小幺弟,细心给他喂糕饼的正是11岁的五哥(梅家按照家族大排行,梅贻琦被弟弟妹妹称为五哥)。梅贻宝用12个字形容自己和梅贻琦的关系:“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他说:“五哥的言行功业,影响余一生至巨”。如今长兄在清华,他在燕京,清华园甲所与燕南园65号相距不远,往来方便,得以时常到清华省视,不亦悦乎?梅贻宝后来回忆说:“论国言家,在我这流离失所的一生中,这几年要算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唯一的不幸:1936年他们的长子、5岁的祖骥因病夭折。婚后,逢吉本已失业,按照燕京大学教职员服务条例规定,夫妇不得同时在燕大服务。待两个儿子略长大,倪逢吉便受聘辅仁大学。伤子之痛,使得她立志专攻儿童福利,转而承担起家政学教学工作,致力于儿童福利人才的培训。梅贻宝说:“不过日日进城授课,较辛苦耳。”
二
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得以勉力维持,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就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梅贻宝夫妇不耐生活在沦陷区受日军欺侮,他们向学校告假,要求到后方参加抗战,并且已受聘为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燕京大学遭日军封校,在校的主要教职员纷纷被投入监狱,校务长司徒雷登正在天津,不久便因为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而被逮捕。燕京大学迎来至暗时刻。燕大临时校董会于1942年2月开会,一致决议在后方复校,并当即成立复校筹备处,推举梅贻宝为筹备处主任。
梅贻宝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业已抗战数年,民生疲困,物价高涨,在后方平地起家,恢复一大学,困难重重。经多方奔走磋商,地点选定成都。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系由美国及加拿大各基督教教会所协力创设。校园在成都城外西南隅华西坝,甚为宽敞。惟在燕京进行复校以前,早有人满之患。抗战以来,南京的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济南的齐鲁大学,先后迁来成都。三校各自与华大合作,另在华西坝边缘,添造临时校舍,维持校务。燕京大学再来成都,华西坝委实无法容纳,只可另作别图。幸蒙张岳军(拿)主席大力维持, 得以租用陕西街华美中学小学两所,并蒙拨给华阳县文庙应用。复承华西大学支持,得以在华西坝进行理科课业。
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成都)燕大办学分散在几处,空间都很局促:理科教学安排在成都锦江南岸的“华西坝”,与华西、金大、金女大、齐鲁合用;租用陕西街的华美中学,一部分作为办公和教学用房,所幸华美女中系三层楼房的建筑,房间小而多,利用这一优势,尽量拼凑,见缝插针,比如二楼一小间校长室的过道上,置一桌一椅和一部打字机便是秘书办公室;另一部分作为女生宿舍;近旁的启华小学为教员宿舍;借用何公巷1号,即成都文庙为男生宿舍和单身男教员宿舍。许多男生都记得文庙前那两棵参天的大桂花树,9月里怒放,香气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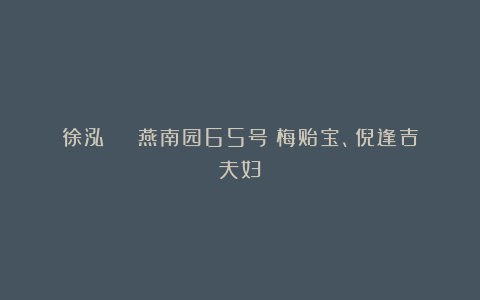
最难的还是办学资金问题,教育部下发一部分战时教育经费,远远不够。梅贻宝遵循张伯苓老校长(梅贻宝系南开中学毕业)的训示“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将募得资金的一部分最终兑换了3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民营事业如重庆大公报,亦竭力支持,于经费捐助外,尤多精神鼓励。另有国际援华会等国际团体,筹款协助,勉强成局”。
当年夏天开始招生,报名者极为踊跃,光成渝两地即逾3000人。而招收名额只限150人,还有150个名额是留给追随而来的燕大学生。1942年10月1日,拥有文、理、法三个学院14个系的成都燕京大学正式开学上课。当天上午全校师生在陕西街校内集合整队,一名魁梧的同学高举着写有“燕京大学”字样的红旗,身后是整齐的队伍直奔西坝河足球场。其时,华西、金大、金女大、齐鲁四所教会大学的师生均已到场,济济一堂。燕大的到来,是华西坝五所大学的首次汇合,在一起听美国落选总统魏尔基访华来蓉演讲也可算是燕大复校上的第一课。成都燕大代校长梅贻宝首次亮相,就当了魏尓基的高级翻译。
成都燕京大学的教员阵容,以原任燕京教员为主体。在后方复校特殊情形之下,夫妇不得同校服务一条,临时失效。不少教授夫人担任了教职:第一个就是梅贻宝夫人倪逢吉担纲家政系主任,还有郑林庄夫人关瑞梧讲授经济学,林耀华夫人饶毓苏讲授经济学等等。英美籍教职员尚有包贵思女士及夏仁德先生惠然来临,设坛施教。
特约教授的阵容,令成都文风为之一振。有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曾远荣等。每次开讲,教室外、窗口边都挤满听众。梅贻宝说:所可惜者,陈寅恪先生即在成都燕大教授任期内,双目失明。原来他左眼膜垂降已有数年,屡治不愈。在成都忽然右眼膜亦不幸垂降。陈公住进同仁医院,院址即在燕京对街。学生们踊跃的组成看护队,轮班侍候,替陈师母分劳。陈公感念之余,向我说道,“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抗战期间,在四川成都,梅贻宝以代校长的身份,主持着(成都)燕京大学;在云南昆明,他的兄长梅贻琦以清华大学校长之职,掌舵着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梅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大学校长,梅贻宝一度与兄长齐名,被称为小梅校长。
抗战末期,生活愈益困难,精神疲惫,教育界人士清苦尤甚。1945年4月,梅贻宝应聘赴美讲学,聘期一年。战时赴美只有美国空军运输机可乘,他当时由重庆、成都飞到昆明,抵达时天色已晚,需次日续飞。正好趁便去看五哥、五嫂。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长公馆’。校长家里来了不速之客,难免有些紧张。尤其是晚饭已过。给我安排吃一顿饭,亦颇费周章。大概是向同院住的陈福田家里讨来的面包牛油。连过夜的行军床……诸侄们看到老叔很是亲热”。
这张床就搭设在书架前、书桌旁,被子也是临时借来的。晚上梅贻琦一面看学校公文,一面和弟弟叙家常。梅贻宝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便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
梅贻宝感慨不已:“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现在想来,近乎奇谈,亦应视为吾国教育界从业员的美谈”。
三
1945年10月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1946年夏天,(成都)燕京大学师生全部迁回北平,与本部正式合并,实现统一办学。这时梅贻宝还在美国参加“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倪逢吉把家安顿在了朗润园20号。那么梅贻宝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
前文已经说过,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是我母亲韩德常的五姑。母亲三岁丧母,是姑姑们把她带大的,最早带她的就是五姑韩咏华。因此我母亲与梅贻宝、倪逢吉很早就认识,称呼梅贻宝为“梅老叔”,倪逢吉为“倪姑姑”。在《梅贻琦日记》1946年9月15日这一天有这样几行字:……后至朗润园20号逢吉处午饭……饭后拍照二三张,与逢吉至南大地徐家,看德常新生男(女?)孩(名徐泓)……笔下两次提到“逢吉”,在她家吃的饭,由她陪着去南大地徐家,都未提及梅贻宝,可见此时梅贻宝还没有回国。我姨姨韩德庄是1945年入学的燕京大学心理系学生,她在1946年9月的日记里写到:“选课:陆先生(陆志韦)、沈先生(沈乃璋),外系还有梅老叔的国文课”。据此推测,梅贻宝结束赴美交流项目聘期一年回到北平,应是在1946年秋天。回校后,梅贻宝即出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燕京校友回忆陆志韦、梅贻宝先生时说过:那些老学究都是牌王。这句话说十人有九人是准的。打牌包括麻将、桥牌,还有扑克。花样翻新,比如麻将,一条龙、门前清,玩的都是新章。
桥牌基本在陆志韦先生家开打。“每个礼拜总得有一两晚在陆家打桥牌。牌手有梅贻宝先生、梅太太、金城银行的汪经理、林启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吴兴华。”文章还披露了燕大教职员桥牌队八人四组的阵容:梅氏夫妇一对、林启武廖泰初一对,汪经理吴兴华一对、陆志韦陈熙橡一对。他们常与清华和北大的教职员桥牌队“三角”比赛。
安逸的日子并不长。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燕京大学校园里思潮涌动。梅贻宝在自传体的《大学教育五十年》坦陈了自己的想法:“燕京墙外可听国军退守脚步。整个局面,已是朝不保夕。余素来认为个人自由、学术自由乃人生至宝。是以水火绝难相融。而且不惯缄默,不肯低头妥协。自谅一朝政变,像我这样出了名的加料‘落伍’教授,难得善果。燕京宣布,学校要维持到底,教员学生,行动自由。话是如此说,我去请假离校,陆校长仍劝我留校留职,维持太平局面。我以为我留下来,不但于我不利,深恐还会挂累燕京,反增疚愧。于是决定请假。”
梅贻宝、倪逢吉夫妇第二次由燕京大学准假留职。第一次还是在1937年,他们不耐日军欺侮,到后方参加抗战。那一次他们很快在成都即回归,继续服务燕大。但这一次,便是永诀了,有去无回。
四
1986年,摄于梅贻宝先生家。前排左起:韩德常、倪逢吉、徐浣;后排左起:梅祖麟、梅贻宝、徐献瑜
1986年7月,我的父亲母亲赴美探亲。刚到罗切斯特,母亲就着急去康奈尔大学探望她的“梅老叔”和“倪姑姑”。
梅贻宝先生见到我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献瑜,你好!你还打桥牌吗?”40年前,他们夫妇每周去燕东园27号陆志韦先生家打牌,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我父亲也会打桥牌,但不是燕大桥牌队的主力,只偶尔在三缺一的状况下做一个牌搭子。
同去的妹妹徐浣回忆:“妈妈将梅贻宝夫妇亲热地称为老叔和倪姑姑。我对这位倪姑姑印象很深,她的气质非常好,很和蔼,是一位善谈的老人。”
同去的妹夫程嘉树,对梅贻宝先生印象深刻,他说:“梅先生中等个儿,胖胖的,有点灰白头发,和爸爸很熟络。他还带我们到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走了走。”
这次写作中,我重新阅读了梅贻宝所著《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他多次谈到自己的一生是流离失所的一生。他办大学教育,前20年在燕京大学,后30年在国外大学执教。1955年至1970年,梅贻宝就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东方学教授兼远东中心主任,倪逢吉也获聘为大学图书馆编目员,负责创设图书馆中的中日文献部门。两人于1970年同时退休。同年9月,梅贻宝受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长,做到1973年6月。夫妇两人一直持绿卡,曾两度侨居美国(1949—1970年、1973—1997年),直到病逝,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名片也一直标注“北平燕京大学哲学教授”,他说:“实际我未尝向学校辞职,学校亦未尝把我撤职”,以示对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消失的燕京大学表达永远的怀念。
1973年以后,梅贻宝、倪逢吉夫妇与儿子一家同住。仁者高寿:梅贻宝逝于1997年,享年97岁。倪逢吉逝于2001年,享年99岁。
儿子梅祖麟,从小在燕园长大,童年时家住燕南园65号;上中学时家住朗润园20号。育英中学在城里,他住校,每周末来往均乘坐燕大校车。
他195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1—2000年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教授,1992—2012年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梅祖麟曾多次来大陆讲学,2005年,他受聘担任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在清华大学开设“近代汉语语法与方言研究”课程,除清华学子外,北大、社科院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
2010年春,梅祖麟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批私人藏书漂洋过海,从美国纽约州Ithaca运抵清华。他的这批赠书共计65箱、2626册,是从私人藏书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外文图书约占七成,中文书以台版书刊居多,出版年代覆盖整个20世纪,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较珍贵图书,如1867年出版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
讲学与捐赠都选择在清华大学,可能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的大伯父梅贻琦先生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的父亲梅贻宝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5级的学生,他的母亲倪逢吉也是清华大学1921年选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
2023年10月14日上午,国际著名语言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先生在美国逝世,享年90岁。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809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