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我这一辈子》,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的对祖国的热爱对黑土地的深情;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北大荒农机事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的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熊映青先生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自己平凡又伟大的一生;用专业的知识和的严谨的态度剖析工作中的问题,攻克一个个生产技术难关;用一张张精心绘制的设计图填补了一项项科研空白,并无私地分享出来。
他是用沾满油泥的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工匠,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家国的赤子。
本期分享的是回忆录的第三部分,1958年3月—1972年10月在855农场和友谊农场期间。
熊映青
(1958.3—1985.10)
十万转业官兵“进驻”密山。
1958年国家发出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十万转业官兵闻令而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片荒原,它使人联想起前苏联对西伯利亚的移民开发,以及美国大队人马翻山越岭向西部地区进军时的历史。我和我爱人就是这中的一分子,当时,因为我们是技术干部,组织已经给我们安排了对口单位,都是安排在中等院校当老师,但我们都报名去了北大荒,这在当时的报纸上都有我们报名去北大荒的名字。我们八航校转业的官兵大概有近二百多人,我被指定为副大队长(正队长是航校教官),从此进入开垦北大荒的行列中。
下图为八校训练部部分转业军官合影(带箭头为本人)
十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都是经过密山县,再奔赴各个地方。密山县是位于祖国东北角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县城,火车到这里就终止了,再往里就是漠漠大荒。我们沈阳空军转业官兵是最早到达的单位之一,暂住在火车站旁的军用帐篷里,由于人数众多,本来就不大的密山镇已经容不下在短时间内来这么多的人,密山镇商店里的商品和饭馆里的食品很快就被用尽,面对密山镇无法容纳众多官兵的困境,王震将军在火车站召开官兵大会,宣布凡是交通暂不通农场的部队需留下行李,由师长带头步行到指定农场,有效缓解了密山的拥挤状况。密山“北大营”原为日本鬼子关东司令部,56年起成为铁道兵农垦总局所在地。转业官兵中,部分技术干部被分配到855农场修理厂,其余则分到853农场,其中包含了著名的北大荒“燕窝。我的爱人舒淑芳是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来的,部队代号201,每当一列火车到站,我都会去寻找201部队,由于到达的部队很多,所以找起来非常费劲,经过十余天的努力,我终于查到从南京来的201部队已经驻扎在距离密山10多公里的“东方红公社”。我急匆匆地赶到那里,找到了201部队的带队队长,向他说明了情况。队长非常理解,随即把我爱人和她的档案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带着爱人和她的档案来到了855农场,这大概是最简单的调动手续了。大规模开垦北大荒由我们这批十万转业官兵开始。
(1958年3月~1963年5月)
855农场总场距离密山20多公里,农机修理厂位于密山北大营铁道兵农场总局旁边。我被分配到修理厂当拖拉机修理工,大约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技术员兼调度。当时修理厂的设备非常有限,仅有一台C-630车床、两台C-620车床,以及万能铣床、牛头刨床、磨床和立钻床各一台。我对这些设备都很陌生,于是开始了白天日常工作、晚上拜师学艺的生活。很快,我掌握了车床的操作。当时,厂里没有人会操作万能铣床,正好对面一家工厂想借用我们的万能铣床加工零件,这家工厂是兴凯湖劳改农场的机械厂,劳改对象全是北京市送来的犯人,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划为右派而来的,来我们厂干活的是一位50多岁的小业主,因偷税而被劳改,修理厂尹厂长让他教我铣床操作技术,这位师傅文化水平虽低,但他的铣床技术非常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加工经验,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学习,我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加工技巧,这些经验对我后期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个月后,他穿着一身新衣服来找我,告诉我他劳改期满新生了,我问他何时回北京,他说:“凡是北京来的劳改犯新生后均不能返回北京,由政府安排就业。”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该劳改农场还有一位一级工程师——潘工(好像是被划为右派),尹厂长指定教我齿轮加工计算……。不久后,我也再未见到这位老师,他们都是我终身难忘的特殊老师。
在855修理厂期间,有两项技术革新让我终身难忘,当时农场条件极差,运输卡车多为苏联二战剩余下来的“吉斯-6”,没有任何备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后桥螺旋伞齿轮。经过多日试验,我终于在万能铣床上加工出了这种齿轮,但由于材质、热处理及加工精度极差,能用上半年就很不错了。
(右一是我的爱人舒素芳,当时安排在工厂当工人)
第二项设计制造了土锻锤-“夹板锤” ,是在锤头上连接1根3米长20×10㎝柞木杆 通过电机→ 离合器→驱动上方皮带轮→ 对夹紧轮“夹紧”、“松开”进行操作, 杆下端连接1个由钢板焊合成50㎏的锤头, 锤砧是用日本鬼子准备攻打苏联大炮弹头做成的。 此“夹板锤”一直沿用了很多年。见下图。
三年自然灾害即1959年至1961年,这段时间是转业官兵们到北大荒面临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旱涝灾害为主,叠加政策因素导致粮食短缺,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这期间出生的,出生时体重都不足5斤。
1959年秋天,因天气变冷爱人即将分娩,被安置在武装部部长的厨房里居住。这个厨房虽然狭小(约2×2.5米),但因为有炕不冷,这让我们感到很满足,在这样的环境下,爱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为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快乐。1960年爱人调入裴德“八一农垦大学”教俄语,裴德距密山很近,乘火车半小时的车程时间。这一时期,大跃进运动与三年自然灾害交织,导致农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农场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供应逐渐减少,由每月的29斤减至27斤,其中还包括需要上交的两斤“爱国粮”。到了年末,这27斤粮食变成了两斤白面和一块豆饼(折算为25斤粮),这时绝大部分人吃不饱、用树皮树根充饥,因此患上了营养不良性水肿,各个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全身无力。值得庆幸的是我爱人单位“八一农垦大学”供应的27斤全是粮食,为我们家渡过饥荒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吃不饱而且又寒冷的的情况下,我们每天仍然坚持工作。记得那年冬天农场要检修拖拉机及农机具,当时因缺少拖拉机零配件,总局通知各农场修理厂去虎林总局备件库查找所需零部件,有什么拿什么,我和修理厂另一位同志去了,这过程中有两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那天,我们前往虎林总库查找零部件,正值严寒,气温骤降至零下40℃!本就有些感冒的我,迎面又刮来刺骨的西北风,鼻子犹如刀割一般的剧痛难忍。没过多久,鼻子竟失去了知觉,摸上去硬邦邦的,像一块冰,同伴一看,惊呼:“你的鼻子尖全白了!”我立刻意识到——鼻子严重冻伤了, 幸好,我在属于北方的沈阳航校工作过,积累了一些应对极寒天气的经验,我没有贸然冲进温暖的室内,而是站在屋外,抓起一把雪,用力搓揉鼻子,直到它逐渐变软、恢复知觉。事后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直接进屋,鼻子尖的冻伤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坏死。从虎林回来后,我意外发现凭火车票竟然可以在食堂免粮票就餐!这个发现让我惊喜的不得了,我们两个人各买了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我同行的同事大概是饿极了,吃得太快,结果一下子噎住了,当时费了好大劲才勉强咽下去,可能是被噎怕了,他不敢再吃那碗还没有吃多少的小米饭,索性送给了我,我一下子吃了近两碗米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垦荒者一个月的口粮只有2斤白面和一块豆饼,能吃到一碗不要粮票的小米饭,简直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难得!这碗饭不仅填饱了我肚子,更让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满足与幸福,那种滋味,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记得那年冬天,修理厂的指导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可以去855农场三分场要些死鸡(因无粮可吃而冻死的鸡),回来补充营养,当我看到这封信后,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于是我立刻坐上了去往三分厂卡车,因为驾驶室里没有位置了,我坐在敞篷的车箱里,顶着零下40℃的严寒,一路颠簸到了三分场,下车时,我的手脚几乎冻得失去了知觉,活动了好一阵子才勉强能走路。 三分场的指导员很理解我的苦衷,一下子给了我10只死鸡,那一刻,我的心情简直高兴的无法形容,仿佛捡到了宝贝一般。我立刻搭上拉粮的车返回修理厂。当晚,我和指导员(我们俩的家都不在密山)一起煮了两只鸡,美美的吃了一顿,那鲜美的味道至今难忘,剩下的8只鸡,我带回裴德家了,这些鸡在那个艰难的冬天里,成了我们补充营养的“救命粮”。
1960年的冬天,粮食极度匮乏。85x农场(具体名字记不清了)是劳改农场,那里的情况更加严峻。没有油、没有粮,人们只能靠树根、树皮、野菜等代食品充饥。这些代食品虽然难以下咽,但勉强还能应付。然而,当他们把水稻壳粉碎后食用时,问题就严重了,有些身体弱的人,食用稻壳粉后,大便排不出来,肠梗阻而死。这件事惊动了中央,相关部门也因此受到了批评。从那以后,我们的口粮全部变成了粮食,每人每月27斤。据说,农垦局还储备了一些粮食,以备应对更困难的局面和来年的播种。
由于缺乏拖拉机修理备件,冬季大修工作几乎停滞,大家都无事可做,几乎每个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走路成了极大的挑战,每走100多米就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走路。后来,我们发现田地里还能捡到一些散落的大豆,于是大家每天艰难地走到田里,弯腰捡豆子,通常一天能捡到1斤左右的豆子,回家后用茶杯装上大豆和水,放在火炉上煮熟后吃,正是这些捡来的大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渡过了那段饥饿的灾荒岁月。 无论是那10只死鸡,还是田地里捡到的大豆,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为了克服灾荒,农场在1961年春天推行了种自留地的政策,农场开垦荒地并起好垅,号召大家去种玉米,我积极响应号召,种了近一亩玉米,到了秋天,收获了160多斤玉米,当时,附近的新建军垦农场有大豆却没有玉米,我便用这160多斤玉米换了一些大豆。接着,我用一部分大豆换了10多斤豆油,剩下的则与附近的朝鲜族老乡换了60多斤大米。这些粮食和油,是帮我们家渡过灾荒的重要物资。 当我将大部分油和大米带回家时,心里充满了欣慰和满足。饥饿也彻底治好了我因吃不惯玉米大茬子而患的胃病,我把它称之为“饥饿疗法”,那段日子,虽然充满了艰辛,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和互助的力量,让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依然能够找到生存的希望。
(963.5~1972.1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百业待兴之际,苏联政府提出协助我国建设一座2万公顷的大型谷物机械化农场。经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项目选址于三江平原腹地的友谊农场。该农场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里程碑,更成为中苏友谊的象征,对后来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吸取苏联垦荒经验具有深远意义。1954年,中苏联合垦荒队挺进三江荒原。由49名苏联专家组成的援建团队携先进技术与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建设者并肩奋战。拓荒者住地窖、战狂风,于1955年1月3日完成野外勘测;1月5日苏联首批农机设备运抵;同年5月3日举行盛大开荒典礼,正式启动机械化垦殖。至1963年,该场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垦样板,直属农垦部管理。1963年5月,我调任国营友谊农场总场修理厂,先后担任发动机车间班长(行使车间主任职责)及主管技术员。此时,该厂代表着国内拖拉机柴油机大修技术的顶尖水平。爱人同期在友谊农场中学担任俄语教师。此外,相较先前工作的密山地区相比,友谊农场的生活设施较密山地区好很多,如设有职工食堂,街上有“小馆”,现在叫餐馆,还配备有托儿所,支持周托制,周一送托,周六接回家,完善的后勤保障使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那个时候常常连续多日驻厂攻关。通过高强度实践,我在柴油机大修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这段经历既充满挑战,又令人倍感充实,见证了个人成长与农场发展的同频共振。
在担任发动机车间班长期间,我成功解决了ДТ-54(苏联)和东方红-54拖拉机离心式机油滤清器转速测量的问题。柴油机的机油通过离心滤清器轴进入离心转子,再由转子外壳上的4个喷油咀沿切线方向喷出,喷流的反作用推动转子高速旋转(转速大约6000 rpm左右),将油中的杂质抛掷到转子壁上。过滤质量完全取决于离心转子的转速,因此大修后如何测定转子转速是否达到6000转/分,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然而,60年代尚未有“闪光测速仪”这样的设备。于是,我采用电动缝纫机上的无级变速电动机驱动一个带转速表的闪光转子,通过调节闪光转子的转速,使其与滤油转子同步,目测滤油转子处于不转动的虚拟图像时,转速表上的转速即为滤油转子的实际转速。这种无接触转速测量方法,成功解决了当时大修离心式滤油器的质量问题,受到了厂里的嘉奖。不久后,我被调到厂部担任主管技术员。
拖拉机气缸盖弯曲变形后会引起漏气,在当时如果变形量小,采用平面磨床磨平的工艺,如果磨去量过大,会影响气缸压缩室的容积,于是,我采用火焰矫正方法来矫正,其效果非常好,因此得到了广泛推广。
中国农机研究所(后为研究院)与我们厂共同研制过一套大修工具,并作为大修工具标准向全国推广。其中,发动机翻转式装配台是由我设计的,这套工具不仅提高了大修效率,还为大修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友谊农场修理厂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我在技术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让我结识了许多技艺高超的师傅和同事。拖拉机驾驶室及发动机外壳蒙皮变形和损坏的修理属于钣金加工范畴。车间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吕师傅,技艺非常高超。他原是汽车修理厂的钣金工,1958年转业来到友谊修理厂。中国第一辆红旗轿车的车身是由全国十多位技艺高超的钣金工师傅手工敲击出来的,吕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拜他为师,学到了许多钣金技艺和经验,也让我结识了许多其它方面技艺高超的师傅和同事。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我在多次改行和挑战中,始终能够凭借扎实的技术基础和不断学习的精神,克服困难,迎接新的挑战。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从1962年就开始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4年底到1965年1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966年5月社教运动初期时,我被下放到友谊农场7分场第5生产队任技术员,主要是负责农业机械在田间耕作、故障排除及保养,爱人及两个孩子也一起去了生产队,我的爱人在五队的学校当老师,该学校是中小学校办在一起的,除了教授俄语,还教过音乐和物理课。
1968年6月30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归管辖。兵团共接收了93个国营农、牧、渔场,合编为5个师(管辖58个团)和3个独立团,分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以及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独立三团。其中,友谊农场改名为兵团三师十八团,我们5队则改名为十八团七营68连。
1966~1972年层层下放的简要经历
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能按照每变换一项工作的顺序,回忆在新岗位上进行的技术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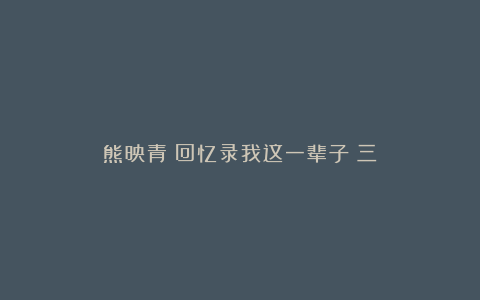
刚下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生产队安排我们与当地一户人家合住。房东一家人非常友善,对我们很关照,房子是南北炕的布局,他们住在南炕,我们住在北炕,睡觉时用帘子隔开。后来,连队为我们这些下放户盖了新房子,房子盖的不错,但炕总是烧不热(不知道别人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请连队来修理,才发现炕面竟然砌了三层砖,难怪烧不热。后来将炕面改为一层砖,问题终于解决了,炕也变得暖和了,可没过几天,炕头的位置就把褥子烧着了,差点引发火灾,原因在于炕头那里的砖是用玉米秸撑着的,结果玉米秸烧着了,砖掉下去了,火烧着了褥子。其实,炕的问题都是当地人故意搞的,因为他们嫉恨我们工资高(我们是转业技术干部)。当时,我和我爱人每人每月的工资都是七十多元,而当地农工一个月只有32元,还要养活一家七八口人(女人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他们把怨气撒在我家的房子上。后来,我就自己动手修炕,每年掏一次炕,这样我家的炕特别的暖和。北大荒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磨练了我,教会了我许多生存的技能。
当时,国营农场实行“大寨工分制”,全年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5队全部采用机械化耕作,拖拉机使用的是“农用柴油”。这种柴油价格便宜,但油中含蜡量高,如果在低温环境下使用,容易凝固,导致拖拉机无法正常工作。如果选用零号柴油(可在8~4℃左右气温下使用),价格要高出2~3倍;如果使用-10号或-20号柴油,价格则要高出5~6倍! 北大荒有一个常规做法:过“十一”后,拖拉机的水箱要放水;过“五一”后,停止放水。我到5队后,进行了一项技术革新,使得5队的拖拉机即使在十冬腊月的严寒季节也能使用农用柴油。 技术革新的具体内容:
1. 贮油罐加热
使用电阻丝将机耕队的贮油罐加热到20℃左右,确保向拖拉机油箱加油时,油温适宜,避免柴油凝固。
2. 拖拉机排气加热油箱
在拖拉机后部的主油箱增加一个外罩,将排出的热气导入外罩内,对油箱进行加热。这种加热方式速度非常快,能有效提高油箱内柴油的温度。
3. 小油箱设计
在发动机滤油器附近设置一个5~10升的小油箱,内装0号、-10号或-20号柴油。这个小油箱的功能是用低温柴油启动发动机。当主油箱的油温提高到10~20℃时,即可切换使用主油箱的农用柴油。
4. 关机前的操作
在当天作业完毕关机前,必须先用小油箱内的低温柴油运转几分钟,然后再关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次日能够顺利启动拖拉机。
这项技术革新不仅解决了农用柴油在低温环境下使用的问题,还在当年为5队节省了不少开支,使“大寨工分”增值了许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总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在5队召开了现场会,向其他生产队推广这项技术。 通过这次技术革新,我不仅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好评,也为5队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注〗:一般来讲,5#柴油适合于气温在8℃以上时使用;0# 柴油适用于气温在8℃至4℃时使用;-1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4℃至-5℃时使用;-2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5℃至-14℃时使用;-35#柴油适用于气温在-14℃至-29℃时使用;-50#柴油适用于气温在-29℃至-44℃或者低于该温度时使用。
从技术员到农工
我是1966年下放到生产队的,当时做技术员,大概1969年麦收开始前,我被解除了技术员的工作,下放到地里当农工,负责锄草、收割玉米、小米等作物。由于过去在部队做单杠“脱手回环”运动时腰椎受过伤,无法长时间弯腰工作,我找到连长要求调换工作,于是,我被调到晒场,负责扛麻袋“座囤”(将晒干的粮食堆放到一种简易的小粮仓内)。 每人扛一个敞开的麻袋,内装160斤粮食,从“之字形”跳板走上去,将粮食倒入粮仓内。一般“之字形”跳板有5~6节(相当于2.5~3米高),要求扛麻袋的人体力强且没有“恐高症”。我第一次上4节跳板,就顺利完成了任务。
晒场的技术革新
当时晒场缺少镀锌铁板,许多镀锌铁桶、壶等工具都已损坏。由于我之前学过一些钣金工技术,很快在晒场仓库内修复了这些工具,并且到总厂买回了几张镀锌铁板,补充了一些新的桶、壶等。 仓库内还有一台电动磨,可以将玉米磨成颗粒(称为大、小茬子)或面粉。队长让我把它改装好,供应队里食堂使用。这台电动磨的电机是6极滚,转速较低。分场粮食加工厂通常采用三台串联的方式加工,但我没有沿用这种传统方式,而是将电机换成4极滚,转速提高到1500 rpm,只需一台就能达到三台串联的标准。 传统的从磨输送到筛子的方式采用斗式(或刮板)提升机,结构复杂且造价高,这也是队里长期未使用的原因。于是,我采用了气力输送方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能够自己加工玉米,大大降低了大、小茬子的供应价格,深受队里好评。 在制作“气力输送粮食”装置时,许多农工不相信这种技术。在即将试验时,围观的人很多。当电动磨磨出的大(或小)茬子被成功送到两米多高的筛子上时,大家都兴奋的鼓掌了。这项革新完成后不久,我接到七营的命令,去营部粮食加工连帮助改造榨油机。
下图是气力输送原理图:
七营加工连改造榨油机
为七营加工连改造榨油机的经历,是我在技术革新中的又一次重要实践。黑龙江出产的大豆,其品质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当时的榨油工艺却极其原始,榨油过程需要在40℃以上的高温环境下进行,因此榨油工人都是男性,作业时赤膊上阵,榨油的方式类似于卷扬机,通过近10人搬动卷扬机给榨油机加压,出油率非常低。
在改造之前,我专门去牡丹江榨油机厂进行了调研。一位接待的工程师告诉我:“如果你们真想学的话,就住下来好好学习几个月……”我只向他请教了两个关键数据:榨油机的压力吨位和榨油时的室内温度。他答复说,压力机吨位应在40-50吨,室内温度应在40℃以上,然后我就回到七营,开始设计榨油机图纸。我选用了东方红-54拖拉机上的CB-46凸轮泵,这是当时性能较好的油泵,其性能显著超过了牡丹江榨油机厂的油泵。基于这个油泵,我设计了一台50吨的油压机,实际最高压力可达70。我将油压机放入一间全为双层玻璃的小房内,房内通过暖气将温度提高到50℃以上,而榨油车间的温度则保持常温。改造后的榨油机由于压力提高到50-70吨,出油率得到了明显提升,还显著改善了工人的作业环境,榨油工人不再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赤膊作业,操作也更加简便,只需搬动液压阀门即可,这种改善榨油环境的方式,当时在国内尚属首次,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六十年代,出于备战需要,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掀起了制造步枪高潮,三师18团机械厂要在很短时间造出10支自动步枪献礼,因枪管“来复线”和“搬机”两零件加工遇到问题,命令我立即去团机械厂完成这个任务。我去后带四个徒弟,一个是哈知青,三个是温州知青,他们都很聪明能干,在万能铣床双班倒加工零件,大概是用了20多天时间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的第二天接到命令在12小时内返回68连,回去后就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渡过了三个月,这期间看守们对我还算不错,我在他们监管下到田里干活,他们不给我定工作量,还把我用玉米桔杆做的玩具带给我儿子和女儿,我从“牛棚”出来后,我们还成为了朋友。
从“牛棚”出来后不久,我和我爱人参加了十八团为期一个月的“干部学习班”。因为孩子在连队无人照看,我们便带着孩子一起到了学习班,并为孩子联系了当地的小学上学,这段时光是我进入北大荒以来最轻松、快乐和悠闲的日子,每天学习各种文件,然后是学习班提供的三餐,晚上可以和家人一起逛逛曾经呆过的友谊农场。1972年调回十八团机械厂,爱人舒素芳回到十八团团直中学继续教俄语,两个孩子正好该升初中了,于是就读于十八团团直中学。1973年三师领导得知我1966年下放以来,一直未重用,下命令调我到三师科研所工作,18团不放,师部再次下调令我才正式到三师科研所报到。
作者简介
主 编:明桦
微 信 号:lucking0526
本期编辑: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