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湖南临澧县城关人, 1977年考入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后分配至北京机械工业部研究所工作。1985年调干入深圳中外合资企业, 后下海自办企业。
1968年下半年, 毛主席发表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 随着临澧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县委会及政府机关等一律解散重组, 除少部分干部留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普通干部基本上回原籍劳动或进五七干校。 因我父母都非当地干部,下放农村一时没有去处,一番商议,决定去临澧县西部山区的太浮公社双福大队插队落户。
县委机关的妇女干部们送高凌母亲(前排中)下乡 。1968年12月摄
临近年底的一个大清早,太浮公社双福大队的一辆板车,早早就进了临澧县城,来到了我家门口。我们已提前将家里仅有的几个简易桌椅和一些箱子准备妥当,两个壮汉三两下就装好了我们的全部家当。临澧的板车并不配马,全靠人力推拉,我和父母亲三人跟在板车后面,紧走慢赶,几乎走了一整天。从四新岗绕斋阳桥再到衍嗣庵,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我们一行才抵达太浮公社距太浮山最近的小集镇——王化桥。此地离县城近80里,进入大山区了,再往前已无大路。
双福大队的社员一众人早在王化桥等候多时,我们到达后,大家简单寒暄几句,没有任何耽误,随着一阵吆喝,车上所有东西就转上了他们的担子或肩膀上。我们一家三人则跟在长蛇般的队列后面,黑暗中摸索着在蜿蜒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向大山深处走去。
又经过艰难的一个多小时乡间小路,队伍终于在一座队屋前停下来。迎接我们的是大队书记杨金富,上二家生产队队长杨成益。 队屋旁边,特为我们准备的一间偏屋早已打扫好,屋内升起了一堆篝火。众人放好行李,安置好我们后就打着火把,分散消失在周边无尽的黑暗中。
下乡太浮山前高凌(后排)和父母亲合影。 1968年12月摄
山乡首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队里安排我们在队屋前面一家农户(生产队民兵排长家)吃面。我实在是又饿又累,这一天还几乎没怎么吃东西,面还没煮熟,我就迫不及待想吃。面端上来了,我连吃两大碗才舒了一口长气。父母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不断给我使眼色,我假借昏暗的灯光,全当没看见。由于那天实在太晚,人也累得够呛,很快我就和衣躺在草堆里睡着了,父母亲则在火堆旁守了下半夜。
天亮后,山村的整体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上二家生产队全村仅有十来户人家,位于大山下的一小片坡地上。村子里铺满了石板路,大石块砌成的石墙和巷道连接各户,背荫的石块表面是深青色的苔藓,石墙上攀爬着开蓝紫色小花的藤蔓,水塘边雷电劈过的古树露出黝黑恐怖的豁口,残缺的石碾和磨盘使村庄显得格外古朴和原始。村子周围三面环山,东面是出山通道,每天下午很早高山就遮住了西斜的阳光,天空早早黯淡下来,夜晚要比山外平原地区早来近一个多小时。
我们住的这间队屋是上二家生产队最大的公共资产,也是全队的活动中心。偏屋约20多平米,间隔成两间,里间住人,可放两张床, 外间是灶房兼吃饭的地方,但现在只是个空屋,我们自带的所谓家具,仅是碗筷厨具、衣物及少量的凳子箱子等,再加上几个纸箱(书籍、课本类),临时摆放一地,连床都没有,可谓真正的家徒四壁。
看到我们如此简陋的家当,第二天起,全生产队的人都在为我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家而忙碌。队里面有的是木材,大家每天烧的柴就足以为我们盖木屋了。队里的汉子们大多数天生就是好木匠。当天,一大帮人就在队屋前的坪地上,摆开了做家具的架势。很快就完成了两张床、一张饭桌,四条长凳。老人们还为我们砌了炉灶、在偏屋外侧给我们盖了一间杂物间,用作茅厕、放置柴火、饲养家禽等。好心的村妇们争先给我们送来了各种蔬菜、干山货、木柴。粮食也派人挑来了,连水桶、劳动工具等也分享给我们。
那几天,以队屋为中心,每天都呈现热闹纷繁的场景,我们家所有事情都是村里最热情讨论的话题。姑娘们、孩子们、老人们、男子汉们,有事没事都会来我们家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只要有哪儿不对劲,大家都来帮手,或者从自己家里搬件东西给我们用,家家都以能贡献一份物质或出点力而高兴。比如,没有柴刀,马上有人提出,我家有,赶紧回家里取了拿来。谁家有点什么新鲜菜,一定要送点给我们先尝。有人捕到了猎物,第一时间会分给我们一份。村民们谁家办个红白喜事,一定要请我们作为座上客。村民们的这种纯朴、好客的真挚感情,确实使初来乍到的我们很温暖、很感动。
没几天功夫,俨然一个像模像样的新农家就初步建立起来了,而且,远比我们原来在县委家属院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新砌的灶台,新搭的柴草偏屋,崭新的充满着松木香气的大床、衣柜、饭桌和板凳,应有尽有。我们来时的一切辛苦和担心,已被乡亲们盛情的迎接和拥有全新家具的幸福感所替代。我也被小伙伴们的热情和友好所陶醉,沉浸在初期的兴奋之中。
这一切初步安置妥当后,父母亲就动身去了趟桃源姑妈家,接回来了寄养在那里的弟妹。我们一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在太浮公社上二家生产队,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村家庭。
寄养在桃源的弟妹(后排和前排左一)和姑妈家人在桃花源合影。1967年摄
在刚刚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全家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情,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我们决心首先实现自食其力。在生产队配给我们的菜地里,翻耕了土壤,整理好洼地,种下了各家各户送给我们的萝卜、白菜、大蒜等蔬菜苗。父亲还撒下了一片高丽参种子,期待收获。
每天一大早,我就和父亲跟随乡亲们去太浮山砍柴。白天,父母亲则和队里的社员们去杨家峪水库修堤。 晚上, 生产队的人们自发打着火把,来到我们家隔壁的队屋大堂烤火,听父亲讲一些国内外的形势。有时虽然不过是念念报纸,学习一些文件,但那些好客的乡亲们,围着篝火,和父母亲一起聊天,畅谈世事,津津乐道讲些村里村外的趣闻旧事。大山村民的淳朴亲切和对我们的接纳包容,让我们感受深切,感激在心。
上二家一角。2017年摄
孩子们则每晚都会在村里疯玩,很晚才回家睡觉。很快,我们就和村里的孩子建立起了友情,村里的大姓是杨姓,队长杨成益,团支书杨开财,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开进(16岁)和开友(13岁),还有另一家的杨成江(12岁)、杨金梅(10岁)等。小伙伴们教会我干农活,手把手教我砍柴、打草鞋、烧野火、捕野物,一起去放牛。还送给我们猫崽、狗崽、猪崽、鸡崽。一时间,我们过去在城里许多想做而做不到的奢望,全都得到了实现,家里充满了蓬勃生机。
随着山区深冬季节到来,山野大雪纷飞,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住的队屋只是简陋的瓦片屋顶,没有天花板,稀疏瓦片的缝隙到处漏风。早上起来,家具上落下了一层雪末,蚊帐也给压塌了。
1968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寒冷,但在大雪地里,我们却玩的分外开心。我们不知疲倦地在雪地里追踪兔子的脚印,或是到村里孩子们的家里去烤火,围着火坑津津有味的品尝烧烤的红薯或芋头。
下雪的时候,队里的活全停下来了,杨队长带着父亲和我踏着齐膝的积雪,向太浮山的大山深处进发。穿过层层山岚,我们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漫山都是遮天蔽日的大松树。杨队长指着一棵有两三人合抱粗的大松树说,就是这棵。原来,他是要带我们挑选一棵为我们做家具的大树。得到父亲认可后,第二天,我们和生产队的几个人再次上山。父亲带了几盒烟(那时最奢侈的支出),在山上折腾了大半天,锯倒了那棵大树,并将树干分解锯成四节,树杈以上全部去除,直到很晚才回家。
锯倒的树干后来在山上躺了一个夏天,待树干基本去除水分,才就地剖开成大块板材,再风干3个月后,才由全队的男人,每两人一块(共16块),经过十几里的山路抬出大山森林。
乡下的第一个春节很快就过去了,爸妈接到了通知,要去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家刚刚建立起来,打家具的木材还躺在山上,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父母亲又一次犯愁了。关键时候,父母亲又想起珠日公社安子冲的张嗲嗲,她之前在县城带过我们,还是得再请她过来。一番联系后,张嗲嗲知道了我们的难处,即刻收拾行李,赶了40多里路,很快来到太浮上二家和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
张嗲嗲(前排左二)和高凌(前排左一)一家合影。1965年8月摄
嗲嗲的到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窘迫。嗲嗲年过古稀,仍然很骄健,关键是她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知道怎么操持一个农村环境下的家庭。她带上我们三个孩子(14岁、10岁、6岁),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解决一系列生活困难,很快实行了从无到有。
首先,我们自己种蔬菜。在老乡的帮助下,种下的辣椒、茄子、 黄瓜、莴笋、豆角、萝卜不仅自给有余,还馈赠给乡亲们不少。我们种的菜瓜是夏天纳凉时的上品。我们在菜地及住屋周围开垦荒地,遍种南瓜。秋天时,南瓜大量丰收,堆满一屋。我们就用南瓜做饼,煮南瓜饭。
我们还养了20多只鸡,夏天的时候,最多每天可产4—5枚蛋。还养了一头猪,打猪草、喂猪,是个折磨人的事,但也熬过来了。年终,猪长到110多斤了,虽然个头还不算大,但它的食量却越来越惊人,每天要吃两大桶,我们几个孩子扯猪草已无法喂饱它。随着腊月的到来,村里开始了一轮杀猪潮,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将猪杀了。尽管猪并不肥,但已足够我们一家自己食用,我们也像当地所有的农户一样,腊肉挂满了灶前,整个冬天直到春季,都在吃腊肉,那是很美味的享受。
我记得,腊肉刚熏挂没几天,我们已馋的不行。一个阴郁的雨天, 嗲嗲煮了一大锅萝卜,并将整个腊猪头炖在里面,香味飘逸半个山村。 下午,当我顶着寒风从学校回家时,离家老远就嗅到了腊肉的香味, 煮了几乎一整天的萝卜炖腊肉,香气扑鼻。晚上,嗲嗲和我们三个孩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围着灶台,大快朵颐地吃光了一大锅萝卜炖腊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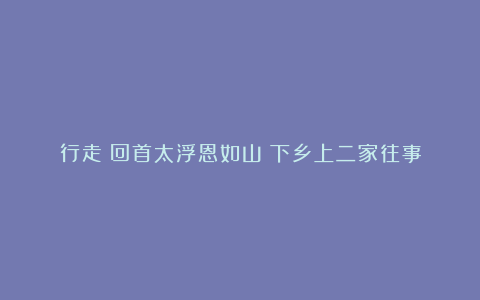
腊肉早已炖得烂熟,完全不用筷子,直接一大块一大块的撕扯。那一餐的美味感受在脑海里,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家里的小狗黑黑也大饱口福,美美的享受了一顿骨头。
高凌弟弟(右一)看望86岁的杨成益队长(右二)。 2017年摄
生活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我们的学业也在新的地方开始继续。妹妹尚不到上学年龄,在家里呆着,混在农家女孩堆里玩石子儿。老弟上小学三年级了,在双福大队部的一所民办小学就读。学校在村后的小山那边,两三里路还算近。他们上学去的晚,回来的早,不在学校吃中饭。村里上那所小学的孩子一大群,一窝蜂似的,他们是几个年级拼班上课,老师也就是同村的大孩子,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我则要去王化桥(太浮山附近最大的集市)上初中了。王化桥距上二家有三四里山路,每天上午9点钟赶到学校,下午4点半放学往回赶,到家一般5至6点。天晴还好,要是遇到刮风下雨,山路泥泞,路途十分艰难。学校中午不管饭,要自己带午饭去学校,嗲嗲每天早上都要给我准备好当天的午餐。
王化桥学校那时刚升级为初中,以前只是一所当地的小学,因增开了一个初一班,就美其名曰王化中学。其实仍然是小学底子,师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初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谭家海,初一数学老师秦月兰(谭的妻子),都是原小学老师升上来的。与双福大队小学的区别只是,王化中学的老师大部分是公办教师。
那年高凌家前面的邻居婶娘。 2017年摄
与我同排(那时流行解放军的编制)的同学有附近屋场(下二家生产队)的杨石金、民富大队的陈勇、双堰大队的袁敏(津市下放的女孩)。我和袁敏是城里来的孩子,学习基础相对要比当地的孩子好, 上语文课总是我得表扬,拿我的作文做范文。袁敏则常常数学拿满分。 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觉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语文倒没什么,主要是数学,初一开始学几何、代数了,什么都要用字母表示,这对于文革辍学近两年的我无疑是极大的难题。26个英文字母还不熟悉,怎么理解数学题。小学5—6年级的知识根本没学过,分数的运算、 图形的概念都没有。但初中的课本里一开始就讲有理数、 正负数运算、 几何证明等。
老师自己也是边学边教,我简直是一头雾水。加上家务事多,在家里几乎没有时间写作业,每天要砍柴、养猪、种菜,还要定期去赶场买米。因此,那段时间的数学基本没搞懂过。好在学校不怎么强调教学质量,考试也只是个形式,期末的时候,仍然给我各科全优的成绩。后来回城后才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拉下了好远。
看望队里的民福大叔和大婶 。2017年摄
那时,我们的户口尚留在城镇,吃的粮食要从粮店买回来, 当地生产队的粮食自给都困难,没有余粮提供给我们。而粮店位于太浮公社所在地衍嗣庵,离上二家生产队有10多里山路,家里包括嗲嗲三人每月口粮近80斤。米怎么到家呢,只能由我每隔10天去赶一次场,到衍嗣庵粮店买米了背回来。
我每次背30斤米,来回近30多里山地,一年四季,不分冬夏,不论雨雪。如果一次赶场没有去背米,家里就是无米之炊,揭不开锅。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走几十里山路已不轻松,还要背30斤大米,这可需要一定的勇气,也的确需要一定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不是一月两月,而是坚持了一年多,想想总共背了多少斤大米,走了多少里山路,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真是难以言喻。尤其是当学习吃力、或身体不舒服、或天气极为恶劣(极热或极寒)时,完全不想出门,但一看到家里米缸已空,弟弟妹妹已经断粮,还是必须挣扎着坚持克服困难上路。路途中,有时实在背不动了,就躺在地上,孤立无助的望着天空和山野叹息。休息一会后,再继续前行。有几次,途中遇到了雷暴雨,为了保护米不被淋湿,我就把衣服脱了裹着米袋,打着赤膊背着米,奋力往家里奔走。也有耽误一两天没有去背米的时候,那样,嗲嗲只得拿着升子去村民家里借米下锅。
这个老屋场曾经是高凌的家。这是2017年春天他弟弟和上二家的乡亲们在老队屋前留影。2017年摄
在太浮乡下的那一年多里,父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一个多月,很快就离开我们在全县各地奔走工作,我想他们也一定有其苦衷,只能听从上级调遣。这样,我每个月除了背几次米,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父母工作的地方取当月生活费。那时不像现在这样交通便利,多远都是靠步行,而且基本上是在乡间小道上行走。母亲工作地点大多在县城,父亲则远在珠日、停弦、修梅、青山。这些地方离太浮动辄50—80里,每次都要1—2天才能往返。当时的联络也不易,根本没有电话,联络主要靠信件,父母亲会来信告诉我取款的时间、地点。接到信后,我会带上家里的土产、我和弟弟的作业本等和他们见一次面。而他们俩回一趟家则至少间隔3—5个月,甚至半年。妈妈工作顺便时偶尔中途回家看看我们,但她一个人返回时,必须走几十里山路。山林莽莽,人烟稀少,野兽恶狗出没,为了安全,每次都是我送妈妈走回县城,然后我一个人走回来。有时怕迷路,我就一路扯下树枝树叶放在路边做标记。常常是天不亮就赶路,天黑了我才返回大山深处的上二家。
重返浮山访乡亲。2017年春
随着秋季到来,我们在山里砍伐的木材,已完全风干。在大队书记的关照下,由当地最好的三个木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为我们家打齐了全套家具,使我们家一次性完成了基本建设。而那棵百年大树的成本才14元,加上全体生产队的免费劳力(仅香烟招待),木工工资花费约108元。家具的油漆,全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刷的。
那些日子里,加上木工的吃喝,全家有六口人的生活需要安排。一时间,背米、挑水、砍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落在我这个年仅14岁孩子的肩上。光每天用水就要挑满好几缸,3—5天就要赶一次场采购物资,记工和支付工钱也是由我来处理。当这些全部完成,新家具塞得满满一屋子时,这个屋才有了点家的感觉。
在太浮山做的两个柜子至今保存在妹妹家。 2018年摄
秋后,父母亲回来了,看到家里发生的一切变化,眼里闪着泪花,抚摸着我的头说:“舒临,你真的长大了,爸妈得力了!”
我记得,这是父母难得对我的一次表扬,但我并未感到幸福,直觉得鼻头一阵发酸……
家具添置大功告成,意味着我们留在太浮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父母亲开始张罗着全家再次迁回县城。这年深秋,我们准备启程搬家了。要离开我们生活了近两年的上二家生产队,离开刚刚走上正轨的小农家,多少有些留恋。在父母亲来接我们再次搬家的日子里,家里有十多只鸡要处理,那几天每天都吃鸡;小狗黑黑也悲哀地宰杀了,用于招待帮忙搬家的村民;小黄猫则装在笼子里带走;菜园里的菜全部处理割掉,带走或送人;没烧完的柴火,用不着了的物件,就近送给老乡。平时对我们颇多关照的邻居,一一向他们道别,小朋友们也得到了我们赠送的课本和文具。
又是一次全生产队大动员,全队男女老少几乎倾巢出动,将我们的所有家当(和那年来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抬的抬、挑的挑、 扛的扛,搬到离上二家几里远的王化桥大路边。公社派了一辆拖拉机,我们的家当塞满了整整一辆车。除了全套沉重的松木家具,还有可观的农副产品。我们辛苦收获的大量南瓜、冬瓜、干菜一点也没舍得放弃,几乎全部带上。拖拉机驾驶室坐着三个孩子、嗲嗲、母亲,再算上两个司机,已无处可坐,父亲只好坐在拖箱高高的家具顶上。
车开动了,我们向乡亲们频频招手道别致谢,动情的话,不舍的话,叮嘱的话催人泪下,每个人的眼里都噙满了热泪。
随着拖拉机的突突声,我们终于启程,离开了这片曾给我们心灵留下深刻烙印的山村,离开了近两年来给我们无尽关照的可尊可亲的山民,离开了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在太浮置办的这套家具,从此一直伴随着我家,也是父母亲一生首套也是唯一一套完整的家具。多年来,父母几次搬迁,这套家具一直没有更换。我长年在外工作,每次回到老家,看到或摸着那套日渐老旧斑驳的家具,就会情不自禁回想起当年的艰难岁月。
高凌(后排左一)和父母、弟妹在一起。1983年春节
多年以后,为了感恩太浮山区的乡亲们,怀念那一段生活的岁月,我们曾数次返回上二家,看望当年的老人、媳妇、孩子们。为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我们带出了他们的后代到城里做工;尽力帮助他们的子孙解决各种遇到的困难;父母亲在生时,也一直都和上二家的乡亲保持来往。
我们家永远不会忘记,太浮公社双福大队上二家生产队的乡亲们,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友爱之手,给了我们那么多无私的关怀,付出了那么多从不计代价的辛劳,让我们在人生低谷的处境,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在生活严寒的季节,体会到了善良的温暖。
感恩太浮山!感恩上二家!感恩乡亲们!
在本平台发布的作品,在腾讯【企鹅号】【喜马拉雅】【360图书馆】等主流平台网页版同步刊出。敬请前往关注并收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