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留真谱》係中国学者首次汇集保存古籍珍稀版本书影的开创性成果,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主要采取传统的摹刻之法,但因工艺精良,所以仍能较准确地传递底本的面貌信息。其所载书影大多来自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珍贵汉籍,每种善本选录较具代表性的若干书影样张。
作为实物版本学发轫的基石,《留真谱》至今仍是古籍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所收的一些版本目前已经无法找到原书,仅能通过《留真谱》窥见一斑。即使是底本尚存者,取与《留真谱》所收书影比较,也能通过二者差异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留真谱》除初编外,另有二编八卷传世,为杨守敬去世后刊行者,其内容可确定源自杨守敬自日本携归之样张或原书散页,但是否係杨守敬亲自编定者则尚无确论,故此次仅影印《初编》全文,《二编》拟嗣后单独刊行。
作者简介
杨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生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十五日。同治元年(1862)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起,作为先后两届驻日本国公使何如璋、黎庶昌的随员赴日工作。在日期间,访购图籍,结交耆彦,代黎庶昌辑刻稀见文献二十六种,题为《古逸丛书》。回国后任湖北黄冈教谕,与修《湖北通志》,并曾担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勤成学堂总教长、存古学堂总教、礼部顾问官等职。
杨守敬博学多识,通晓版本、书法、金石、古泉等各种学问,尤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代表作为《水经注疏》。其在日本期间访求古籍,著成《日本访书志》,编刊《古逸丛书》《留真谱》,开创了域外汉籍回归中国的新时代,是近代文献学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目 录
《留真譜初編》十二卷,清楊守敬編,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辛丑(一九〇一)刻本影印。
楊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生於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四月十五日。四歲喪父,稍長從母受學,十一歲時因家庭需求開始從商,但仍讀書不輟。十九歲以府試五場俱第一中秀才。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應鄉試中壬戌科舉人,時年二十四歲,可惜此後屢應會試而不售。容肇祖將其生平分爲五段,同治元年以前爲少年時期,除日常事務外,已因獲聞汪中緒論、影繪六嚴《輿地圖》而初識本朝諸儒之學及地理學之門徑。自同治元年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三月爲第二階段,期間六次參加會試均落第,只能藉教讀謀生,但在京結識了潘存、鄧承脩、李慈銘、譚廷獻等好友,蒐羅金石,談文論道,學問既進,聲望亦隆,『都中之士多有知守敬之名者』,潘存題《水經注疏初稿》至以『妙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譽之。光緒六年四月,應何如璋之約,東渡爲駐日本國公使隨員,黎庶昌接任公使,惺吾仍得留任。其在日期間訪購圖籍,結交耆彦,收穫頗豐,又代黎庶昌輯刻希見文獻爲《古逸叢書》二十六種,至光緒十年四月差滿,是爲第三階段。此階段雖未必如袁同禮所云爲其研究目録學之始,但確實是以訪書刻書爲中心,其在文獻學上的地位亦由此奠定。光緒十年五月,惺吾歸國『赴黄岡教諭任』,並因黎庶昌保奏,以知縣遇缺即選,加五品銜。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與修《湖北通志》。次年進京參加最後一次會試,仍不中,嗣後絶意科名,專心著述。十四年(一八八八),於黄州築藏書樓,因鄰近東坡雪堂,故名鄰蘇園,自號鄰蘇老人。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張之洞聘其爲兩湖書院地理教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得奏保爲勤成學堂總教長。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選授安徽霍山縣知縣,以年老不耐簿書辭之。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與馬貞榆同爲存古學堂總教。陳寶琛咨舉爲禮部顧問官(湖北僅兩人,另一名爲柯逢時)。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辭去存古學堂之職。自歸國訖於是年,基本都從事教育之業,故容肇祖定義爲『作教官到作學堂總教的時期』,其重要著作大多撰成或刊行於此階段。七十以後,精力漸衰,以名重藝林,得賴鬻書爲生,並續補增訂舊著。晚年旅居甘翰臣家時『求書者踵接於門,日不暇給,繼之以夜』,辛亥革命後避地上海,仍有日本水野疎梅等人前來拜師習書。此階段出任之公職,一爲湖北通志局纂校,一爲民國參政院參政(後者常被斥爲晚節有虧,但容肇祖已辯明其受迫之故)。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一月九日,『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七。『自歸道山,海內外新聞稱道先生者,連篇累牘,不絶於書』,生平事跡除見於自述之《鄰蘇老人年譜》外,亦可參考《清史稿》卷四八六本傳、陳三立《宜都楊先生墓誌銘》、陳衍《楊守敬傳》、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袁同禮《楊惺吾先生小傳》、汪辟疆《楊守敬熊會貞傳》、郗志群《楊守敬傳略》等文,吴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楊世燦《楊守敬學術年譜》,程翔章、程祖灏《楊守敬年譜》三書所記尤爲詳盡。
楊守敬博學多能。從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宫島誠一郎《栗香齋筆話》稿本所載對話來看,其擔任公使隨員時已在政治、外交問題上有一定見解。辭章方面,『工儷體,爲箴銘之屬,古奥聳拔,文如其人』。[一]書法尤爲傑出,其赴日時帶去一萬三千餘種碑版搨本,震動東瀛,明治時期的書壇泰斗巖谷一六、日下部鳴鶴等人皆向其問藝,巖谷一六甚至稱『金石之學, 將以先生爲傳燈祖師,弟奉尊歸』。[二]但其所以『爲湖北師儒宿學之冠』[三]『爲鄂學靈光者垂二十年』[四],主要還是緣於學術上的成就。『守敬年二十即好輿地之學,壬戌計偕入都,始嗜金石文字,庚辰至日本,又致力目録,此三端者,皆自信不隨人作計,而於輿地尤始終不倦。』[五]陳衍亦評價曰:『同光以來,熟目録版本之學者,有桐城蕭穆、江陰繆荃孫。精金石考證之學者荃孫、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學,其所獨擅耳。』[六]其著述等身,據王重民《楊惺吾先生著述考》[七]統計,凡一百〇二種(包括各類印本、未刊稿和書中提及者),地理學之要者有《水經注疏》[八]、《水經注圖》、《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金石書法之要者有《三續寰宇訪碑録》《楷法溯源(正續編)》《寰宇貞石圖(正續編)》,目録版本之要者有《日本訪書志》、《叢書舉要》、校勘群書之札記[九]以及此次影印的《留真譜》。
《留真譜》清光緒辛丑刻本卷端刻楊守敬手書序文,敘述原委甚詳,今移録全文,分段考釋:
著録家於舊刻書多標明行格,以爲證驗。然古刻不常見,見之者或未及卒考,仍不能了然無疑。余於日本醫士森立之處見其所摹古書數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關考驗者),使見者如遘真本面目,顔之曰『留真譜』,本《河間獻王傳》語也。余愛不忍釋手。立之以余好之篤也,舉以爲贈。顧其所摹多古鈔本,於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補之,又交其國文部省書记官巖谷脩与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得見其楓山官庫、浅草文庫之藏,又時時於其收藏家傳録祕本,遂得廿餘册,即於其國鳩工刻之,以費重僅成三册而止,歸後擬續成之,而工人不習古刻格意,久之始稍有解,乃增入百餘翻。友朋見之者多歡賞,囑竟其功。至本年春,共得八册,略爲分類印行,觀者不以爲嫌,當并所集之廿餘册賡續刻之。光緒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記。
中國學者講求古籍版本甚早。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讎群籍並撰書録。其《晏子書録》云:『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十]即存區分版本之志,但當時關注者僅爲文字內容之不同,忽視實物面目之差異。晚唐五代以來,雕版盛行,學界開始關注刻本版本的問題,南宋時以尤袤爲代表的文獻家率先主動著録同書異版者(同時期的晁公武、陳振孫、張淳也有類似意識,只是不如尤袤典型),但如何用文字傳遞版本信息,尚欠考量,僅能粗略地通過版刻地區、字體大小等指標擬定版本名稱(偶爾標注重要異文)。記録版本的行格,劉肇隅認爲始自清初的何煌,其《〈宋元本書目行格表〉序》云:『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記》、《黄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備焉。』無論是以地區冠名還是記行格數字,都過於抽象,既不免混淆版本(不同版本每見行格一致者),也可能誤判來歷(如楊守敬將宋監本《爾雅》定爲蜀刻本),這些文字描述的版本信息都不足以作爲充分的證驗,所以序文説『古刻不常見,見之者或未及卒考,仍不能了然無疑』。
通過圖像來記録版本特點自然比文字更精確,然而在攝影術引入出版業前,複製圖像必須依靠摹寫或影刻,這兩種方法的難度和成本都遠高於複製文字,以致於中國學者在設計版本信息的義項(行款、板框、牌記、墨釘等)時精益求精,卻未見匯集複製版本圖像的成果,儘管清乾嘉以後,對古籍版本的關注和研究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種背景下,遠渡重洋的楊守敬在森立之家見到匯集古籍書影的《留真譜》數巨册,不難想見其欣喜之情。有趣的是,楊守敬在不同場合的相關表述存在抵牾。
楊守敬《留真譜序》云:
余於日本醫士森立之處見其所摹古書數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關考驗者),使見者如遘真本面目,顔之曰『留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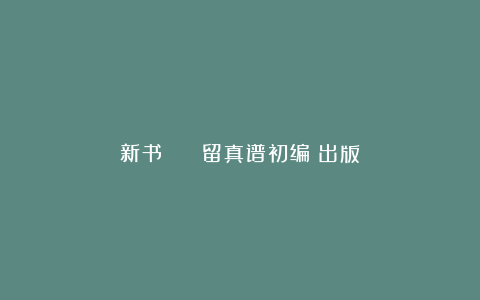
《留真譜》卷一《左傳》舊鈔卷子本書影後刻楊守敬跋語云:
右《左傳》舊鈔卷子本,舊藏楓山官庫。三十卷首尾完具,最稱奇籍。余來此託掌秘書者蹤跡之,竟不可得,蓋散佚於明治之初。原本每卷後有題識,詳見森立之《訪古志》,此從小島尚質摹本,僅末卷兩題,原卷當尚在人間,願後來者按圖索之。
楊守敬跋影鈔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解》云:
舊讀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各經皆有古鈔本,唯左傳經注本、注疏本,皆只據足利學所藏宋槧本,因疑日本左傳無古鈔本,及得小島學古留真譜,中有摹本第□卷首葉,字大如錢,迥異日本諸鈔本,問之森立之,乃云此書全部三十卷,是古鈔卷軸本,藏楓山官庫,爲吾日本古鈔經籍之冠,山井鼎等未之見也。余因託書記官巖谷脩,於楓山庫中檢之,復書乃云無此書,深爲悵惘,故余譜中刻第□卷首一葉以爲幟志,而森立之力稱斷無遺失理。[十一]
《日本訪書志》卷一《春秋經傳集解》(古鈔卷子本)條云:
初,森立之爲余言,日本驚人秘笈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爲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數。此書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託書記官巖谷脩訪之,則云偏(當作徧)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爲言,此書不容遺失。[十二]
縱觀引文,可知楊序所謂森立之摹寫《留真譜》之説不確,[十三]該譜實小島尚質所編鈔,後歸森立之庋藏,故楊守敬得以在後者家中見之。按小島尚質(一七九七—一八四七),初名和戚,字學古,號寶素,通稱喜庵,後又稱春庵,係江户時代末期幕府醫官,曾任職於江户醫學館。森立之(一八〇七—一八八五),字立夫,號枳園,通稱養真,後稱養竹,曾任江户醫學館講師,被稱爲明治維新後醫學考證派第一人。除醫者身份外,二人都喜藏書校書,與楊守敬可謂同道,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最倚仗者便是澁江全善、森立之等人合編的《經籍訪古志》,[十四]其《日本訪書志》中涉及小島尚質藏書的條目亦指不勝屈,故《日本訪書志緣起》稱『日本收藏家……又有市野光彦、澁江道純、小島尚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又稱『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爲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今只就余收得者録之。』[十五]
《留真譜序》未記録其初見小島氏《留真譜》的時間。按楊守敬到東京後初次登門拜訪森立之的時間是日本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一月廿一日,[十六]即光緒七年。其跋影鈔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解》落款爲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夏六月,可推知其在森立之家見到小島氏《留真譜》的時間即在這兩點之間。
楊守敬後來編刻《留真譜》的行動無疑緣於小島氏摹本的啟發,但對比上述引文,不難看出《留真譜》卷一跋語書於楊守敬訪得金澤文庫本之前(當時還誤以爲金澤文庫本已散佚於明治之初),影鈔本跋語書於訪得金澤文庫本並影鈔完成後,《日本訪書志》定稿更晚(初刻於光緒二十七年,即一九〇一年),關於楊刻《留真譜》的表述也隨著時間推移越發明確。最初只説『此從小島尚質摹本,僅末卷兩題,原卷當尚在人間,願後來者按圖索之』,意謂摹刻小島氏本,成一零葉,給後來訪求金澤文庫本提供參考。到了光緒八年作跋時已稱『故余譜中刻第□卷首一葉以爲幟志』,卷數處仍空缺,蓋欲保留修改餘地,但既提到『余譜』,足見此時已有匯集多種書影編成『譜』的計劃,但新譜採用何名似尚未定。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六月『又理舊業,檢點藏書,擬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真譜》』,四年後『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真譜》成』[十七](前者序署『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自記於兩湖書院之東分教堂』,後者序署『光緒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記』)。
從現存資料來看,《留真譜》和《日本訪書志》幾乎是同時發願、同時付梓、同時刻成。楊守敬於光緒七年記《日本訪書志緣起》,光緒八年有編《譜》之舉。《日本訪書志》現存版本有兩種牌記,一曰『光緒丁酉(一八九七)嘉平月鄰蘇園開雕』,一曰『光緒辛丑(一九〇一)宜都楊氏開雕』,筆者所見《留真譜》牌記皆爲『光緒辛丑三月宜都楊氏梓行』,但《日本訪書志》無論是丁酉開雕還是辛丑開雕,實際上都是同一套板片,只是歷經持續的挖改調整,遂衍生出內容有異的多種版本來,[十八]那麼以常理度之,《留真譜》付梓之初應該也是『光緒丁酉嘉平月鄰蘇園開雕』,只是通行本已統一成辛丑的牌記罷了。光緒二十七年初,楊守敬致函沈曾植云:『《留真譜》或可系葉,《訪書志》亦成八册,大約四五月間可印,届時再以聞。』[十九]過去關於《日本訪書志》版本的研究,大多只能確定其年份而不知其詳,現在明確了《日本訪書志》與《留真譜》的聯繫,參考《留真譜》的牌記和楊氏書札,也可據之反推《日本訪書志》刊成的具體月份當在四月前後。
比較小島氏與楊氏的《留真譜》,其同當在作爲版本著録圖像時代的先行者,爲兼顧內容、效率和成本,都不得不採取僅複製一些有助版本考辨的書籍局部特徵的形式,即所謂『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關考驗者』之意,但這種截取局部的形式(如一行僅存首尾二字,一葉僅存開端兩行,楊氏自稱爲『節刻』),顯然與『使見者如遘真本面目』的目的還是存在距離的。其異首先在於複製手段,小島本係摹寫,楊本係摹刻,而楊氏據以摹刻的底本除自己藉傳統的影鈔方式獲得外,還可能包括照片和小島本的原葉。
《留真譜》『《尚書》鈔本』書影後刻手書識語曰:『《古文尚書·洪範第六》一卷,見《訪古志》,守敬影照得之。』按影照、照影當時即指攝影,也是楊守敬的習慣用語,如其跋《南華真經註疏》云『以西法照影刻書,前世未聞』,[二十]其跋《春秋穀梁傳》影照本云『此本爲日本阿波所藏,無一字損失,因從森立之假得,用西洋影照法摹之』,[二一]則《留真譜》此句應該也理解爲據照片覆刻。
《留真譜》『《文選》宋槧』書影後刻手書識語曰:『此爲小島原圖,獨惜其未摹籖題也。』『《論語》鈔本』書影後刻手書識語曰:『其原本則未知今藏何家,此圖亦據小島摹本也。』小島本已被森立之贈與楊守敬,由《留真譜》識語明確區分『小島原圖』和『據小島摹本』可知前者可能是據小島本原葉上板,後者則是二次摹寫。在小島本已不可蹤跡的今天,楊氏《留真譜》恐怕是我們想見其面目的唯一途徑了。
除複製手段外,更重要的是焦點轉移和內容擴張。日本古文獻的傳承授受以鈔本爲中心,與中國以刻本爲主的狀況大相徑庭,所以楊序稱『顧其所摹多古鈔本,於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補之』,雙方都是合乎理性的選擇。但楊守敬在日本遍蒐公私藏書,歸國前自稱『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板藏書五千六百册,大約在本朝唯錢遵王藏書可以相並,其他皆不足言也』,[二二]所得遠逾於小島尚質,其《留真譜》可采擇者自然也較前者爲多,於是在日本時『遂得廿餘册,即於其國鳩工刻之,以費重僅成三册而止』。此『廿餘册』與小島本『數巨册』類似,都是零散的影鈔件或照片匯集而成,此『三册』則是在日本刻成的《留真譜》初印本。如《日本訪書志》卷四『《一切經音義》日本古鈔本』條云:『余於癸未嘉平月十四日因舊局長町田久成始得見之,意欲影鈔之,以歸期迫不及待而罷,僅摹首葉款式入之《留真譜》中,然耿耿於心,未能釋也。書以告後之渡海者,其勿忽諸。』[二三]歸期迫促,當然没有時間覆刻,所以『摹首葉款式』必是影鈔的零葉,爲『廿餘册』中一種,而其手批《留真譜》識語云:『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以初印本與加藤直種子易貞觀古寫佛經一段』,[二四]當即所謂在日本刊刻的『僅成三册』者。
本書內封題『留真譜初編』,共十二卷,顯然有將來續編之意,可惜與《日本訪書志》情況類似(《日本訪書志》與《日本訪書志初編》實爲一書,作者並未續編),《留真譜》在楊氏生前也僅成此初編。自序稱『共得八册,略爲分類印行』,繆荃孫辛丑(一九〇一)五月十七日日記亦云『湖北老陶信寄《留真譜》八册』,[二五]但到戊午(一九一八)六月初六日梁啟超爲《留真譜》作跋時,已改稱『凡經部二册九十二種,小學一册五十二種,史部一册四十七種,子部二册七十五種,醫部二册六十八種,集部二册七十五種,佛部一册十九種,雜部一册二種,都四百三十種』。[二六]每册對應一卷,此次影印的上海圖書館藏本同樣分十二册,每册封面印有楊守敬手書題簽『留真譜卷□』,而非內封所題『留真譜初編』,蓋改裝時已擱置續編計劃(《日本訪書志》也是如此)。
全書未編目録,大致按經史子集比附(未標類名),而小學書、醫書、佛教文獻特多,亦有不便歸類者,故梁啟超除四部外又冠以小學部、醫部、佛部、雜部之名。其中大部分文獻選刻正文一葉,如有重要序跋、牌記,則同樣摹刻聚之,尤其是特殊標誌(如卷末字數、陰刻標記、版心花式)都精心保存,其中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就是卷一宋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正文僅收卷一首葉的前半葉,且不過完整摹刻前三行,後五行都只刻首末兩字而已,卻摹刻了宋本原附的校記《經傳識異》全文(共四個筒子葉),其他書籍也往往如此。可見《留真譜》編纂之目的純粹是服務於版本考辨,也可以説這是實物版本學正式成立的起點(之前的版本學著述未見剥離文本版本如此徹底者)。
楊守敬編刻之書多呈現動態演變的形態,如《古逸叢書》『隨得隨刻』,又如《日本訪書志》雖整體是同一套板片,但在刻印過程中不斷抽出或補入單篇題跋,竟衍生出至少六種版本。[二七]《留真譜》也不例外,各家皆著録爲光緒辛丑刻十二卷本,[二八]筆者所見諸館藏本卻幾乎無一完全相同,或增減品種,或調整葉次,這些細節變化頻繁出現又無規律,只能視爲零散個案,但光緒辛丑刻本的先後印本之間存在一次重要的統一改變:早期印本的板框邊緣(一般是左下角外圍)常有大面積的墨釘,後期印本的對應位置都已改刻爲標識卷次葉次的文字。以此標準衡量,此次影印的上圖藏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與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在綫上公佈的藏本都屬於早期印本,而筆者所見國家圖書館藏本、天一閣藏本則屬於後期印本。這有力地證明了《留真譜》編刻之初的隨意性,先刻成預留墨釘的單張書影,再根據內容確定位置並加刻卷次葉次,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各部《留真譜》順序錯亂的深層原因。後期印本已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而此次影印的上圖藏本既真實地保留了編刻之初的原貌,有助於研究《留真譜》的流變,又因刷印較早,筆畫若新發於硎,自然更便於觀摩摹刻葉面的細節。
楊序『歸後擬續成之,而工人不習古刻格意,久之始稍有解』一句,亦有關《留真譜》之刊刻事跡。按楊守敬在日本主持校刊《古逸叢書》時,已以精擅雕版技藝著稱,自述『日與刻工磋磨善惡』,『閲工人所刻之板,不用印刷樣本,即以白板分好惡』,曾於十八人所雕板片中一眼看出領袖所刻者,『其時合坐起立,拍掌之聲如雷。次日新聞出,皆詫爲異人』。[二九]其歸國後指導本土刻工,又有他人文獻可印證,如汪辟疆《楊守敬傳》云:『鄂省槧工拙俗,守敬教以影雕宋元板式,而陶子麟尤有名,故四方精槧,集於武昌。守敬各印其首葉備檢校,即世所傳《留真譜》也』,[三十]楊氏致柯逢時信云:『刻書伊始,選工不易。……湖北工人所刻仿宋字體多整齊者,此《大觀本草》則以圓潤爲主,故雖有能者,亦不得不另授筆法,故每一葉刻成,或修改,或竟棄之而易工重刻。』[三一]《古逸叢書》是楊守敬訓練日本工人刻成(以木村嘉平爲代表),《留真譜》是其訓練中國工人刻成,故本書在傳佈文獻之餘,正可作爲一手材料用於近代中日雕版工藝差異的比較研究,也應得到更廣范圍的關注。
《留真譜》又有二編八卷傳世,牌記曰『丁巳(一九一七)秋雕於觀海堂』,[三二]體例格式與初編無異,唯板框外圍加刻『二集』字樣,論者多徑稱爲楊守敬編,只有程翔章、程祖灝《楊守敬年譜》稱『民國六年,楊守敬之孫先梅將祖父所編輯之《留真譜二編》(八卷,收書二五二種)刊行面世』。按楊守敬逝世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至丁巳已逾兩載,且二編全書無證明楊守敬編輯的文字,更無類似初編的自序,其內容多來自東瀛舊本,可確定是楊氏攜歸之樣張或原書,但二編究竟能否視爲楊守敬編輯,恐怕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楊守敬年譜》對此説法也未解釋出處),故此次僅影印《初編》,或免李戴之譏。原書既無目録,今據各卷所屬編成分類簡目冠於卷端,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留真譜》又有王揚濱手書目録,詳載各種書名版本,雖國圖藏本與上圖藏本內容次序多有出入,王揚濱目亦不能適用於本書,但取之相較,正可見《留真譜》演變之一端,故移録王目於本書目録後,庶便參考。草成此文,以爲讀書者助,容涉附會,仍賴方家正之。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