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布衣祭祀庄子大典于霜降日正式礼成。参祭嘉宾与学人感而抒怀,或以文,或以诗,致意庄生,自事其心。故别辑札记锦集,与诸仁砥砺。
▲ 祭众列队逍遥堂前
01
大目 学人
演门枢机
题记:乙巳蒙城布衣祭庄,先生拈“演门”二字作主题。典出庄子《外物》篇。人生一大演门,不只是简单理解为“人生是一场戏”。不见其真者外于物,着于相,终生蝶梦一场。不言之言,不演之演,色空不二,会么?
祭庄大典前一日,在庄子祠逍遥堂前举办演门诗会。我刚布置好茶席,一只蝴蝶翩翩而至,上下飞舞,三次落在我的杯子上。昨天晚上我回到广东住处,一开门,竟然又有一只蝴蝶在屋里飞来飞去,最后落在门楣上。我没有惊扰它,只是在睡觉前把门窗开大,一夜没有梦见蝴蝶,早上它也不见了……
有人说见到蝴蝶是祭庄的感应,那么在梦里没见到它,是不是把庄周梦蝶搞颠倒了?我不禁哑然失笑,着相于蝶岂能感应庄生?悲乎!是庄周梦蝶抑是蝶梦庄周,这么好的一个话头沦为“成语”,无学,久矣。
祭庄必以讲学先行,令祭众学人斋心诚意,先生敬天爱人之用心一以贯之。今年祭庄两天讲学的内容虽是《人间世》篇,先生却以《外物》篇里的“演门”为主题词,可知庄子三十三篇凡六万五千言,是不二之言,是不言之言。老子言:强名之曰道;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人生不是演戏”。先生在这次拈提以“演门”的《人间世》讲学里的这句话斩钉截铁,振聋发聩。所谓“人生如戏”,是不是戏?如何演?能否如如不动?能否安之若素?这与财富地位无关,也不是谁嘴硬就可以拣择的。
人生于世八苦交煎,五蕴炽盛。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能随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必遭者,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先生云:人本天真,却渐渐为人欲驱使将假当真,而终于把人生演成了戏。唯学,可颠沛造次必于是。所谓学达性天者,只是戒之慎之。但尽凡情,别无圣解。
每年祭庄讲学也是庄子契心班每年四次线下课的年度第三次。上一次契心班三天课程在杭州,内容也是《人间世》篇,三天基本上只讲了第一节。这次祭庄两天讲学,也只讲完了第二节和第三节。这前三节分别讲了三个寓言故事。第一个是颜回向夫子请行,要去卫国影响国君,匡正扶危,夫子喻之“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第二个故事是叶公子高被派去出使齐国而忧人道、阴阳之患,夫子戒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托不得已以养中”……第三个故事是颜阖将要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而心怀警惕,蘧伯玉赞之“善哉问乎!”,寓螳臂当车、饲虎、养马以言道不可逆,唯戒慎以行……三个故事道尽人间世之演门枢机,至矣。
庄子寓言岂是讲故事?先生讲庄子岂是讲庄子?学人听讲听的又是什么?先生说,学问学问,治学就是学会问。而问,却断不是为了要去得个正确答案。
正如有学人在课上问先生为什么能够从早讲到晚还那么神采奕奕?先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回答;有学友课后问我,为什么先生能够把千把个字讲足两天十个课时?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而我所不知道的又岂止于此?知无涯而生有涯,治学不是消灭问题。只有存疑,才有不断叩问的生机,才有烦恼即菩提的转机。
行其庭先生曾说,人在性上都是本自具足的,只分学人和不学人两种。先生说,所谓君子,不是与富翁、穷人、专家、文盲并列的概念。高官巨贾名士专家亦多五浊妄想,囚徒败将村野老夫不乏自在慈悲。
天下有大戒二,命也,义也。义命得正者,性也,此正是演门之枢机转轴。一念转,则凡圣别。 若一志,不离自性,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则天地一宅,演门无门。
▲ 左起:司香虚云子女史,司茶大目学人
02
子复 学人
祭庄圆满完成,虽名为祭,实是自我徵圣。
祭祀的每个设置紧扣修身进境。从起礼“启户”,庄子祠缓缓打开,众人依次步入,接着,“尊天下、尊物、尊生、朝徹、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一门一进,一关一新,直到最后礼成、归藏——大门合上,“庄严”二字赫然呈现,不禁泪流满面。
祭祀,让人从生到冥,从冥到生,通幽明,无古今。
03
赵旭 学人
祭庄是在我的老家,已经举办了十三次,这次是第十四次,可确是我的第一次。
慎戒从文庙祭孔子开始,祭祀开始前山长在孔子像讲述时红了眼眶,我也忍不住哽咽。
平时的文庙没什么人,我自己来过两次只是匆匆的转一圈,孔庙已经一百年整没有人来祭祀,孤零零无言护持了蒙城数百年。
在无礼的时候人们开始追逐自由。在祭祀之前,在需要有礼的场合我会装的很有礼貌,装的很累,我就呼喊着要自由。其实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是不想装的有礼,不想被束缚。
当穿起祭服站在庄子像前我感觉无比自由,虽然祭服很重,压的肩膀很累,但我深刻的感受到,那发自心灵的自由。
祭服束缚住了四肢,何尝不“约”呢?祭服是外在的事物,我们不能脱掉,同时也让我时刻感受我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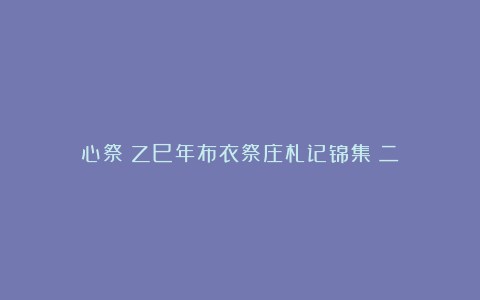
宏大的庄严,我不再单纯的是我自己,我血液里流淌着祖先的血,那看不见的千年前的勾连不能在我这里断掉。
一切是那么有律动,有节奏。我不是一只蝴蝶,可是我的心像蝴蝶一样起舞。我确实是一只蝴蝶,我知道庄子,庄子亦知道我是蝴蝶。
现在我没有更多可以言说的东西,需要时刻我在的路还很长很长。
04
知著 学人
第二次参加祭庄是2018年霜降,祭庄茶会上演了一场诗乐剧《花木兰》,我唱演了花木兰的角色,当时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演戏。也是在当时隐隐地觉得,在书院也是有不同的角色,学人、学生、喜欢唱诗的人。这令我有些恐惧,却被兴奋盖过,在因缘和习性的推动下,将自己卷入了演门。
人在世间必然会遭遇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但人若是内无主,没有主体的人,必然演不好任何角色,做什么就溺于什么,成为什么就耽于什么,最初的恐惧感是良知的强力提醒,人尚无学,根本接不住这宏大又惟微的提醒。
形就而入,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努力演一个人设,终究是要塌房的。学是重生的唯一可能,形莫若就,自己就位,人间世,此间要有人焉。
05
闻和 学人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祭庄,因事20日才得至蒙城,所幸那天下午先生的讲学正好给了我一直困惑的答案,仿若是在说给我听的一般。
基于生活中的困,一直以来有个关于“改变”的问题。刚学习传统文化时,先下手改变的就是家里人,结果你想改变谁谁便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你,这时不免心生悲怨。好似有一个印证,如很多人说的“你永远无法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因碰过壁所以觉得此说法很是正确。
但后来又发现既然改变不了你自己以外的人,那为何孔子要周游列国?孟子也去各国游说?孟子到梁惠王那儿,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听语气孟子他老人家也没被太尊重,那他在干什么?还有佛家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们不是在想改变什么吗?若改变别人不可能这种说法正确,那这些圣人为何明知不可还要为?又或者是可以改变的?
正好听到先生讲到《庄子·人间世》“颜阖问蘧伯玉”篇。先生讲到孔孟周游列国与苏秦、张仪之不同:一者,是为使王成为王而为;一者,则是为己之私利。应自我问题而琢磨之,原来孔孟是基于道义而为,本质不是为了改变谁,而是在守为人之本,礼崩乐坏的时代,而孔孟犹如行走的明灯,无论走至何处,也许会有人因着这丝光明而照见本我,回归自性而为人。与其说是一种改变,倒不如说是一种感召。而我自己之前所谓的改变别人,则是一种“自美”,如螳螂用臂挡车自以为能改变别人,结果被碾压在车辙下;自以为对别人好,岂不知一厢情愿是一种逆伤。看似同样的改变,本质却完全不同。可不慎戒!
至此,虽明改变的本质,但好像仍然解决不了我目前想要改变别人的问题。我已知反求诸己,不敢自美,但还在学好好做人的路上,还没有圣人般的光明,可看到亲人活在相互伤害中,不免悲伤想要改变什么,我该如何做?然后先生好像又给了我答案。讲到“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先生引申“孝”以说明之:“父子之间,若父没尽父之责,儿子尽儿子之责,只是作为儿子的责任,不涉及对象,回报与否并不是期许的事情。”“人若真诚的活在世上,尽你所能即可。”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我要做的便是守好自己的本分,在父亲面前我是个女儿便做好女儿该做的事,在哥哥面前是个妹妹便做好妹妹该做的,至于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我既不能指责谁又不能强行改变什么,守好自己的本分尽好自己的责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琢磨至此,内心一下子豁然,有了力量,感觉好像明白了。
此困在学人发言环节本想分享以求印证,思忖良久未能说出,今呈出望提点指正,不盛感激!
06
纯常 学人
这次祭庄《人间世》讲学期间,我被一个问题袭击和纠缠:如果一个人具有明辨是非的眼目,他如果不以自己为正确,他怎么能判断出错误?他如果以自己为正确,他怎么能忍住不去用自己的正确更改这世界的错误?他如果不去更改这世界的错误,那他的正确有何意义?先生讲课其实经常触及这些问题,我以前也做过思考,但是从没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明确地深深攫住我,让我不能释怀。回到前文去看颜子之卫,恍然发现起手点就在这里。
人间世要说正事,只有教学这一件正事,失教的人心,做任何事都将助推人成为非人。祭祀是未病的教学,征伐是已病的教学。
我们习惯了的教学就是,我知道A正确,然后把自己或别人的BCD都改成A就好了。这也是我前面一系列问题的预设。有反省的人,会谨慎于A的正确,转益多师质正,宽容一个更正确的A随时替代;有自谦的人,不敢以为A正确,潜意识奉着一个遥远的终极正确。拿A指导自己,越勤学的人,对自己越克核,越卡在自己距离A之间的夹缝中扭曲,或者卡在A与对别人的期望之间不能自拔。
圣贤之教和大人之学之所以难行,是因为本意不是教人如何正确的——老僧不在明白里,但是却逃不掉被鲁莽者解读为A的集合的命运。因此,不信圣人的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鲁莽者的反抗:手握正确的圣人,为何拿这世间的错误没有奈何?如果真有上帝,怎么不管人间疾苦?如果真有佛陀,怎么不直接度我成佛?
教学是曲致的,说“曲”好像也还有一个弯路可以循而至,其实也没有。先生总拿鸡蛋孵小鸡举例子,我现在才明白,何为时空。小鸡真是不知道怎么孵出来的,成人也不会知道是怎么成的。如果知道就可以量产孔孟了。唯一知道的就是,你具有成人的种子,所谓教学就是,把包裹的膨大剂催化剂致幻剂种种清除,还你一颗干净澄澈、通天彻地的种子,待时空化成,盛放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我们坐在自己色身的船上,色身的船泛在这个大化之流上,二而一,一而二。这是家,也是远去的方向。当祭祀绝,教学失,我们的船搁浅,却在荒芜的岸上幻想一片海,作为自己的承托。可不悲耶。
07
鸿蒙 学人
这次来到蒙城祭庄,有学人问我什么因缘来到的。我回应,因着多年大布师父的脚步而来,也是延续。
于蒙城参加乙巳年霜降祭庄,张真先生以演门一词为这次讲学主题。演这个词很贴切,在各种角色之中嘈杂的事情之中演来演去,假的也快成真的了,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而且现在很多人外在物质上拥有的东西越多越觉得很难幸福,如何才能够有可以真正幸福的能力?治学就是为了贵天真,当取物的能力变强后,就会不担心在人世间中被搅扰。
我是第一次来到蒙城参加祭庄,没想到祭服穿到身上没一会的时候就感受到衣服带来的沉重,两个肩膀十分酸痛,可也就是这样的沉重感,会提醒着自己,此时此刻“我在”。正在与先贤发生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连接。
其实没有一个在外的圣人等着你去祭祀,每一个人都是在明明德的人,是我们需要庄严生命的时刻来唤醒被遮蔽的本心。
▲ 学人鸿蒙布茶席「二年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