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闻说金微郎戍处》
—王国维
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
不知今又过辽西。千屯沙上暗,万骑月中嘶。
郎似梅花侬似叶,朅来手抚空枝。
可怜开谢不同时。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
隆冬的风,总带着一股子凛冽的寒,刮在脸上像细针,却偏有那红梅,要在这刺骨的冷里挣出一抹艳色来。你看那枝头缀着的朵朵,哪里是寻常的花开?分明是攒了一整年的力气,把春的柔、夏的烈、秋的静都揉进了瓣儿里,才敢在这寒风里舒展着,把极致的美绽得那样决绝。
可春风是最不懂怜香的。它慢悠悠地暖过来,拂过梅枝时,那些艳色便慌了似的,一片、两片,打着旋儿落在泥土里。等风再软些,枝丫就成了光秃秃的模样,立在春光里,像个丢了心事的人,静得让人心疼。又过了些日子,才见嫩绿的芽儿悄悄冒出来,怯生生地舒展着叶片,像是要寻那梅花的踪迹 —— 它定是听说过,这枝头上曾有过怎样热烈的绽放。可低头望去,只有满地黄梅的残痕,风一吹,便碎成了无法拼凑的回忆。
世人总叹梅花开得短,却不知这花叶从来不同时的宿命,早被天地写进了光阴里,成了一段说不出口的遗憾。就像那句 “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字里行间裹着的,哪里是梅花的故事?分明是世间多少来不及说出口的深情。你想啊,有那样一个女子,把爱恋揉进了日日夜夜的等待里,想对着心上人说一句 “我心悦你”,可转身时,那人却早已走远,只留她站在原地,抱着满心的牵挂,连回忆都带着凉。
古往今来,这样的遗憾,总在诗词里绕着不肯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不过十个字,却把时光错位的苦写得那样痛。就像梅叶,等它攒够了力气冒出头,梅花早已香消玉殒;就像那女子,等她敢把心意说出口,心上人却已隔了山海,连背影都模糊了。还有李白写的《子夜四时吴歌・冬歌》,“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你仿佛能看见冬夜里,女子坐在灯前,指尖冻得发红,却还是一针一线赶着征袍 —— 她想把牵挂缝进衣料里,盼着驿使能快些,再快些,让远方的人早些穿上。可她哪里知道,或许征袍还没到临洮,战火就已吞了爱人的性命。那份没来得及递出去的思念,就像梅叶寻不到梅花一样,空留着,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连民间的传说里,都藏着这样 “花叶难逢” 的怅惘。尾生抱柱的故事,谁不曾听过?他和女子约在桥下,等着等着,洪水就漫了上来。他明明可以走的,却偏要守着那句约定,抱着桥柱不肯松手,最后竟被水卷走了。等女子匆匆赶来,只看见湍急的河水,哪里还有尾生的影子?她满心的歉意与爱恋,再也没了说出口的对象 —— 这多像梅花与梅叶啊,一个守着约定等,一个赶着重逢来,终究是错过了,连一句 “我来过” 都没法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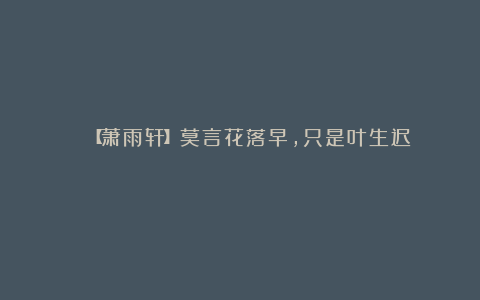
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扮着男装,和梁山伯同窗三载,把喜欢藏在 “兄友弟恭” 的幌子下,不敢说,也不能说。等她终于卸了男装,红着脸把心意讲出来时,梁山伯却已病得重了,没几日便去了。她穿着嫁衣跑到坟前,哭着喊着,最后竟跳进了坟里 —— 后来的人说,他们化作了蝴蝶,双宿双飞,可谁又懂那蝴蝶翅膀上沾着的,是多少 “叶生迟” 的遗憾?若祝英台早一点说,若梁山伯能再等一等,他们或许也能像寻常夫妻那样,守着柴米油盐,过一辈子安稳日子,不必用这样惨烈的方式,去寻一个 “在一起” 的结局。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古诗里的女子,也是这样把思念熬成了长长久久的牵挂。她日日夜夜想着远方的人,只能在梦里与他相见 —— 梦里他就坐在身边,笑着说 “我回来了”,可一睁眼,只有空荡荡的房间,连他的气息都抓不住。还有那句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更是把人心揪得生疼。春闺里的女子,还在梦里和爱人说着悄悄话,却不知她心心念念的人,早已成了无定河边的一抔黄土。她的爱恋,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永远失去了听众,像极了梅叶,永远错过了与梅花并肩的时光。
可我总想着,那些错过的时光,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恋,未必就是全然的空。就像梅叶,虽没见过梅花的盛放,却能在枝头上努力地长,吸着阳光,饮着雨露,替梅花守着这棵树,让它在没有花的日子里,也不至于太孤单。等明年冬天,梅花再开时,它依旧不能与梅花相见,却能在风里,默默念着那句没说出口的 “我等过你”。
那些思慕的女子也是啊。她们的爱恋或许没被心上人知晓,却在岁月里酿成了最温柔的回忆。每当想起那个人时,心里或许会疼,却也会暖 —— 毕竟曾那样热烈地喜欢过,曾那样执着地等待过。终有一天,那些深埋心底的牵挂,会像破茧的蝴蝶那样,挣脱遗憾的束缚,在时光里轻轻飞。那时的爱恋,不再是痛苦的思念,而是化作了永恒的祝福 —— 跨越了生死,越过了时空,告诉远方的人:纵使花叶开谢不同时,纵使我生君已老,我曾那样真心地爱过你,这份心意,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