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同海 图/网络
四叔四强姑姑和我
文◆徐同海
实行工程承包制后,我如鱼得水。我的故友旧交,轻车熟路,帮衬最多。好人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脉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处处留后路,和谐共处,让我呼声日高。
水上工作的特殊性,让我染上了酒瘾,不能自拔。我好喝,酒友广杂乱,什么人都喝,什么样品种的酒都喝。上有地方官员,下有渔民、农民。扒沙的,电鱼的,贩夫走卒,偷鸡的摸狗的,人民政府捉放的,都是我的酒友范畴。我抓起酒杯,除了给官员大佬殷勤,无论老少男女,均称兄道弟,没有性别。这些友人,不讲菜品,唯讲酒不断供,喝到尽兴。
最骇人最能提高我酒界声望的,是我酒友中一位特殊病人,病名骇人,几不能提,最为惹眼。这位老哥,为多年的中学教师,肇患恶病。病的蹂躏,致使眉毛胡子脱落,眼珠血红,时时流泪,手指痉挛变形,面目狰狞丑陋,形似恶鬼,离开村庄,在湖心小岛居住。他的居住地离航道一百五十米。这人,饱学之士,做事走心,注意影响。很自觉地躲闪着过往的人们。包括刮什么方向的风,都注意,自觉将自己处于下风头的位置。他理性缜密,有自知之明,让人尊敬。要说喝酒,只是象征性的。我们与他为邻的过程中,我钦佩他的学识做人,他欣赏我的平易豁达,好人相遇,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我们心如明镜,他茶我酒,谈笑风生。这是别开生面的酒宴,让方圆有名。有他的鼎力帮助,施工中的地理地貌,人情世故,了解细致,少走弯路,解决了不少难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挣得钵满盆满。他为我帮下大忙,无以为报,赠钱送物不收。他怕我心理失衡作难,坦诚点名要了几套书籍,留作纪念。湖区坏蛋痞子不少,民间高人更多。处处是码头,站站有江湖,鱼目混珠。过关显将,全靠自己。
以往,到哪里施工,有人纠缠头就大。经过十来年的酒瓶子历练,周围太风平浪静,没有几个操蛋猴溜溜鬼出来搅局,倒显得不热闹。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掺和,喝这样的酒,似乎显得冷清,不过瘾。
我们酝酿他与四强姑姑的婚事前,征询了他的意见。他曾喜欢四强姑姑多年,凭家庭条件和大老粗的实际,也知道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矮她三分。没生病前的四强姑姑,细腿个挺,素雅白净,是个人见人爱的人,还上过学,心境高着呢。她挑挑拣拣,中意的人不多,常常给娘抱怨,说有头有脸的,都让人家选走了,剩下布头线脑的,让她没处拣了。她虽能看中四叔的外貌,的确看不中家庭,不识一字,有时还冒出楞青傻相。
近几年,干木匠的大叔,顾及兄弟,主动将爱学习又有一身蛮力的二叔三叔聚到一起,借钱买来机械,加工木料赚钱。四叔不趁这热闹。凭着一身力气,跟着邻村扒铁路、抬道板、翘钢轨。等二叔三叔成了家,三爷爷去世,随后,操劳了一生的三奶奶也去了她永远享福的地方,四叔已是刁然一身了。以后,他在我工地干了一年多。没技术,没调换心眼,爱抬死杠,跟工友合不来。大家评价他是笨屌日死牛。他自动离开,我顺水推舟。他对我性格外向,喜欢打顺风旗,看不惯。处处以老人家自居,叫我小名,喝斥我,骂我。他内敛,爱生闷气,常跟我吵得脸红脖子粗。以我俩的性情,两便最为妥当。我们分开了,虽恼了皮,但没有恼到瓤。
我是一胆大皮脸不害羞的人,朋友满天下,亲戚到处有。听风是雨,拾到嘴头是话。见人单拣好听的说,擅长吹吹拍拍。什么社会都饿不死这样的鸟。我有自信,就是长着赖疤的母猪,经过我的夸耀洗脑,它会信心大增,去大街上放浪一番,都有可能主动扎情人,玩自拍,发抖音。我能把亲戚、朋友、同学,各种关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入水如鲇鱼,滑溜如油锅里的钢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驴学驴嚎,见鸡学司晨。是跟坷垃头子都能对话的人,最喜欢顺杆子爬。腰里别着香烟,肩上扛着笑脸,为了利益甘于免三辈。领导家里有丧事,二话不说,就问丧家要孝饰。自认为失去的尊严,可以用成功来弥补。我愿效法不少的歌星影星的作为,先是无底线地脱,最后再有尊严地一件一件地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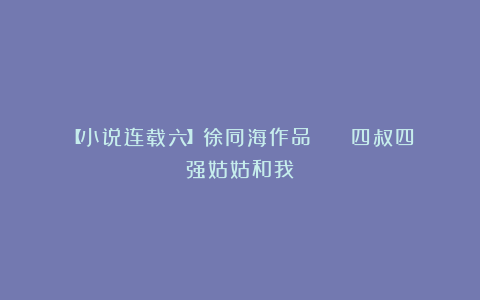
近几年兴起的同学聚会,我是见到新面孔最多的。在不短的求学生涯中,一般同学多有固定,而我,同班同学常换常新,起码两年一换的个案,是少见的。故聚会的几率高,机会多,年龄差距大。我的同班同学,比一般人多出几百人,加上同级不同班的人更多。由于我小有成功的现实,消费慷慨,让人高看。即便愚蠢的胡言乱语,也被人当成警句妙论。我的亲戚也多。同姓认本家,异姓拜把子。人家有叔伯兄弟,我发明了叔伯仁兄弟。我舅家姓刘,姑家姓陈,姨家姓张,这些姓氏都是我的老表,张口就来,从无顾忌。还有丈母娘家那一摊子,妻侄小舅子加连襟,姐夫小舅,惹不好就揍,热闹着呢。这叫十亿人民九亿表,没有亲近裙带找。有人说,你亏得没有当过兵,若是进过军营,恐怕光战友,又是不小的数目。我说,有,银行信贷主任牙孩就是。我和他是在基干民兵营集训过半个月的战友,现在是铁哥们,关系比钢枪都钢。我善于拉关系,寻信息。光酒友,就是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人说喝酒喝不出感情,我不这么认为。保持感情的新鲜,需要智慧。喝酒是各种合作的调节剂,是战斗间隙的项庄舞剑。那种一昧追求沉重的崇高,那种扪心自问式的所谓的情真意切,憨憨的较真,只能代表愚蠢。无目的的社交,叫社交吗?酒肉的朋友不是朋友吗?我算得上小能人,在大家庭的地位不被小觑。大小事都少不了我的参与。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有我在,不能冷场,起码喝酒结账时,有人买单。时至今日,四叔是家族中为数不多仍叫我小名的人,也是不爱沾便宜的人。
今天的议题是四叔的婚姻问题。作为事主,四叔显得不自然,因为家宴是我安排的。二爷爷上首高坐。每人的眼前都斟满一杯酒。四叔先摆手,示意撤下他的酒杯,说他今天的四两酒已喝过。说了算,定了干,他不会毁了自己定下的规矩。二爷爷小心地看了他一眼,很有耐心地说,放你跟前吧,你看,我不喝酒,脸前不是也看着一杯吗。
大家庭中的人都到齐了。四叔家的弟兄,除了五叔远过天涯,都已到场。作为长支长孙,我先发言:我们老少几代,聚在一起,是商量俺四叔的婚姻大事。在这之前,我和二爷爷、大叔进行了碰头,也到四强姑姑家作了沟通。四叔同意这门亲事。女方除了让四叔戒酒之外,没提出任何要求。就四叔戒酒一事,他们要求二爷爷作为老家长做出保证。我当时就自告奋勇,全部包下:四叔戒酒,除了二爷爷,还有我。我们祖孙三代作保。有关住处的改造,四强姑姑过门后的治病等等,我全拍下胸膛。他们一家看我们准备得还算充分,她哥哥们提出,我家就这一个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共同帮助解决。四叔说,娶得起媳妇,管得起饭,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干。刚才二毛提出的几条,我一一砸实。今天同着众人说,我再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好歹能掂量得清。第一,酒这件事,我保证戒了。从明天,啊哦,不,现在开始吧。他把脸前的酒杯端起向众位举了举,低头把它撒到地上,把杯子扣到桌上,接着又把它反过来,往中间推了推。第二,俺大哥二哥三哥,咱爹也没有给咱撇下什么,你们能把自己的家过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你们拖家带口的,我绝不拖累你们。老五在外地,我更不去指望。我现在住着老五的宅子,抽时间找村里,要一块宅基地,条件允许,就把房子盖起来。首先声明,我还不穷。这几年打工,攒下几个钱。我计划,既然跟王莺歌结婚,就要负责到底,至于好坏,就看老天爷的造化了。接着,他自嘲地说,我没上过一天的学,但懂得这样的道理,还是自己的耧耙上柴禾。你们作我的后盾,紧要的时候,在后边托一把就行。咱丑话说在前头,我不管向谁伸手,绝不坑谁赖谁。兄弟爷们明算账,坑兄灭弟的事,我干不出来。还有一句话,咱不能像别的姓的人笑话的那样,看徐家人口不少,只怕摊上大事,就如大粪堆上的屎壳郎,一泡骚尿给冲走了。我说,四叔,你放心,我这只屎壳郎壳厚底盘大,再大的尿,也冲不走。说得大家都笑。
我们赞同四叔的意见,接着,就房屋的改造装修,集思广益。大到家具,小到厨房厨具,厕所改造,事无巨细。我平时嘴大舌长,加上财大气粗,当场表态,我兜底。
我穿针引线促成四叔和同学王莺歌的婚事。眼见婚期将近,见了四强姑姑,我直接叫四婶,她没有反对,但有几分羞涩。见了她娘改叫姥姥,嘴上如抹了蜜。还将我老婆给四婶精心挑选的衣服拿给她。她黄黄的瘦脸上,肤色凝重,眼圈变红。
水到渠成,徐家响起了唢呐鞭炮声。
四叔的婚事办得隆重但不热闹。原因,这次的婚事,由于义务、责任等神圣的成分过重,把种种事情预计得过于透彻,犯了既看透又说透的忌讳。过度的筹事周密,料事如神,前瞻后顾,成熟明了,压抑了以婚姻为主体,生儿育女为目标的的喜庆元素,少浪漫,缺激情,消弱了朦胧之美。因理智的成分过多,责任细化,将许多神秘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知根知底的通透宣扬繁多,反而让人心有余悸而无所适从。就如还没有举行婚礼的一对男女,就已讨论好所生儿女的上学就业和结婚,遥远而沉重。四叔似乎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大胆娶回了一个病秧子,甘愿成为主动揽包袱的人。四婶则哀叹人不能与命争,挑三拣四没耽误窝在这不到二百米的方框里。二人都心如明镜,一个孤胆英雄,四面楚歌,破釜沉舟;一个黛玉葬花,凄凄凉凉,盼暖望春。就如太有准备的两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走到了一起,苍凉又实际。当然,二人笃定信念,互相绑定,齐心协力,共闯难关。他们年龄偏大,亮丽的盛典喜庆,变得似行云流水,平平淡淡,活像老夫老妻间搭伙过日子的日常再现。这就造成了徐家红白事该笑的时候不笑,如四叔婚礼的严肃刻板。该哭的时候不哭,如三爷爷的殡事的戏虐松懈。
庆典因过于重视婚后的生活,备足力量看病等过于沉甸的话题,把吉祥喜庆变成联想和奢望,让新人及家人心怀忧虑,犹如黎明前的黑暗,压抑而沉闷。一对新人,本来是金童玉女般冰清玉洁,因为大家太熟悉,太夜里千条路的思虑多,造成五味杂陈。四叔太不注重仪式,被我当场严厉更正,还压制住他拐驴倔骡脾气的萌发。让他听从安排,耐心走典礼流程。
我调皮捣蛋,平时闹新媳妇的本领花样百出。我是晚辈,加上三天不问大小,在此,只有大显身手。我脸抹锅灰,额上画彩,耳挂响铃,吵着闹着,偎近四叔四婶,一本正经地请求晚上要跟着新郎新娘睡觉。我说,我乖,不尿铺,我是小能蛋。要他们亲亲我的红脸蛋,给我抹香香。他们不依,我就撒泼,满地打滚,把脸抓得龟儿瓜儿,要钱买哇哈哈。这不要脸的孩童把戏,让不少人笑岔了气。我妻子,把我的小儿子,丢进四婶子怀里。小家伙不认生,拱着喷喷香的新四奶奶找奶吃,羞得她乱躲。他张着没有长牙的嘴傻笑,鼻涕抹了新娘子一身。经这样一逗,新人高兴了,气氛热烈起来。连没有几颗牙齿的二爷爷,也咧开丑陋的大嘴,笑个没完。
两家住得近,加上四婶身体有恙,闹新媳妇的不敢放肆。本应和悦的婚礼,欢不起场子,始终萦绕着悲怆氛围。娘家人的出场,使我刚渲染起来的气氛再次暗淡。我抢先拉过来四婶的哥哥,提示他们:大舅二舅,今天是我叔婶大喜的日子,咱只谈喜酒。几声舅舅,被我喊得心里烫贴,果然没人再提起那些早已谈过数次的郑重话题。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徐同海,男,1962年7月生于微山县。自由撰稿人,为济宁市作协会员,现居江苏徐州。1990年至今,曾在《山东文学》、《故事大观》、《鲁北文学》、《乌金潮》《济宁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多篇,获过小说奖。
微山湖区特产:微山湖麻鸭蛋、荷叶茶、荷叶饼、双黄蛋等,厂家直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