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东去找水井。”
这句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起失踪案的全部线索。
四十多年前,他在罗布泊留下这张字条,此后,彻底失联。
他叫彭加木。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们回罗布泊”
1980年6月,新疆罗布泊。
地面温度逼近50℃,鞋底踩在地上像贴在铁板上,水倒地立即蒸发成雾气。这样的地方,连苍蝇都嫌热。
可就在这片一望无际、死气沉沉的盐碱地里,三辆军绿色吉普车正在慢慢向东推进。车身布满灰沙,车轮深陷在细密的沙粒中,发动机声嘶哑沉重。
副驾驶座上,一个中年男人戴着草帽,脸被晒得通红,额角渗出密密的汗。他手里拿着地图,不停地抹汗、记笔记。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
这年,他55岁,名气早已传遍学界,就连郭沫若都亲自为他题过诗。
按理说,这样一位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坐镇办公室写论文都来不及,怎么会跑到这个连指南针都失灵的“死亡之地”?
原因其实很清楚:国家需要他。他自己,也有准备。
罗布泊,并不是一片普通的沙漠。
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面积最大时超过一万平方公里,几乎有两个上海大。清代以前,湖边绿洲连绵,过路商队都以此为生命补给站。
西域古国楼兰就位于湖畔,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但到了20世纪中期,湖泊迅速萎缩。垦荒、采矿、水库建设让它再也承受不起压力。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湖水彻底干涸,留下的只是一片光秃秃的盐壳地。
从卫星照片上看,它形状怪异,像一只人耳,所以后来有人叫它“上帝之耳”。
更神秘的是,它的位置并不固定。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了一整本书《游移的湖》,讲的就是它会“移动”的奇特现象。
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说,这地方的危险程度远远被低估了。
除了自然条件,这里还藏着中国战略层面的大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爆成功。三年后,第一颗氢弹也在这里爆炸。接下来的几十次核试验,全都选在罗布泊。
这地方,长期是国家最高等级的军事禁区。
但科学家知道,核试验场往往也是地质资源宝库。罗布泊下方蕴藏着巨量的钾盐、重水等战略资源,尤其是重水,对核能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想摸清楚罗布泊的“底”,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彭加木身上。
不过,彭加木来这里,还有另一层原因。
就在不久前,他刚刚被确诊为癌症,他想要为国家做自己最后的贡献。
具体病情他没跟外人细说,只告诉同事:“我要抓紧时间干完这点事。”
他明知道这次任务凶险,却还是亲自带队,连方案都是他一页页亲手拟定的。
他组织了两位化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地质学家,还有负责动植物采样的科研人员各一名,外加两位保卫员、一名报务员,三辆吉普车配三名司机。
5月8日,罗布泊综合科考队正式出发。
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进入罗布泊后,他们连续20多天都没走出去。白天走不出沙丘,晚上气温急降,队员们只能挤在车里取暖。
水资源极度匮乏,每天仅能分到5升水,全队共用。
而最让人沮丧的,不是苦,而是找不到目标。
走了半个多月,矿藏影子都没见到。
队伍陷入极度疲惫和迷茫。
就在大家几乎要放弃时,有队员用望远镜发现远处竟有几株胡杨树。
这不是幻觉。
胡杨不可能无水生长。果然,树下竟有条浅河在流动。
他们冲出沙海,站在河边,把脚伸进水里互相泼水取乐,这是久经生死边缘后的宣泄。
此刻,他们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穿越罗布泊腹地的科学考察队。
任务完成,活着出来,意义非凡。
可彭加木却没笑。
他坐在不远处的土堆上,皱着眉,盯着地上的采样数据出神。
他知道,这趟虽然走出来了,但最重要的目标没完成——资源找得太少了。
这不是他要的结果。
思考许久,他站起身,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会议。
一句话,把所有人震住了:
“我们回罗布泊。”
“我往东去找水井”
1980年6月11日,罗布泊。
三辆吉普车再次驶入荒漠,热浪从四面八方扑来。
风沙肆虐,车窗几乎看不清前路。发动机在高温中咕哝喘气,车轮艰难地碾过一座座沙丘。
这时候的气温,已经接近人体极限。
考察队员的状态越来越差,有人呕吐,有人昏倒,有人躺在车后厢喘不上气。
而彭加木,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样的气候,哪怕多待一天都要付出代价。
但他比谁都清楚,这趟必须走完,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三天过去,队伍到达一个叫“柳树沟”的地方。
所有人以为快到了,但一查地图才发现,他们只完成了一半行程。计划中的“3天穿越”,变成了“3天挣扎”。
更麻烦的是,汽油见底,饮用水也所剩无几。
当时,他们离最近的补给点还有将近400公里。走,可能走不出;留,也坚持不了多久。
队伍当即开会讨论。
意见出奇地一致:不撤,绝不后退。
这一夜,天降狂风。风速接近10级,帐篷被吹翻,沙子灌进耳鼻口,车子差点被掀翻。
彭加木坐在车头,通宵未眠,一直在翻资料和地图。
6月14日,队伍继续出发。
两天后,他们进入了从未被正式考察过的库姆塔格沙漠。
这里是新疆第三大沙漠,号称“无风三尺沙,有风一丈高”,真实得不能再真实。
他们发现了野生骆驼,第一时间拍照、采样、记录标本。那是唯一让人兴奋的瞬间。
6月16日,队伍终于抵达库木库都克。
可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忽然意识到,汽油最多只能再跑几十公里,饮用水也只剩下一桶,还已经发臭。队员们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
他们派人尝试在附近找水,整整一天,什么也没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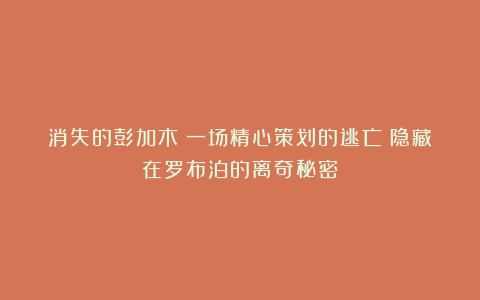
这一夜,没人睡得着。
彭加木在帐篷里走来走去,不停地翻资料。
他的副手汪文先记得很清楚,凌晨三点,彭加木对他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飞机运水,1kg要二十来元,比油还贵,不划算,我们还是要自己找水,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
他讲得很理性,也很坚决。“找到了水源,也可为今后的考察提供方便……还是得自己去找。”
但谁都知道,一旦找不到,就意味着加速死亡。
天亮后,大多数人反对。彭加木没再说话。他站在沙丘上,盯着东边,眼睛一眨不眨。
6月17日上午9:50,考察队发出求援电报。
10:30,没有回应。
11:00,仍然没有。
11:30,终于收到回信:“飞机18日送水到库木库都克,请原地待命。”
营地瞬间炸了锅。有人鼓掌,有人大叫:“我们有救了!”
一名队员兴奋地去找彭加木报喜,拉开车门,人不见了。
车座上只留着一张地图和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我向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
并且彭加木的黄帆布包、铁皮水壶不见了。大家终于意识到,出事了。
没有争论,第一时间组织了小分队往东追。
营地里的人烧了水,煮了饭,等他回来。
接应小队往东走了8公里,一路上没有发现任何脚印或遗留物。
夜晚降临,库木库都克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所有人都沉默,谁也不敢说出最坏的猜测。
他们点起篝火,在高地竖起火把,希望彭加木能看到。三辆吉普车开上沙丘,打开所有灯光,朝三个方向持续照射。每隔一小时,还会发射信号弹。
一夜过去,没有回应。
有人开始注意到,除了地图,彭加木留下的还有——所有照片底片、考察记录、标本标签、仪器数据……都整整齐齐地放在副驾驶座。
这一细节,令人心头一沉。
他是做好了最坏打算。
凌晨两点,搜救队正式发出消息:“彭加木同志失踪。”
6月18日,罗布泊再次起风。10级大风夹着细沙扫过营地。队员们裹着防风布,再次全体出动。
没有发现。
6月19日,他们转向疏勒河古道东南方向,沿一条干涸的河道前行。
在一个沙包下,他们发现一行浅浅的脚印和一张糖纸。
有人忍不住叫了出来:“是他!”
所有人都精神一振,沿着断断续续的脚印追踪。
但走到盐壳地带,脚印突然断了。
地面坚硬如石,风沙翻滚,什么也看不到。
彭加木,就这样消失了。
标题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失踪的电报由米兰基地紧急发出。
中央立即下令:“全力搜寻,不惜一切代价。”
当晚,新疆军区调集空军和地面力量,甘肃方面也紧急派员支援。
大规模搜索行动正式展开。
最初五天,搜索主要集中在出事地点东西方向的30公里区域,覆盖了周围大部分雅丹地形、盐壳区和沙丘带。
空军动用多架飞机,在50公里范围内进行离地仅三四十米的低空搜索,几乎贴着地表飞行。
但结果令人沮丧。
到了6月26日,部队、中科院与地方政府已累计出动近150次,涵盖空中侦查、地面搜寻、坐标交叉等多种方式。彭加木依然像人间蒸发。
7月7日,第三次大规模搜救再次启动。这一次,范围扩大,投入更大,路线更细致。
结果仍是没有任何发现。
彭加木彻底消失了。
这件事,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罗布泊。
几个月过去,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同事仍不愿放弃。他们提出申请,请求重新组织科考队,再进库木库都克,完成彭加木未竟的工作,同时继续寻找他的下落。
第四次行动从敦煌出发。车队共16辆,成员超过60人,除了中科院的各学科研究人员,还有解放军官兵。队伍沿古丝绸之路进入疏勒河古道,向库木库都克推进。
这一次,他们制定了更系统的搜索方案。
采用“拉网式推进”方法,每10米站1人,队伍呈横排平行向前推进。两个月时间,他们几乎踏遍了500平方公里区域的沙丘、雅丹、盐碱地和断裂带。
依旧,什么也没找到。
没有脚印,没有衣物,没有骨骸。
这片“死亡之海”,再次将答案彻底埋葬。
但事情远未结束。
彭加木的失踪事件迅速登上各大报纸头版,不仅引起国内高度关注,也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大量报道。
一些境外媒体开始围绕事件发酵。最初的报道还算克制,但很快出现了大量带有猎奇、阴谋论色彩的内容。
真正引爆舆论的,是1980年10月,香港某小报的一篇文章。
文章言辞激烈,声称:彭加木根本没有失踪,而是“叛逃”到了美国。
文章里写得有鼻子有眼,说他在华盛顿某咖啡馆被“老友”周光磊当场认出。故事编得非常完整,还煞有介事地配上了“证人回忆”。
新华社记者迅速采访了彭加木的妻子夏叔芳。
她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丈夫也从没提起过有这号朋友。
但舆论并未因此平息。
紧接着,这家香港报纸为了“自证清白”,又抛出了一封所谓周光磊“亲笔信”。
结果这封信,反而彻底暴露了谎言。
信里把“夏叔芳”的名字写成了“夏淑芳”。
熟人之间会记错至亲的名字?这显然是编故事的人太草率。
随后媒体调查发现:整件事纯属虚构。这家报纸为了博眼球、卖报纸,捏造了整个情节。
“叛逃说”,彻底站不住脚。
可这些无稽之谈并未止步。
陆续又出现了“劫持说”“被杀说”“遭遇特工说”等多个版本。
比如所谓“劫持说”,有人猜测彭加木可能被外部势力劫走,尤其是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的苏联。
但罗布泊地形极端恶劣,昼夜温差大,气温常年超标,无水无植被。一个外籍间谍要在这里完成劫持、转移、撤离,几乎是天方夜谭。
还有“掩埋说”。
有人推测,彭加木在寻找水源途中,可能躲在雅丹土包下避暑休息,结果不幸遭遇坍塌被掩埋。
这种说法有一定逻辑。但以彭加木对地质的专业素养,他应该知道雅丹结构极不稳定,不可能主动靠近那些极易风化塌陷的土包。
所有推测最后都只能停留在“猜”,无法成为证据。
彭加木在1958年生重病时,曾讲过一句话:
“我准备让我的骨头,为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
22年后,这句话像是一种预告。
彭加木失踪了,但他并未真正离开人们的视野。
他的精神,他的勇气,他的选择,成了后来几代科研人心中的榜样。
可讽刺的是,这样一位献身科研、在沙漠中消失的科学家,却一直被部分人肆意污蔑。
是非对错,有时不是靠谁声音大。
但当真相缺席的时候,理性就必须坚守。
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国家从未放弃过搜寻。中科院从未停止过调查。每一代地质学者、探险队员、卫星研究人员,也从未停止过追问。
他们不是为了解谜,而是为了敬重。
敬重一个用生命写下科研遗嘱的人。
参考资料:
彭加木:纵穿罗布泊第一人
黄林
彭加木塔克拉玛干失踪内幕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