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墙壁
布面油画
157.5 x 172.7 cm
2023
肖:是这样,爱尔兰裔美国人可能是最典型的组合。我出生的时候人都住在大街上,也没房子。我确实天生就是一个流浪者。对我来说,来回来去的搬家是常事;就像大车前面的一头驴一样,你对它说:“走!”——就又出发了。起初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到我八岁的时候,我已经住过不下八个不同的房子了。我家里有很多能歌善舞的人;但没有一个跟我一样接受过正规教育,没人上过大学。他们都是到处飘,这就是为什么爱尔兰人叫他们——流浪者,吉普赛人。我们经常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来回跑。爱尔兰和英格兰是混合在一起的。大多伟大的爱尔兰艺术家,像弗朗西斯·培根、塞缪尔·贝克特和詹姆斯·乔伊斯,这些都是所谓的“英爱混血”,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融合,因为他们既有热情也有纪律。
背心
亚克力 画布
198.1 x 304.8 cm
1970
影
亚克力 画布
243.8 x 365.8 cm
1970
闪耀
亚克力 胶带 画布
216 x 388 cm
1971
玛:热情属于爱尔兰,纪律属于英国,是我猜的这样吗?
肖:是,这就是我作品中的基本内容。
玛:我了解一些关于您祖父的悲惨经历,他因参与 1916 年的起义而在狱中自杀,当然,这次起义也为爱尔兰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肖:我“天不怕地不怕”的祖父因拒绝被执行枪决而自杀。他自杀是为了反抗,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大英雄——也是我的榜样。我的父亲也让我感到很自豪,他在战争期间当了逃兵,因为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战争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就是我反感美国的一个原因——美国军事化程度太高。这是美国文化中可憎的一面。
玛:也许是因为美国比欧洲经历的战争要少得多。
肖:是的,所以它们仍然还是这么愚蠢。
后与前
油彩 麻布
243.8 x 609.6 cm
1981
艺术家自藏
蓝
油彩 画布
214 x 207 x 6 cm
1981
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 IMMA 藏
玛:说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您在美国和欧洲的经历对您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肖:有。我用了特别特别长的时间才在美国真正走红。在欧洲火得更快一点。我认为现在艺术在欧洲更有趣。
玛:为什么?
肖:因为它是一个拥有高度复杂性的统一大陆,里面有很多像你这样不断提出问题的人。美国是一个更加注重资本和产品的社会,而欧洲则更关注事物背后的原因。这对我来说恰好,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哲学性的艺术家。我过去常说,我在北半球总是遇到问题。我的作品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南部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墙壁粉红
布面油画
71.1 x 76.2 cm
2023
玛: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
肖:是的,那里的接受度最高。我在荷兰和瑞典总是有问题,因为我的作品太“脏”了。
玛:您的作品倾向于——我并不是说宗教性,但确实有一种超越感,这在这些新教国家是存在问题的。
肖:这很成问题,因为人们不相信这种情感。我在英国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那种深刻而形而上的情感,而在美国就被接受了。
威尼斯的一个房间
油彩 画布(x2)
243.8 x 304.8 cm
1988
凯瑟琳
油彩 画布
254 x 304.8 cm
1988
微暗的火
油彩 画布
243.84 x 372.11 x 13.97 cm
1988
玛:您不认为欧洲的一个弱点恰恰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吗?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肖:是的,他们不会,这也是我被美国吸引的原因之一,因为我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我是一个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浪费时间。我会直接进入工作室创作一幅画。我不会被怀疑所困扰。在美国,他们曾经把约瑟夫·博伊斯形容为“欧洲最能胡扯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也抓不住他的点儿”。这种批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美国的问题在于,他们会先采取行动,比如入侵伊拉克,然后再考虑后果。我认为,在做某事之前先思考一下会更好——而不是在杀死了数十万人并制造了数百万难民之后,还说出“我们要让他们无处藏身”这种蠢话。我认为,欧洲所持有的怀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怀疑可以使人更像个人,因为在欧洲,我们已经学会了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一切之上。当然,这让我们看起来有些优柔寡断,但又怎么样呢?这不是一个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出结论的比赛。 我认为那些轻易下结论或固执己见的人其实大多只是爱说大话的人。他们外强中干,这就是反驳的点。
玛:说得好。显然,您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不过我了解到,在您年轻的时候,曾经还混过社会,并且在空手道方面表现出色。这是为了最坏的打算做的准备吗?
肖:加入帮派混社会是当时的一种外部环境。基本上,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加入帮派,而且确实也很刺激。我加入一个大的街面上的帮派。我们参与了好几次战斗,基本上是为了争地盘,但那正是我反抗的东西。当然,空手道在打架的时候确实比较狠,我也参与了很多次,但同时干架又是正式的、讲规矩的——你就像一个骑士。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脑子里充满了来自古时候的种种神话。
肖恩·斯库利摆出空手道的姿势
玛:您现在还有在练习吗?
肖:我会自己练一下,但我不适合待在一个小团体里太久。因为它们要求你放弃个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玛:让我们聊聊您的充满个性的创作。您已经创作抽象绘画作品很长时间了。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抽象艺术?
肖:我想创造一种世界大同的艺术。把世界串联在一起,打破分歧。我把自己看作是传递和平与理解的使者——抽象艺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特别是我运用这些基本结构来进行表达时,这些结构是所有人都共通的。
黑,白,白
油彩 麻布
203.3 x 190.5 cm
1996
凯瑟琳
油彩 画布
254 x 224 x 9.5 cm
1991
玛: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任何的想法投射到您的作品上。
肖: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任何事物上,包括我的作品。 [都笑了]我的作品有结构,有完整性,严肃且深刻,它源自北欧浪漫主义与来自非洲或南美洲的原始结构的混合。可别在我的作品上投射出来恋童癖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可以将任何想法投射到我的作品上是不够准确的。我的作品代表了一些人文价值。它包含了一定的古典主义元素。作品的标题是对其含义的强烈提示。你可以投射你自己的想法,但作品本身也有自身观点的。它并非完全是中立的——它是人文主义的。
玛:您也给出了如何解读作品的线索吗?
肖:是的。我的作品是将情感、个性和人性注入那些实际上主导我们的结构。这就是作品的主要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墙壁和网格构成的世界,一个充满几何和超结构的世界。我的作品就是应对这种状况,使之变得诗意、深刻和深远,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其专制——因为没有间歇的秩序是危险的,会导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分子喜欢几何,但希望它干净利落。他们不喜欢像我这样脏的几何,或者有误差的几何。我的几何更像保罗·克利,有点偏离常规。
光之壁, 红
油彩 麻布
243.8 x 243.8 cm
1998
阿尔巴之墙
油彩 麻布
190.5 x 215.9 cm
2001
Hugh Lane Gallery 藏
阿兰之光之墙
油彩 画布
182.9 x 213.4 cm
2022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藏
玛:您提到了网格,这是一个在近期艺术史上带有争议的术语。您的作品是否与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绘画理念有关联?
肖:没有,我是在错误地使用那种秩序感。比如,我画了一幅名为《错误的坠落》的作品,人们对这个标题感到非常困惑。从格林伯格的理念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个理念全部关乎和谐、品味和完美——而我的作品与完美八竿子打不着。当事情出错时,它们是对的;当事情正确时,它们又都错了。我一直在质疑权威和秩序。
玛: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绘画时,绘画已经被宣布死亡,这可能意味着根本没有人对您的绘画创作感兴趣。
肖:没错。
玛:那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听到“绘画已经过时了”这样的话,一定很失落吧。
肖:过不过时这是他们(评论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非常独立,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常叛逆的人。我代表的是可能被威胁的东西。每当有东西要被摧毁,我总是尽力去拯救它。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光热墙2
油彩 麻布
190.5 x 215.9 cm
2012
灰红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2
光之墙红色条纹
油彩 画布
216.5 x 190.5 cm
2013
绿色光之墙
油彩 麻布
150.4 x 140.3 cm
2013
玛:这听起来是个很牛的想法,但我也能想象当时您作为一名年轻艺术家,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如果没有人对您的作品感兴趣,那怎么应对?
肖:好吧,我不介意成为少数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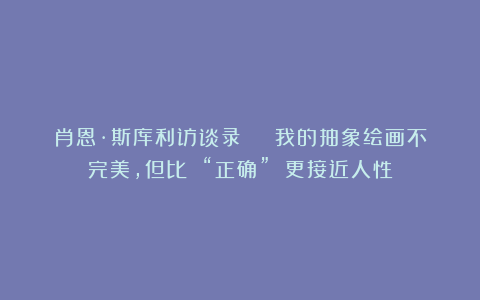
玛:但就实际角度出发,您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肖: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首先是因为我的精神非常强大,不容易被打垮。从十三岁起我就开始工作,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回家后继续画画我也毫无怨言,我从未指望过会因此赚钱。也从未想过我的生活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画画并不是为了谋生。我认为绘画在文化中占据着一个非常深刻、存在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位置,这是必要的,正是这一点支撑着我。
玛:您选择了绘画后,您就读的艺术学院有给您带来什么新的问题吗?
肖:1968 年我进入纽卡斯尔大学时,整个艺术系都充斥着观念艺术。根本没有人画画。学校里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学生可以把自己的画挂在那儿,但学生认为不挂画才是最牛的,就像在说“去你的吧!”,所以我开始画画并将作品挂在墙上。一开始,其他学生都认为我傻,或者认为这就是个笑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嫉妒我,然后也纷纷开始画画并挂在墙上——这就是人性。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改变世界。
肖恩·斯库利与自己70年代在纽约创作的作品
要塞 #2
布面油画
213.7 × 214. 2 cm
1980
玛:这真是一个双向的故事。首先,它告诉我们需要有强烈意愿去改变的人,同时也揭示了人们极易表现出羊群行为的倾向。我对您在毕业后去摩洛哥的经历很感兴趣,那次经历让您转向了抽象艺术。
肖:不能说我转向了抽象,因为我那时已经在画抽象画,就像编篮子一样。我一直对编织非常感兴趣——小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编织、钩织,并制作餐桌垫,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女人干的活。我去摩洛哥时看到了不同的几何形状。我以前见过和研究过的几何是约翰内斯·伊顿、包豪斯和至上主义的几何学,这是一种秩序化的几何学。而在摩洛哥,我看到了一种充满情感、运动和精神的几何形状。通过这次经历,我内心有所触动,因此当我回来时,我开始创作非常重复且有节奏的条纹画。这次摩洛哥之行彻底改变了我。我甚至开始穿上了拉巴长袍,然后睡在地上,我对它爱不释手,以至于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中。
摩洛哥的瓷砖花纹
玛:这听起来像是非常精神上的体验。
肖:是的。这完全改变了我的创作。
玛:接着您就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并一直沿用至今,大致如此。
肖:是的。我创作中的基本元素,不是像卢西恩·弗洛伊德那样的人物,而是条纹。我把条纹放在人物的位置上,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不错的具象画家。英国人也是因这一点喜欢我,当我决定创作抽象时,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和不满。
阿尔勒文森特之夜
油彩 麻布(x3)
160.5 x 160 cm(单幅)
2015
阿尔勒深渊
油彩 麻布
215.9 x 190.5 cm(单幅)
2017
玛:您之后就没有被诱惑过回到具象绘画?
肖:我前不久刚在海滩上给我儿子画了二十幅肖像。有了小孩,再一次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完全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如果你十五年前和我说话,你面对的是一个更固执、更烦恼、更情绪化的一个人。小孩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光彩。我想要创作一些画作,展示他在每年我们都会去的海滩上。我唯一能做的,来留念这一切就是通过绘画。所以我画了二十幅大尺寸的肖像画。
Eleuthera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7
Eleuthera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7
Eleuthera(蓝色竞技场)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7
Eleuthera(粉红色竞技场配海军衬衫])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8
玛:您会一直保存好这些画吗?
肖:我们会保存好这些画,但我更喜欢去展出。我想奥尔加·茨维布洛娃会在莫斯科的即将举行的展览中展出这些作品。
玛:您的绘画中宗教扮演着什么角色?您最近还向西班牙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捐赠了许多画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动,与永恒相连,同时也与宗教的永恒相连。
肖:嗯,我从没说过我什么都不信,相反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人曾经告诉我,因为我喜欢所有宗教,所以我是个印度教徒。最后我说我是一个融合主义者。我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这一点,听众中有一位女士一直让我很困扰,她不停地问,“你说的’融合’是什么意思?”最后我说,“杂交”然后她说,“哦,明白了!”[我们俩都笑了] 我想我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禅宗背景的天主教徒。我对所有宗教都非常包容,我认为宗教是我们想要到达的更高境界,最终我们有望达到。我希望我们能够进化成更加统一、更加仁慈、更加灵性的存在,而我的作品就是为此努力的一部分。
西班牙蒙特塞拉特教堂
意大利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展出 2019
玛:您的作品都是个人手绘完成的。
肖:全部都是我自己画的。
玛:没有请助手帮您画吗?
肖:我不像杰夫·昆斯那样养一群奴隶。
玛:但他给助手付酬劳了啊。
肖:我的钦佩之情都溢于言表了。
玛:对您来说,作品是否必须由您亲手完成,是否与您的思维和情感相连很重要吗?
肖:当然,这是一体的行动。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这是最高形式的智慧。
肖恩·斯库利在工作坊创作
玛:这意味着您既是有生产力的,但同时在产出上也是有限制的。我了解到您创作了大约 1400 幅画。现在可能有 1500 幅了吧。
肖:可能吧。
玛:有一部分您自己保存了吗?
肖: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藏。这是我喜欢拥有的东西。这使得展览变得特别容易,因为我只需要往镜子前面一站,问自己能不能借这幅画,然后回头看看自己,然后说,“行了。”
玛:您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保留了早期职业生涯的作品吗?
肖:早先因为没有人愿意买我的作品,所以很容易保存这些画。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英国,我意识到自己生不逢时,那时候没有人真正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这促使我移居到美国,在那里人们对我作品的兴趣特别浓厚。到了 80 年代,我在纽约出名了,我的作品甚至出现了长长的等待名单中。可以说,在 80 年代,我算是抽象艺术的主流代表。
绿金色袍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8
2020富艺斯伦敦
橙色衣袍双联
油彩 铝板
114.3 x 203.2 cm
2019
玛:当时您在纽约的代理画廊是谁?
肖:大卫·麦基(David McKee)。他也代理了菲利普·古斯顿。由于大家把我画画的方式与古斯顿画画的方式联系了起来,这一下为我打开了美国博物馆的大门。之后,我就更难把作品留在手里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收这幅画。比如有人会说他老婆下个月过生日,他想买这幅画——你还有话说吗?你还真不能拒绝人家。
玛:对您的职业生涯来说,哪个更重要:机构还是私人藏家?
肖:我一直支持机构。但我希望我的画作能进入博物馆,因为我认为作品就是为大众服务的。
玛:可博物馆现在没有那么多经费了。
肖:不,你必须帮助他们。当你把经费数字列出来以后,你必须为他们把零头给抹掉,直到策展人的脸变得有点缓和和轻松。随着零头的减少,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玛:您是不是把零抹掉了给重要藏家了?
肖:没有,因为人家有能力买到他们想要的。
左起:肖恩·斯库利,《小立方 11》(2023)、《多利克式 天使》(2011)、《黑色方块的夜》(2020),“肖恩·斯库利:离开海水的地方”展览现场,和美术馆,2024年
(左起)肖恩·斯库利,《陆线 星》(2017)、《无题(陆线)》(2021)、《陆线立方》(2015-2020)、《缺失》(1988)。“肖恩·斯库利:离开海水的地方”展览现场,和美术馆,2024年
玛:您为什么对中国的情有独钟?您近年在中国已经举办了五次展览了。
肖:中国,是一个能够吸收很多正能量的国家。他们从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过去中走了出来。现在他们需要以一种不会导致灾难的方式处理好当下的问题。我对中国这一发展进程很感兴趣,并希望为此做出贡献。我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并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希望帮助他们的发展进程,因为从外部抨击别人是毫无意义的,最终会导致自己的孤立。
玛:您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您并不参与那边的政治活动。
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抽象艺术有时会遭禁。这恰恰展示了抽象艺术的力量,因为禁止它是有道理的……你无法篡改抽象艺术,因为如果你看我的一幅画,你会舍弃其中的哪一部分吗?全部?还是不能?如果去掉其中一条条纹,并不会改变这幅画的意图。因为无法对其进行编辑。抽象会引发颠覆性的思考……
玛:这就像一个特洛伊木马,看起来那么无害。
肖:就是这么回事。就跟特洛伊木马一样,肚子里面装满了坏水。[两人笑]
玛:您的中国学生WW持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会因为您到中国举办展览有什么看法吗?
肖:不会的,他敬爱我。前几天我在墨西哥城路易斯·巴拉甘的画展开幕式上,WW和他的家人出现在现场。我们俩的小孩还在一起玩,他还不停地给我倒大杯的威士忌。很糟糕,但也挺有趣。我也不喝酒,但他一直给我灌威士忌。[笑]
红色模块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6
棕色模块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6
玛:您喜欢教学吗?
肖:我喜欢影响事物的发展,而教学就算其中一部分。所有伟大的人物,包括甘地,都当过老师,因为他们想要带来改变。
玛:教学不会让您分心,影响到您的创作吗?
肖:不会,这完全不会阻止我的教学工作。教学只是另一种活动。就像写东西或者和你交流。我现在正在和你说话,也没有在画画吧,这算不算很糟?[笑]
玛:您已经在艺术这个圈子里驻足了四十多年了。如果您从整个时间跨度来看,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肖:在我这一生中变化是巨大的。我出生的时候连电都没有,小时候我们用煤气灯照亮。当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时,我幻想自己能创作画作或许会有一天能做一个回顾展。但事实上,我已经有大概二十个回顾展了。探讨艺术圈的变化是,艺术变得非常强大,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宗教。艺术成为了一股巨大的正能量,其影响力变得空前强大。我曾经和Bono讨论过摇滚,他说摇滚乐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发明的,当然,这主要是指他自己。但我认为现在艺术正在改变世界,因为它的力量赋予了它巨大的影响力,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艺术已经成为和音乐产业一样强大的产业,而技术使得图像、观点、思想和理念的传播不再受地域限制。你可以跨越国界,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因为我希望推翻这些障碍。[笑] 艺术已经变得像摇滚一样了。
什么造就了我们
油彩 亚克力 油画棒 铝板
299.7 x 571.5 cm
2017
卸载
油彩 亚克力 油画棒 铝板
299.7 x 571.5 cm
2018-2020
玛:您说的完全正确,艺术确实变得非常流行,但问题是:人们是真的对艺术感兴趣,还是仅仅对与艺术相关的娱乐感兴趣?这也没什么不好。艺术一直都很精英化,这也无可厚非。
肖:我知道这个说法。昨晚有人提到过一个关于大厅墙壁上动态图像的事——人们觉得活动的图像比静态的更吸引眼球,因为静态图像更容易被忽视。这家伙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谈技术对绘画的破坏。然后一个女的接茬说:“是的,它之所以不断分散注意力,正是因为里面没有艺术性。它只是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会看一眼,没有任何意义。”她说得是对的。体验的层次会有所不同——艺术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谈就非常精英化、密集且深刻,它关乎历史和文化,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当然,人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对此感兴趣,但其中一些,这种历史文化的残留,正在进入文化之中。
玛:您把音乐的发展与当代艺术的发展进行比较,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肖:随着艺术变得越来越流行,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像摇滚了。对吧,大多数摇滚乐都很随意:“我爱你,我爱你,请不要走!你让我感到很不安”,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摇滚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影响了文化,使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我认为艺术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例如,在音乐界,仍然有人在创作严肃的作品,比如我们最近关注到的艾格尼丝·欧贝尔(Agnes Obel)。这股力量是积极的。如果你听了鲍勃·迪伦或披头士的歌,然后再听弗兰克·辛纳屈的歌,辛纳屈就像是掉蜜罐里了——《夜晚的陌生人》《爱是最重要的》透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蓝色海洋地平线
油彩 铝板
2016
灰色地平线
油彩 铝板
215.9 x 190.5 cm
2015
Hugh Lane Gallery 藏
玛:您认为像互联网图像这样的新技术对你的艺术也很重要吗?你是否也注意到,互联网的图像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
肖:是的,它让艺术变得强大。你可以去蒙特塞拉特山顶的我的教堂,但那里每天只有十几个人能亲身体验。然而,这些图像也非常强,并产生影响。我从未去过马丘比丘,但当我看到这些图像时,我确实能感受到它的精神力量,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对我特别有利,因为我的作品相当重复,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它要适应计算机的世界,也要适应需要浪漫的世界,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玛:如果我们思考艺术圈的变化,您对艺术家所处的定位有什么看法?以前,艺术家是前卫、波西米亚、浪漫、革命性的,而现在的艺术家则截然不同,您之前也提到过杰夫·昆斯。您认为他今天是什么定位?
肖:当然,艺术家各不相同,就像其他很多领域的人一样。现在我注意到的是观众的人数变多了。比如,在莫斯科举办展览的时候,观众人数竟多达 35 万人;而且主要是年轻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年轻人比老年人好——而有趣的是,这群人对艺术有着巨大的渴望,展览也非常成功。如今,艺术家不再是流浪的吉普赛人或蹲在阁楼里思考存在主义的人物了——这种定位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更像是鲁本斯,他曾是伦敦的外交使节,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认为现在艺术就是这样的。我想不出有哪个时代,艺术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因为艺术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它是完全自由的。如果你以一种方式去阻碍它,它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发展——就像水一样。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个人的象征——水。因为它是不可阻挡的。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