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
10 月 11 日,《对话》“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特别节目《破题银发善终》播出,我们试图探讨的核心,是一个与公众认知尚有距离的话题——安宁疗护。它不以治愈为目的,而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身体照料与人文关怀,提高生存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400多万人需要安宁疗护,而实际得到照护的人数不足7%。
生死教育是安宁疗护的土壤。关注安宁疗护,就绕不开“死亡”。
初次见到研究死亡问题的社会学家景军教授时,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们:“这个选题做得顺利吗?”后来当我置身于节目的实际推进过程,时而因“这个话题很有意义”的肯定而振奋,时而又因各种“敏感”、“不适合”的提醒而自我怀疑、踟蹰不前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作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他太清楚触碰“死亡”这一话题,在社会观念与公共话语体系中会遭遇怎样的处境。
但这期节目的初衷,不止于记录“一群好心人做了好事”。感动之外,我们更想呈现的是现实困境,以及改变的可能。
当老龄化、少子化成为长期趋势,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家庭单元日益难以独自承担照护之重,老年照护、养老服务、安宁疗护就注定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议题,从家庭伦理责任上升为社会公共服务。
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社会不缺聪明人,也不缺能做事的人。前提是,我们要共同意识到这项问题的紧迫性与公共性。
景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被忽视的“刚需”:1.5亿人的生命议题
安宁疗护是刚需吗?
死亡离我们有多近?路桂军医生在节目中给出了震撼的数字:中国2024年死亡人口是1093万,如果每一个逝者按四个直系亲属算,大约有4000万人经历丧亲哀伤;如果每一个人有十个朋友的话,去年一年,中国就有1亿人经历丧友之痛。丧亲之痛、丧友之痛,加上逝者本人,一年就有1.5亿人与”死亡”正面相遇。
认知在哪里,资源就会被调配到哪里。如果死亡话题长期被当做‘房间里的大象’,相应的社会支持就难以建立,那在中国这个人均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度里,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就很难获得一个有尊严的告别。现实情况往往是:医院因顾虑“死亡率”等考评指标,对开设安宁疗护病房态度谨慎,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有需求的家庭要么无从知晓,要么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与社会文化影响,许多家庭在“尽孝”与“抢救”的压力下,忽视患者本人意愿,不惜耗尽积蓄,让亲人在过度治疗中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这种医疗资源的错配与患者尊严的失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灾难性卫生支出:家庭自付医疗费用的比例超过可支配收入的40%
事实上,死亡也有“质量”可言。 国际上常用“死亡质量”指数来评估一个地区临终关怀的水平,其指标包括疼痛管理与心理支持、安宁疗护体系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专业人才配备、社会认知与志愿者参与等。近十年来,中国的死亡质量排名有所上升,这背后,正是自2017年起国家推行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所带来的积极改变。它证明了,当社会开始正视死亡,改善就成为可能。
要打破现状,必须从根源入手,去补充现有医疗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正如宁晓红医生所强调的:‘我们特别亟需在中国建立缓和医学这样的学科。有了学科,我们就能培养专业的人才;有了人才,我们才能去更好地帮助病人。’“去告诉那些痛苦的人,现在止疼很重要,让他把心愿完成很重要,让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走完最后一段路很重要。”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安宁疗护绝非仅与老年人有关,它是我们所有人——无论年龄、无论健康与否——都应了解和拥有的生命选项。当前,全球的安宁疗护服务普遍偏重于老年群体,而忽视了罹患白血病、先天性遗传病等危及生命的儿童的需求。未来如果这项事业只在“银发”层面打转,将不仅是理念上的局限,更意味着其体系化的发展将面临先天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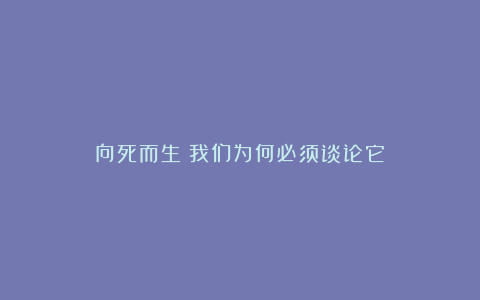
生命的完整:不止于“活着” 的意义
每当探讨人文话题时,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中国人吃饱饭才几年?”似乎一切超越物质生存的追问都属奢侈。但我想,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不正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孜孜以求吗?
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渗透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们以为:只要存在新的技术或药物,生命就理应被不计代价地延长——哪怕是浑身插着管子,在失能失智的状态下“活着”。在教育领域,激烈的竞争下,孩子作为“完整的人” 的丰富性,被简化成了分数和排名;他们的情感需求、人格成长,甚至是课间15分钟,都难以保障。我们追逐技术突破和效率极致,却让那些柔软的、构成生命本质的价值——尊严、陪伴、倾听,让位到了边缘。
安宁疗护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抵抗。一个生命末期的患者,不是一堆需要维修的器官,而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有尊严的“人”。安宁疗护关注患病的人,乃至于背后的家庭;不仅追求生理指标的稳定,更在意一个人在生命末期的舒适、尊严与内心的安宁。正如节目结尾AI给出的回答:“治疗的极限,正是关怀的起点。”
关怀的起点,源于尊重——尊重人的意志,尊重生命的完整性。学习面对死亡,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去表达爱。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爱常常与“剥夺”微妙地相伴:成年人习惯于替孩子做决定,也习惯于替老人做决定。有个数据让我很震动:中国每年离世的千万人中,约有70%将生命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他人。这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子女。当面临生死抉择,我们究竟该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还是以“爱”的名义替他们做主?安宁疗护并不提供唯一的答案,但它的意义在于能够促使家人之间坦诚沟通,让那份深藏的爱,能以更真实、更少遗憾的方式彼此呈现。
从无力到有力:行动者 有选择
如果说节目的经历,让我尝到了现实的厚重和观念的壁垒,那和这群安宁疗护实践者的相遇,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我看到,人可以在看似固化的系统里,从“无力感” 中,长出希望和行动力。
宁晓红医生坦诚地分享她的初心:“我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我个人的无助。”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当患者问她“真的没有方案了吗?”时,她曾感到彻底的无力。“我们其实还想帮他,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去帮他……我是因为从这儿我开始想,我该怎么办?”
宁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
当一位坚信“医学需要人文,重症更需要人文”的ICU医生踌躇半天说“但是我们医院并没有推广安宁疗护”的时候,宁晓红医生对他说:“没事,这是你自己的本领,没有人夺得走……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给患者和家属一个选择——你有选择。”
李旭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ICU副顾问
“你有选择”——这句话,也帮助了我。
这段从无力到有力的心路历程,让我对媒体的使命有了更深的体会。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提出,报刊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句跨越时空的论述,在时至今日的工作中一次次回响在我脑海里:如果我们只盯着板上钉钉的“成绩”宣传,却忽视了为普通人的困境、为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微小努力发声,是不是就背离了媒体最根本的使命?媒体独立的人文品格,不仅在于反映现实,更在于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应当凭着专业判断和良知,主动去发现、去传递那些关乎社会进步和普通人福祉的声音。帮助一个人活得更好、走得有尊严,这本就是社会发展该有的样子,也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秉持这份前瞻与担当,是我们职业生命的价值所在啊。
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你有选择”。
后记
录制中,路桂军医生还讲了一个让我难忘的故事。他问一位绝症患者是否想过为何得病,患者说:‘我一生抽大烟、喝大酒、熬大夜,得病也是情理之中的。’路医生问:‘那你后悔吗?’患者答:‘后悔的是没做过的事,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
路桂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
我们今日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希望将来站在生命终点时,能坦然地“不为没做过的事后悔。”
毕竟,我们如此认真地谈论死,正是为了更加郑重、更加真挚地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