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谭家岭古城是早于五千年前中国最大的城址,地位突出,价值重大。通过对谭家岭遗址遗存的年代分期及文化性质的梳理,对比谭家岭城垣解剖出土的遗存,进一步明确城垣的兴修年代为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废弃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的兴建与屈家岭下层文化强势崛起、龙嘴古城衰落相关,废弃则与石家河聚落群的发展壮大及石家河古城的兴起相关。谭家岭古城是长江中游首次完成文化整合和迈入文明进程新阶段的重要实证。
谭家岭古城的发现与确认是近些年来系统开展石家河遗址群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1]。它比此后兴起的石家河古城年代更早,从而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区域文明中心的年代大大提前。规模虽然逊于石家河古城,却是后者形成的基础,甚至是连接石家河古城与更早龙嘴古城的中间环节。从年代、规模、区位等方面来说,谭家岭古城在长江中游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地位突出、意义重大,有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兴废年代与背景作进一步的补充和梳理。
一、谭家岭遗址年代分期与文化性质
谭家岭遗址的发掘工作始于1980年代初[2]。此后于1987和1989年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揭示的早期遗存(即第一至三期)成为完善石家河遗址群分期标准的重要依据[3]。谭家岭是石家河遗址群中延续时间最长、年代序列最完整的关键性遗址。谭家岭古城城垣解剖所获资料中,尤其早期阶段遗物偏少,需基于遗址本身已有的年代分期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就谭家岭城址兴废年代相关的油子岭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分期及性质界定作简要的梳理。
(一)关于第一至三期遗存
这一期遗存分布于1987与1989年发掘的III、IV区,而又以III区最为丰富。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大部分探方未发掘到底,故发表的遗存和可作分期的资料甚少。从地层及墓葬出土的器物组合来看,以鼎(足根外侧有一按窝为特色)、浅盘粗圈足豆、折沿罐、碗、子母口深腹豆、盘口饰荷叶边形器盖为基本组合。墓葬以M13、M17为典型单位,以浅盘粗圈足豆、折沿罐、碗、盘口饰荷叶边形器盖为基本组合(图一)。
图一 谭家岭遗址第一期陶器的基本组合
谭家岭第一期遗存见于京山油子岭第一、二期[4]、天门龙嘴[5]等遗址。龙嘴遗址这一类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ⅡT0707⑤、ⅡT1034⑥、H28、H36等单位为代表,晚期以ⅡT0707③、ⅡT0435④、H26、H38、活动面Ⅰ等单位为代表。从早到晚器物演变规律明显,如:罐形豆由敛口到直口;罐(簋形)由折腹到圆腹;器座由亚腰到中部外鼓等(图二)。谭家岭遗址第一期遗存,罐形豆显得更为瘦高、浅盘豆多无孔等特征,显示其年代与龙嘴遗址晚期遗存更为接近,或更为偏晚。
图二 龙嘴遗址油子岭文化遗存分期
第二、三期遗存主要分布于III区,较第一期更为丰富。第二期以IIIT1106⑤C、IIIT1108⑥为代表;第三期以IIIT1106④B、IIIT1108④、H15为代表。与第一期相比,两期在文化面貌上更为一致,器物组合以彩陶碗、鼎、器盖、壶、曲腹杯、豆、盆、罐为主。报告中重点介绍了彩陶碗与鼎的演变规律,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曲腹杯的上腹逐渐变浅;器盖由侈口到外折沿出现(侈口并未消失),杯形圈钮由高到矮,乳钉钮和塔形钮在晚期逐渐流行。早晚之间的差别还表现在器类组合和纹饰等方面。器类方面,早期以鼎、器盖为主,另有少量的曲腹杯、盆、盘、罐、壶、纺轮等类;晚期在器类上虽无多大差别,只是属于早期的个别器类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器物类别增多。纹饰方面,早期以凹弦纹为主(主要体现在鼎上),彩绘仅见于彩陶碗;晚期彩绘逐渐流行,开始出现在碗、盆、壶、罐、盘、器盖、器座、陶球等多种器类之上(图三)。
图三 谭家岭遗址屈家岭下层文化遗存分期(左-早期,右-晚期)
器物形态到组合的差异在第一期与第二、三期之间表现明显,比如墓葬组合,前者以圈足罐、豆和碗为基本组合,后者是以鼎、器盖为基本组合,另有曲腹杯、彩陶碗等。对于这样的差异,余西云先生将早晚有别的两批遗存分别称之为“油子岭文化”和“屈家岭下层文化”[6]。笔者赞同此观点。依此,可将谭家岭遗址第一期遗存归为“油子岭文化”,第二、三期归为“屈家岭下层文化”。
(二)关于第四期遗存
第四期遗存主要分布于III区,属于屈家岭文化,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以H1、H2、H16、H18、IIIT1106③C、IVT2210⑥B为代表,晚期以H7、H23、F1、IIIT1106③B、IVT2210③C为代表。器物的演变规律是:双腹鼎腹深到腹浅,足根位置有下移的趋势;罐形鼎腹部的最大径下移;壶腹由圆鼓到锐折;器盖顶部三钉由分散到捏合;双腹豆、双腹碗类除了仰折由明显到模糊外,还有圈足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即台座出现,另外,早期流行镂空且孔数较多,晚期带镂空的器类减少,单个器物的孔数也在减少;壶、碗、豆、高柄杯等类的圈足逐渐显得瘦高(图四)。
图四 谭家岭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分期(下-早期,上-晚期)
以上年代分期与性质界定的梳理是建立在谭家岭遗址过去已有的成果基础之上,是进一步辨析谭家岭古城年代的重要参考。
二、谭家岭古城兴废年代
这里着重讨论兴修年代与废弃年代。
(一)兴修年代
谭家岭古城的城壕未解剖到底,故而,城垣内出土遗存与城垣上最早遗存的年代分别代表了城垣始筑年代的上限与下限。
1.城垣内出土遗存年代
由简报可知,2015—2016年揭露的谭家岭城垣部分可分八层,第2、7、8层未见陶器,其余各层有少量陶器。可辨器形有小鼎(包括鼎足)、釜、盆、罐(或瓮)残片。已公布的6件器物中,年代最早当属城垣第⑤层的1件泥质夹炭红陶釜(图五:1)和小鼎(图五:2)。泥质灰陶小鼎常见于谭家岭遗址二、三期,根据过去发掘的统计显示,第二期的小鼎的特点“多数为泥质红陶或橙黄陶,个别涂红色,少数为黑色或灰色”,第三期“体型缩小,腹变浅,足变矮”,全部为泥质灰陶或黑陶,纹饰很少并且简单。由此可知这件泥质灰陶小鼎为谭家岭第三期的可能性较大。
图五 谭家岭古城城垣出土遗物
城垣第4层出土泥质黑陶盆(或称大口罐;图五:3)既与其上第14层大口罐相似[JT6183(14):3]相似,只是其卷沿的风格代表其年代或许更早,如关庙山大溪文化第三期就出土有满饰密弦纹的高领罐(T64④AH80:1),当属于长江中游最早的一件[7]。
城垣第1层出土的凿形小矮足(图三:5)多见于谭家岭第三期;小罐形鼎(图三:4)折沿,年代稍晚于城垣⑤:2卷沿及领部较竖直的风格;罐(瓮)可能为肩部残片,薄胎,饰密弦纹,同类器可对比屈家岭第三次发掘M12:35。第1层仅有的3件器物中,2件为泥质黑陶,1件为泥质灰陶,与谭家岭三期的风格相似。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城垣①层为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城垣第⑤层或其下的年代或偏早,但仍然不出屈家岭下层的年代范畴。不排除城垣有多次修筑或修补的可能。
2.城垣上遗存年代
城垣及城壕上的堆积最浅处厚1.8米,统一划分为十五层,第3~5层为后石家河文化,第6~10层为石家河文化,第11、12层为屈家岭文化晚期,第13、14、15层为屈家岭文化早期。与城垣年代直接相关的是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13层分布于发掘区西南部的城垣内坡上,14层分布于发掘区的中南部,15层分布于发掘区的中南部。
值得一提的是,叠压于城垣之上原归属于14层的3件可修复完整器(图七)的年代并非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在此有必要对这三件完整器的出土情况作一个补充说明。据后期照片整理时发现,这三件陶器(简报中均称为罐)出土时集中在一起,其中4号置于3号之中(图六)。鉴于三件器物的埋藏状况,推测原应为开口于14层下的一个遗迹单位(如灰坑,或为活动面)。另需说明的是,15层为局部分布,主要分布于JT6038、6138的西部,即为城垣内坡堆积,与14层无直接的叠压关系。三件陶器出土于JT6183偏西部,即开口于14层下,打破城垣。
图六 谭家岭城垣解剖第14层下陶器出土情景
图七 谭家岭城垣解剖原第14层出土陶器
这三件陶器(以及所代表遗迹单位)的年代是谭家岭古城修筑年代的下限。小口罐[JT6183(14):4]矮领、溜肩、中部鼓腹、平底,相似器形见于谭家岭遗址第三期ⅢT1108⑤:71[8]、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ⅠH11:1(1)[9],属于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敛口罐[JT6183(14):2],子母敛口、深圆鼓腹、小圈足较高,颈、腹中部与下腹部等距饰一周附加堆纹,相似器形见于谭家岭遗址第三期ⅢT1108④A:384[10],稍晚的器形则见于邓家湾遗址屈家岭文化早期AT504④A:8[11]。大口罐[JT6183(14):3]仰折沿,垂鼓腹,小矮圈足,下腹部饰两周凸弦纹。相似器形见于谭家岭三期ⅢT1006⑧:4、屈家岭第三次发掘M12:5[12]、六合M9:18[13]。大口罐同样流行于屈家岭文化,虽同为仰折沿、带圈足,但后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多仰折沿,沿外缘下撇,圈足普遍偏高大,最大区别还在于屈家岭文化多为斜腹(图八)。
图八 谭家岭城垣上地层出土遗物及对比
(二)废弃年代
根据城垣上和城壕内的文化层堆积情况,简报称“谭家岭城址在屈家岭文化早期仍然使用,但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其城壕功能逐渐被废弃”。城壕因未发掘至底,仅揭露第6层,故接近底部堆积的年代不详。但从城壕内第1~6层出土的陶器来看,小鼎多系凿形矮足,豆的圈足镂孔小而多,双腹器腹部折痕明显,壶形器饰有规则的网纹,这些都是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的特征与风格。
城垣上有墓葬、灰坑、基槽和灰沟等遗迹,这些遗迹多开口于11层下,也均显示在屈家岭文化早期,谭家岭城垣就逐渐遭受破坏。M5开口在第11层下,打破第12层,未揭露完整,从出土的4件随葬品来看,高领罐肩部饰多道规则凸弦纹与碗口沿内敛的风格常见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二者组合可对比钟祥六合H2[14]。M6开口于第11层下,打破第14层,通体宽矮的罐形鼎与邓家湾M104:1[15]、朱家坟头M1:6[16]相似(图九),同样当属屈家岭文化早期。
图九 谭家岭墓葬随葬品与其他遗址比对
目前一般认为,屈家岭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跨度在距今5700至5300之间,早晚期的界限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的绝对年代跨度在5300—4500年之间,早晚期的界限在距今约4800年左右[17]。综合以上年代对比分析,谭家岭古城兴起于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绝对年代距今约5500—5300年。废弃年代当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年代下限在距今4800年左右。古城的兴修到使用经历了数百年,绝对年代在距今5500—4800年之间。
三、谭家岭古城兴废背景
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进入社会复杂化加速阶段。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升,如制陶技术出现了慢轮修整,陶器制作更加规范。遗址数量及人口大大增加,大型聚落出现,出现贫富分野。特别是进入5500年左右的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技术进步与社会复杂化更为明显。社会生产力提高、专业分工及阶层分化出现,是谭家岭古城出现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具体到谭家岭古城的兴起,还与汉东地区自身文化发展及长江中游文化变迁等背景相关。
一、汉东地区文化中心的转移。谭家岭古城的兴起与龙嘴城址的废弃及谭家岭的兴起紧密相关。一则,龙嘴遗址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发掘显示,城内的遗存主要以油子岭文化为主,晚期堆积极其单薄、遗迹稀少。与龙嘴晚期相衔接的是,谭家岭遗址在油子岭文化晚期,开始作为一处重要聚落登上历史舞台。二则谭家岭遗址自身规模的发展。1980年代发掘显示,谭家岭遗址屈家岭下层文化的分布广泛,说明至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谭家岭遗址已发展至相当规模。
二、屈家岭下层文化的强势崛起。屈家岭下层文化兴起于汉东地区,直接源头是油子岭文化。自形成后,“向北、东南都有少量渗透,主要是向西、西南大规模扩张,与大溪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8]。目前该类文化的分布及影响范围是:东至鄂东南黄冈一带,北至南阳盆地南缘、西至西陵峡,南至洞庭湖北岸。典型遗存在汉东地区主要见于天门谭家岭[19]、张家山[20]、应城陶家湖[21]、荆门屈家岭[22]、殷家岭[23]、京山朱家咀[24]、油子岭[25]、钟祥六合[26],鄂东南见于新洲香炉山[27]、武昌放鹰台[28]、黄冈螺蛳山[29],汉水以西见于宜都红花套[30]、宜昌中堡岛[31]、宜城顾家坡[32]、荆门龙王山[33],峡江地区主要见于宜昌白狮湾[34]、清水滩[35]、巫山大溪[36]、江陵朱家台[37]、巴东楠木园[38]、李家湾[39],洞庭湖北岸见于松滋桂花树[40]、公安王家岗[41]、枝江关庙山[42]、澧县三元宫[43]、冯家岗[44]、丁家岗[45]、城头山[46]、宋家台[47]、安乡度家岗[48]、划城岗[49]、华容长岗庙、车轱山[50]、李家屋场[51]、石首走马岭[52]等,其影响范围在随枣走廊的枣阳雕龙碑[53],汉水中上游在郧县郭家道子[54],鄂东南在黄冈螺蛳山[55]等遗址等。汉东地区屈家岭下层文化的崛起,迅速完成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整合,为之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鼎盛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视为长江中游文明的第一次奠基。谭家岭古城并非孤例,同时期修筑的还有石首走马岭古城[56]、澧县城头山第三期城垣[57],后两者在规模上均小于谭家岭古城,且谭家岭所在的汉东地区是屈家岭下层文化的策源地,由此推知,谭家岭古城当是屈家岭下层文化的中心。
谭家岭古城废弃的原因主要在于石家河聚落自身发展壮大的结果。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随着人口增多,石家河遗址群规模逐步扩大,已有的谭家岭一片不再满足人们对居住、墓地、专业作坊等规划需求,继而向周边区域扩散。调查显示,谭家岭周边的三房湾、邓家湾、蓄树岭、肖家屋脊、罗家柏岭、京山坡、王家台、罐山、昌门冲都发现了屈家岭文化遗存[58]。其中罗家柏岭、邓家湾、肖家屋脊、三房湾,朱家坟头、周家湾曾先后开展系统发掘[59],表明至迟在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址分布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后来兴起的石家河古城内部,还扩散至石家河城壕外围。石家河古城的修建正是聚落扩大发展的结果。邓家湾遗址发掘显示,石家河古城始于屈家岭文化早晚之际[60],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4900—4800年左右,此时正是谭家岭城池功能彻底废弃的年代,两者一兴一废,有着紧密的衔接关系。随着石家河古城的兴起,原有以谭家岭古城作为主要活动区的规划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邓家湾作为墓地和祭祀区的功能区划开始凸显,肖家屋脊作为分支社群开始拥有独立的居址与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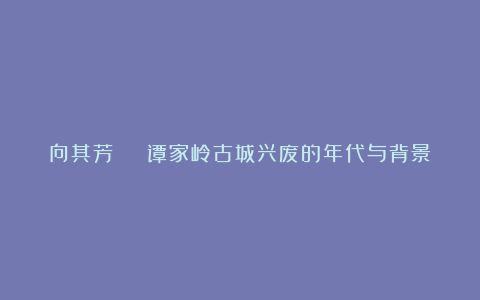
四、小结
谭家岭古城是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是长江中游早期文明进程的重要实证,地位突出,价值重大。通过对谭家岭遗址已有分期及性质的梳理,对比谭家岭古城解剖所出的遗存,初步判定谭家岭古城始建于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废弃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兴建及使用前后延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绝对年代在距今5500—4800年之间。古城的兴修与废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屈家岭下层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尤其两湖地区首次完成了高度的文化整合。这一整合是生产力发展、文化交流频繁的必然结果,实则背后还充斥着剥削压迫与暴力征服。以龙王山M132为代表的大型墓葬及普遍以象征财富的猪下颌骨随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明显。顾家坡、李家屋场等墓地中突出石钺在随葬品中的地位,另在顾家坡墓葬中还随葬有大量的骨镞,表明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交叉接触地带,武力征服成为解决矛盾的常用手段。谭家岭古城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背景下开始修建。谭家岭古城的兴起并非孤例,同时期洞庭湖北城头山和走马岭遗址也开启了新一轮的筑城运动,表明在同一文化内部,不同族群与不同阶层之间同样存在暴力冲突与武力征服。谭家岭古城的兴起,是屈家岭下层文化强势崛起,并对外迅速扩张和对内强化管控的一个缩影,是长江中游社会迈进文明国家的重要实证。
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迎来了新一轮的筑城高峰期,已发现并初步确定属于这一时期的城址多达十余座[61]。从分布上来说,除最为靠北的大悟土城和襄阳凤凰咀,其他多数城址大体呈半月形分布在两湖平原的西部和北部的山前过渡地带。又大致以汉水、长江为界,可将这些城址分为汉东、汉西、洞庭湖北三个“城址群”。其中,汉东地区最为密集,与屈家岭下层文化形成以来长江中游文化发展重心转移至此并得以长足发展的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另外,这些城址大小规模不一,可作明确的等级之分,石家河古城处于这一层级体系的最顶端,以石家河为核心的社会很有可能是以军权和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石家河是这一王权国家的都城[62]。以石家河为统领的聚落层级体系,表明当时的石家河王国已构建起明显、严格的分层管理控制体系。同时,城址早已不仅仅限于最初的防御功能,还成为彰显等级和礼制规范的象征。汉东地区是屈家岭下层文化、屈家岭文化的策源地,石家河作为中心遗址,庞大的石家河古城取代谭家岭古城,不仅仅是聚落发展壮大的结果,更是满足统治阶层开展礼制构建、表明身份等级、彰显王国气派的政治需要。
作者:向其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 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