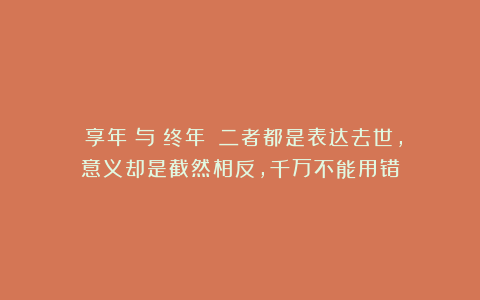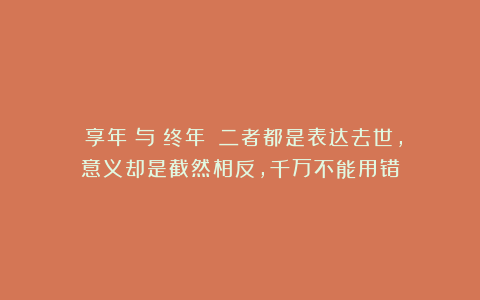|
浙江绍兴的一场传统丧礼上,曾发生过了这样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仙逝,前来吊唁的宾客却发现灵堂挽联上写着’终年八十有三’,几位年长的乡贤当即面露难色,表现得非常不高兴。
原来,这位去世的老者一生乐善好施,乡邻全都很尊敬他,按照礼仪,应该用’享年’才合情理。
这个细节背后,藏着一组极易混淆的词语——’享年’与’终年’。
看似都是对逝者年龄的表述,实则承载着中华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礼仪精髓,错用一字,便可能违背传统伦理,引来非议。
‘终年’一词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初并非专指死亡。
《诗经·小雅》中’霰雪其雱,终风且霾’的’终’,意为’整段、全部’,‘终年’本指’全年、一整年’,如《墨子·节用上》’久者终年,速者数月’,描述的是时间的延续性。
直到汉代,这个词才逐渐引申出’生命终结时的年龄’这一含义,《汉书·外戚传》中’太后终年,上亲临丧’,首次将其与死亡关联,但仍侧重于客观记录生命终止的时间节点。
‘享年’的出现则晚得多,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碑文。
‘享’字在甲骨文中像’宗庙中祭祀的礼器’,本义与祭祀、敬奉相关,引申出’享受、拥有’的含义。
‘享年’一词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庄重色彩,《魏书·列女传》记载某位夫人’享年七十,内外咸哀’,这里的’享’不仅指生命的长度,更隐含’安享天年、德行配位’的评价。
它将时间计量与道德评判结合,使对逝者的描述超越了单纯的事实陈述。
颜真卿为其曾祖撰写的《颜勤礼碑》中,对品行高洁者用’享年七十有九’,对早夭或生平有争议者则用’终年四十’。
可见在唐代,这两个词的使用已形成明确分野:‘终年’是中性的时间记录,’享年’则包含着对逝者的尊重与肯定。
首先是年龄门槛,古人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未满六十者去世通常不用’享年’,《礼记·曲礼》中’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的记载,为’享年’的使用设定了年龄基准。
清代《称谓录》更明确指出:’享年,谓享世之年,六十以上方可言享年。’这源于古人对’寿数’的敬畏,认为短寿者未得’天年’,用’享年’有违天道。
北宋司马光在《书仪》中强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享年之称,必待有行之士。’
明代大画家徐渭为友人作墓志铭时,因为朋友曾经对他有所亏欠,徐渭特意将初稿中的’享年’改为’终年’,并在跋文中解释:’其人虽寿,行不配德,未可称享。’
这种将道德评价纳入词汇选择的做法,体现了’太上有立德’的儒家价值观。
对于早夭者,如《红楼梦》中秦可卿’终年二十有一’,用’终年’既客观陈述事实,也隐含惋惜之情;
对于身份低微或生平不详者,’终年’可避免因过度评价而失礼;
而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史书往往以’终年’回避价值判断,如《明史》中对奸臣严嵩的记载仅称’终年八十八’,一字之差,褒贬自明。
古人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往生’的开始,对逝者的称谓如同对生者的称呼一样,必须符合其身份地位与道德品行,这便是’慎终追远’的具体实践。
在传统丧礼中,从’初终’时的招魂仪式,到’殓殡’时的衣衾等级,再到’祭奠’时的祭文措辞,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
‘享年’与’终年’的选择,正是这种规范在语言层面的延伸。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称谓者,礼之末也,然失其末,斯害于其本。’
用词的恰当与否,被视为是否尊重逝者、是否恪守孝道的重要标志。
几年前,某知名企业家去世,媒体报道中’享年’与’终年’的混用引发热议。
支持者认为应与时俱进,反对者则强调’礼不可废’。事实上,这种争议恰恰说明,这些看似陈旧的词汇,仍承载着人们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对是非曲直的坚守。
到了当今,许多传统礼仪逐渐被简化,但’享年’与’终年’的使用规范仍值得珍视。
它提醒我们,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基因的载体。
在追悼会上,正确使用这两个词,是对逝者的基本尊重;在历史写作中,恰当选用则能体现对人物的客观评价。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