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进入香港的时候,把全香港的米仓和银行,全都封锁掉了。因此,香港的居民不管多么有钱的人或一个打工仔,同样地困难到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单单为了救济朋友和熟人,我想了各种办法,等我回到部队时,报道部部长对我说:
“你在部里的职务,终于决定了。在部里必须处理的工作当中,如果不精通广东话和中国话,是无法处理的。也就是说香港的很多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各种剧场、都要加以指导和管理;还有,酒吧、舞厅的唱歌的演员、评书演员、各种演员之类,都必须取缔。嗳,是属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所有部门吧。这么大的范围,很难找人管啊!就叫做文化艺术班,你来当这个班长,给我好好干吧!”
后来我得到了参谋长的许可:可以给我所管辖的范围内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属,发放配给米。
梅兰芳与薛觉先
当时,在香港代表中国电影戏剧界,甚至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的三位大明星,各人有各样的原因,也包括战争的原因,从大陆避居到香港来。这三位大明星就是梅兰芳、胡蝶、薛觉先。如果说中国的“京剧皇帝”是梅兰芳,那么多年来在上海、香港位居中国电影界的“电影皇后”就是胡蝶;薛觉先则被美誉为“北有梅兰芳,南有薛觉先”,是粤剧的瑰宝。
粤剧的大老倌,除了薛觉先之外,还有马师曾等人,可薛觉先和我的关系比较深。
许多喜欢看广东戏的广东人这样说:
“像薛觉先这样的好演员,不会再出来了吧。他虽然是扮演小生,可扮演花旦也很出色。不管传统剧或新编剧,要演的话,一定会博得全场大喝彩。而且舞蹈和武打都很好啊!”
我和薛觉先见面,是在香港旧跑马地附近他的住宅里,在我和胡蝶见面后两天。因为我自认是“薛觉先迷”(现在想起来,一个占领军的文艺组长,去看自己管辖下的戏子,是不成体统的。可在我的头脑里,钟鼓一响,二胡一拉,《西厢记》、《西施》、《花染状元红》等等剧目,他在许多有名的舞台上的形象,好像走马灯一样,一隐一现,他从我的神态中也看出来了吧)。在薛觉先的脸上,认为我来看一个敌国的演员这种不安的神色也很少。
薛觉先之《西施》
“听说你经常看广东戏啊,而且广东话又讲得很好,您令尊或令堂是广东人吗?”他一本正经地问,使我苦笑了。两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往外走出一步,战争的余烬还在冒烟的时候,不能光聊天,我就以随便的口气问他:
“你有什么困难吗?大家暂时可以吃几天的米,已经送到厨房来了吧。只要我能办得到的,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请你不要客气地说吧。”
我打从心里这样说,反复说了好几遍请他不要客气。薛觉先起初吞吞吐吐的,不一会儿,好像下了决心似的,终于开了口:
“其实,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也知道,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同样地困难啊!”
我从里面的衣袋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在他面前打开,把所有的军票都给了他,我说:
“我住在军队的宿舍里,吃饭也不要钱,虽然一点点,你先拿去用吧。”只有两百块钱,还是刚刚发我一个月的军饷。
这时,从薛觉先闭着的眼睛里,揩也揩不了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拿手帕一边揩一边说:
“请你原谅,我哭起来了……我很惊奇……很感谢你,不由得哭了起来。你尽管广东话说得很好,还是日本人。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认为你们为了实现自已的野心,把中国作战场,虐杀无辜的老百姓,我们认为你们这些日本人是无耻的、臭不可闻的鬼子。可是,被我们骂作日本鬼的日本人却来同情我们,把钱包里的钱全部拿出来给我,我感激得哭起来,是很自然的。”
薛觉先说着,拉住我的手。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你一定是有什么要求的。请你不要客气说吧。”他相反地来问我。
薛觉先充满真情的话和态度,使我非常感动。又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到刚才还是敌对双方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够如此深切地作内心的交流,实在令人激动。
《胡不归》薛觉先饰文萍生
“快,先说你的要求吧。”他再次催促,我便坦率地说了。
“由你来剧场开台好吗?一开台,因战争而动荡的民心和街上的情况都会稳定下来吧。首先,我作为薛觉先迷,很想早一日看你上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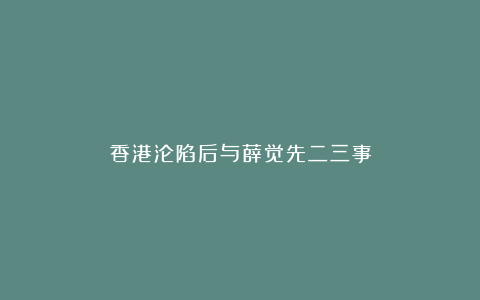
薛觉先的脸上重新恢复了微笑。他说:
“那,没有问题。把大家召集起来,三四天内在利舞台开台!因为大家也是不干活的话就吃不上饭了。”他又说:
“对,开台第一天,在我的刚目中,你想看什么?请你说说你想看哪一出戏?”
我一时说不出来,便说:
“比起新编剧,我倒喜欢传统剧。我不客气地说吧,我想看你的《西厢待月》。”
过了三天的晚上,薛觉先主演的《西厢待月》开幕,利舞台全场爆满。
后来,薛觉先和我的交往,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证实了在第一次见面时那些令人感动的话。因为彼此都很忙,不能每天都这样在一起,可我只感到薛觉先在我身边,就很快乐。而且激励我全力投入电影戏剧界的管理工作。
在抗日、抗战的口号下,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意气昂扬的重庆政府,坚持抗战,薛觉先和我之间,不能长久保持平安无事。
尽管薛觉先是个大老倌,演得多么好,可是在香港这样的小地方,即使变换剧目,也不能只由一个戏班子一直演一年多。来看戏的人当然就渐渐少了。和香港就像眼睛和鼻子那么近的澳门,当时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以赌博、鸦片、妓女而闻名于世。居民和香港一样以广东人为主,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有一天,薛觉先来找我商量说:
“因为有人来邀请,我们想到澳门去巡回演出,好吗?”
由于上述的情况,又没有什么理由好反对的,我提出这样的条件:不要越过澳门的边界跑到重庆那边去,也不要跑到和重庆那边邻近的法国殖民地(从事抗日的)广州湾那边去。就容许去澳门巡回演出,并发给了护照。
但是,薛觉先在澳门演出一个月结束后,却没有回香港。并且我听到消息说,薛觉先他们应邀到广州湾去了。另一方面,又接到了意外的通知,香港的宪兵队为了要追究这件事,就以薛觉先一班人既没有得到日本军的许可,在护照上也没有登记就跑到广州湾去为借口,对薛觉先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后贴上了封条。
《清宫恨史》薛觉先饰光绪皇帝
“干出这样的事,薛觉先再也不能回到香港来了。”我又想到宪兵队。
但是,薛觉先和梅兰芳、胡蝶不一样,他在日本军占领下的香港,已经登台演出一年多,从最坏的情况考虑,我担心他会被重庆方面当汉奸对待,强制把他从广州湾带到重庆那边去。
薛觉先之所以留在香港,重上舞台,并不是为了协助日本军,他作为粤剧界的栋梁、负责人,是为了演员、乐师、后台等全体粤剧界的生活。说得明白一点,是大家苦苦央求他,让他们有碗饭吃。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薛觉先等于受到汉奸的待遇。因为,不久他被迫发表了声明:
“我背弃祖国,留在日本占领区,没有立即参加抗战行列,罪恶深重,悔悟前非。”
不仅如此,据来自重庆方面的情报说,国民党和民众并没有轻易地原凉他。
薛觉先、谭玉真之《花染状元红》
是谁把薛觉先赶进这样的苦境?不用说,就是我。毕竟是应我的邀请,他登上利舞台才开端的。我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不胜自疚。
而且,不仅仅是一个薛觉先,我对香港电影戏剧界保证的三个条件,在当时虽然说是破格的,他们接受了,哪怕是一时的,给予我协助的中国人,在战时就不必说,在战后也一直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吃苦。也就是说,我深信是正确的三个条件,却成了把他们赶上难以言喻的痛苦的道路的甜言蜜语。
我打从战前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很友好,在心里认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是可耻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来,也是必然的。日本军陷入战争的泥沼,局势越对日本不利,我越对中国人采取同情的态度。不,毋宁说采取了人道的态度。渐渐地被日本军当局视为“叛逆”。
我发给薛觉先他们护照,也算作帮助他们逃亡的罪状之一,被打上具有和“中国奴一样的思想”的烙印,遭到香港宪兵队的逮捕,我受到反复的审查,就这样被戴上思想犯的帽子,被遣送回日本了。
(《明报月刊》)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