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月底要掰了,到时回去帮忙挑几担。”父亲进城给我送菜,聊起母亲的忙碌,他如此说。父母都年过古稀,玉米地在高高的半山,身为子女,农忙需要帮助,自然责无旁贷。
老家在歙东深山,崇山峻岭,肩挑背扛,是祖辈出门的日常。挑猪粪、人粪上山,挑玉米、山芋回家,这是记事以来的农村生活。父母肩上,不是锄头就是扁担,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黄色的扁担,都挑出了包浆。
山里的土地,耕种的粮食不够筷子扒拉,翻越竦岭去百十里外的旌德挑粮,是数百年来的常态。等到我有印象,一山之隔的邻村修建了粮站,来回8公里。我跟去挑粮那年,读小学三四年级,具体已经忘记。父亲说,到粮站买米,一起去?
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哪知担滋味。小小的扁担,歇气的打杵,我自己扛。家里出发,沿着山脚走两里路,爬上陡峭的松树岭,穿过桃岭,然后是一色的石板路下到山脚,出坞口就是粮站。
父亲给我装好了担子,两只小小滚茶袋,米担也就二十多斤。我在前,父亲在后。担子挑在肩上,起步并不觉得多重,沿着仄仄的石板路进了山坞。晃晃悠悠的担子,在肩膀上感觉就那样,小小的打杵放上肩膀,从后面翘起扁担,使劲朝下按着,担子的重量匀在两个肩膀。
石板路先是平缓,台阶不是很多。走了百余米,脚步慢下来。父亲在身后说:“吃力了,就歇一下。后面的袋子要找个稍高的台阶,米担就平了。”我看着四周,刚好有斜坡走出的路阶,后面的袋子放上去,打杵松下来,撑稳妥了扁担,人从担子下钻过来,扶着担子,伸直了腰杆。
父亲叮嘱:“歇一下就行,歇长了就使不上劲。”我赶紧钻到扁担下,松开打杵,担子在肩上,继续沿着石板路上行。担子不重,路越来越陡,台阶感觉就高起来。走不了多远,感觉又没劲了,赶紧找地歇口气。父亲不急不缓的跟着,我歇,他也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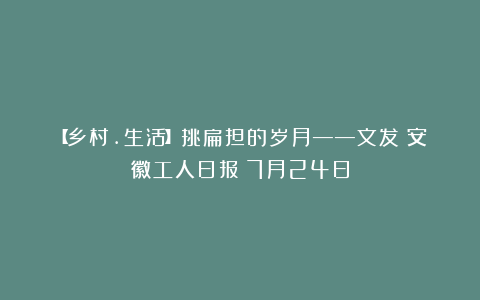
石板路沿着山势,高低不齐,走的每一步,也就高高低低。稍不留神,前面的袋子就磕石板上,或挂茶棵上,袋子不自禁的旋转,我使劲拽着,面红耳赤。父亲伸手扶着我的米担:“挑担,也是要看到路的。”我心里不服,第一次挑米,不是没有经验嘛。
那担米怎么到家的,我已经想不起来。记得祖母后来问:“挑米苦不苦?以后不好好学习,在家里做农,就是跟大家一样,日日两根棍夹着头颈。”要是在以前说,我真是不了解,有了挑米的亲历、肩膀的红肿,扁担和打杵夹着头颈的感觉,哪有手握钢笔来得轻松呢?
读初一那年,学校征了村背后的半山腰做教学楼。运输车把沙子和砖运到车站,倒下就走。搬沙子和砖,就成了学生的劳动课。工地紧张,一个人任务一百块煤渣砖,搬好进教室。车站与学校,隔着村里的小河,下车站,过桥,爬半坡,二百多米。
吃过中饭,挑了家里长荚的竹箕去。一边7砖,一担十四块砖。双手伸出扶着前后的竹箕,第一担绝对是快步如飞。家在山上的同学没有工具,双手捧着五六块砖,弯着腰一溜小跑。穿村的小路不宽,你来我往,很快就拥挤在一起。挑好了自己的,就把山上女同学挑一担,男同学就让自己挑。
给学校挑砖的日子,持续了半年。来年三月,学校布置任务,到山那边的绩溪县上庄镇余村去挑瓦,每人60片瓦,自带劳动工具、干粮。只要不上课,干啥都有劲。到上庄,15里。我挑了一对小茶篮,爬过竦岭,跟着大部队到余村。先到的老师站在窑口:“不用急,挑瓦回校路上注意安全,打碎就没用了。”
挑瓦,不分男女,不分年级,60片瓦,现在想来也就三四十斤,这对农村少年来说,其实不算重,可走了15里山路过来,已经一身汗,再翻山挑回去。远路无轻担,这对“豆蔻梢头二月初,袅袅婷婷十三余”的初一学生来说,是需要考虑耐力的。教室在村里老社屋的楼上,楼下的茶厂,阴暗而嘈杂。想着有新教学楼,肩上的担子就不是瓦,而是初二的新教室。劲道也就来了,路程再远,也是回家的路,担子再重,也是为了新教室。
那年月,县里茶厂到山里收茶,在山峦上开收茶点。搬运,是从山上挑到车站,大概三四里路,一担茶一元二毛钱,大家都抢着去。我下坡的路挑不惯,也怕茶袋勾住路边的荆棘,扯破磨破。茶叶散了,是要赔钱的。一担茶一百二十斤,份量是固定的,我负责在山脚接母亲的茶担,专挑平路到车站。一个早上,一家人挑十几担。
浇粪施肥是母亲的事,挑粪是我可以做的。猪粪是稻草茅草杂混一起的,挑着就是了。人粪却是晃荡晃荡的,母亲扯根稻草绾个结,放在上面,起步轻盈,重心稳定,就不会晃到身上。一担粪挑到地里,不晃出一滴来,就是本事。挑着挑着,就长大了。
进城读书,又在县城谋生,扁担也就逐渐远离了肩膀。挑扁担的日子也就难得了,茶季里回家,或暑假收玉米,偶尔挑个几次。扁担在肩上,是那么的亲切。从挑扁担的岁月过来,吃过了许多挑担的苦之后,我过上了不再是“两根棍夹着头颈”的日子。可那段生活,却长进了我的骨头,成了生命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