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落后,国家和百姓都很贫穷,农村更是穷得叮当响。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农村不仅缺粮,更缺种粮所需的肥料。当时,除了计划供应的少量碳氨、氨水等少数几种化学肥料之外,农村普遍使用的都是传统的农家肥。这些农家肥,不是农家自己产生的人畜粪水(土话垩壅ǒ yōng),就是通过种植秧草(红花郞)、罱河泥等方式沤制的草木灰肥。
所谓河泥就是沉积在河床底部的淤泥,这淤泥中含有的丰富的有机物质,对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通过罱河泥这个过程,把淤泥从河底提取上来直接播撒或通过与秸秆、杂草等沤制成有机肥施到地里,就能有效增加土地肥力,促进粮食稳产增产。所以,每年冬至到春分这段时间,人们为了新一年的丰收,都会组织部分劳力在河塘里罱河泥。
印象中只要是在积肥季里,村里那不宽的小河边,总会停泊着几艘专门用来罱河泥用的小木船,这船在当年就算是生产队里与耕牛同样重要的生产资料了。初看,那小木船似乎有点像简约版、微缩版的“宝船”(郑和下西洋时用的船只)。船长8米左右,中间宽两头窄,两头微微向上翘起,船底稍呈弧型,整体为木质结构。共分三个船仓,前后仓均不足一平方米,前仓主要用来搁置罱泥的工具,而后仓主要是供罱河泥人员站立活动。中间的仓最大,长约2米,宽1.5米左右,仓底距船面高约50厘米,用来存放罱上来的河泥。整个船只的载重最多也超不过一吨。
罱河泥的工具主要有三件,罱泥夹子、篰钎、篙子。罱泥夹子是合并在一起的两个蚌壳形的竹编网兜,通过铁构件连接成钳状,合在一起时呈河蚌形状,高40公分左右,宽近50公分,深约20公分。两根10米多长的竹杆(罱竿)将其牢牢地固定在底部,作为罱泥夹子的握柄(撬扛)。看似构造简单的罱泥夹子,却凝聚了农人们不少的智慧在里面。 那“大嘴巴”似的罱泥竹兜上下颚都有留有竹篮似的漏孔,用于沥去多余的水分,以减轻罱泥人的操作负荷。两根长长的握柄似两根杠杆,越往上抓就越能轻松地操纵罱泥夹子的开阖。篰钎是一种用木头做成的,类似于长柄勺子的木锹,用铁丝固定在一根粗粗的竹棍上,作用就是如铁锹抄货般将船里的河泥送上岸去。篙子,是一根长约七八米的竹竿,粗的一头装着带有弯钩的铁制尖形篙头,是用来撑船稳船的主要工具。
在旧时,罱河泥可以称得上是江南水乡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每每走在树影婆娑的河塘边,抑或是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埂上,常常都能看到那农田边的河道里,一条条罱泥小船正在河中作业。几名罱泥人正稳稳地驾驭着小木船在河面上忙碌着,一根根长长的罱竿在他们手中很有节律地舞动着,不时泛起一朵朵飞溅的水花,连同一股股淤泥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只见他们左脚心踩住竹篙子紧贴在船沿上,将船稳住,双手把栓着罱泥夹子的两根罱竿从右側张开,倾斜着朝河底趟去,再稍稍用力往下一戳,感觉淤泥充满竹兜时,便将罱泥夹子的两根罱竿合拢,双手提竿从河底往上一拉,将罱泥夹子搁于船舷,稍稍沥掉部分河水。同时,将船的右側倾斜贴住水面,握紧罱竿根部,双腿微屈,两臂同时发力,将满含河泥的罱泥夹子拖入船仓,松开合着的罱竿,“哗”的一声,那满兜河泥拌着河水便泻入了船仓。如此循环往复,罱满一船河泥后,将船撑到河边的小泥塘边,用一根绳索将船系在岸边的木桩上,然后再用篰钎一锹一锹地将泥甩上岸去。那罱泥人从船上向泥塘里甩送河泥的动作也是极富韵律的,弯腰抄泥、抬头举起、挺胸甩送,“啪嗒”一声那乌黑发亮的稀泥便向岸边的泥塘里“飞”去。小船也随着罱泥人身体的摆动而有节律地摆动着,泥浆声声,节律划一,“啪嗒、啪嗒”,煞是动听。甩到塘里的河泥再由另一名社员(村民)用长柄撩勺一勺一勺地舀往更高处的河泥塘里,边舀边把红花郞等绿植搅入塘中,等塘里的泥草快要满塘时,再灌入部分河水盖住塘里的泥草,尔后进行搅拌让其腐烂发酵,沤上一段时间,便可以用来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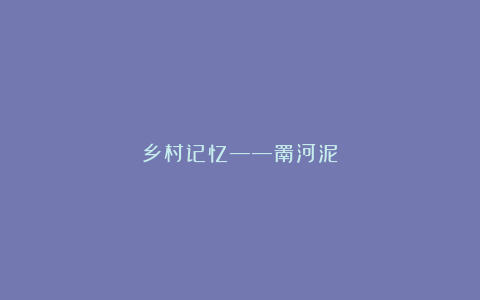
在生产队里,罱河泥既是一项力气活,又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苦活脏活,一般人难以胜任。因为费时费力费脑筋,所以罱泥工所得的工分较一般社员要高出许多。那个时候,常常会看到罱泥人冒着严寒下河罱泥的情景:一船泥罱好,半个身子湿透,双手更是被冻得通红通红。当年,我们村里前后两个生产队分别都有两到三条罱泥船,参与罱河泥的社员,都是队里的男性壮劳力,他们有着多年的罱泥经验。对村里的河道、水塘的深浅、沟泥淤积状况等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够在作业时既保持好小船的稳定,不让其随意漂动,又能顺利地操纵罱泥夹子,把河泥“抓”上船来,这非常考验人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再说罱满一船河泥,船舷已经和水面基本平齐,在旁人看来只有船头船尾露出了水面。这个时候,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撑船水平,因为稍有不慎,就有翻(沉)船的危险,这在检验人平衡性的同时,更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当小船停靠岸边,用篰钎把河泥凌空甩入岸上的泥塘里,也是一项既需要臂力,又需要的技巧过程。
“冬天一船泥,秋收几担谷”。在农家,河泥与绿肥、粪肥、灰肥一样,都是优质的有机肥。罱河泥,可谓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既能增加耕地的肥力,又清淤疏通了河道,更净化了水质。偶尔还会将那些小鱼、小虾、河蚌、螺丝等一并带上船来,这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无疑是一顿非常难得的家常美食。特别是待河泥塘里的泥浆稍稍沉淀后,还会有螺蛳慢慢冒出,在乌黑的淤泥上,形成十分美妙的图案,或水墨淋漓,或淡雅清新,浑然天成,意趣盎然。
很小的时候觉得,罱河泥就应该是乡村生活的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河流与农田。看着那一担担被挑到田里的河泥,仿佛就看到了不久之后田野里长出的绿油油的庄稼,感受到乡村生活的生生不息。而一到夏天,那系在河边的罱泥船也成了男孩子们争相乘坐的“游船”。两个人分别坐在船的头尾。一边用竹竿撑在水中,船只犁开平静的水面,在身后荡起波光粼粼的涟漪。一边趴在船沿上看着来回穿梭的小鱼和水中晃动的倒影,好像伸出手臂就能抓住那自由活动的鱼虾。看向岸边,那些焦急着等待上船玩耍的小伙伴正翘首以盼地大喊大叫着“快点上来,轮到我家咧哇!”,他们大多背着空空的草篮,急切地等待着玩上一阵后再到田间把篮子装满,玩累了换上另一拔人继续玩。那个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艘小船,一群伙伴,便是整个夏天。也是在那个时候,通过玩罱泥小船才切身体会到了罱河泥的不易,要想学会罱河泥就得先学会在小船上站稳。因为船小吃水浅,人站在上面重心很高,在水中很难掌握平衡,如果再加上手脚配合做着动作,就更加不易了。那些夏天,与小伙伴就着小船,练了多少回站立着撑船,差不多就落了多少次水,像我一样,许多人一直到离家上学谋生也都没有学会稳稳地站立着在河中的小船里撑船。
地处水乡的河塘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宽有窄,相连的、单独的,星罗棋布,极不规则,镶嵌在同样也不规则的田野和村落之间。一条河或一个水塘里的河泥罱完了,就得转移到另一条河道去罱。因此,罱泥最麻烦的事就是移船(土话称之为“拔船”),从一个水塘到另一个水塘没有河道相通,只能把船从一条河里抬出,由人工扛着经过高低不平、宽窄不一的田埂再送入另一条河道。拔船时要几个人站在河边相互配合着,使劲把船拉上岸后,再把船翻一个身,船底朝上,两个人一人一头用肩扛着,移到另一条河中。因为船只长年浸泡在水中,船体吃足了水分,妇女或体力不济者是难以堪此重担的。
每年夏天,生产队里都会对船体进行一次维修保养。把船只清洗干净后,拉出水面,抬到社场,将船底朝天搁在两条长凳上,连续晒上几个太阳,让其晒干晒透,露出腐烂和开裂的部位。需要更换的地方,则请来船匠,将腐烂的船板取下,换上新的木板。然后用桐油与石膏粉调好腻子,加麻丝搅拌成油灰。再把油灰镶嵌到已经清理干净的木缝中去,新油灰晒干后,将船身涂上两至三层桐油,待晒干后便可下水继续使用。
随着化肥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尤其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罱河泥这一农活就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那长期不进行挖河清淤的河塘也日渐变得杂草丛生、狭窄淤塞,水质越来越差,严重影响着周边的空气质量和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增大了洪涝灾害的风险,偶尔“隔靴搔痒式”的清淤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每次回村总喜欢在河塘边走走看看,当年河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鱼虾成群,垂柳轻佛的美丽景象,以及生产队里罱河泥沤肥垩田的热闹场景,犹如晨光里的剪影总会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