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书坛,鲜于枢与赵孟頫并称“双璧”,但若说赵孟頫是温润如玉的帖学典范,鲜于枢便是恣肆汪洋的性情书家。他的《张彦享行状稿卷》虽为记录友人生平的草稿,却在不经意间展露了元代文人书法最本真的精神——以笔墨为骨,以性情为魂,于方寸之间掀起狂草的风雷。
草稿里的天成妙趣:无意于佳乃佳的笔墨哲学
这卷行状稿以行草书写就,纸本上可见明显的涂改痕迹:某处姓名被墨块覆盖,某段文句旁添注小字,甚至有整行笔画因疾速运笔而出现飞白。但恰恰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作品最动人的特质。鲜于枢下笔时全然沉浸于撰写行状的情境中,笔随情动:写到张彦享生平功绩时,笔画骤然加粗,中锋行笔如斧劈刀削,“力透纸背”四字在“赈济灾民”等段落里化作具体的墨象;写到感怀处,笔锋忽转轻盈,连带的牵丝映带如流水潺潺,尤其是“呜呼哀哉”数语,枯墨与浓墨交替间,似能看见书家搁笔长叹的身影。
这种“草稿美学”暗合了中国书法“真率为上”的精髓。与赵孟頫刻意经营的精整不同,鲜于枢在此展现的是“解衣磅礴”的创作状态——比如卷中“孝友”二字,“孝”的撇画甩出锐利的锋芒,“友”的横画却顿笔成块,一放一收间,既见魏晋笔法的传承,又有元代文人“以书抒怀”的自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笔力扛鼎:鲜于枢“雄强书风”的终极诠释
鲜于枢善用硬毫长锋,在这卷作品中尤为显著。他的笔法融合了唐代张旭的狂草气势与宋代米芾的“八面出锋”,却又自成一格:起笔常以侧锋切入,随即转为中锋涩行,如“疾恶如仇”四字,“疾”字首笔侧锋如刀砍,“仇”字末笔中锋绞转如藤绕,墨色由浓至枯的渐变里,可见笔锋在宣纸上的激烈“搏斗”。这种笔法让线条兼具“骨”与“肉”——粗笔处如青铜器铸纹般厚重,细笔处似游丝飞空却韧劲十足,尤其是卷尾“尚飨”二字,枯墨扫出的飞白竟如裂帛之声,将祭奠的肃穆与悲怆凝于笔端。
字的结构亦耐玩味。他打破了唐人“平正”的结体法则,常将偏旁欹侧错位:如“彦”字上半部分左倾,下半部“彡”画却右斜取势,看似险绝却因笔势连贯而稳如泰山;“状”字的“犬”部撇捺开张如大鹏展翅,“爿”部则紧收如弦上之箭,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让整卷文字如乐曲般有了强弱起伏的节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元代文人的精神镜像:在草稿里看见时代风骨
作为元代中期的重要书家,鲜于枢的书法始终透着一股“不随流俗”的倔强。彼时赵孟頫倡导复古,书坛多趋平和秀逸,而他偏以雄强笔法对抗时风。《张彦享行状稿》虽为应用文,却暗含文人的精神密码:张彦享作为元代士人,其生平中的“刚正不阿”与鲜于枢的性格高度契合,这种情感共鸣让书法超越了技巧层面——当他写下“不畏强权”等句时,笔锋的狠厉实则是对时代不公的无声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卷中多处出现的“渴笔”(枯墨)技法,并非偶然为之。鲜于枢曾言“书法贵在用笔,用墨次之”,但在此卷中,墨色的浓淡枯润却成了情感的注脚:写到张彦享仕途坎坷时,墨色渐枯,仿佛墨汁也随文句一同哽咽;写到生平高光时刻,浓墨重彩又似豪情喷涌。这种“墨随情变”的处理,让草稿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一幅“情感心电图”。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当行状稿成为不朽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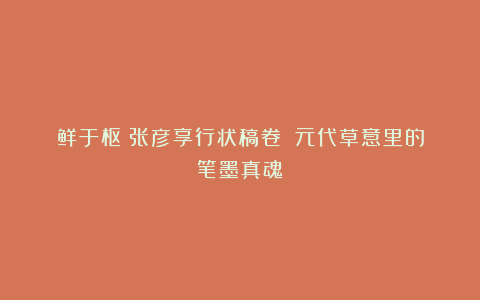
如今再看这卷纵25.5厘米、横135.2厘米的纸本墨迹(现存于某海外博物馆),其价值早已超越了记录友人生平的初衷。鲜于枢以“无意于佳”的率真,在草稿中留下了元代书法最鲜活的生命印记——它没有碑刻的庄重,没有馆阁体的拘谨,却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文人在时代洪流中坚守的笔墨尊严。对后世而言,《张彦享行状稿卷》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刻意雕琢的产物,而是当灵魂与笔墨相遇时,那一瞬间迸发出的永恒光芒。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