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记忆与无意识
作者:托马斯·福克斯
译者:张涛
……“并没有什么内在之人;人存在于世界之中,
并且只有在世界中他才认识自己。”
——梅洛–庞蒂
摘要
在传统精神分析中,无意识被理解为一种首要的内心心理现实,它隐藏在“意识之下”,只能通过以元心理学前提与概念为基础的“深度心理学”加以探知。与这种垂直式的观念相对,本文提出了一种现象学取向,将无意识理解为一种水平性的维度:身体的生存经验、所处空间以及身体间性。此取向建立在“身体记忆”的现象学之上,身体记忆被界定为:由身体所调节并在既往经验过程中沉积下来的知觉与行为的全部隐含性倾向。
属于身体记忆的,并不是以明确记忆形式保存下来的东西,而是以一种“存在的风格”(梅洛–庞蒂)而延续下去的。这样的身体性与身体间性的无意识,“……不应当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意识’背后去寻找,而应当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经验场域的结构”(梅洛–庞蒂)。无意识的固着,犹如一个人的空间潜能上的限制,它是由隐含于当下并抗拒生命前行的过去所造成的,尤其是创伤性经验。它们的痕迹并非隐藏在某个内在心理世界中,而是——如同图像与背景的关系那样——以“盲点”或“空白”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
它们表现为:反复跌入其中的行为模式;不自觉地回避的行动;或是生命所给予的机会,却既不敢把握,甚至不敢看见。由此,身体记忆的无意识便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不存在被遗忘或被压抑的经验,另一方面却在身体性与身体间性的当下空间和日常生活中保持其在场。
1 引言:精神分析与现象学
精神分析与现象学,这两种大约在同一时期兴起的理论,都自视为关于主体性的基础科学,但却始终彼此陌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它们对于意识的角色持有根本对立的看法。对精神分析而言,意识不过是一层闪烁的涂层,掩盖着深不可测的心理力量与过程,而这些才是真正有效的。相反,对现象学而言,意识则是媒介或光照,一切现象正是通过它才得以显现和呈现。
因此,可以尖锐地说,意识在二者中分别被视为**虚饰(Schein)或显现(Erscheinung)**的领域。相应地,它们对于无意识的理解也对立:或者无意识被视为心理生命的真正源泉,一种隐秘的意义结构与驱动力,甚至以种种编码的方式与主体的意识意图相对抗地显现出来;或者无意识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隐含的意识,这种意识始终处于可能被显现或反思的状态,并且无论如何,不可能从根本上异于主体自身。正如胡塞尔所言:
“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即在我的经验、想象、思考、行动中没有作为被感知、被记忆、被思考之物呈现给我的东西,它不会‘影响’我的心灵。而不在我经验中的事物,不论是被忽略还是被隐含地、意向性地排除掉的,甚至在无意识中也不会对我构成动机。”(胡塞尔 1952, 231)
这两种观点似乎几乎无法调和。然而,尽管它们看起来对立,但若进一步分析,精神分析与现象学事实上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笛卡尔关于意识的观念——把意识视为“清晰而分明的知觉”,也就是假设意识在涉及自身内容时对自己是透明的。对胡塞尔而言,“我思”就是当下的证据,是观察意识中一切内容的必要“伴现”;若没有这一点,一切内容便会融化或逃逸,坠入过去或未来的不真实之中。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意识可能性,都必须依附在这个显现的当下,否则便会解体。
但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看法其实也差别不大:意识只是“……当下出现在我们意识中并且被我们所感知的观念”(弗洛伊德 1943, 29)。因此,如同古典思想中所理解的那样,意识被视为当下观念或表象的场所;而无意识则被理解为容纳所有那些此刻不在场观念的空间。弗洛伊德拒绝承认一种暧昧的“既知又不知”的意识,他说:“……一种对其一无所知的意识,在我看来比起一种心理的无意识更为荒谬得多”(弗洛伊德 1940b, 243)。意识必须对自己透明,否则它根本就不是意识。
由此,精神分析虽然反抗古典意识哲学,但不仅未能超越它,反而在无意识中采纳了它的前提而不自觉。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当今神经生物学与古典哲学的冲突中:神经生物学认为必须推翻的那个主权的、自主的意识主体,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二元论的建构。这个主体与身体和生命分离,被限制在当下的“心理状态”中,因而变得无身、无力,容易成为神经生物学还原论的猎物;此时,无意识作为真正有力的基质的角色,便被物质性的脑所取代。这样一来,主观性便面临被自然化的威胁,而这种实体化的效应甚至可能比弗洛伊德把人解释为“自然人”(homo natura)的做法更严重——这一点早已为宾斯万格(1957)所批评。
然而,现象学逐渐突显出来的主体的身体性维度,其实本也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不仅将自我的起源归于身体。身体在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该理论设想了一种逐步展开的局部驱力的发展,而这些驱力受制于身体的某些部位,其“命运”会持续影响个体的成长。然而,尽管如此,身心二元论还是深刻影响了精神分析理论。对弗洛伊德而言,驱力在最终分析中并不是活生生的身体现象,而是客观的躯体数量;而这些驱力的表象,也不属于主体的情欲之身,而是已经归入心理的内部、隐匿的装置之中。在那里,驱力的派生物与驱力能量彼此转化,并分配到心理的不同层次——这个装置只能通过外部迹象(例如身体语言或言语)来解码。最终,身体仅仅作为符号或想象意义的所在而引人兴趣,充其量不过是心理的一个原初投射场,总是需要被剖析其潜藏的意义。而在二元论的范式下,精神现象同时也是身体现象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心理装置”这一概念的提出——它无疑可追溯到弗洛伊德早期的脑理论——一种实体也被建立起来:它作为一个内在的容器,用于储存外在现实的图像与记忆。这些内容以内摄的“客体表象”“意象”(imagos)等形式存在,充斥在心理的不同区室中,并在驱力能量的推动下获得了某种自主的生命。如此一来,自我与这些区室中的重要部分之间保持着一种彻底的隔绝: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拓扑学式的、动态的无意识,与前意识作为潜在的、隐含的“先前已知”内容有着根本区别(弗洛伊德 1940c, 77f.)。在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着压抑的经济性机制;而被压抑的东西与压抑机制本身——即压抑的动机——则都逃逸于意识之外。
作为这一理论的证据,弗洛伊德可以指向一些现象:身体症状或弗洛伊德式的口误,它们对于自我而言显得陌生或毫无意义;又如显梦内容与潜梦内容之间的差异,这被归因于一个无意识的审查者;最后,还有病人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的抗拒,即对意识化被压抑内容的抵抗。
然而,这种对无意识的彻底分离,是以付出代价为前提的:无意识不得不被置于一种暧昧的位置,徘徊在主观经验与客观过程之间(Waldenfels 2002, 294)。实际上,在最终分析中,它还是被归入心理装置的客观性之中。弗洛伊德试图解决他自己发现的悖论,即“人既知道某物,同时又不知道它”,或者说“眼睛看见了,却依然是盲的”(弗洛伊德 1957, 175 注)。他的解决方式是将心理分裂为两个部分。结果,无意识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异国”(弗洛伊德 1940c, 62),换句话说,是自我内部的某种外在之物,它的意义与效应对于主体而言是陌生的。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仅需要牢记胡塞尔对于“完全异于主体的动机”的批评;还必须进一步追问:如果某种意义既在起源上也在潜伏状态中并非始终就是主体自己的意义,那么,主体又如何可能重新据为己有?在这种前提下,精神分析治疗也就只能传达一些关于个体内心机制的理性洞见,而无法促成真正的人格整合。其目标——“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当为之”——最终只能停留在显性的知识层面,而非真正的自我把握。
现象学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则沿着不同路径展开:
1萨特认为,无意识并不是一种来自外部对主体的限制,而是主体与自身之间的基本关系方式,即自欺(mauvaise foi,恶意信仰)(萨特 1962, 91ff.)。主体对自己采取一种暧昧的关系,允许自己陷入一种“意向性的疏忽”:人既不知道某物,又不愿知道它;既不看见某物,又不愿看见它;如此一来,主体就同时成为了受骗者与欺骗者。
2伯内(Bernet 1997)则指出,在胡塞尔对图像感知、再生意识、记忆,尤其是想象的分析中,可以找到一种类似的双重意识形式:这些意识形态在每一处都包含着在场与不在场的二重性,因此自我同时栖居于两个世界之中。由此,它们也可以作为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典型范式。
3另一种克服意识与无意识二元对立的方式,可以说是垂直地扩展主体性的空间,使其能够涵盖驱力与冲动等现象,作为主体性的一个基本层面。这种将弗洛伊德元心理学术语重新诠释为生命的基本活动、并认为其总是先于自我意识经验的思路,部分上被马克斯·舍勒(1983)采用,后来更主要地由米歇尔·亨利(1992)发展。
4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从梅洛–庞蒂所理解的身体的暧昧性出发,将主体性向水平的维度扩展,并在身体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以及在个人的生存空间结构中遇见无意识。身体记忆在此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把个体的身体性与跨身体性的经验转化为隐含的有效倾向,为日常生活提供主要是无意识的基础。
–以下我将沿着这一路径展开(但并不否认前述的其他可能性)。因此问题在于:无意识是否可以定位在一个人所生活的关系与行为之中——换言之,在身体的水平维度与跨身体性之中?这样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弗洛伊德无意识的要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首先要发展身体记忆的概念以及它所构成的关系场,然后再考察这一场域的结构,在那里,无意识或许能够“栖居”。
2 身体记忆
如果依循梅洛–庞蒂的观点,把身体看作的不只是可见的、可触的、可感的物理身体,而是首先作为我们看、触、感的能力,那么,身体记忆便指称了这些身体倾向在我们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整体——换句话说,是它们的历史维度。在身体记忆中,过去所经历的情境与行为似乎被融合在一起,而没有哪一个单独突出。通过经验的重复与叠加,一种习惯性的结构被形成:熟练的动作序列、反复感知到的格式塔、行动与互动的形式,都成为了一种隐性的身体知识与技巧。身体记忆并不会把人带回过去,而是使过去在当下隐含地发挥效力。这一思路与当代记忆研究的结果相契合:内隐记忆在我们的习惯性行为和无意识的行动回避中具有核心意义(Schacter 1999;Fuchs 2000c)。
因此,身体是一个由机体发展而来的整体,包含感知、行动、欲求与交流的能力。它的经验被锚定在身体记忆之中,如同一张无形的网络覆盖环境,把我们与事物和他人连接起来。正如梅洛–庞蒂所写:“身体是我们‘采取姿态’的永久手段,从而建构出虚拟的现在”,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下实现我们的过去,并由此让我们在情境中感到自在(Merleau-Ponty 1962, 181)。更进一步,在身体经验的结构中,他者始终已经被包含在内——他者在表达中被理解,在欲求中被意向化。在我能够反思自己通过手势或言语所传达的东西之前,我的身体早已创造出一种与他者同在的感觉;它通过姿态与手势来表达,同时对他人的印象作出回应。这种“跨身体性”(Merleau-Ponty 2003, 256)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主体间的系统,从童年开始,身体互动的形式就在其中被建立并不断更新。它包含自我与他人,意识与无意识:“我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他人,我在自己的经验中就找到他们,他们居住在那些我看不见但他们却能看见的隐秘角落”(Merleau-Ponty 1974, 166)。
3 身体记忆与生活空间
身体记忆——如同身体图式一样——因此并不仅仅构成一个局限于物理身体的内部系统。相反,它形成了一个感知–运动、情感与互动的场域,作为具身之人,我们不断在其中运动与行动。在这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1969)的场论心理学术语,尤其是生活空间(life space)的概念,显得特别适用。为了将其与身体记忆的结构联系起来,下面我将作简要的阐述。
生命空间以个体及其身体为中心。根据勒温的观点,它的特征在于经验性的属性,如亲近或疏远、狭窄或宽广、联结或分离、可及或难以接近,并且它由提供对运动的阻力的物理或象征性边界所结构化。由此产生出或清晰或模糊的区域,例如自身身体周围的近身空间、被占有的领地(财产、家庭)、某人所散发出的影响范围,但也包括被禁止或带有禁忌的地带。生活空间还被具体的“场力”或“向量”所渗透,首要的是那些吸引或排斥的力量。生活空间中彼此竞争的吸引力或排斥力导致了典型的冲突,例如吸引与排斥的对立,或吸引与吸引之间的冲突等。这些可以被视为处于某种境况中的人所面临的相互冲突的运动方向或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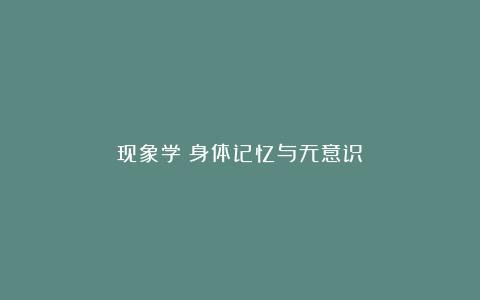
一个关于场力冲突的很好例子是小孩在与母亲的依恋和对世界的好奇之间摇摆不定的情境(参见 Stern 1991, 101)。母亲首先是“安全的港湾”,是重心所在,她使孩子的生活空间弯曲,以至于孩子始终停留在她的身边。空间因而呈现出梯度:孩子离母亲越远,空间就变得越空旷、越孤单。尽管在陌生人周围空间会再次凝缩,但孩子宁可绕道而行:在他们附近的空间曲率是“负性的”。随着时间推移,孩子的探索冲动和环境的吸引逐渐松开孩子与母亲的联系,使得孩子能够逆着梯度增加与母亲的距离——直到这种联系被拉得太紧,孩子最终又跑回母亲怀中。——这个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相应的场结构是如何建立在身体记忆上的,本例中就是孩子与母亲亲近与联结的经验史。另一句谚语“狗咬过一次就怕棍子”则说明了身体记忆的厌恶效应。第三个例子是禁令区域,它们限制了孩子能够移动的方向,使得孩子的自发冲动与父母的命令相冲突,因为这些命令在孩子的生活空间中留下了负面的痕迹。
因此,生活空间——依照一个人相应的经验、能力和动机——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重要性或价性。类似于物理场,在其中可能出现“引力效应”、不可见的“空间曲率”或屏障,这些会限制或阻止自发性的行动。特别是在精神病理学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生活空间的变形,例如强迫症患者的禁忌区域和恐惧症患者的回避区域,这些都基于某些存留于身体记忆中的过往经验。
4 无意识的现象学
借此,我勾勒了一种能够以不同方式提出和回答无意识问题的路径与术语。
如果我们拒绝将无意识理解为超越意识的一个拓扑式结构——即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内在过程,从外部作用于经验主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问:无意识是否可以被视为另一种经验方式,它在生活之身与生活空间的水平维度中表现出来?其范例便是身体自身的歧义:身体在看见的同时始终保持不可见,而我往往对它的倾向一无所知,实际上,它以外在之物的形式来迎面而来,即吸引或排斥的对象、充满诱惑的特质以及我环境的场结构。这样的无意识便如梅洛–庞蒂所写:“……它并非存在于‘意识’背后我们内在最深处,而是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场域的结构”(Merleau-Ponty 1986, 233)。它是我们经验与行为未被觉知的背面,或者说是其他、隐秘的意义。
作为起点,让我们先考虑被压抑愿望的场结构。在短篇小说《酒鬼与柏林的钟声》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讲述了一个酒鬼士兵的故事:他在反复的训诫与惩罚后决心戒酒,但仅三天后便再次酩酊大醉。当被问及为何在立下良好决心后仍复饮时,士兵辩解说这是魔鬼的手笔,因为他在城中漫步时突然在钟声中听到了各种烈酒的名字——例如在市政厅钟声里听到“葛缪!葛缪!”,在大教堂钟声里听到“橙酒!橙酒!”等等。最终,他无法抵抗这些阴险的声音。——这个幽默的例子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被意志压制而非被真正压抑的愿望,但它很好地说明了相反的身体冲动或驱力如何以间接的方式从外部得到满足。经验场可以说被压制的愿望所渗透,最终在某些知觉上结晶——这些知觉必须足够模糊,同时又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在这个例子里就是钟声。模糊或暧昧之处正是潜在或隐秘意义成形的位置。未被满足的冲动或愿望以迂回和外在的方式突破,由此我们便能够辨认出移置的机制。真正渴望的东西通过某个相似物得以满足。
表达性主题和非主题意义方向的类似干扰也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弗洛伊德口误”中。弗洛伊德本人指出:“……口误是两种互相干扰的不同意图的结果,其中一种可称为被干扰意图,另一种则为干扰意图”(Freud 1940a, 56)。误听最类似于克莱斯特士兵的例子:潜在渴望的意义会从类似的声响序列中被“解读”出来。在口语、书写以及物品(错误)摆放中的错误中,另一种意图干扰了明确意图的行为,使得“右手——字面意义上——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最后,在遗忘中,原本产生但令人不快的意图被抹去,并被其他意图所替代,例如日常惯例行为。因此,在自发发生的身体感知或动作中,相关的潜在意图会突破表层——以一种逆向或交错(chiasm)的方式,这在语言上通过前缀“mis-”体现出来。
口误的制造者可能会立刻或稍作思考后意识到其意义,并归因于自身;或者他会觉得这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与自己无关。例如,弗洛伊德关于“说错话”写道:
如果后来我们将其[导致口误的意图]呈现给说话者,他可能承认这是熟悉的东西,因此它只是暂时的无意识,或者他可能否认它属于自己,这意味着它是永久的无意识(Freud 1940c, 77)。
正是在这种差异上,弗洛伊德建立了前意识与真正动态无意识之间的严格区分,后者被“生命力”排除或压抑在意识之外(Freud 1943, 436)。防御机制及对应的对潜在意义的抵抗,其前提显然是抑制趋势及其动机本身被排除在意识之外。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证明为动态无意识建立一个特殊的心理内在空间。反对这一点的观点在于,上文弗洛伊德引用中只是暂时无意识与永久无意识之间的渐进差异。毕竟,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意图的二重性,在第二种情况下仅仅附加了额外的压抑倾向。但如果我们不把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生命力”归于意识之外的心理机制,而是将其视为场力,那么我们很容易在身体或生活空间中找到其模型。
最先想到的例子是:受伤后自发采取的保护姿势——自然地避免将受伤的肢体暴露于危险物体中,而无需真正考虑事件。回避行为因此被纳入隐性身体记忆中。此外,我已经提到儿童面临的禁令区,当儿童“自发”遵守时,负向场力会阻止其接近。更接近动态无意识的,是禁忌区或禁忌物。与禁止不同,禁忌具有特殊结构和效果:它不是明文规定,而是通过他人的回避行为产生,就像共享生活空间中围绕禁区的负向曲率。禁忌最有效的情况是社区成员对此并不自知。违反禁忌不一定会受到公开惩罚,但会自动在违法者身上产生羞耻、内疚或厌恶感,并被他人的轻蔑与排斥性沉默所强化。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经验与行为都受负向——即“排斥性”——场力的无意识影响,因为主体(如“被咬的人”)逐渐避免了潜在冲突。回避已成为隐性、身体化的行为模式,从而使环境中潜在的威胁不再被意识所感知。然而,排斥力并未以外来形式显现于意识,而是以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他性显现。它们与经验场共延伸,但作为其负面。生活空间中越过屏障时产生的明显恐惧、内疚或羞耻感,早在潜意识中已存在,为这些屏障赋予了情感负载。
就像口误的例子一样,动态无意识对自身被意识化会产生抵抗。这种抵抗本身既非意识,也非前意识,但因此并非完全在意识之外。它更像是一种意识本身的歧义或二重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体碰到隐藏意义的表现,她至少会隐约意识到它在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即关于她自身的他性。梅洛–庞蒂写道,无意识“……不能成为‘第三人称’的过程,因为它自己选择何者被纳入官方存在,它绕过我们抗拒的思想与情境,因此不是不知,而是不愿容忍的未被承认、未被表述的知识。在语言仍不精确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正是在此发现了他人更正确称之为的歧义感知”(Merleau-Ponty 2003, 79)。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防御机制——投射——来理解这种意识的歧义。在投射中,自己眼中的梁木变成他人眼中的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冲动和动机,正是自己曾构筑防御去抵御的冲动和动机。当然,这种感知也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对他人冲动的过度否定,其能量恰恰来自于个体为了中和自身冲动所付出的努力。自我意识的盲点——在这里弗洛伊德无疑是正确的——并非单纯的“忽视”,而是源于积极且情绪充沛的压抑。然而,这种压抑仍然是主体自身的努力和行为,而非外在机制的作用。
5 创伤与重复性
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现象,即情绪创伤的无意识效应,这一现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进行了阐释。他写道,被压抑的东西如同截肢者的幽灵肢体,因为身体的某种能力仍然存在于主体之中,但与当前现实不再相符。习惯化的身体与当下的身体发生冲突。同样,压抑也在当前主体性中创造了一个空隙(Merleau-Ponty 1962, 87),仿佛未处理的经验所留下的负面效应在每一个新情境之前悄然介入,从而将受创者囚禁在仍然存在的过去中。
(这类固着)不会融入记忆;它甚至排斥记忆,因为后者在我们眼前展开,如同图像,一段过去的经验,而这一真正的当下[创伤,T.F.]不会离开我们,而是始终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后,而非呈现在眼前。创伤经验并不以客观意识模式或“有日期”的瞬间作为表征而存续;它的本质是仅以存在的方式并以一定的普遍性存续(ibid., 83)。
这一描述将被压抑的创伤归入身体记忆:身体记忆承载了那些“看不见”的隐秘内容,并在一种总体存在方式中持续存在,而非作为明确的记忆。伤害已经渗入主体的身体,并留下了持久的反应性,即随时准备进行自我防御。受创者对与创伤相似的威胁性或羞辱性情境变得高度敏感,即便这种相似性并未被意识到,并会设法规避这些情境。
“这种抵抗针对某一特定经验领域、某一类记忆或某一类型的记忆”(ibid., 194)。
尽管如此,受害者在每一步仍可能遇到触发创伤的因素。往往会形成一种永久性倾向,每当门铃响起,或感到被陌生人跟踪或观察时,就会产生恐惧和紧张的反应。
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自犹太作家阿哈隆·阿佩尔费尔德的回忆录,他从七岁到十三岁,在乌克兰的树林中度过二战时期的隐藏生活:
“二战结束已逾五十年。我忘记了很多,尤其是地点、日期和人名,但我仍能在全身感受那段时光。每当下雨、寒冷或风暴,我就回到隔都、集中营或我长时间隐藏的森林。记忆显然在身体中有深深的根。”
“那时发生的一切已在我身体的细胞中留下印记,而不是在我的记忆中。身体的细胞似乎比记忆记得得更清楚。战后多年,我从不走在街道或小径中央,总是靠近墙壁,总是在阴影中,总是匆忙如同逃亡的人……有时仅闻到食物的气味、鞋里的湿气或突如其来的响声,就会将我带回战争时期……战争在我全身骨骼中。”
“……手、脚、背和膝盖知道的比我的记忆更多。如果我能深入其中,画面会一下子涌现出来”(Appelfeld 2005, 57, 95 f., 8 f.)。
这里影响的不仅是某一特定事件,而是他整段人生经历对身体的深远和持久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比自传记忆更为深刻:本体感知、触觉、嗅觉、听觉,甚至某些天气状况,都可能突然使过去重新鲜活;甚至身体动作模式,如贴墙行走的被追逐者动作,仍然模仿逃亡者的行为。
因此,创伤对个体的影响可以被理解为两方面:首先,它表现为其生活空间的特定变形,这种变形对应于个体对引发焦虑或“排斥区”的无意识回避行为。在这些区域周围,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负曲率,从而阻碍了生命运动的自由发展。其次,生活空间中充满了与创伤相似的元素,使创伤从外部不断接近受创者,从而无法避免。因为在个体的态度、姿势和感知倾向中,创伤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入她的世界。
精神分析中的重复强迫概念正是与此相关。这一概念基于临床经验,即患者即使在意识层面试图避免,仍会被吸引进入相同、通常是有害的行为或关系模式。在这些区域周围,她的生活空间可以说呈“正曲率”,换言之,这些区域对她施加了一种不自觉的吸引。例如,如果一个人的早期经历以虐待和暴力关系为特征,这些经历也会决定她后来的关系模式。虐待类型可能各异,但存储于身体记忆中的隐性行为模式会促使她重现熟悉的关系类型。这些今天被称为无意识实施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看来是移情的一种形式。他写道:
“…在分析中,我们必须说,分析者对那些被遗忘和压抑的内容完全没有记忆,但他会将其表现出来。他不是以记忆的形式再现,而是以行为的形式重复,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重复。例如,分析者不会说自己记得曾对父母的权威表示反抗和怀疑,但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医生”(Freud 1946, 129)。
人际关系的无意识前史通过身体间记忆得以重现。然而,这意味着无意识不再是心理内部的隐秘空间,而是交织在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身体行为中,作为一个对她本人隐藏、但对他人可见的亚结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始终隐性地指向他人。意识中心的“盲点”也可被视为人际关系的另一面,我们自身与他人在一起的存在必然对我们保持隐藏,因此自我黑暗的一面只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被照亮。正如梅洛–庞蒂所言,在我的世界中,他们存在于“……那些包含对我隐藏但对他们可见之物的角落里”(Merleau-Ponty 1974, 166)。
6 总结
从生活身体的现象学角度来看,无意识并非存在于“意识之下”的心理内部实在。它环绕并渗透着意识生活,就像画谜中隐藏在背景的形象环绕前景一样,也如生活身体在运作中自身隐藏。无意识并非位于心理的垂直维度,而存在于生活空间的水平维度,主要寄居于与他人交往的身体间性之中,作为日常生活的隐藏反面。它并不位于个体内部,而存在于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中。
无意识的固着如同潜在过去在个体潜能空间中产生的某些限制,这些过去隐性但始终存在,拒绝参与生命的持续发展。然而,这些痕迹并不隐藏于内在心理世界,而是以生活空间中的“盲点”、“空隙”或曲率的形式显现:在言语和行为的“失误”中;在个体反复陷入的关系模式中;在无意识回避的行为中;在未进入的空间、未抓住的人生机会中,甚至是那些不敢面对的机会中。这些痕迹可被视作“负像”,以抑制或遗漏的形式体现出个体特性。它们也可以通过神经症或身心症状在象征上或物理上呈现。在这种程度上,症状既非毫无意义,也非习惯缺陷——如学习理论所假设的——其意义也不在无意识内部的心理空间之外。相反,它存在于身体间的表达中,换言之,它源于症状在互动场域中的意义,即使这些意义并不显而易见,也需要被理解和阐释。
因此,无意识是在场中的缺席,是被感知中的未被感知(Merleau-Ponty 1986, 308 f.)。如同形象掩盖了它所凸显的背景一样,意识、知觉与语言也遮蔽了无意识的反面——那些未被感知与沉默,它们始终与意识紧密相连。然而,这一反面并非完全隐藏,而是在逆转、交叉纠缠以及意识的模糊性中得以表达:人既不知某事,也不想知道;既不见某物,也不想见——换言之,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它。意识对自身并非完全透明,因为它自我隐藏了自身。
这种意识的双重性对应于身体的模糊性,其显现方式在主题化与非主题化、**物理身体(Körper)与生活身体(Leib)**之间波动。同时,它也对应于我们存在本身的矛盾性与易冲突性:作为自然的、有身体的存在,我们总是会面临自身本能与自然属性。这构成了我们自我关系的矛盾性,或者用Plessner的话说,是“偏心性”(eccentricity):自发性与反思性、身体与灵魂、自然与教养、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持续冲突。可以说,弗洛伊德即便怀有怀疑精神,也未必完全理解人类,他试图减轻人类意识中这种固有的冲突,将对立意志置于无意识的独立空间,从而将这一意志从主体的责任中抽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