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舆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各·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而构成“舆论”(Opinion Pbulique)一词,用以表达人民对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舆论”一词的起源。迄今为止,西方语源和语境中的“舆论”,其主体本身有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所谓“公众”都具有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即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意识和相应的意见表达能力。离开这一点,舆论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公众意见。中国当代的“舆论”定义众说纷纭,但总体上说与西方的“舆论”定义并无二致。
然而,由于19世纪晚叶和20世纪初叶中国学人引入“舆论”概念时径直借用了本土古籍中的“舆论”一词,却没有就两者的异同做出严格的界定和语源探索,从而导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舆论”概念的使用也比较随意。尤其是一旦进入中国古代舆论史研究领域,“舆论”一词所指称的意见主体是否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意识显得颇为含混,从而对中国古代舆论的发达程度产生了过低的评判。所以,意欲进行中国古代舆论史研究就必须首先从语源学角度对“舆论”加以稽考和界说,这对于认识和估价古代社会的“舆论”作为君主制和君主专制下一种社会批判力量而存在的基本意义是有益的。本文所考察的先秦“舆”和“舆人”,恰为中国“舆论”概念的语源之一。
中国古代史籍中开始固定使用“舆论”概念是在三国时期。魏晋时人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记载,王朗给魏文帝曹丕上疏讨论孙权遣子为质之事时说:
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很,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
王朗是魏国的重臣,文帝时担任御史大夫和司空等要职。他的上疏是劝诫文帝发布圣旨要避免因舆论不畅而造成严重后果,担心得不到“舆论”的支持。这里,“舆人未畅圣旨”和“舆论之未畅”是同义而异词的两种表述。毫无疑问,“舆”、“论”二字直接组合实际是将“舆论”的主体规定为“舆人”。
《梁书·武帝纪》似也使用了“舆论”一词,萧衍在南朝齐做丞相时上表于和帝,言曰:
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屦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崖涘,造请自息。
这里的“余论”恐系“舆论”的误写,结合下文“庶人识崖涘”云云,其意义也是指平民庶众的议论、意见,“余(舆)论”的主体是“庶人”。
《晋书·王沉传》载,王沉出任豫州刺史时曾贴出告示征求政治改革意见说:
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
在王沉看来,古代贤圣所听“舆人之论”、“诽谤之言”就是下层民意的反映,刍荛、负薪之徒指代的就是下层平民。可见,这里的“舆人之论”和同时代“舆论”一词相当。
上述材料表明,魏晋时期“舆论”一词在最初的使用上是和“舆人”、“庶人”等主体相关联的,“舆论”当为“舆人之论”的简化,而“舆人”和“庶人”可以相互替代,大体上指代下层的平民百姓。
如果进一步追溯到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数见的“舆人(之)诵”则可与“舆论”一词相对应。《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子产执政后受到“舆人”两次不同的诵诗评议: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与《昭公四年》所载“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正相发明,证明春秋时期“国人”和“舆人”的含义有相近性。又《国语·楚语上》载,楚国大夫子张劝谏灵王曰:
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轸诸侯,不敢淫逸,心类德音,以德有国。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周诗有之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
子张把齐桓公和晋文公重视“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的行为称为具有君主自觉的“德政”。显然,谏、谤、诵都是发表意见、评论和批评的行为,主要是言论行为,从而和君主的意志形成一种张力,而且“以言取罪”的人并没有社会阶层和身份的区别。但是,子张特意引用《诗经·小雅·节南山》的诗句,大体是将“庶民”和“舆人”对等起来了,可见“舆人诵”也就是下层平民庶众的讽谏。
总之,魏晋“舆论”概念确当源自先秦“舆人(之)诵”,两者特指下层平民庶众的意见和呼声,但“舆人之诵”只是诸种讽诵、谏诤之“言”的一种,还没有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舆论”。这和西方的“舆论”(Opinion Pbulique)概念的主体区别明显。
魏晋“舆论”源自先秦“舆人之诵”,本无疑义,但是学界在先秦时期“舆人”的阶层、等级归属上还存在着争议。换言之,“舆人(之)诵”究竟是先秦贵族政治的一环,还是原始氏族民主的孑遗,成为讨论“舆论”语源内涵的关键,有进一步予以考论的必要。
“舆”字起源甚早,据《古文字类编》和《甲骨文编》所录,甲骨卜辞中即已两见。按照董作宾先生的分期,两个“舆”的字形都属于殷墟一期,即商王武丁时期。《说文解字》说:“车,轮舆之总名也。舆,车舆也。从车,舁声。”又:“舁,共举也。”罗振玉认为“舆”字“像众手造车之形”,显系从车、舁两字合体造型的角度来考释“舆”的造字本义。考古发现可证殷墟时期马车制造技术已经成熟,传世文献所载武王伐商之时马车已经应用于战争。可见,甲骨文“舆”的造字是和“车舆”制造技术的成熟直接相关的。
在先秦文献中,用及“舆”字(包括“舆人”)的,除《左传》、《国语》外,《诗经》有二例,《周礼》有五例,《易经》有五例,《论语》有二例,《老子》有三例,《墨子》有一例,《庄子》有四例,《孟子》有十例,《荀子》有十五例,《韩非子》有九例,《晏子春秋》有二例,《商君书》有二例,《战国策》有七例,《逸周书》有四例。“舆”字用例,其词义一是确指在车的整体结构中供人乘坐的箱体部分,或者说是车床部分,如《论语·卫灵公》:“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二是以局部代表整体,指车乘,如《诗经·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荀子·大略》即作“我出我舆,于彼牧矣。”又如《论语·微子》“执舆者”,《荀子·劝学》:“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都是这样以“舆”代“车”。
东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有云:“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舆”是指木工中制作车厢的那个工种,这也是由其本义演变而来的。《孟子·尽心下》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舆”和“梓”、“匠”、“轮”一样,指那些持有专门技艺的工匠。这种由指称工种的概念向指称工匠的概念演化是很自然的。《考工记》又云:“舆人为车”,依《周礼》职官称“人”的体例可知,“舆人”为主持车舆制造、管理制舆工匠的低级职官名称,已经与“攻木之工”中的“舆”不同。这说明先秦时代和“舆”有关的概念都应当是与其造字本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的,换言之,“舆人”概念的形成是和“造车”这一职事密切相关的。
但是,汉晋以来学者多将《左传》、《国语》中的“舆”或“舆人”训释为“众”或“众人”。例如《国语》“舆人诵”韦昭注:“舆,众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舆人之谋”杜预注:“舆,众也。”殷商甲骨文的“众”、“众人”多指庶众、族众,其身份是平民,韦、杜的训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舆”的字义,显得颇为含糊。《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人过析,限入而系舆人”,当代学者杨伯峻注曰:“舆人,众人也。或为士兵,或为役卒。”似是从人数众多的角度来训释,并没有就“舆人”的社会等级和身份给出明确的意见。
《左传》、《国语》所载至晚不超出春秋时期,其中将“舆”和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联系起来的概念计有“舆帅”、“七舆大夫”、“舆司马”、“舆尉”、“舆臣”、“舆人”和“舆”数种。前四个称谓指代的人都是和主持管理军队车辆的较高军职,殆无疑义。而“舆”、“舆人”和“舆臣”所指是否相同,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则很值得讨论。
从西周至春秋是一个等级社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贵族统治阶层,庶人、工、商等等则为平民被统治阶层。《左传·桓公二年》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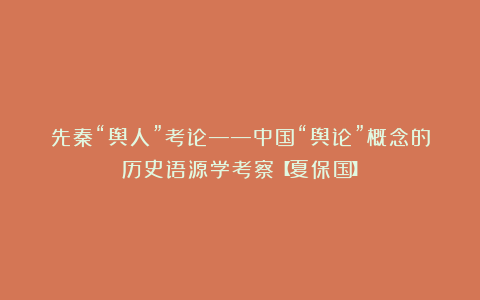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襄公十四年》亦云:
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两则文献虽然没有明确显示出奴隶阶层,而按照其他文献记载,奴隶被称做“罪隶”、“四夷之隶”、“奚隶”、“胥靡”等等,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皂、隶、牧、圉究竟是属于庶人、工、商还是奴隶,是问题的关键。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国大夫无宇在捉拿逃入王宫的“阍”时曾有一段说辞:“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据此,他理直气壮地认为手下的“逃臣”必须交由其主上,并且暗示如果楚王不允,就和商纣一样成了“天下逋逃主”。结合上下文来看,无宇言论的主旨十分明确,他所谓“十等人”,士以上的是贵族,士以下的是贵族封邑、家族内庶众、奴仆。只不过,他是从家族内的主仆关系推衍到国家的君臣关系的,甚至以圉马、牧牛来比喻的核心是强调主从、主仆关系,看不出他要说明这些庶众和奴仆的社会身份。
《左传·昭公三年》提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杜注:“皂隶,贱官。”既然是贱官,就绝非奴隶,而只能是接近“庶人”的社会阶层。晚清学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也曾辨正说:“皂者,《赵策》所云’不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非今皂役也。士则卫士之长,舆则众也,谓卫士无爵又无员额者。”可见,“舆”是大夫、士家族之内的庶众。无独有偶,《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载:“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舆臣和使曹显然和上述皂、隶一样,泛指大夫的家族庶众、臣仆。如果联系驱逐绞的行为来看,这里的“舆臣”和“舆人”并无二致。所以,黄中业先生考证认为包括“舆”在内的皂、隶、牧、圉都属于平民阶层是正确的。然而,晁福林先生在以这两则材料解释舆人并非奴隶的同时,又用相同的材料来提示“舆人”和单称“舆”者的区别:“春秋时期……’舆’已经明显地归于奴仆之列,所以有’舆臣’之称”,颇有自相矛盾之嫌。
实际上,西周到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的家臣、奴仆是以本家族的庶众来充当的,甚至还有高级家臣本身也为贵族,如《左传·昭公八年》载,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顾炎武《日知录》曰:“舆嬖,嬖大夫也。言舆者,掌君之乘,如晋七舆大夫之类。”从大夫的角度来说,掌管家族事务是贰宗,从士的角度来说,承担家族职事的是隶子弟。《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谓“分亲”、“亲昵”都是讨论家族亲缘关系中的主从关系,并据此划定社会关系的大格局。而被称作“罪隶”、“四夷之隶”、“奚隶”、“胥靡”的奴隶根本不在家族关系之内来讨论。所以,从上述“舆”、“舆臣”、“使曹”以及皂、隶、牧、圉担任一定官府职事和贵族家臣、奴仆职责来看,就是承担杂役的人。如果放入社会阶层的等级系列中就只能归属于“庶人”阶层,即“庶人在官者”。即便一国君主身边,也一样存在这样的高级家奴。另如《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子产是郑国执政,里析是郑国大夫,迁柩完全是公事,“舆”的职事与驾车运送的官差杂役有关。《孟子·万章下》:“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往役,义也。”说的就是这种承担杂役的人。由此可知,无宇所说的“十等人”并不是对当时社会阶层和等级地位的科学系统的划分。
“舆人”在《左传》、《国语》中习见,我们认为春秋时期“舆人”和单称“舆”者相当。从上面所引《左传·襄公三十年》的“舆人之诵”的内容上看,舆人有自己的田畴、财产和家族组织;若再结合“子产不毁乡校”的事迹,“舆人”议论执政大夫即当与乡校里的“国人”之谤相类。总之,从职事来看,“舆人”有与军职有关的,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伐鄀……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又《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由此显见,“舆人”不仅参与战争,承担的职事似能有机会贴近晋侯,以致发表“舆人之谋”。有与力役相关的,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自言“臣小人也”,可见也是役卒之类。有与运输相关的,如《左传·昭公四年》讲到“藏冰”事:“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杜预注曰:“舆、隶皆贱官。”如此则可断言,“舆人”、“舆”、“舆臣”社会身份和地位基本一致,看不出三者有什么明显差别。童书业先生认为春秋时期“舆人”是“国人”中从征从役者,可有田地,且可有“衣冠”,并能有教育之“子弟”,应当没有大问题。
上文已经提到在“子产不毁乡校”的史载之中,“舆人之诵”与“国人”之谤相类,实则先秦文献中常见“国人”之称,是一个有着特定政治含义的概念。西周以迄春秋,在贵族政治或大或小的活动中几乎都有国人的参与,贵族政治的决策、施政也就摆脱不了国人的影响。一般地说,国人在贵族的政治中既是维持“国脉”的“卫士”,又是主持“正义”的化身,政治气候的“阴晴”可从国人的舆论褒贬中反映出来。
西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都邑,其中能够称为“国”的只有天子王城和诸侯“国都”,它们构成了两级政治中心。为了区分族属,西周实行国野制度,“国人”即为“国”的城内和城外近郊范围内(统称“国中”)的人,是与王室、诸侯同姓的族人及其受封的异姓贵族和附属族人,具有承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兵役的权利;而被征服的异姓蛮荒土著,居住在远郊之外的“野”中,称为“野人”。由于西周和春秋的政治是以上述两级政治中心为舞台,卿大夫采邑和贵族重戚的所谓“大都”,当然不能称“国”而只能称“都”、“邑”,如春秋时期晋国桓叔以迄武公把持的曲沃、郑国公叔段把持的京、鲁国季氏的采邑费和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的采邑薛等等,居住在这些都邑的贵族家臣和“庶人”,自然也就无见称“国人”者。这表明,所谓“国人”是包括很多社会阶层和职业,不包括奴隶、刑徒的国都之人,有如今天的“首都人”的概念,主体是隶属于各个贵族家族的“士”和平民“庶人”。
根据文献记载,在西周到春秋的政治生活中,“国人”除了当兵的权利义务之外,还能够纳君、出君、逐君、弑君,能够决定执政的命运,具有议政、“咎公”的自由,每遇大事国君需询之以定可否,贵族在内部斗争中也要与“国人”订盟以求得其支持。赵世超先生根据“国人”集团特殊政治地位而认为“舆人”是“国人”中的下层群众,大概为“小人”之属。就国都而言,这个结论是对的;但就巨室、贰宗的都、邑而言,则未必。因为在这些都邑之中,士和庶人虽然不得称“国人”,却无碍于“舆人”之称的存在。尤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卿权不断加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孔子弟子“问政”所涉内容,大夫和家宰们据以壮大自身实力的都邑更当形成了独立的政治系统和武装力量,“舆人”职事的存在是极其自然的。
所以,就“舆人”与“国人”、“庶人”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国人”概念只与王城和诸侯国都相关,是一个兼有仕、农、兵、工、商等职业阶层的集团,因此和“庶人”有交叉,“庶人”居于“国”中者为“国人”,而“舆人”则为“国人”和“庶人”中从事上面所论相应职事的人。三者不能画等号。而且,这三个概念本身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有着动态变化。不论如何,“舆人”是具有一定参政权利的自由平民,具有自由表达政见的权利,从整体社会结构中属于“庶人”阶层,在王城和诸侯国都的特定政治格局中又属于“国人”集团。所以,《国语·周语》记载西周厉王时有“国人谤王”。
另外,赵锡元先生认为,商周时期车作为最先进的代步交通工具和最先进的战争工具,并非下层民众乘坐的,乘车之人必为士阶层以上的贵族。武士中的贵族有权利乘坐在车上,所以被称作“舆人”,从而成为最初的“舆人”概念的来源。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文献证据。晁福林先生在强调“舆人”和单称的“舆”者有较大的区别时指出,“舆人”是有自己私有车辆的“国人”,而非广义的“国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认为“舆人”是“国人”中的“有车一族”,即至少是“士”。这也是可以商榷的。
文献和考古材料均已证明,车战出现于商代,到西周、春秋时期车、步结合作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此表示国力强盛与否可以拥有战车的多少为标志。但是,殷商和西周时期战车数量是有限的,《孟子·尽心下》所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的说法大体可信。《司马法》云:“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即一乘战车,配有甲士十人,徒兵十五人,另有厩养五人,这种车兵的编制是可信的。显然,不论是甲士,还是徒兵,或者厩养,不可能人人拥有战车。又,按照殷墟宗庙遗址北组以“车”为中心的葬坑中,发现在中组最前的一车的左右并列三个较大的坑,每坑埋人五名,这十五人即当为徒兵。而从商周时期以“族”参战的角度来推测,这乘战车的拥有者只能是这些战士所组成的一个或三个家族。因此,如果在源头上追溯“舆人”与车乘拥有者的直接联系,就只能说“舆人”是出战车的“族”编制中的战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谋”,《国语·楚语上》有载:“在舆有旅贲之规”,韦昭注曰:“旅贲,勇力之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趋,车止则持轮。”两者所指相符,说明在战争中能够给“在舆”的君主、将官们以规谏的“舆人”、“旅贲”,都只能是出车而从战的甲士、徒兵。
到了春秋中晚期,经过无数次的战争掠夺和征服之后,诸侯国已可拥有战车千乘,叫“千乘之国”,如鲁、莒,而齐、晋之国或可拥有数千之乘;势力极大、拥有较大都邑的大夫才可拥有战车百乘,叫“百乘之家”。“千乘之国”包含着一批“百乘之家”,而“百乘之家”则包含着众多的各级“士”家族和贵族的家臣之族。由此可知,春秋社会各级贵族拥有数量不等的车辆,并无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士”都一定拥有私人车辆,甚至拥有私人车辆的“士”亦不为多数。《论语·先进》记载: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这一方面说明春秋晚期贵族拥有的私人车辆已经转让、买卖,另一方面说明孔子以“从大夫之后”的社会地位拥有一乘车已属不易。若此,大量在礼崩乐坏之下身份不断下跌的“士”又怎么可能拥有私人车辆呢?如果按照晁先生的看法,难道“舆人”的身份在不断上升为贵族吗?从春秋战国时代“舆人”概念和“庶民”概念越来越接近的趋势上看,这也是显见的矛盾。因此,所谓“舆人”乃拥有私人车辆的“国人”的推论,值得怀疑。
及至战国时代,国野制度几乎完全破坏,“庶人”和“野人”的界限取消。《孟子·万章下》云:“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可见,士、农、工、商的“四民”阶层逐渐形成,与“君子”相对立的“庶人”和“小人”、“贱人”等概念逐渐混杂而无别。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舆”和“舆人”概念也只体现出“造车之工”的本义。这样的证据有如下几则:
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周礼·考工记》)。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其中的“舆”和“舆人”等等都是具体指向那些持有专门技艺的工种和工匠的。另外,《庄子·天道》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故事虽属寓言,“轮人之议”和“舆人之诵”却几无二致。此外,《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所谓轮人、匠人等等,都只能属于“四民”中的“工”。
当然,春秋之末以迄战国,由于重农思想的影响,“舆人”的社会身份有下降为缺少人身自由的奴仆阶层者。《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舆人”,但“人臣、隶、圉”当是“皂隶牧圉”的另一种说法。又如《管子·治国》还将“舆厮之事”列为耗费粮食的四种行为之一;《吕氏春秋·为欲》亦有言:“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舆隶至贱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又《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当代学者蒋礼鸿说:“重当作童。……《说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童为僮奴本字,厮舆徒童四字同类并列。”
由此看来,战国之后称作“舆”的人至少有一部分已经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是“庶众”阶层中最低下者。但是,迄于汉晋,“舆人”仍然不失其与“车舆”本义的联系。如《汉书·严助传》:“厮舆之卒。”唐代颜师古曰:“厮,析薪者。舆,主驾车者。此皆言贱役之人。”这是汉代社会阶层已然不同于春秋时代的情形了。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秦时代的“舆人”与“舆”的造字本义始终存在着语义上的联系,即“舆人”概念的核心没有游离于修造车舆、车舆运输这类职事之外。所以,“舆人”的社会阶层只能从承担这类职事的人的具体身份和地位来确定,大体上是属于“庶人”平民阶层的。黄中业先生说“舆人”是以修造战车为主要职事的平民,是比较正确的。因此,“舆人之诵”是西周以迄春秋时期“庶人”的舆论,它尽管不同于士大夫的谏议,但也具有一定的舆论张力。而且,再引申一步考量,先秦“舆人”的社会阶层虽属于“庶人”平民,却由于车乘乃为贵族阶层代步工具和重要战争工具,“舆人”客观上具有联系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特殊地位。正如《荀子·劝学》所谓“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的传播特性,“舆人”自然具有借由这一交通工具的轮转往来而起到沟通消息的特殊作用,从而也就具有了舆论传播的特殊功能。
还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时代是以贵族政治为主导的社会,与秦汉以后以官僚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大不相同,两者之间发生了由“血而优则仕”向“学而优则仕”的重大转变,所以,秦汉以后的“舆人之论”是可以通过士、庶的科举进身而转变成为“臣谏”的,“舆论”在这时就具有了有限的普遍意义。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引进西方概念时径直借用古代“舆论”概念时习焉不察的重要前提。(节选自夏保国《先秦“舆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学习与探索》 2011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