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题字:关山月
摘要
ABSTRACT
作为前南斯拉夫实践派“这个独特星丛的哲学中心”,彼得洛维奇以其革命之思主张革命、存在、思想的激进同一,从内部实现了对前南斯拉夫实践哲学的激进化。从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前南斯拉夫实践哲学,特别是其彼得洛维奇式激进形态的形成,与实践派在其独特主义马克思立场下的海德格尔思想接受密不可分。这种“接受”长久以来以其“难以置信”的方式遭受多方质疑。然而,在海德格尔接受语境中考察革命之思,或可澄清的是,实践哲学的激进化形态是以革命人本主义的主义马克思立场批判性地吸收乃至激进地转化海德格尔思想而形成的。就此而言,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意义上,彼得洛维奇的革命之思在其所处时代无疑是一种真正的主义马克思式“冒险”。
关键词
KEYWORDS
实践派;前南斯拉夫实践哲学;革命之思;彼得洛维奇;海德格尔
作者
AUTHOR
杨 栋,(西安 710049)西安交通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国外主义马克思研究所教授。
前南斯拉夫实践派在20世纪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思想关系的承认性建构进程中占据重要一席。哈贝马斯在回望其与实践派哲学家的交往时指出:“我现在所了解的实践派哲学让我想起了青年马尔库塞……实践派哲学……在不了解其先驱(青年马尔库塞)的情况下,第二次走向了海德格尔式的主义马克思……在萨格勒布,我立刻感觉到,实践派哲学家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以高度原创性的方式发明并发展了现象学主义马克思的人类学方法。”[1]这种“高度原创的方式”是指,实践派将“左翼的进步意识和革命意识与某种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的哲学难以置信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的哲学传统被认为表现了一种相当保守的、在纳粹时期一直没有改变的思想。”[2]事实上,实践派哲学家对哈贝马斯所指明的这种“难以置信”的结合方式亦有所自觉。作为实践派“这个独特星丛的哲学中心”[3],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指出:“正是在世界上被称为’主义马克思’或’新主义马克思’的代表、并随后疏远了’主义马克思’和’新主义马克思’、而始终强调马克思是一位伟大思想家和他们老师的’实践派哲学家’,在南斯拉夫接受海德格尔这个’反主义马克思的’保守思想家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这位海德格尔至少有一段时间是纳粹分子,或者甚至像一些人最近声称的那样,他的哲学为纳粹主义做准备、并试图在哲学上为其辩护,即便不是完全以官方承认的类型和方式。”[4]那么,如何理解并说明这种奇特的状况?这是否表明实践派哲学家们敌不过海德格尔思想和话语的诱惑,在未看透海德格尔思想的情况下屈从于这种思想?这是否表明实践派哲学家们在丧失了某种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后,向海德格尔思想寻求庇护?还是说,这表明了实践派哲学家们试图沿着青年马尔库塞未竟的努力再次尝试某种海德格尔式主义马克思的冒险?在实践派接受并转化海德格尔思想的语境中,本文尝试通过对彼得洛维奇这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之典型思想形态的考察,来回答这些问题。
▴
加约·彼得洛维奇
Part.1
一、实践派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般接受
总体而言,实践派哲学家的关切并非找寻自身与海德格尔的孤立联系,而是力图发现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筹划与他们试图从马克思出发制定的那种思想方案的某种近似性。这种近似性是“将朝向存在的追问和朝向人的追问统一在一起。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想把传统的抽象存在论和存在论上未被奠基的哲学人类学带入一种新的综合,而首先是想把朝向一般存在的追问和朝向人的追问以一种新的方式共同来思考”[5]。这种新的方式在于通过三个基本追问,即对朝向此在之基本建构、此在之存在、此在之存在意义的追问,来重新建构存在与人、存在论与人类学的关联。这使得不满于对人之本质的传统追问——这预设了人之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特征的二分法——的实践派哲学家看到了深入关于人的理论的新进路。
但是,实践派哲学家对海德格尔的深入关切,并不意味着毫无保留地追随海德格尔。事实上,他们从以下五个方面反思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其一,海德格尔并未实现从此在之存在意义问题向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的真正过渡。这一划分并未清楚表明两个问题的权重和关系,不仅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并未展现出解答此在问题到解答存在问题的真正过渡,而且《存在与时间》已发表的篇章也未能很好地解决朝向此在的追问。海德格尔严格区别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即此在的存在和非此在式存在者的存在,以及适合它们的概念或语言,即生存论性质的语言和范畴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阻碍了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的解答。
其二,海德格尔虽然用前述三个基本追问代替了朝向人之本质追问,但具体实施方式是成问题的。海德格尔没有细致地解释这种追问的三分法本身以及三个追问之间的关系,同时,“本质”这一古老概念的保留,容易让人产生困惑。
其三,尽管朝向本真性的追问具有启发性,但也蕴含了许多困难。海德格尔对此在之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的区分不是对纳粹行话的预演,而是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和非异化的人类存在之区分的独特吸收。然而,尽管海德格尔的本真性话语并不追求纯理论之外的任何主张,但恰是这种理论性的主张隐含了人类恒定天性的观念。这表明,《存在与时间》的最大缺陷在于“建立在一个非历史性的预设之上,即,人的恒定的、即非历史性的天性将在这种天性与存在的非时间性关系中被描述。虽然时间性和历史性也被设想为这种非时间性的和非历史性的天性之要素,但时间性和历史性这二者复又被理解为非历史性的”[6]。事实上,这与传统本质概念的缺陷是一致的。
其四,海德格尔以非历史性的方式把握人与存在及二者的关系,但却以历史性的方式把握人的思想。就此而言,从对存在被遗忘状态的克服、到存在离弃状态下对存在重新到来的期备,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并被要求提升为存在之思。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存在之思是真正摆脱既定束缚、面向作为实事本身的存在之真理的思想,这与亲近海德格尔的那些实践派哲学家谋求的思想具有同样的特质。
其五,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虽然从存在论-人类学的层面上深刻反思了技术现象,但这种思想本身是对技术的抽象存在论化。让实践派哲学家们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抽象存在论化,最终引向对不依赖于人的自主性技术的阐扬。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用“泰然任之”刻画人对待技术的行为,是过于简略和无力的。
因此,实践派主张,对海德格尔的诠释,应当以实事求是的哲学批判方式,避免任何一种无批判的辩护和过度批判。这种主张的主要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法里亚斯(Victor Farisa)和奥特(Hugo Ott)等人的海德格尔传记研究,引发了有关海德格尔政治立场根源的新一轮探讨。这种探讨使得长久以来针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看法激化为两种彻底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彻底否认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其纳粹政治经历之间的关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整体都具有纳粹主义的倾向。实践派哲学家总体上主张,应当区分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换言之,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不一定由其哲学思想决定,但可能有其哲学思想上的根源。一方面,应当避免将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混为一谈,即不能将海德格尔思想视为绝对的统一和封闭。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总体上一以贯之,细节却又十分复杂,不同的观念、思路、视角和环节交织其中,因而应当仔细辨析海德格尔思想中与政治有关和无关的部分。因为海德格尔思想中与其政治立场无关的哲学部分,可能恰恰蕴含了海德格尔最为基本的观念和原则性的论述。因此,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过度批判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即便海德格尔的核心哲学思想并不必然与其政治立场有关,也不意味着这种哲学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思之伟者迷误必巨”[7],或许应被解释为“哲学上思得伟大之人,哲学上一定会大大地犯错”[8]。由此出发,应当对海德格尔哲学做批判性的分析,其目的不是确定海德格尔的伟大,而是通过海德格尔去认清哲学上真正伟大的问题。
在实践派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般接受中,彼得洛维奇的革命之思是以哲学批判方式接受并转化海德格尔思想的典范。一方面,革命之思就其彻底朝向真理的激进性而言,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具有真正的相似性。但不同于海德格尔最终从存在的自主发生角度把握真理,革命之思从人的问题出发,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将人连同其世界的共同改变视作革命,由此将革命思为真正的实事即真理本身。在此意义上,“革命之思没有把自己设想为社会行动的工具,而恰恰设想为一种指向真理的思想,但这种思想通过打开关于当代世界及其可能性的真理,就不仅是为真正的人本主义革命做准备,而就是这种革命的一部分,即,已经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了”[9]。另一方面,革命之思与存在之思有着根本的不同。这表现在双方对于哲学作用,亦即人类特定活动方式之效用的构思差异上。在海德格尔那里,不论积极还是消极,人类扮演着真理之婢女的角色,作为有限的、终有一死的凡人,人类需要在真理的诸种发生方式中寻求庇护。与此相对,“在革命之思中,人被视为自由的思想着的生物,而自由则是人之诸种创造的可能性的发展,即’人性的扩展和丰富’”[10]。就此而言,相较于海德格尔思想,革命之思是相对自由的;而相较于革命之思,海德格尔思想是相对保守的。正是这种差异表明了革命之思更强的批判性。
Part.2
二、创造性主义马克思语境中的革命人本主义:革命之思的基本立场
彼得洛维奇革命之思的基本立场,是通过批判教条主义主义马克思和重新诠释马克思而赢获的。尽管彼得洛维奇在诸多论述中反复阐明并完善这一立场,但它作为一种新的主义马克思立场则始终充满争议。在《哲学和主义马克思》(1965)[11]中,彼得洛维奇区分了教条主义的主义马克思和创造性的主义马克思,并将这种区分贯穿其思想道路始终。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斯大林版本的主义马克思哲学,作为教条主义主义马克思的典型形态,成为彼得洛维奇的主要批判对象;而批判的依据则来自前南斯拉夫实践哲学的基本倾向,这也被彼得洛维奇认作创造性主义马克思的典型表现形式。
▴
Gajo Petrović, Wider den autoritären Marximus,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总体上看,斯大林主义以极端教条主义和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主义马克思哲学的遗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被尊为“主义马克思经典作家”,他们原本不同的学说被斯大林主义视为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基本问题的完备哲学体系。在此意义上,主义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只能通过证实、诠释和深化来实现。换言之,主义马克思哲学事实上被当作极端教条的体系而失去了真正的发展。另一方面,“主义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之内和之外的、不符合斯大林主义设想的部分,都以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方式被对待。譬如,斯大林主义贬低青年马克思和晚年列宁的同时,又从相应时期的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攫取对其有利的论述。又如,斯大林主义将“主义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之外的重要思想,以不符合实情的方式刻板划分为对主义马克思的通俗化、修正主义和非主义马克思。
具体而言,斯大林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定为主义马克思哲学基本内核的做法导致了许多问题。其一,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义马克思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斯大林主义认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12]的辩证唯物主义,连同由其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主义马克思政党的理论基础”[13]。哲学由此成为主义马克思政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工具,导致其效用和价值要由政治来判断。但这种观念既没有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根据,即便是在对列宁主张哲学具有“党性”(Parteilichkeit)的引用中,也误解了列宁实质上用“党性”指向哲学上不同派别的用意。因此,哲学应当回归其自身,即“哲学是其自身的裁判”[14]。在彼得洛维奇看来,南斯拉夫的主义马克思者通过克服斯大林主义所获得的这种对哲学的认识,并不代表推脱哲学对于现实的责任,而是将哲学的责任还给其自身。这同时意味着哲学不能远离现实,而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
其二,更重要的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义马克思哲学忽略了人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概念不包含人,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5],也不包含人的概念。然而,二战后,南斯拉夫哲学的基本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被斯大林主义当作抽象物所排除掉了的人,而这恰恰是真正的、创造性的主义马克思哲学所思考的核心。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不是斯大林主义当作自明前提的经济动物概念,而是在全部天性和结构上都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概念,即人是(ist)实践。在此意义上,自由创造力(die freie Schöpfungskraft)是人的本质可能性。
其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义马克思哲学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教条化。一方面,对辩证法四个特征——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质量互变、对立面的斗争——的概括是斯大林借自布哈林的,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辩证法的把握均不相同。马克思看重辩证法,并以其全部著作展现了辩证法的成就,但从未专门论述过辩证法。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法阐释,从自然和社会的实例出发,将辩证法把握为关于一切运动的规律的科学。列宁则主张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辩证法。就此而言,即便在“主义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不仅对于辩证法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自然辩证法”的观念也并未得到充分的奠基。因此,斯大林主义对辩证法的教条化并无充分根据。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将唯物主义视为科学的和进步的世界观,与非科学的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哲学史的发展由此被固化为两军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被视为从部分科学和部分进步到彻底科学和进步的发展。作为科学的和进步的世界观的唯一代表,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教条化为三个特征: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先于意识、世界是可认识的。这种教条化的做法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的积极看法,也与列宁后来对“聪明的唯心主义”的肯定相悖。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丧失价值,但是斯大林主义对这二者的教条化,不但使之背离了马克思及其重要后继者思想,而且使主义马克思哲学丧失了应有的改变世界的能力。
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彼得洛维奇主张回到“真正的马克思”(der wahre Marx)。首先,真正的马克思意指马克思本质性思想上的统一。客观的、自在的马克思,以及研究者主观建构起来的马克思,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是历史归功于他的那个马克思,而且’真正的’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对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16]在此意义上,青年马克思或晚年马克思都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马克思。对人是实践生物(Wesen der Praxis)的理解以及由之出发的异化理论是真正的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也是青年马克思哲学和晚年马克思哲学所共有的本质。真正的马克思因而是“反对自我异化、非人化和剥削的斗士;马克思是争取人的完全人性化(Humanisierung)、争取属人(menschlich)可能性的全面发展、争取废除阶级社会和争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同体的斗士”[17]。就此而言,“真正的马克思”主张马克思思想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其次,“真正的马克思”并不排除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性和开放性。马克思的著作本身是不断的自我批判,即马克思对其自身观点的持续检视。就此而言,任何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诸如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二分法之类,都是不完备的。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性使其并未成为一个无所不包和完结了的体系,马克思著作中充满了开放的问题。因此,真正的继承者们有责任继续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发展一方面在于实事求是地深入研判马克思思想之外的哲学进展,为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寻找可资利用的恰当资源;另一方面在于在认清马克思思想本质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基础。彼得洛维奇指出:“事实上,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对的,他们感觉到需要更加明确和更加充分地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在马克思的水平上做马克思本该完成的工作,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毫无疑问,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基础的发展仍待完善。认为’纯粹的’人类学或脱离普遍存在论预设的’关于人的存在论’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是一种幻想。认为普遍存在论的追问只是某种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部分,这种想法也值得怀疑。” [18]
最后,揭示“真正的马克思”就是要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对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不同看法,根据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目的,具有各自的论据。在彼得洛维奇看来,“马克思思想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人本主义,只有将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为争取民主的和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19]。要系统阐明这一论点并非易事,而对马克思不同时期坐标性文本的诠释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这一论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被彼得洛维奇视为马克思三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70年代——的代表性文本。这三部文本虽然都是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且其间关系常被那些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非连续性的观点看作“断裂”或“鸿沟”,但是这些文本中的基本问题和结论从基础层面决定性地影响了各自所在时期的其他文本。表面上看,经济学对象是这三部文本共有的,三者最大的区别体现在方法上,即第一部文本运用较为抽象的哲学演绎,而后两部文本使用具体的实证分析。但事实上,三部文本的内在共性都是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且这种批判都不仅仅是纯粹实证科学即经济学的,而是哲学式的。这表现在“所有这些文本都包含了一种理论基础,并呼吁实现一种真正属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不再同自身相异化,且不再是经济动物,而是将自身实现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生物”[20]。实现真正属人的社会和扬弃自身异化,意味着人与其世界的共同变革,为这种共同变革提供理论基础的是一种革命的人本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所在。
作为马克思思想连续性体现的革命人本主义,同时表明了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在于“我们时代基本的意识形态可能性,即现代人关于自身及其世界的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21]。从思想的可能性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是开放的。换言之,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把握不仅仅是寻章摘句,而是要“通过马克思精神下的创造性思想……与马克思一道的思想、对马克思主导思想的彻底思考”[22]来实现。因此,斯大林主义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教条主义,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非本质,与作为马克思哲学本质的革命人本主义相对立。就此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观点并非没有意义,而是不够彻底。在彼得洛维奇的语境中,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革命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revolutionären Handelns)和自然主义-人本主义(Naturalismus-Humanismus)——消除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对立的那种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der naturalistische Humanismus)或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der humanistische Naturalismus)——是意指“革命的人本主义”的同义词。但是,革命的人本主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局限于人类学(人本学),而是指马克思的整个著作和思想都在为那种将被实现为实践生物的人而斗争,这预设了人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转换,即革命。与此同时,实践就被把握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结构。[23]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不仅关乎人的问题,而且关乎存在的问题。质言之,马克思哲学具有存在论和人类学的双重特征。
Part.3
三、革命之思:作为存在论-人类学的革命人本主义
▴
Gajo Petrović,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Modelle für eine Marx-Interpretation; Mit Quellentexten,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71
在存在论和人类学双重特征上被把握的革命人本主义,是一种作为新形态哲学的存在论-人类学(Ontologie-Anthropologie)。这不是在作为最普遍的专门科学意义上来把握哲学,而是“通过批判以往哲学的陌异于世界的状态(Weltfremdheit),马克思也看到了哲学的本质可能性,即哲学成为革命之思的可能性,这种思想开辟了革命的本质并参与了革命的演历”[24]。在此,思想在思考属人的存在可能性的意义上是介入性的,而革命被把握一种激进的存在可能性,即人与其世界——社会——从异化状态向真正属人状态的激进转变。在此意义上,行动或者实践的哲学并不足以刻画马克思的哲学,而只有在革命之思的指导下,行动或实践才是革命性的。因此,革命并非马克思思想的其中一个面向,而是马克思最为根本的关切。就此而言,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诠释,有必要从实践哲学的范式进展到革命之思的模式。
作为激进化了的实践哲学,革命之思呈现了彼得洛维奇的思想完型。在哈贝马斯看来,彼得洛维奇的这种思想是一种锚泊于生存的思想(ein existentiell verankertes Denken),其核心是“一种独特的无条件的有关未被沾染的革命性演历、即变革性演历的概念”[25]。从被抛、在世和有限性的角度来看,生存无疑始终受到沾染。但革命性演历又具有“未被沾染的”特征,那么如何从生存上溯至一种未被沾染的革命性演历?那种“独特的无条件的有关未被沾染的革命性演历、即变革性演历的概念”又指什么?
在《哲学与革命》(1971)中[26],彼得洛维奇尝试通过20组问题将革命概念置于哲学的核心关切之处,同时基于这种关切,展现一种新的革命概念和与之相匹配的新哲学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中,彼得洛维奇实际上用革命概念表达了他的存在论-人类学式的存在理解。
传统上,革命并非哲学的核心关切。尽管传统哲学采取系统阐明和逻辑论证的论述形式,但史诗、小说、故事、戏剧、散文诗、对话乃至书信和游记等形式也始终表达着哲学。即便在黑格尔用恢弘的论述体系范例性地将传统哲学的形式推向极致之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以提纲的形式、尼采以训诫的形式也成功地表达着哲学。这或许说明,不同形态的哲学可以采取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彼得洛维奇看来,问题(Frage)是思想的食粮,于是他尝试用追问(Fragen)的方式表达一种异于传统的哲学形态。在此背景中,彼得洛维奇提出这样的问题:“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思想,还是关于革命的思想?”[27]从传统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几乎匪夷所思。众所周知,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是关于存在的思想。但是,“如果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思想,那么它是思考存在的思想,还是存在思考的、并通过它来思考的那种思想?……如果存在是哲学思想所思考的存在,那么思想所思考的这种存在是什么?……如果哲学是思考存在的思想,那么它是否也是存在思考的那种思想?”[28]通过这些问题,彼得洛维奇试图表明:思想与存在或许处于一种交互关联中,即哲学思考存在,存在也通过思想显现出来。换言之,如果哲学是存在之思,那么哲学不仅是关于存在的思想,而且思想也归属于存在。就此而言,人的某种特定生存方式或许同时应和于存在自身显现的方式。那么,革命是不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如果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思想,那么它也可以是关于革命的思想吗?”[29]
革命通常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对象,而绝非哲学的对象。革命不存在于哲学的概念谱系之中。即便哲学试图探讨革命,也不会脱离社会学和政治学基础、政治和政治活动基础来看待革命。这就表明,革命或许仅仅只是一种特殊的现象。那么,革命是什么呢?或许每一次暴动、个人或团体的权力更迭都被认为是革命,但从更大的范围来讲,革命也指权力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改变、一种社会秩序对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取代。但如果社会秩序有高低之分,是不是高级秩序对低级秩序的取代是革命,而低级秩序取代高级秩序就不是革命呢?如果用革命来指代社会秩序的改变,那么这是指社会秩序的部分改变还是全部改变?按照彼得洛维奇的看法,从社会和政治的层面来看,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在于“建立一个本质上不同的、无阶级的社会,即建立这样一个真正属人的社会——在其中自我异化终止、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真正属人”[30]。在此基础上,社会秩序中的人的活动之改变也是革命。但是,革命不是指人从一种活动向另一种活动的转变,而是指向人的整体改变,这是指“创造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存在’方式’、亦即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本质上有别于一切不属人的、非人的和尚未全部属人的存在”[31]。作为自然界的生物,人的独特性在于可以超越其单纯的自然性而成为革命的生物。就此而言,脱离了与人的关联去谈论自然界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自然界的革命要从属人的角度去把握。如果从属人的角度去把握,那么对人而言,真正自然的即天然的革命就是历史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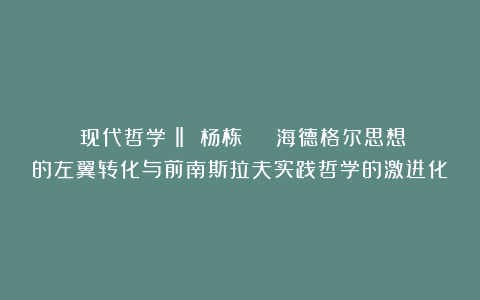
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是革命的本质。一方面,革命刻画了人的某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成为哲学的对象。如果从人的不自由的、非创造性的存在方式来看待属人的历史,那么革命就蕴含了反历史性(Antihistorizität),就不能随意被编入历史。但正是这种反历史性,即对人的不自由的、非创造性的存在方式的否定,才是那种使历史真正成为属人历史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此而言,衡量进步的内涵、判断诸种进步与革命的关系,要从朝向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可能性的角度出发;组织性不应当成为革命的标准,而革命行为即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应当成为革命组织的标准。作为对现存事物批判的革命在于使尚未存在的事物焕发生机,因此常常发生在既定组织和制度之外。组织化并不是革命的目标,革命本身就是自我发动和自我组织、自我创造和自我治理的持续过程,因此,革命唯一可能的、真正的胜利是继续革命。
另一方面,作为持续的本质现身,革命就是自主发生性的存在本身。不能在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过渡意义上理解革命,革命也不是中断和飞跃,而是最发达的创造形式,是为可能性开放的领域。革命就是持续到场的存在本身。因此,如果存在理解指向革命,那么存在之思就是革命之思:其一,没有革命之思,就没有革命,因为革命以人们对革命的自觉为前提,而思想就是自觉的自发性的内在形式;其二,在与革命的结合中,哲学转化为一种新的形态,不再是为现存事物辩护的学问,而是在面向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的前提下,对现存一切事物的批判。因此,革命之思不仅是关于革命的思想,而且是思想的革命。对革命的普遍沉思是对历史性现象之激进性、历史性生存归属于其中的存在历史现象的透彻思考,是真正革命行为的必要前提。
然而,从激进性上去把握历史性现象的可能性,是否表明革命之思颠覆了对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诠释?人本主义的主义马克思者在不断被斯大林主义攻击为“修正主义者”“抽象的人本主义者”“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同时,一些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主义马克思者也认为,较之人本主义,革命理论更能表达主义马克思的实质。激进且常常以非人道方式发生的革命,似乎对立于以渐进为特征的人本化。那么,主义马克思可以兼具革命和人本主义的特征吗?彼得洛维奇在《人本主义和革命》[32]一文中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通过辨析主张人本主义和革命相互对立的诸种观点,彼得洛维奇主张人本主义和革命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实则奠基于彼得洛维奇对于人本主义概念和革命概念的激进性理解。一方面,激进的人本主义要求彻底否定现存非人道的状况,要求创造一种质上不同的、真正属人的社会。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从不满足于微小的社会改变,而是要求创造一种质上不同的、真正属人的人和社会。因此,着眼于完整的革命过程,社会制度的进步和新人的产生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换言之,人本主义的过程和革命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彼得洛维奇总结道:“没有革命的态度,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本主义;没有人本主义,也不会有真正的革命。只有革命的人本主义才是唯一完整的人本主义,只有人本主义的革命才是唯一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革命的人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革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33]
Part.4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以彼得洛维奇为代表的实践派哲学家,恰恰基于独特的主义马克思立场,才有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这种接受并非屈服,而是批判性地找寻与其主义马克思立场和筹划相符的整体相似性。倘若滥觞于青年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主义马克思”意指基于主义马克思立场去承认性地建构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思想关系,那么以彼得洛维奇为代表的实践派哲学家无疑是在继续青年马尔库塞未竟的“冒险”。之所以是一种“冒险”,是因为彼得洛维奇以其革命之思主张革命、存在、思想的激进同一。这不仅是对前南斯拉夫实践哲学的激进化,也是从左翼方面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激进转化。这种哲学活动无疑符合彼得洛维奇所把握到的“真正的马克思”所具有的精神。但或许正因如此,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彼得洛维奇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从自由和理性的角度将现有的制度和做法置于审判——给自身带来的麻烦,可能比海德格尔据说在纳粹那里所经历的麻烦,还要更多一些”[34]。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国外海德格尔式主义马克思的研究”(19CZX004)的阶段性成果。
[1] Jürgen Habermas, “Zum Gedenken an Gajo Petrović”, Gajo Petrović- čovjek i filozof, hrsg. von Urednik Lino Veljak, Zagreb: FF Press, 2008, S. 16.
[2] Ebd., S.16.
[3] Jürgen Habermas, “Die Grußadresse”, Gajo Petrović, filozof iz karlovca, hrsg. von Lino Veljak, Zagreb: Hrvatsko filozofsko društvo, 2014, S. 9.
[4] Gajo Petrović, “Heidegger und die jugoslawische Praxis-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sche Aktualität Heideggers: Symposium der Alexander von Humbolt-Stiftung vom 24.- 28. April 1989 in Bonn-Bad Godesberg, Bd. 3, hrsg. von Dietrich Papenfuss & Otto Pöggeler,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2, S. 221.
[5] Ebd., S. 228.
[6] Ebd., S. 233.
[7] Martin Heidegger,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GA Bd. 13,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3, S. 81.
[8] Gajo Petrović, “Heidegger und die jugoslawische Praxis-Philosophie”, S. 239.
[9] Ebd., S. 235.
[10] Ebd., S. 236.
[11] 该书连同《哲学与革命》(1971)和《革命之思——从“存在论”到“政治哲学”》(1978)组成的三部曲,被认为是彼得洛维奇最重要的著作。该书1965年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首版,1967年德文本和英文本出版,中文本据英文本译出。(Gajo Petrović, Filozofijia i marksizam, Zagreb: Naprijed, 1965; Gajo Petrović, Wider den autoritären Marximus, Frankfurt a. M.: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Gajo Petrović, Marx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A Yugoslav Philosopher Reconsiders Karl Marx’s Writing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7; [南斯拉夫]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姜海波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德文本和英文本均无译者信息,考虑到彼得洛维奇精通德语和英语,笔者推测这两个版本都是他本人翻译或勘定的,因而都是较为可靠的。德、英两个版本的篇目和标题一致,但与塞文版略有差异。
[1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5页。
[13] 同上,第115页。
[14] [南斯拉夫]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第13页。
[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16页。
[16] [南斯拉夫]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第24页。
[17] 同上,第25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18] 同上,第27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19] 同上,第30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20] 同上,第34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21] 同上,第47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22] 同上,第47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
[23] 同上,第151页。
[24] Gajo Petrović,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Modelle für eine Marx-Interpretation; Mit Quellentexten,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71, S. 9.
[25] Jürgen Habermas, “Die Grußadresse”, S. 9.
[26] 这是《哲学与革命》一书的导论部分,此文可被视为彼得罗维奇“革命概念三部曲”的第一篇文章。(Gajo Petrović,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Modelle für eine Marx-Interpretation; Mit Quellentexten, S.11-18. )
[27] Ebd., S. 11.
[28] Ebd., S. 11f.
[29] Ebd., S. 12.
[30] Ebd., S. 13.
[31] Ebd., S. 13.
[32] 这是《哲学和革命》一书的结论部分,此文可被视为彼得罗维奇“革命概念三部曲”的第二篇文章。(Gajo Petrović,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Modelle für eine Marx-Interpretation; Mit Quellentexten, S.290-302.)
[33] Ebd., S. 302.
[34] Gajo Petrović, “Heidegger und die jugoslawische Praxis-Philosophie”, S. 236.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5期
。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