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刊名题字:关山月
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
本专栏得到敦和基金会支持,谨此致谢!
摘要
ABSTRACT
“通三统”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理,在汉代董仲舒与何休那里得到全面的阐释。董仲舒与何休的“通三统”说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同的表述,但在核心义理层面上则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论是从《春秋》“存三正”来论证“三统”之可通,还是根据“通三统”的原理进一步阐发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等观点。对于董、何而言,“通三统”关注的不仅是时王之一统去通前两代王者的两统,更关注的是《春秋》如何作为“新王”去拨乱反正,从而如何建立未来之“新统”的问题。
关键词
KEYWORDS
《春秋》;《公羊传》;董仲舒;何休;通三统;王鲁
作者
AUTHOR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郭晓东,(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092)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敦和经学讲席教授。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通三统”之说最初见于《尚书大传》[1],后为《公羊》家所采用,遂成《公羊》学的核心义理之一。汉代所传的《公羊》“三科九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何休的说法,另一种是宋均的说法,二说内涵各不相同,但均将“通三统”视为“三科”之一。[2]清代刘逢禄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3]按照刘逢禄这一说法,没有“通三统”说,就没有《公羊》学。即使作为非《公羊》家的朱一新,也曾指出“《公羊》大义在通三统”[4]。云云诸说,足见“通三统”说在《公羊》学义理中的核心地位。
汉代《公羊》家中,最早提出“通三统”的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相当全面地讨论了“通三统”的学说,强调夏、商、周三代政权之天命合法性,进而提出了“王鲁”的学说。东汉的何休则提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以之为“三科九旨”之“一科三旨”,[5]也相当系统地阐明了“通三统”与“王鲁”的思想内涵。董仲舒与何休的师说各不相同,何休在《公羊解诂》中称“略依胡毋生《条例》”[6],只字未提及董仲舒。但后世相当多学者认为,何休“通三统”诸说实本之于董仲舒。例如,魏源在《董子春秋发微序》认为,“通三统”说在《春秋繁露》中的《楚庄王》《三代改制质文》《爵国》《符瑞》诸篇中都得以体现。[7]又如皮锡瑞在《春秋通论》中说:“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8]还有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指出,“何氏九科三旨,所谓’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三代改制篇》;’异内外’,见《王道篇》”[9]。现代学者中有代表性的如赵伯雄先生说:“何休的第一科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完全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10]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董仲舒与何休“通三统”说中内涵的差异性,特别是由“通三统”说所衍生出来的“王鲁”说在董仲舒那里只略略提到一句,而“王鲁”在何休那里则是《公羊解诂》的核心义例之一,于是多有学者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认为“王鲁”是何休造作的理论。鉴于董仲舒与何休在《公羊》学史上的奠基性地位,董、何二人关于“通三统”论说的异同遂成为《公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公羊》学之基本精神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相对而言,何休关于“通三统”的论说更具有系统性,我们不妨以何休的观点为参照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董仲舒与何休论“通三统”与“王鲁”的异同,进而揭示这些思想背后的政治与哲学内涵。
Part.1
一、何休的“通三统”说
据徐彦所述,何休在《文謚例》中提出“三科九旨”之说,其中以“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为“一科三旨”。后世学者一般称之为“通三统”。[11]“通三统”或“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不见于《春秋》,亦不见于《公羊传》。那么,何休何以以之为“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呢?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何休画像
“通三统”之义本于“存三正”。按照《春秋》书法之常例,每年“正月”前书“王”字。然而,《春秋》又在有二月、三月前也书“王”的现象。一般来说,《春秋》当年首月是正月则书“王正月”,首月是二月则书“王二月”,首月是三月则书“王三月”,其他月份则不加“王”字。然而,《春秋》何以在正月、二月、三月前书“王”呢?在《公羊》家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历法有所不同,其具体的表征就是岁首之月的不同,夏建寅,以周之三月为正月;商建丑,以周之二月为正月;周建子,其正月便是周之岁首。因此,《春秋》经里所记之正月、二月、三月,便分别是周、商与夏三代的“正月”。[12]那么,“正月”又意味着什么?《春秋》开篇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3]在何休看来,“元”是天地未判前之元气,由“元”而判分天地,是以为“天地之始”。天地既判,遂有四时,春为四时之首,故“春”系于“元年”之后。[14]何休又认为,《公羊传》之所以将“王”解释为“文王”,是因为“王”字写在“春”字的后面:“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15]据此,“元年春”即天命所在[16],“王”即受天命的王者。有此王者,遂有王者之政教,是为“王正月”。[17]因此,《春秋》所谓“正月”乃受天命之王者的正月,是受天命之王者的“政教之始”[18],故《春秋》大之而称“大一统”。所谓的“大一统”,即以此受天命之王者的“政教之始”为大。
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二月”作为“殷之正月”,“三月”作为“夏之正月”,同样也当为受天命之“王”者的“正月”,所以《春秋》于二月、三月前书“王”,也就意味着《春秋》承认殷、夏两朝同样具有“王正月”,承认其各有受天命的“王”。换言之,这表明《春秋》承认殷、夏两朝的政权与周一样,同样是受命于天、具有天命的合法性。这样,在何休看来,《春秋》书“王二月”“王三月”,表明《春秋》兼具有三代之“正月”,是以又称之为“存三正”。《公羊传》既称“王正月”意味着“大一统”,则殷、夏两朝在他们各自的朝代同样可以说“大一统”。在此意义上,“存三正”亦可称“存三统”或“通三统”。[19]也就是说,以“三正”并存于《春秋》,以此可以证明“三统”共通于《春秋》。
《春秋》既然以“存三正”的方式承认前两朝政治的天命合法性,《公羊》家们便进一步提出了“存二王后”的说法,即在新王朝兴起的时候,将前两代王朝之后裔分封为诸侯国,让他们在各自封国内保留旧有的礼乐制度,即何休所谓“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20]于周王朝而言,存二王后,即分别封夏后为杞国,封殷后为宋国,爵位为最高等级的公爵。《公羊传》隐五年曰:“王者之后称’公’。”[21]又隐三年何休《解诂》曰:“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22]从某种意义上讲,“存二王后”就是“通三统”在制度上的标志。[23]一方面,这表明历史上之诸王朝之“统”均是合法的,其治世之法都具有天道的合理性,值得新兴王朝加以借鉴,从而以成新一代之治法,此即何休所谓的“师法之义”。另一方面,这同时表明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24]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通三统”说潜在的逻辑前提是,任何一个王朝都可能因其失德而不有天命。这一说法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当下的王朝失去天命,就有可能被新受命的“新王”所取代。如果“新王”取代了现有的王朝,则“二王后”也要随之变化。[25]庄二十七年冬,《春秋》记“杞伯来朝”。杞本为夏后,作为“二王后”,应该称“杞公”。而所以称“杞伯”者,何休注曰:“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26]按照何休的意思,《春秋》杞国国君不称“公”,是因为《春秋》不再视之为“二王后”,这就是所谓的“黜杞”。杞国既然被黜出“二王后”的序列,也就意谓着有“新王”代周而兴。既然有代周而起的“新王”,那么周就自然要被降而成为一诸侯国,此即所谓“新周”,且周国与宋国一起成为“新王”的“二王后”。宣十六年,《春秋》记“成周宣谢灾”。宣谢是周宣王的庙,宣王有中兴之功,其庙不毁,但是,宣谢发生火灾,天灾周宣王中兴之乐器,何休以为这意味着周王朝不再复兴,所以《春秋》书“成周”于“宣谢”前,就好像“成周”是一个诸侯国,即周王朝被黜而成为新封之诸侯“周国”,与原先的宋国共同构成新王朝的“二王后”,而作为夏后的杞国则不再被视为“二王后”。[27]这也就是如陈立所说的,“合宋、周,《春秋》为三统”[28]。
当春秋时,周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天子已名存实亡,天下实际上进入一个无王的时代,正如《公羊传》多次提到的“上无天子,下无方伯”。[29]这也意味着,周已失去天命,而有待于“新王”之兴起。但现实世界中并无真正之“新王”代周而兴。孔子有志于复三代之旧,却有德无位,不能成为现实中的“王”,只好退而修《春秋》,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抱负,行天子褒贬进退、存亡继绝之权。孔子通过其独特的书法在历史记录中加以“王心”,于是在董仲舒、何休等人的心目中,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以《春秋》当“新王”,通过《春秋》行王者之权,从而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践。
因此,对何休而言,《公羊》述“通三统”之义,并不仅仅只是论述“存二王后”作为一种制度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何休论“通三统”是在两个层面上讲:其一,通过《春秋》存夏、商、周之“三正”,以此证明“三统”是可通的;其二,对何休来讲,三统之更迭,本身就意味着前一王朝因丧失天命而为后王所取代,应有“新王”一统之兴起,是以其“通三统”说又具体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从某种意义上讲,何休之“存三正”说,仅仅是为了论证“三统”之可通,而一旦证明了“三统”之可通,则“通三统”原理之运用就可以指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此而言,何休对“通三统”的两说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何休论“通三统”,真正的意义是通过将杞国黜出“二王后”序列,并增加新封的“周国”,以此来论证“以《春秋》当新王”的合理性。因此,何休论“通三统”或“存二王后”,目的都是要引出“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核心结论。
Part.2
二、董仲舒的“通三统”说及其与何休之异同
何休依据“存三正”来论证“通三统”,董仲舒也是如此。《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30]
对董仲舒而言,“正月”的意义在于“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之后才有“正月”,因而“正月”也就成为天道天命的象征,这一说法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何休的先声。正因为“正月”是“王者必受命而王”所制月,所以说“正统正,其余皆正”,从而谓之“法正”。[31]《三代改制质文》又有“三正”之说,即夏、商、周三代的岁首。在董仲舒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其岁首也相应不同。夏建寅,物色尚黑;商建丑,物色尚白;周建子,物色尚赤。因而,夏、商、周三代分别为黑统、白统与赤统,每统各有其相应的礼乐与制度。[32]需要指出的是,何休虽然也认为三正有尚黑、尚白、尚赤之不同,[33]但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将三统明确地区分为黑统、白统与赤统。
“正月”是天道的象征,《春秋》统三正者,则意味着夏、商、周三代政权都有天命的合法性,所以董仲舒称“具存二王之后”,[34]这一思路与何休完全相同,即从“存三正”引申出“存二王后”。其又曰:
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35]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对于“存二王后”的具体说法,董仲舒同于何休,即封夏后于杞、封商后于宋、俱以大国,此即何休在隐三年注所说的“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36]然而,董仲舒与何休又有所不同,其不仅主张要“存二王后”,同时对于“二王”之前的更古老的王朝亦以“五帝”“九皇”而“下而极为民”以优遇之,如其说:“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37]不过,董仲舒的这些说法后来并不为何休所取。
与何休的思路相同的是,董仲舒述“通三统”“存二王后”,不仅要论证夏、商、周三代政权都具有天命的合法性,而且强调“通三统”说所要揭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永恒地拥有天命。“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38]按照这一逻辑,周王朝如果失德,那同样要失去天命,而为受天命的“新王”所取代。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中,董仲舒提出应当有代周而起的“新王”,此“新王”即是《春秋》:“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39]对董仲舒而言,《春秋》既然代周而为“新王”,则所谓的“二王后”就自然是殷、周两代王者之后,此即“亲周、故宋”之义。而原本作为“二王后”的杞国,在新的“三统”序列中就不再继续成为“二王后”。董仲舒以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为例,他根据隐公五年传“王者之后称公”的说法来追问杞国国君何以称“伯”,由此引申出“《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之说,又谓“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40]意味着不将杞国看作是“二王后”。杞不再被视为“二王后”,那么所当存的“二王后”自然就是周与宋,这也就进一步可以得出“以《春秋》当新王”的结论。相较而言,何休对“杞伯来朝”的注释与董仲舒的说法可谓如出一辙。
由上可见,除个别细节的说法之外,何休的“通三统”说几乎全同于董仲舒。何氏以“存三正”见三代俱有天命之合法性,进而由三代俱有天命之合法性而说“存二王后”,再通过《春秋》之“黜杞、新周、故宋”见周之不再有天命,而使《春秋》当新王,云云诸说,可谓俱见于董生之书,正如康有为所说:“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著。”[41]
Part.3
三、董仲舒与何休论“王鲁”
从上可见,董仲舒与何休之“通三统”说,最终都指向“以《春秋》当新王”。然而,《春秋》如何才能行王者之权呢?为了不使“以《春秋》当新王”流于空言,就必须有所假托,正如陈立所说,孔子“以匹夫行天子之权,不能无所寄”[42]。而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国,于是《公羊》家就设想假鲁为《春秋》之“新王”,这就是“王鲁”说。从这一意义上讲,“王鲁”说可认为是“通三统”思想应有的题中之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
“王鲁”之说首倡于董仲舒:“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43]在《春秋繁露》中,“王鲁”仅此一见,且对“王鲁”并没有太多深入的阐发。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董仲舒的文本,则可以发现董仲舒所述之“王鲁”当与“《春秋》当新王”同样有密切的关系。董仲舒在《王道》篇中说:“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44]这段话相当不容易理解。对于诸侯而言,相互朝聘本来是邦交国之间的常礼,[45]那么为什么董仲舒在此称“诸侯来朝者得褒”?为什么董仲舒又认为它是“王道之义”的体现?至于“邾娄仪父称字”之类的说法,更是令人费解。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放在《公羊传》语境下,同时再参看何休对这段文字的解读,那么,它的含义应该就可以涣然冰释了。
董仲舒称“诸侯来朝者得褒”,举了四个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不妨逐一对此加以分析。第一个例子是鲁隐公元年三月的“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称:“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46]然而,邾娄国与鲁国的结盟,为什么就要对邾娄国国君进行褒扬呢?《公羊传》本身对此并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对此我们只能参考何休所作的诠释。在何氏看来,邾娄仪父的本爵是子爵,之前因罪被周天子黜去爵位,按“名例”应该以“名”相称。[47]但是,因为《春秋》假托鲁隐公为始受命王,邾娄君能慕“新王”而率先前往结盟,所以《春秋》书“字”来表示对他进行褒扬。[48]第二个例子指的是鲁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滕、薛都是小国,《公羊传》称:“其兼言之何?微国也。”[49]作为小国,当以伯、子、男相称,爵不当称“侯”。[50]那么,为什么这里对滕、薛两国的国君却以侯爵相称呢?根据何休的解释,滕、薛两国是鲁隐公即位以来第一个正式朝鲁的国家,也就是率先来朝《春秋》之“新王”的国家,所以《春秋》对他们有所褒扬而称之曰滕侯、薛侯。[51]第三个例子是鲁庄公二十三年的“荆人来聘”。《公羊传》认为,《春秋》以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进退夷狄。[52]荆指的是楚国,从常规的书法来讲,不应该称“荆人”。而《春秋》之所以书“荆人来聘”,何休认为是楚国作为夷狄能慕王化,所以可以“进”而称人,这也是“王鲁”的体现。[53]最后一例是僖公二十九年的“介葛卢来”。介是夷狄小国,葛卢是介国国君的名字。僖公三十一年“介人侵萧”书“人”,而这里却称其名葛卢,何休以为,因为介国国君能“慕中国,朝贤君”,所以称其名以示进之。[54]这四个例子都是外诸侯来朝鲁国。如果视鲁国为周天子之下的一诸侯国,外诸侯来朝亦属常礼,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专门褒扬的地方。但是,如果根据何休《春秋》“王鲁”的思路,这些外诸侯能来朝《春秋》所假托之“新王”,所以就应该对他们有所褒赏。如果我们可以授受何休的这一说法的话,那么董仲舒所称“诸侯来朝者得褒”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从而也就可以进一步从中推出董仲舒所说的“王道之义”。
董子进而称,“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内出言如”,是指鲁国国君或大夫到其他诸侯国朝聘时,不称“朝”或“聘”,而称是“如”,例如庄公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陈”,就是指鲁大夫公子友到陈国去行聘礼。何休注云:“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55]依邵公之意,鲁国君臣到别的国家《春秋》用的是“如”字,从而与其他诸侯国到鲁国来用“朝”“聘”两字区别开来,这就是所谓“尊内”。《公羊传》隐十一年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何休解释说,鲁国的国君作为“王”,就不应该去“朝”其他的诸侯国,也就是说,“朝”字有降低“新王”地位的嫌疑,所以鲁国君臣到其他国家《春秋》都写作“如”字,在书法上与其他国家来鲁国称“朝”“聘”相区别开来。[56]从邵公《春秋》“王鲁”的角度看,董子所谓“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是“王道之意”的体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王道》篇这段文字就是对《三代改制质文》中“王鲁”说的最好阐释,清代的陈立在《公羊义疏》中即引用了董仲舒的这段文字来解释他所理解的“王鲁”。[57]
这种“王鲁”的精神,被全面地贯彻于何休对《公羊传》的解读中。如隐公三年宋穆公去世,《春秋》书“宋公和卒”,按照周代礼制,诸侯去世曰“薨”[58],则宋公去世当书“薨”。而《春秋》所以书“卒”,在何休看来,既然《春秋》“王鲁”,鲁君作为“王者”,死掉应该有“王文”,即用与王者相称的称谓书“崩”。但是,孔子作《春秋》所用文辞逊顺,鲁君去世不书“崩”而书“薨”。若然,鲁君又与外诸侯没有区别,所以就通过贬外诸侯之死曰“卒”的方式来体现鲁国的特殊地位,这就是所谓贬外以褒内;[59]反过来说,外诸侯死曰“卒”,较鲁君之死称“薨”低了一个位阶,则恰恰证明了以“王鲁”来解读《春秋》的合理性。又比如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公羊传》曰:“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在何休看来,“战”字意味着一种彼此对等的关系,所以称之为“敌文”。但是,既然《春秋》“托王于鲁”,鲁国被看作具有“王”的地位,那么鲁国与其他诸侯国在位阶上自然就是不相匹敌的,所以《公羊传》认为,凡是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交战,都不应该用具有对等关系的“战”字,这就是所谓的“内不言战”。[60]不过,如果是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交战并打了败战的情况,就必须对鲁国有避讳,就用“战”字来表明鲁国已经失败了。也就是说,《春秋》之“新王”与他国在身份上本来是不对等的,而现在用表示对等身份的“战”字,以此委婉地暗示了鲁国的失败。又例如鲁成公二年,《春秋》经记载“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手及齐侯战于鞌”。何休认为,曹国是小国,本来不应该书大夫之名,经文书“公子手”而不按常例书“曹人”,是因为曹公子手能追随鲁国的大夫亦即“王者大夫”征伐不义,所以书其名氏,即许之有大夫。又季孙行父等人都是鲁国的大夫,他们与齐侯交战,按照《公羊传》“大夫不敌君”原理本应该予以贬斥,而经文对他们不加贬斥,是因为《春秋》托鲁为王,那么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等四人就可以被认为是“王者大夫”,“王者大夫”在地位上相当于普通诸侯,而郤克等人则可以被认为是追随“王者大夫”,从而就可以与诸侯相敌而不必加以贬斥。[61]像这样的例子,在《公羊解诂》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如果说董子的“王鲁”说尚语焉不详的话,那么到了何休那里,“王鲁”有了更明确的内涵,并在其对《公羊传》的诠释中得到了系统表达,因而有学者认为“王鲁”说在何休“通三统”理论中具有核心的地位[62]。其实,如上所述,“王鲁”说在董仲舒的“通三统”理论中同样具有核心的地位。
Part.4
四、关于董仲舒、何休“王鲁”说引起的争论
自从董仲舒与何休提出“王鲁”说,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就有相当多的讨论,或毁或誉,或曲为之说,可谓不一而足。《史记·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63]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64]但司马贞对《孔子世家》的解读恐怕不太合乎汉代《公羊》家的本义。黄开国指出:“若据鲁为以鲁为主,就绝不可能与亲周、故宋形成所谓运之三代。”“此处的据鲁就是董仲舒的缘鲁以言王义,即以《春秋》当新王,在此意义上,据鲁与故宋、亲周,才形成了新王与周、宋的新’三统’。”[65]这一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吕绍纲指出:
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篇讲得很混乱,既言“亲周”,又言“存周”、“王鲁”,自相矛盾……细细寻绎,便可发现董氏以为《春秋》“亲周”而不以为《春秋》“黜周”、“王鲁”。[66]
吕先生不承认董仲舒有“黜周”“王鲁”之说,这一说法相当具有代表性。清代孔广森就认为,“黜周”“王鲁”绝不见于本传,而是东汉时博士弟子“因端献谀”而炮制出来的东西,因而不是董仲舒的思想;[67]至于“新周”,根本没有何休所说的“黜而新之,使若国文”的意思,不外乎因为周敬王避王子朝之难而迁徙至成周,因为是新徙至成周,所以称“新周”。[68]陈澧、苏舆等人就认为孔广森以新郑、新绛例“新周”才是正确的读法。[69]苏舆进而以此区别董仲舒与何休,认为司马迁的“亲周”不误,又称“史公学于董生,故其说颇与之合”。[70]因而,他批评何休误读董仲舒,称“劭公昧于董”,又称“新周则何妄推”,称何休“因王鲁造为黜周之说”,从而认为后人“为何注所误,读董子未明也”[71]。
后世学者对“王鲁”说则有着更多批评,即认为何休的“王鲁”说有悖于尊周,是悖礼诬圣,甚至以之为“《公羊》之罪人”,有代表性的说法如唐代的啖助与宋代的苏轼。[72]从某种意义上讲,诚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自魏晋以降,《公羊》学一蹶不振,颇有受“王鲁”说的牵累。[73]
但上述云云诸说,事实上是对董、何“王鲁”说的极大误读。《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74]《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75]据此,“王鲁者,即’缘鲁以言王义’,其义则在借鲁事以言王义、加王心而已。可见,在仲舒那里,鲁国只是假托的王者,而非事实的王者”[76]。刘逢禄指出:“且《春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且鲁无可觊焉。”[77]这说得非常清楚,“王鲁”只是假托,与尊周并不矛盾。[78]廖平指出,
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董子《繁露》言《春秋》有王法,其意不可见,故托之于王鲁云云。何氏因之,遂专主其说。[79]
康有为进一步阐述此义曰:
“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80]
总而言之,“王鲁”之说实本于“以《春秋》当新王”说,这正如刘逢禄所说的:“王鲁者,则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81]在这一意义上,董仲舒与何休并无异辞,因而段熙仲先生才说,“此真《公羊》先师之传,非何君一人之私言也”。[82]
Part.5
五、结 语
董仲舒与何休师法各异,他们在“通三统”说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细节上的不同表述,但在核心义理层面上,则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第一,从“三正”论证“三统”之可通,并由此推导出“存二王后”的主张;第二,根据“通三统”的原理,借《春秋》“黜杞、新周、故宋”来论证“以《春秋》当新王”等观点;第三,“王鲁”说作为“通三统”说的延伸,同样源于董仲舒,经何休进一步阐发,他们在托鲁为王这一核心要义上并没有大的分歧。尽管后世学者对“王鲁”说多有误解与批评,但其本质是借鲁史来寄托改制王法,是“新王”改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第一层的内含来说,所指的更多是时王之一统去通前两代王者的两统,更多关注新统与旧统之间的关系,这是汉儒的通说,董仲舒与何休虽然也这么说,但这不是其重心所在,黄开国先生说“何休实际上并不重视’通三统’”,即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在笔者看来,董仲舒与何休“通三统”说的真正精神在于后两个内涵,即“以《春秋》当新王”及“王鲁”诸说,这里所关注的不再是周与夏、殷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春秋》作为“新王”与周、宋的关系,而是《春秋》作为“新王”如何拨乱反正、如何“文致太平”[83],从而如何建立“新统”的问题。晚清的苏舆不能认同“以《春秋》当新王”说,其批评康有为曰:“三统改制,既以孔子《春秋》当新王,则三统上及商周而止。而动云孔子改制,上托夏、商、周以为三统。此条贯之未晰也。”[84]但苏氏此说,事实上未能抓住董、何《公羊》学的基本精神,真正“条贯未晰”者不是董仲舒、何休或康有为,而正是苏舆本人。事实上,正是“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才使得《公羊》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春秋》三传学术通史”(19ZDA252) 的阶段性成果。
[1] 《尚书大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7,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8页。)
[2]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关于何休与宋均“三科九旨”说的异同,参见郭晓东:《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论何休“三科九旨”说与宋均的异同》,《哲学与文化》2022年第11期。
[3] [清]刘逢禄:《春秋论下》,《刘礼部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4] [清]朱一新撰,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页。
[5]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页。
[6] 同上,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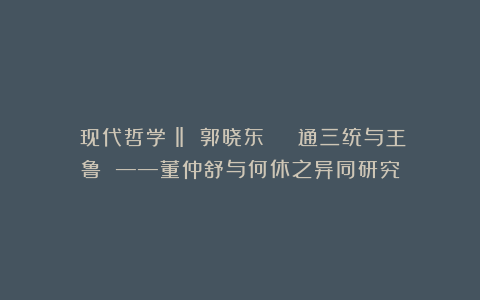
[7] [清]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5页。
[8]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98页。
[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玉杯》,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页。
[10] 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
[11] 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9页;林义正:《公羊春秋九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12] 何休指出:“’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7页。)
[13] 同上,第6-12页。
[14] 何休注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同上,第7页。)
[15] 同上,第10页。
[16] 徐彦疏曰:“元年春者,天之本。” (同上,第12页。)
[17] 何休注曰:“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同上,第11页。)
[18] 同上,第12页。
[19] 徐彦疏曰:“’统’者,始也,谓各使以其当代之正朔为始也。”此即三代各有其“王正月”之意。(同上,第57页。)
[20] 何休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同上,第57页。)
[21] 同上,第86页。
[22] 同上,第64页。
[23]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诏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成帝纪第十》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8页。)
[24]《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谨谦让之至也。”([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6页。)汉成帝时,刘向亦曾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参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第六》第7册,第1950页。)
[25] 刘家和先生指出:“三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同时并存,但三统则一个接替一个;虽同时有’三王’之称,但其中必有两者是先王,而真正的王同时期中则只有一个。”(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
[2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22页。
[27] 何氏曰:“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687页。)
[28] [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4册卷49,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85页。
[29]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下册,第220、367、368、377、658页。
[30]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4-185页。
[31] 同上,第197页。
[32] 《三代改制质文》曰:“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同上,第191-195页。)
[33] 隐公元年《解诂》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11页。)
[3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2页。
[35] 同上,第198-199页。
[3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7、64页。
[37]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8、199、202页。
[38] 同上,第187页。
[39] 同上,第187-189页。
[40] 同上,第197-200页。
[41]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8,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42] [清]陈立:《春秋王鲁说》,《句溪杂著》卷2,民国九年番愚徐绍启重印广雅书局丛书本,第7页。
[43]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7-189页。
[4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116页。
[45] 如《周礼·大行人》指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57页。)
[4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20-21页。
[47] 同上,第20页。
[48] 何休曰:“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同上,第20页。)
[49] 何休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同上,第108页。)
[50] 《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 (同上,第84页。)
[51] 何休《解诂》曰:“称侯者,《春秋》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隐公,故褒之。”(同上,第108页。)
[52] 《公羊传》庄公十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注曰:“《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孙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同上,第264页。)
[53] 何氏《解诂》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同上,第303页。)
[54] 何休《解诂》曰:“’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义。”(同上,第491页。)
[55] 同上,第315页。
[56] 何休曰:“传言’来’者,解内外也。《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同上,第110页。)
[57] [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1册卷1,第15页。
[58] 《礼记·曲礼下》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公羊传》亦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60页。)
[59] 《解诂》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64页。)
[60] 《解诂》云:“《春秋》托王于鲁,战者,敌文也。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战乃其已败之文,故不复言师败绩。”(同上,第171页。)
[61] 《解诂》曰:“《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明诸侯有能从王者征伐不义,克胜有功,当褒之,故与大夫。大夫敌君不贬者,随从王者,大夫得敌诸侯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704-705页。)
[62] 参见黄朴民:《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84页;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63]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孔子世家》(修订本)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52页。
[64] 同上,第2352页。
[65]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191页。
[66] 吕绍纲:《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第79页。
[67] 孔广森曰: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清]庄存与、孔广森撰,郭晓东、陆建松、邹辉杰点校:《春秋正辞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2-723页。
[68] 同上,第548页。
[6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0页。
[70] 同上,第189页。
[71] 同上,第190页。
[72] 啖助批评“王鲁”之说曰:“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宗指议第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0页。)苏轼也指出:“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论春秋变周之文》,《苏轼文集》第1册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页。)
[73] 张厚齐:《春秋王鲁说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5页。
[7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奉本》,第279页。
[75]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俞序》,第159页。
[76]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册,第269页。
[77] [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78] 此正如黄铭所说:“既然’王鲁’’《春秋》当新王’是假托,自然不会明显与’时王’产生矛盾。”(参见黄铭:《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231页。)
[79] 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41页。
[8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春秋例第二·王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4页。
[81] [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第152页。
[82] 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474页。
[83] 郭晓东:《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论何休“三科九旨”说与宋均的异同》,《哲学与文化》2022年第11期。
[8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例言》,第3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