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军(IDF)及其装甲部队的历史与谢尔曼坦克密不可分。从最初拼凑几辆英军遗留的翻修谢尔曼坦克作为装甲力量,到最终演变为索尔坦M68自行火炮和L33自行火炮等终极改型,以色列的“谢尔曼传奇”堪称现代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篇章。基于实战经验与作战需求演变,对二战时期这套可靠底盘、车体和炮塔系统进行的一系列装甲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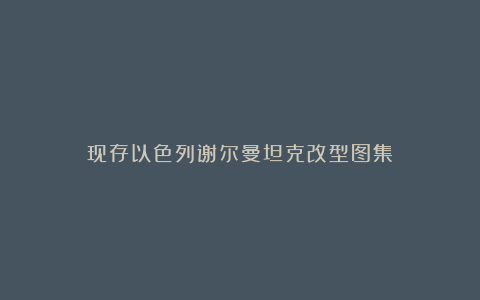
其中最早且最具战略意义的改型当属M50及后续M51坦克升级。换装新型75毫米/105毫米火炮并加装炮塔配重。1956年苏伊士战役期间,仍采用VVSS悬挂和原装发动机的M50首次接受战火洗礼。此后它们与M51并肩参与了’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而M50的谢幕演出则是在黎巴嫩基督教武装和南黎巴嫩军中服役。另一些M50/M51在智利沙漠坦克靶场结束了漫长生涯。此前它们曾在这南美国家长期服役。
谢尔曼底盘的另一重要发展是自行火炮系列,如M50自行火炮和“怒吼”自行火炮。这些武器在美国M109/M110大量列装前承担关键火力支援任务,甚至1982年贝鲁特战役中仍有’怒吼’火炮参战。1982年’加利利和平行动’期间,以军还出动了其他谢尔曼衍生型号。当时仍在服役的Makmat 160毫米自行迫击炮、装甲救护车、火箭发射车、观测平台、推土坦克以及驾驶训练坦克等。但在这一系列的改造中,或许最彻底的改型当属’戈登’或’开拓者’装甲抢救车。它不仅是以色列人对谢尔曼坦克情有独钟的见证,更是对这匹历经数十年以军服役、多重形态蜕变的老战马其朴素可靠品质的致敬。
谢尔曼迫击炮载车俯视图。索尔坦(Soltam)160mm重型迫击炮占据车体中央位置。车体两侧清晰可见的阶梯式弹药存储架,可快速取用160mm高爆弹/烟雾弹。该改型是以色列将二战M4谢尔曼坦克底盘与国产Soltam M-66迫击炮结合的产物,专为城市战和山地作战设计。160mm迫击炮射程约9.6公里,可打击掩体后目标,开放式战斗室便于快速装填,但无顶部防护,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曾用于戈兰高地反炮兵作战。以色列装甲兵博物馆保留唯一完整实物,其弹药架结构与炮座细节为研究以军炮兵改装思想的重要标本。
拉特伦博物馆M51’超级谢尔曼’坦克,改装为L44型105mm主炮。该炮为法国AMX-30坦克CN-105-F1主炮的以色列改进型,超长的44倍径炮管与巨大的炮口制退器是鲜明特征。炮塔后部新增储物篮(用于放置步兵电话、备用履带等),车体侧面加装附加装甲支架,发动机舱上方的防弹格栅。
以色列M50’超级谢尔曼’坦克技术解析。装备法制CN-75-50型75mm坦克炮,该炮为德国二战Panther“黑豹”坦克KwK 42 L/70主炮的法国授权仿制版,身管长度5.25米(70倍径),可发射APCR(硬芯穿甲弹)与HE(高爆弹),炮口初速达1,000米/秒,理论上可击穿T-54/55的正面装甲。采用47度倾角的M4谢尔曼原始车体,保留VVSS悬挂系统,发动机仍为原装R-975汽油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役中,该型坦克凭借高初速火炮成功对抗埃及装备的IS-3斯大林坦克,但暴露出三大缺陷:车体装甲无法抵御100mm以上火炮射击;火炮俯角仅有-8度,限制山地作战效能;弹药基数仅55发,持续作战能力不足。
M50’超级谢尔曼’坦克炮塔俯视图。炮塔后部焊接大型钢制配重块(重约1.2吨),用于平衡CN-75-50型75mm L/70主炮的前置重量,配重块内部设计为空腔结构,兼作储物箱使用。采用单扇向右开启的圆形舱盖,1960年后被双扇舱盖取代,未配备机枪架基座,仅保留潜望镜安装孔。炮塔左侧可见原厂铸造序列号,防盾处带有以色列军械厂改装标记。这辆坦克1956-1967年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服役,1970年代移交南黎巴嫩军基督教派武装,最终在1985年贝鲁特战役中被真主党武装俘获,现为黎巴嫩军事博物馆展品。
以色列M4工程坦克前侧视角解析。采用M1型液压推土铲,最大推土宽度3.2米。铲刃可调节至45度角进行斜坡作业,车体前部加固支架可承受3吨冲击力。保留105mm M4主炮,备弹36发。炮塔顶部加装M2HB 12.7mm机枪。同时存在VVSS悬挂和HVSS悬挂两种版本。后期型换装T80E1加宽履带。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用于戈兰高地战场清理。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参与苏伊士运河沿岸工事修筑。部分车辆加装反应装甲应对RPG威胁。该型是美军M1推土套件与以色列105mm火炮改造方案的结合体,其战斗/工程双功能设计开创了以军装甲工程车的先河。
谢尔曼坦克驾驶训练车顶部照片。移除炮塔的上车体结构,前部驾驶员舱门改装为双开式训练观察窗。该车疑似安装了’基尔雄’电子对抗系统,车体中部可见电子对抗设备的底座安装孔,发动机舱右侧保留电缆管道接口,原用于连接雷达干扰装置。为了实现训练功能,方向盘机构改为双操纵杆控制系统。该训练车现存于以色列塔尔希哈军事基地,其车体序列号(CT-42871)与1975年生产的‘基尔雄’电子对抗系统车批次范围重叠,但以军档案中该车被归类为’非武装教学资产’。
谢尔曼实弹射击训练车。炮塔搭载可遥控操作的M1919A4 7.62mm机枪。车体内部加装电子命中记录仪,通过激光模拟器判定’伤亡’。侧面焊接T-34/85坦克的后发动机舱装甲板,车体正面加装沙袋填充架。主要训练步兵在车辆10米范围内完成步坦协同动作,机枪发射空包弹配合爆音装置模拟战场环境。该车底盘来源于1944年生产的M4A4坦克。车身侧面的T-34装甲板,取自1967年六日战争缴获的埃及坦克,切割后重新淬火处理。以色列国防军装甲兵学校保留最后1辆完整车辆,其右侧装甲板仍可见阿拉伯语原厂铭文’乌拉尔坦克厂 №2176’。
M50自行火炮。炮尾下方增设弧形储物箱,带三防密封条。左侧工具架整合多功能支架,可固定斧头/镐头/牵引绳等设备。备用履带板垂直固定在车体右后侧,诱导轮外侧加装防淤塞护板,采用VVSS悬挂但升级为T62E1型履带。携带20发备用弹。后部储物箱主要携带炮膛清洁工具组和伪装网。智利陆军第6装甲团博物馆展品(编号C-147)仍保留希伯来文编写的《储物箱操作守则》原装标签。
以色列MAR-240多管火箭炮系统。1967年后,以军频繁遭遇埃及/叙利亚BM-21、BM-24火箭炮袭击。以军利用库存HVSS悬挂的谢尔曼底盘,整合法国’拉哈德’240mm火箭发射器与美制火控系统打造了MAR-240火箭炮。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部署在戈兰高地对抗叙利亚BM-24火箭炮,采用’打了就跑’战术,其履带底盘可穿越沙地/碎石地形,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轮式BM-21则难以通行。部分车体前部加装推土铲,自主平整发射阵地。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全面退役,部分技术转移至后来的LAR-160火箭炮系统,现存1辆完整样车于以色列炮兵博物馆展出。
以色列’EYAL’观测坦克。1967-1973年战争期间,以军为应对埃及炮击威胁,将退役谢尔曼坦克改造为全天候观测平台,替代易遭打击的固定观察哨,’EYAL’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雄鹿’,象征快速机动与战场感知。该车安装了可升降8米液压桅杆,集成SAGEM热成像仪+激光测距仪。每日前沿观测时间长达18小时,可以精确定位埃及炮兵阵地。并以“EYAL’观测坦克为核心创造了三车联动’战术,即以1辆EYAL+2辆自行火炮组成火力打击小组,完成即时打击。1970年10月,EYAL引导以军自行火炮,摧毁埃军12个122mm榴弹炮阵地。以色列装甲兵博物馆保留了唯一实物,其桅杆基座仍可见1972年9月遭迫击炮破片打击后的弹痕。该装备标志着以军从传统观测向数字化战场感知转型的关键一步。
以色列M32装甲抢修车(早期型)。采用VVSS悬挂。适配T48橡胶块履带,宽度420mm。安装A型架起重机,起重能力15吨。 车尾安装手动绞盘,拉力25吨。1967年升级后,换装HVSS悬挂,改装大陆公司AVDS-1790柴油机,车体侧面加装20mm间隔装甲。黎巴嫩迈尔季欧云军事博物馆展出1辆HVSS改型,其车体仍保留以军原装的希伯文‘זהירות! כבל משוך’(小心缆绳!)警示标识。
以色列早期型M4A4谢尔曼坦克。安装中期生产型M3炮塔,早期M34型防盾,单螺栓固定式火炮护套,采用克莱斯勒A57发动机。1956年退役后,火炮拆解用于海岸防御工事,底盘改造为’萨姆森’推土坦克。比尔谢巴装甲博物馆展出该型唯一完整车辆,其防盾上仍可看到修复焊痕。
以色列’阿基里斯’自行火炮。1956年苏伊士危机前,以色列通过法国渠道秘密获得12辆英制安装17磅炮的M10’阿基里斯’自行火炮。仅用于装甲兵学校反坦克战术教学,未参与实战。开放式炮塔侧壁加装法国CS-60型烟雾弹发射器。保留原装QF-17磅炮。其中3辆改为内盖夫靶场固定靶标。现存唯一完整车体,战术编号“T-731”,存放于以色列装甲兵学院。
以色列’螃蟹’扫雷坦克。1967-1973年间,面对阿拉伯军队在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布设的密集雷区(平均密度达2000枚/平方公里),以军将英制’螃蟹’扫雷套件与美制谢尔曼坦克结合,打造出扫雷版谢尔曼坦克。坦克安装的旋转链锤系统,共有44组锰钢链条,单条重18kg,可在90秒内完成扫雷/行军状态切换,有效扫雷宽度3.2米。车体底部加装15mm钢板,驾驶员观察窗换装75mm防弹玻璃。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 开辟了7条戈兰高地进攻通道,并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清除埃及混合雷场。戈兰高地旅博物馆展出了唯一可动实车,其链锤上仍嵌有1973年留下的埃及TM-62地雷破片。
以色列早期型M4A1(76)W装甲救护车。原装R-975发动机移至车体中部,新增液压散热系统。车体延长1.2米,可容纳4副担架或8名坐姿伤员。加装手术照明系统和-4℃恒温专用血浆冷藏柜。保留原76mm炮塔座圈,用作紧急出口。1973年10月14日泪谷’战役中,该型救护车在8小时内转移127名伤员。其发动机中置方案直接影响了后来’纳格马肖特’装甲车的设计理念,现唯一存世车辆保留于以色列军事医学博物馆,舱内仍可辨认1973年士兵用希伯来文刻写的’生命方舟’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