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艺术特征表现为神与人同形同性,抑或更为复杂的文化象征性转化。其艺术魅力不仅在于有高超的表现力,还在于其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新奇而丰富的想象力,尤其是所展现出的初民对开天辟地、波澜壮阔的创世之举的叙事,生动地再现了神话艺术超自然的神力,被后世广为传颂。故而,借助艺术史中的神话题材从叙事到隐喻的剖析,再到诠释思想,品评人类生命意识的意旨,集中到一点,即源于初民的敬神思想,可以展示出既独立又依附于历史环境的叙事与幻想双重特性。随着艺术学与神话学相结合的学术成果日渐丰富,从艺术史研究视阈出发,不仅可探讨神话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还可利用神话传说整合考古资料模糊了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研究界限。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对于全面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与信仰所带来的益处,也符合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加之,如今艺术创作领域对于古代神话题材往往有着新的现代化解读,这也使得重新审视艺术史中的神话佐证更具现实意义。
艺术史;神话学;神话题材;上古艺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夏燕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夏燕靖,艺术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与美育研究》集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八届学科评议组(艺术学学科)成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及艺术史学、艺术文献及理论、艺术教育史料。承担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专项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术著作《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文库,并荣获2024年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论文《艺术史研究中的史学观念》,荣获2025年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引 言
艺术史中呈现的神话主题,其关涉的内容无比丰富,并通常具有信史化的倾向,即许多神话事件被当作真实历史在艺术创作中投射,而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其创作动因多与先祖们根深蒂固的“敬神思想”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两类即为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这是先祖们对自然界的山、河、风、雨,以及干旱、雷暴和太阳星辰的崇拜,与早期人类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时因无法用科学知识解释,从而归因于神的支配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那些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做出贡献的先人们,也受到人们的崇敬与爱戴。因而,在上古时代产生灵魂意识之际,但凡人们遇到困难都会期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指引,于是自然而然产生祖先崇拜。这一情况集中体现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之中,即夏朝以前的神话和传说之中。这一时期,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涉及的人物大多无法直接考证,因而对于该段历史的叙述,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同样,对于域外而言,亦是如此。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传说,作为艺术家的表达方式,也自然需要通过艺术的渠道与世人达成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沟通,而艺术作品的神话主题尤为关键,体现出有智慧和创造力的艺术家必定会以人们所熟悉的“神话传说”为创作题材,以圣人为模样代替神的形象,让其充满想象力,又不缺乏亲切感,进而感化民众,达至人神合一、尊贵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古典时期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借用神话传说复兴“人文主义”的目的。
至此,艺术史中的神话题材表现特征,从创作形态来看,神话作为集体性的有意识的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体现了群体思维认知的共同性;从造型特征看,其神灵塑造多呈现为神人结合或人兽结合,反映了初民赋予自然以人性,同时也将人性融入自然界的双向想象。这类艺术形象融合了对自然的崇敬心理、部落图腾的信仰传统与对先祖膜拜的精神内核。更有甚者,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神话创作普遍采取了虚幻性构思、夸张性表现、理想化与集中化等艺术方法,这些都是艺术史中必然触及的神话主题。况且,中外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组合到艺术创作中,不仅将日常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而且创造出了无数巧夺天工的精彩作品,尤其是在表现远古时期历史变迁的风貌中,当初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和凶险的困境,自然就演绎出对无穷宇宙的追问和浪漫的想象。
上古神话的象征性是将神话看作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
艺术史中的神话主题起源于神话传说,中国本就是一个充满神话和传说的国度。这些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主要见诸先秦两汉的文学与编撰增补的典籍,诸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列子》等,从而被分散保存下来。虽说是片段,可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甚至是完整的故事叙事且伴有鲜明的象征形象,其神话涉足的领域异常宽广,叙事情节也极为丰富,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胚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典型性的又莫过于《山海经》,其记载的神话内容多具备开端式的性质,故而明朝人胡应麟赞其为“古今语怪之祖”。书中记述了先人们同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孕育出理解和把握世界一切规律的智慧法宝,将自然界无穷变化和威力,归之于神灵意志和力量的显现,从而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经典神话,并通过口头流传,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产生了诸多灿烂辉煌的艺术作品。诸如,山西道教宫观的永乐宫壁画,流传于市井中的民俗年画,还有戏曲音乐中的敬神乐章,成就了神话类戏曲的多彩绽放。应该说,中国上古神话的精神特质和艺术特征,在这些上古艺术中展现的就是尚德精神和民族特色,讴歌远古圣贤与历史英雄,展现了先祖无畏的精神品格,同时表达了对神圣形象庇护众生、造福人间职责的敬仰之情。这种精神特质和民族性集中体现在神话人物的品格塑造上,即“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这直接体现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众多神话故事的传颂中,这些形象始终充满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舍己利群的担当精神、憧憬未来的梦想精神与和合同心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特质通过对圣贤与英雄的歌颂得到彰显,如上古圣贤尧、舜、禹等,正是通过他们的智慧和德行,“表达着上古文化建构时期的国家政治理想,其垂教后世,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虽说这些形象总是带有神话般的想象,但皆源于远古生命实践,展现出初民对德行、力量、生命与自然的敬畏情怀,已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重要象征。
自然,神话不同于传说,二者绝非雷同。神话演述的是神,传说演述的则为远古或古代英雄。然而,在千百年流传历程中,逐步演化为神话和传说的混合体,也可说比比皆是。因为这两者都同时记载着我们先祖的超凡能力和心中梦想,所以传说也往往作为神话流传而不分彼此。质言之,远古神话展现的是初民的浪漫主义创造性特质,通过幻思与艺术夸张的手法,诠释出初民对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认知与畅想。可以说,这些神话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底蕴,其内容歌颂生命不断繁衍的创生力量,彰显出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赞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体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追求。如是,在艺术表达上,神话具有绚丽的情感色彩,特别注重情感的夸张表达,反映出初民对所感知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独特理解,这些体验经由“幻想”与“幻象”的加工处理及升华,形成既具神性色彩,又有映射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更显示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探索,塑造坚持不懈、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形象。
例如,在上古神话意象性艺术特征中,中国神话在表现形式、意象体系和记述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以神祇意象为核心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与“华夏先民以’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有关”。又如,上古玉器的形制、纹饰和琢玉风格大多采用象形与转喻的创作思维模式,即“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的象形与转喻。通过雕刻各种象形的神灵形象,就赋予和转喻了这些玉器通神的法力”。这些不同时期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遗存,不仅展现了初民们对自然万物、宇宙人生的认知演进,还体现了初民通过艺术创造来理解世界的创举意识。可见,中国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本源的精神创造,既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思考,将初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全都融入艺术的表现之中,既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头,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基石,对我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此,神话虽说产生于远古时代,但却反映出初民凭借其历史有限的认知能力,对自然界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现象做出的切合实际的阐释,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来,历经风雨的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念,使得我们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记忆,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每一个成员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并构成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各民族虽说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但都具有相互贯通的民族话语,尤其是其中蕴含着的人文哲理与文化主题,终将紧紧汇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艺术发展的主流。进而言之,中华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应该说自远古社会文明孕育初始,各民族各地区流传的神话就赋予了人类社会无穷的魅力。比照域外地区来看,如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乃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等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度,也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远古神话与不同文明并存,只是他们的民族观与我们的差异较大。诸如,中国古代神话源自盘古开天辟地、引生万物,而域外神话则多沉浸在创世故事的描述中;中国神话突出体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内涵,而域外神话则多体现“天人二分”的观念;中国神话中的神是理性的化身,而域外神话故事中的神则显现感性特质。就考据来说,神话作为文明的源头,既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线索,又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难以磨灭的信仰印记,尤其体现出神话源流与社会文明的同源同流,一直以来备受历史学、民族学、文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高度重视。
进而言之,在探讨神话的艺术特征时,比照中西方神话,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就西方神话而言,“神与人同形同性”的特征可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其不仅体现在神与人的外貌相似性上,还深层次地反映在其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当中。这种拟人化的特征使得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高度的人性化特质,如宙斯、赫拉等神祇不仅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同时也展现出爱、恨、嫉妒等丰富的人类情感,学者王以欣认为“希腊神话的拟人特征可能有其近东渊源,但希腊人将之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希腊人的理性、人性和审美情趣决定的,是希腊宗教世俗化的产物”。
再有,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将神话视作生命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进而阐明神话展现了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以及情感的外在呈现,并进一步探讨了艺术与神话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这种关系在空间结构、时间逻辑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体现,即“神话思想坚持总体的描述和自身满足于想象所发生的事物的单一过程。在这个事件中,某些典型的特性可能再现,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个法则、一种特殊限定的形式化条件”。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神话主题与圣人造物思想
相比之下,中国神话在“神与人同形同性”的基本构形上有了进一步转变,呈现出独特的“人兽同体”特征,抑或是在神与人之间发展为更加复杂多样的关系,这种特征反映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与“人文”统一性的深入理解。
首先,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神祇常常以动物或超自然的形态来呈现。例如,龙、凤、麒麟等神话生物通常是自然力量或高维度生命体的象征。至于女娲、伏羲这样的人头蛇身形象,则属于人兽同体的超自然形态,它们与人类形象差异显著,更注重神话叙事中的人性象征性表达。这种特点在《山海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中记载了大量人与鱼、人与鸟、人与蛇相组合的形象,这些丰富多样的神话内容不仅展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社会和宇宙的深刻认知,也反映了他们卓越的想象力。与此同时,这种“人兽同体”的形象塑造,实则是初民通过神话叙事来理解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独特方式,它们既展现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表达了对理想秩序的追求。这些形象往往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显现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事实上,神话作为文明的源头,既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线索,又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难以磨灭的文明信仰之印记。况且,从中西方神话艺术特征的比对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不同文明对神性的理解与表达。诸如,西方神话人物主要体现在对个体英雄主义的歌颂与塑造;东方则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然现象的拟人化解释,实现对神性的表达。这种神话源流与社会文明的同源同流关系,不仅揭示了神话艺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出不同文明在神话艺术表现上的独特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最高层次的追求。
进一步说,以中国远古神话为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传说、女娲造人的生命神话、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居、燧人氏开创钻木取火等神话传说,流传久远。然而,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从近代考古学、古生物与古人类学以及地质学的发展角度给予窥探,其揭示的都是有着历史事实的依据,或是对人类认知世界的懵懂揭秘,抑或是人类作为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历程写照。对于考察而言,当我们论及中华文明所涉及的源头,或者说中国艺术史和远古艺术形态的考据,往往都有着“圣人造物”的理念作祟,并以此证明“人神共存”的纽带联系。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尤其是关于造物艺术的部分,均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如《周易》《周礼》及诸子百家的论著,其中关于造物、造物者,乃至《考工记》中的“智者创物”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这些文献资料显示出一种“被神化”的阐述特质,如在器物层面,一是玉器艺术,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鸟”及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等,这些器物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深厚的神话象征意义;二是青铜器艺术,尤其是商代青铜器,因其神秘感和威严感而被神化,成为统治者巩固地位所需的观念物质化产物,其装饰艺术既体现了社会生活和思想认识上的审美观念,又带有明确的“神话与仪式”的目的。同时,这种神圣化特质在礼制文化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正如《礼记》中所言:“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其突出了祭祀器物在典礼中的关键作用,印证了造物艺术“被神化”的内涵。这种传统亦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史中重要的理论特征,而这些记载由于历史原因,有的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了辩证唯物论思维的阐释,但多数却被后人有意或无意地赋予了神性色彩,成为神话和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巢氏雕像,巢湖南岸巢父生态园
旧石器时代的用火遗迹
燧人氏钻木取火
回顾历史,就中国神话史构成来看,曾有过三次创神过程。首先是“五帝”“三王”时代(夏禹、商汤和周文/武王)的历史神话化,其具有神秘性思维最为高扬、神权思想最为浓厚的时代象征。其次是黄帝、蚩尤之战的反映与论述,再次证明构成中国神话的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且是依附于历史文化思辨的形态。再者是关于气候变化的记载,反映出初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的客观认识,凸显出主体历史观所发挥的应有作用。具体而言,这些神话均涉及我国远古时代,初民们对造物的认识过程,可以从大量的文献典籍中获得线索,这里列出传说和史籍记载来加深理解。比如,远古神话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如果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在旧石器与新石器过渡时期,距今约9000年。传说初民巢氏,又称“大巢氏”,为远古时期教民巢居的圣人。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可知,有巢氏构木为巢,使得人们由穴居到巢居,以此规避早期人类受到野兽威胁的风险。至于燧人氏,乃开创钻木求火之术的先贤,见于“燧人氏钻木出火。造火者燧人也。因以为名也”,说明燧人氏以取火为业的身份。又如,神话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时代,也是相传黄帝创始蚕桑、舟车,以及开创饮食文明的形成期。诸如“炎帝于火死而为灶”,“轩辕······艺五种,抚万民”,“黄帝始蒸谷为饭”。可见,随着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兴起,初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转变,以谷食为主、蔬食为辅,并搭配少量肉食,这一发展既推动了初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在神话传说中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早期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创造,提供了关联性的证据,进一步显示出文明乃是社会进步和开化的标志性写照。又如,《易经》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经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表明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均以自然为参照,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就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状态的向往,万物竞生、事象和谐,这是初民们摆脱“野蛮”进入文明发展的启蒙思维。
黄帝轩辕氏
陶甑·新石器时代,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战国尖首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
四轮独辕木车,秦陵西区陪葬墓
由此可见,以上这些神话内容都与圣人造物的叙事内核密不可分。在这类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一些被后世视为神话传说的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等古代先王,他们作为中国古代设计文明构成的代表,被认为在设计创物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往往都带有神话的特殊色彩。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神话内容不仅是初民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表达,还是对古代设计思想经过神话演绎的一种传承。通过对这些神话传说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设计造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往往会受到质疑,但属于神话研究的路径终究可以破解,即神话不只是远古人类单纯的文化行为的记录,更是为后人发挥造物想象提供的一种溯源依据,其包含着历史意义的记录和人类心路历程的印迹。至少它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其蕴含并表达了心理的真实性,尤其是从古代文献中研究中国古代设计与设计思想的构成时,解读这些神话故事已成为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其实,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关于创世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都可以说是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的辉煌篇章,并在全世界各民族流传的神话中尤为突出。在东西方关于神话传说中的“圣人造物”这一母题上,可以说无论是盘古和女娲,还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帝,世人对他们的能耐的颂扬都表现为一个十分相似的主题,就是赋予圣人造物的丰富想象。就像在中国远古的创世神话中,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类,而在《圣经·创世记》中,同样表现有上帝七天创世的传说。从这一角度来看,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的神话,与《圣经·创世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唯有不同的是我国的神话将开天辟地与造人大业做了明确分工,让男人开天辟地,让女人繁衍生息,而耶和华创立天地、创造人类却是圣人独自所为。当然,在这背后还存在着东西方许多不同的世界观、自然观和文明观。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张岱年阐释道,中国古代文学较之西方文学传统,呈现出独特的人本特质与理性思维。在上古神话体系中,中华初民尊崇的并非如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中超然于世的神明,而是富有非凡才智、创造文明功业的人间智者。由此观之,中华上古造物神话叙事中的圣人,仍是“人”而非“神”,体现着人文色彩而未全然神化。“这些神并非超脱于人的异质力量,实则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凝练与升华,他们立足尘世,专注于化解灾厄、安抚黎民、开创文明等功绩,是对原始生产实践的艺术性表达。”可见,中国上古神话彰显出的鲜明人文色彩与理性精神,既是其文化特性,也是其艺术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
概括而言,尤其从艺术史或者说设计史的视域来看这些涉及造物活动的神话内容,可归纳为三方面的共性认知。
其一,上古造物神话、传说中的创造物是真实存在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其记录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然而,这些记录与记述不应被视为客观的历史真实,特别是此类创世传说倾向于将文明发展的重大创造归功于某些超凡智者,如“神人”“圣人”,这些不一定是事实,但有着“祖先崇拜”等信仰及幻想成分,因此可归结为当时的一种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普适性的社会意志。
其二,探究创造万物的神话与传说,能窥见初民对创举的认知模式、理解方法及其思维轨迹。以《周易》的“观物取象”这一思维为例,此种取象造物的理念,既体现了形象创造的方式方法,又蕴含当时人们深层的设计理念与哲学。这些流传至今的设计理念与造物智慧,并非纯属神话中的虚构或夸饰,而是保留了宝贵的历史信息。由此观之,对此类神话叙事中蕴藏的创造思维与设计方法进行深度解析,对于构建完整的古代工艺史与设计史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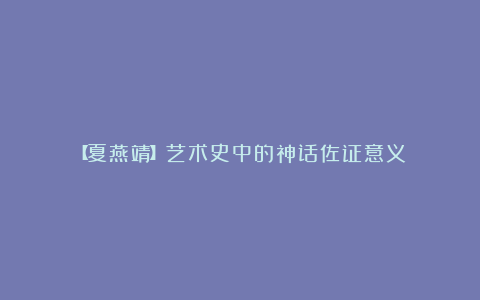
其三,神话故事除却其表层的叙述与阐释功能外,通过考察远古创世传说,还能从新颖的维度上探究上古文明中所潜藏的史实依据与文化内涵。此类研究有助于阐发艺术史学中的人类学思维,解读华夏民族在物质文明创造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认知与文化思想。进而言之,创世传说彰显了与人类创造行为密切关联的发展轨迹,体现了初民对艺术与设计创作的审美评判。基于此种观照,作为我国古代艺术发展研究的关键环节,造物神话亦映射出艺术实践背后的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就造物神话而言,其中可用于艺术史学理论研究的部分,均起到了文献支持的作用,是需要通过深入挖掘与解读,尤其是要辨别同一则神话中出现的论述,到底是“历史”还是“故事”而给予判别。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客观事实和主观解释的综合体,它不仅涵盖了实际发生的事件,还包括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在古代神话体系中,对历史的叙述和历史事件的“叙事”本身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以至于神话虽然源于社会生活,但与历史现象本身的“真实性”存在差异。神话通过幻想和夸张的手段,以超现实的形式表现社会生活,因而它并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然而,神话中又确实包含了大量历史事件的影子,如圣人造物、氏族更替、部落冲突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性。与之相比,神话以及关于神话的评述,还往往叠加着较大的时间跨度,一个神话母本随着时间的推进,衍生出无数版本,以及反映出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无数片段,而不同版本中对相同人物和事件的差异性反映,也往往体现出当时社会的意志和统治者的意愿。若从这一角度出发,确实可将艺术史中的神话佐证视作一种兼具客观真实与虚构幻想特征的文本材料,其丰富性、复杂性和想象性是交织存在的。
三
神话与中华文明互证中的艺术史观呈现
中国神话源远流长,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的创世神话,到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的英雄神话,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和深邃的哲理。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中。这些神话不仅是初民的想象和智慧的写照,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的独特展现,尤其是神话以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独特的艺术形象塑造,展示了神奇而又充满哲理的世界,反映出初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初识,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爱情和死亡的看法。这种以寓言和象征的形式进行表达,其传递的初民智慧和价值观,从中可窥见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文化传承价值。可以说,中国神话是文化与艺术源远流长历史的重要源泉。
故此,见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神话故事也常常融入历史的叙事之中,这些故事不仅赋予了作品深邃的思想和情感,而且神话元素的加入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内涵,更成为历史佐证的价值之所在。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上古“人神共存”的年代里,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仙人居于上。又如,西北甘肃平凉是广成子得道成仙的修炼之地,还有泾川西王母、泾川玉都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闻仲等。相传天水是伏羲故里、黄帝问道所在的崆峒山,即广成子修道之地。远在黄帝出生之前的上百年,阐教高徒广成子驾驭仙鹤,降临崆峒胜境。只见山中林海葱郁,峡谷含翠,泾河与胭脂河宛如银带盘绕山脉,波光潋滟,面对此般清幽秀丽的仙境画卷,遂生驻足修行、涵养道法之意。于此,甚至可以言之凿凿地认为,神话与区域文明有着佐证历史的必然联系。
纵观上古神话《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直至如今的仙侠网络文学,可见神话的叙事脉络始终贯通其间,其构建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审美维度。就戏剧舞台艺术而言,神话故事借由表演者的艺术诠释与舞台意境的营造,升华为多维度的感官体验。从传统戏曲到地方剧种,神话叙事皆构成其重要的艺术内核。此外,在造型艺术范畴上,创作者们通过绘画、雕塑等多样的艺术语言,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场景具象化为形神兼备的视觉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代岩画、石雕遗存,至今日的现代插画、漫画或数字影像,神话元素的融入不断激发艺术表达的创新可能。可见,神话故事并非仅停留于远古遗响,其当代价值也持续彰显,为当今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与素材。
举例来证,最近一款十亿级的国产爆红游戏在全球大放异彩广受欢迎,使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及其主角孙悟空再次成为热门讨论的话题。当然,《西游记》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属于经典化的文学作品,其经典性不仅源于时间的沉淀,还源于其延伸作品的不断创新。作为一部融汇各时代众人智慧、代代相传的文学巨著,《西游记》的雏形源于《大唐西域记》,后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游记平话》及《西游记杂剧》等演绎,构成了一系列演变中最具关键价值的基础文献。再经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之手,演化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魔小说,可谓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性作品。书中主人翁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唐僧从投胎到取经归来共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抵达西天取得真经。这个故事历经世代传播与不断丰富,成为世代积累、不断衍生的“神话”叙事巨著。其中,“’一记一传’共同开启了’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如《诗话》奠定了《西游记》文本演化的神话性方向和降妖模式,《杂剧》与《平话》则使《西游记》人物全面定型,情节构架宣告固化”。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古典奇幻小说的代表,这部作品始终拥有广泛的阅读人群,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促使其跨越时空,成就不朽地位。这部巨作的经典性与深远影响实则根植于唐僧求法的历史事件之中,并在探究域外文化的同时,将中华思想播撒异邦,堪称古今罕见的文明交流使者,而西游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反而不断地在时代的辗转中被改编和续写,从文学创作到搬上荧幕,唐僧师徒的形象不断被演绎与诠释。不同的时代对这个西行取经故事有着不同的理解,大量基于原著的二次、三次、四次的改编创作,将原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断丰满,融入大量原著中未曾出现过的,但却在民间神话中与之相通或关联的形象与概念。于是,便有了游戏科学公司制作的《黑神话·悟空》的问世。该游戏深度汲取了佛教、道教以及民间神话传说的丰富素材,并将其中的某些概念与意象巧妙串联,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内核脉络。例如,穿插于游戏六个章节中的六件被称为“大圣根器”的重要道具,分别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六件根器不仅代表了悟空的六个部位,还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原型来历。
《黑神话:悟空》游戏
《黑神话:悟空》游戏中建模与实景对比
以第一件名为“眼看喜”的大圣根器为例,其视觉表现为一只重明鸟,其“双睛在目”为重瞳,故名之“重明”,源自“尧在位七十年······有祇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眼在目······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以重明鸟之形象比作孙悟空,恰是象征着两者皆有着驱恶辟邪的神通。又如,第三件根器,则为“鼻嗅爱”,其造型为十尾金鱼,是游戏科学公司的原创,但原型也参考了“泚水出焉······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芜,食之不”。《山海经》中“茈鱼”的形象,这里将一首十身的“茈鱼”重设成了十尾金鱼,除了造型喜感更加易为大众接受之外,还借用了《山海经》中的一个有趣传说,将“茈鱼”能发出蘼芜的气味,乃是初民用于装在香囊中的“香料”,恰与游戏情节对应,实为巧妙。再如,第五件根器“身本忧”的对应造型为双头猪,这一形象同样出自《山海经》,在《海外西经》篇中提到一种名为“并封”(亦称“屏蓬”)的怪兽,其云:“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双头猪的形象油然而生,象征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与游戏中的情节适配。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在神话故事的构建和角色形象的塑造上,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风格。同时,游戏还巧妙地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说书以及民间戏曲音乐的元素,进一步丰富了游戏的文化内涵。它不仅重新诠释了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魅力,还以“重走西游路”的创意设定,为传统文学艺术作品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当然,这款游戏中造型设计的原型无不出自古籍经典或者民间传说,而造型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寓意和意象,则反映出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游戏中的道具“大圣根器”——眼看喜,原型为《拾遗记》中的重明鸟
游戏中的道具“大圣根器”——鼻嗅爱,原型为《山海经》中的茈鱼
回归到艺术史的角度来说,上述案例可归纳出关于中国神话艺术创作的一大特点,即“非显性”,这种特质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思维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艺术整体表现形式上,中国神话并非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是通过构建神祇形象(神话意象)来进行象征性表达。这种意象化的表现手法,使神话叙事超越了表层的故事摹写,转而通过丰富的象征和隐喻来承载更为深邃的文化内涵,强调的是内在精神与情感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现特征亦与早期中国神话的叙事结构存在内在关联,即神话中看似零碎、残缺且不成体系的非叙事形态,实则依赖于意象化的艺术图像叙事来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系统(或曰“故事系统”),通过描绘超自然的力量和幻象的形式来塑造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自然需要观者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感知去体验其中的丰富意蕴,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思维特点,还揭示了深层的文化表达逻辑。另一方面,在神祇形象的艺术塑造上,中国神话更显示出与西方神话迥异的审美取向。中国神话中的神祇形象往往呈现出神秘而内敛的特质,较少具有明显的生物性特征,与人的相似度也并非过高。这种意象表现方式,使得神祇形象超越了自然拟人的演化,而被赋予千奇百怪、扑朔迷离的形象释解。这一超越迥然不同,可谓是灵魂世界的重新塑造,转而面向精神境界和文化内涵的深度追求。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重神韵”“寄意境”的艺术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重视内在精神传达,而非外在形式呈现的审美追求。可以说,这种“非显性”的艺术表现特质,不仅构成了中国神话艺术的独特魅力,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艺术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此外,这种艺术特质更深层地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神话的演绎态度之中,并在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比如,在日本汉学家白川静的《中国神话》一书中,专设有“中国神话学的方法”一节,就特别指出:从祭礼实修形式去探寻中国神话意义的解释学方法并不有效,因为中国神话连同其祭仪形式与具体内容都几近失传,呈现出隐藏性的存在状态。故而,中国神话研究须以发掘这些被隐藏的神话为起点,继而复原其原初形态。当然,这种“隐藏性”的确广泛体现于儒家、道家的著作之中。比如,提及儒学总会浮现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等孔子言论,让人产生疑惑。当探讨孔子是否信奉神祇鬼灵等超自然存在时,就断言其不信鬼神,则无法自洽于其“敬鬼神而远之”的论述。并且,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尊重而非怀疑,他强调“敬”,这表明了他对鬼神的基本立场。更进一步解释,孔子提倡“敬而远之”,这与历史上宗教信徒对神圣事物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相一致,此说旨在避免过度亲近而导致不敬或亵渎,这种态度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深深的虔诚之意。由此可见,将“敬鬼神而远之”诠释成否定神灵或纯然世俗的立场,与孔子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一点也可从《论语》中看出——孔子对鲁国太庙和乡村祭祀活动表现出庄重和恭敬之举,看出儒家与宗教礼仪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在分析隐藏在“不语怪、力、乱、神”这句儒家经典话语背后所蕴藏着的非无神论内涵以后,才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考工记》,其中提出的造物智慧之原则“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的观念,实则也是基于神话思想渊源的造物理念的摹写。
自然,不同历史阶段皆具特定的想象维度,各类文明亦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艺术史学与神话学研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相辅相成、联系紧密,两者均需深入剖析符号与象征体系的内在结构,以达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和比照阐释。而要获取此种认知并非易事,首要前提便是需要确立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摒弃传统的自我中心论的文化倾向。此点再次凸显出当代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人类学思维转向”的关键地位。同时,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核心要素,持续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丰沛养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价值,为艺术史研究与写作开拓了多元思路与方法转变。
四
神话与艺术史研究的构成关系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
其实,就艺术史研究的叙事结构而言,其呈现出以“神话”“宗教”和“图像”等核心母题为基础,并从贯通古今的“历时性”内在结构展开,建构出一条探究“共时性”的史学路径。在西方史学领域,像意大利历史学家乔万·维柯的《新科学》一书就阐明了他对研究历史问题的主张与神话学内涵关系密切。他认为,穷本溯源应以部落自然法为起点,论证人类及社会制度的发展进程。以此,维柯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历史划分的设想,如历史可分为神、英雄、凡人三大时期。在《新科学》中维柯举证“发现了真正的荷马”,结合古希腊神话研究解读荷马史诗,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路径:将文学作品的文本解析与时代语境、作者阅历、社会变迁等要素融为一体。这一方法论奠定了其历史发展理论:历史呈现递进规律,各民族发展皆需经历神性认知阶段,并承认神意主导着历史的发展。
有意义的是,维柯提出的三个时代的历史划分为后世历史哲学奠基,启发了赫尔德、黑格尔和孔德等人的思考,即对历史的研究需遵循某种不为人知的规律性目标,这一观点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历史思想中确实有所呈现。历史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这一点在伏尔泰、赫尔德、席勒等哲学家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而维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则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作用的多方面剖析上。在《新科学》一书中,他从“诗性智慧”“语言形成”“文明源起”以及“历史循环”四个维度出发,以神话为切入点,结合原始社会的特征和思维方式,为理解早期人类文明开辟了一条独特且富有价值的路径,也为解析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框架。书中对神话进行解读并揭示了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轨迹,对神话的价值予以肯定,进一步在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研究中运用该种方法,对后续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一种富有启发性意义的研究思路。可见,维柯的这种将神话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不仅影响了后世的历史哲学研究,还为艺术史研究中神话文献的采集与运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因此,艺术史中的神话佐证意义,其实并不难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逻辑的话题。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有足够的史料、实证可以阐明这一点。举例来说,日本讲谈社推出的百年华诞献礼之作《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十二卷,就是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当代中国。首卷作者宫本一夫,是京都大学文学博士、考古学家,现任教于九州大学,专攻东亚考古学。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曾参加过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内蒙古岱海遗址群等中日联合考古发掘工作,至今仍然热衷于在中国从事水田农耕的考古研究。宫本一夫的第一卷《中国史研究》,是从三皇五帝到夏朝。根据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夏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终于公元前16世纪,距今至少3500年。那么,关键是神话时代比夏朝更早。在首卷书的序言中作者提出了三个主要解决的问题:其一,对于神话时代和夏王朝,为何不能完全相信史籍的记载,而要用考古学作为验证?其二,关于夏王朝的历史定位问题,考古学界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其三,针对中国文明源头而提出的“两条文化轴”理论该做何解读?由此,对这三问的追寻,可以发现将神话内容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资料需要很多先决条件做基础,比如考古学研究成果的融入,要考虑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性,以及从多元视角出发,考虑到不同文化因素在多民族地区存在的交流与互动现象,等等。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书影
事实上,神话是初民在日常生活里,透过幻想世界中的想象,积极地寻求自己对生活目标的满足。神话乃是原始社会的种种现象在初民原始意识中的积淀反映,以上古现实生活与经验作为基础,它反映出初民的意识形成和生活经验。所以说,上古神话除了具有文学研究价值之外,可以当作研究上古时代艺术历史的重要文献素材。诸如,从神话思维的角度可以佐证出原始宗教和神话构成的密切联系,这是成为艺术人类学的初开研究项目。再之后,便是明确地认识神话与艺术之于艺术史的开篇意义,如《三皇本纪》中出现的伏羲、女娲和神农(也有以燧人代替女娲的)。在汉画像石上,伏羲和女娲是蛇身人首造型,神农则是人身牛首造型。从这些描述可以判断这部分记载属于神话。而神话作为艺术史考证范畴,不应仅仅当作历史记载的问题来讨论,还应与原始宗教、哲学和种种上古社会生活形态联系起来,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创造观念,追求对人类文明观念下的艺术史整体客观的认识。于此,探究艺术史中的神话佐证意义,与艺术史的构成可谓一脉相承,并且,它是用神话与考古发掘来佐证艺术史的缘起、发生和发展。
史前艺术指人类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没有文字记录之前的艺术范畴,大概在距今30000至8000年之间,在五大洲都有分布。这个时期的艺术形式主要有雕塑、岩壁和建筑,有写实也有抽象,与现代艺术很相似,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交感巫术、崇拜,且是人类对世界观的一种表达,尤其是宗教和文学艺术起源后,人们再以神话作为它们某些方面的研究资料。至于研究方法则是采用西方的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从神话思维、原始宗教、上古神话三方面着眼。先提出神话思维,再按顺序阐明神话思维流传到原始宗教乃至上古神话的历程。着重阐述神话的起源和它对艺术的影响,以艺术的形式确立民间信仰与上古神话之间的实质关系,并且可以肯定地宣称神话思维是中国上古神话和民间信仰的基础,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进而显现出艺术与神话及宗教起源的探讨是必要而且有价值的工作。
换言之,神话是古代先民对周围自然和社会现象带有幻想性质的一种解释,即通过想象力的加工,将真实历史转化为“被神化”的版本,这些故事体现了初民试图理解和掌控自然及社会的愿望,因神话在物质文明较为匮乏的史前时代,即人类尚未具备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能力之时大量产出。
因此,在将神话学融入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无法以文字资料加以佐证的艺术作品,自然需要结合神话传说起到历史实证的参照作用。例如,当代艺术史研究借鉴人类学这一新视野,结合图像证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先秦竹简中大禹建夏的记载,阐明大禹治水,受禅让于舜。禹即位后,居于阳城,定国号为夏,夏朝建立,召开诸侯大会于涂山,铸造九鼎,天下一统。但诸多文献对此事的记述差异较大,如《竹书纪年》与《史记》对于大禹在位时间与所行地域的记载有所不同,虽不至于影响史述的基本面貌,但关于先秦时期大禹治水的真实性问题仍产生了一些争议点,但好在彼时虽然中国还没有步入大一统时代,无论是西边的秦国还是东边的齐国,都将大禹的功劳事迹镌刻在了青铜器(秦公簋、齐侯镈)上,甚至连自嘲为“蛮夷”的楚国,也在歌颂大禹治水的功劳。再加之分析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十余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关键实物证据,阐释了鲧、禹、羿等夏代君王化熊神话的内涵,进而揭示了周礼中“熊虎为旗”制度的文化渊源关系,从而将这一文化传统上溯至夏代。其中,“将三件出土的二里头铜牌饰分别解读为神鸮神熊和神虎,给’中国’的国旗之由来,找到和黄帝有熊国同样悠久的熊神原型,并对后代所谓兽面纹和饕餮的解读,提供比较图像学和历史发生学的解释线索”。
二里头铜牌饰
又如,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于二号祭祀坑出土商文明时期的青铜神树群,这批文物现今珍藏于三星堆博物馆。据考古资料显示,该批神树共计八株,其中规模最大且经修复完整后高达39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单体青铜器,被称作一号神树。另有一棵仅存下半部分的,被称作二号神树。一号神树由底座和树干构成,顶部已损坏,底座形似三山相连,树干分三层,从山顶逐层上升,树枝也分为三层,每层三枝,分别向上和向下延伸,枝头硕果累累,全树共有九只鸟栖息于上翘的果枝上,一条龙沿主干蜿蜒而下,似欲腾飞。此外,二号神树的三个面向均铸造有铜质跪姿人像,惜臂部前段已残缺。此青铜树群不仅见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成就,还代表了当时铸造技艺的最高造诣,体现了古蜀人民神话意识中人与神沟通的形象化表达。而这些艺术解读,其参照资料即为《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太阳神话,如,“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该内容表明,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被神化为金乌的形象,神鸟在汤谷之间往返,象征着昼夜更替和时空的流转。也正是因为神鸟和神树这两个艺术意象与神话故事的核心元素相对应,使得以《山海经》中的太阳神话来释读三星堆神树的艺术学分析显然是较为合适的。
三星堆青铜神树
若回顾艺术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从中国学界的情况看,神话学通常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20世纪后期,随着楚地出土的帛书和帛画等图像资料的丰富,大大促进了神话学与艺术史的交融,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以及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等,可以说这些论著为这一交叉学科的融合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近年来学界涌现多篇论著,系统探究中国古代艺术的物质内涵与审美传统,以及它们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的文章著作也开始出现,使得更多学者认识到这类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化中神话元素的多维价值,由此为神话学与艺术史学的跨门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进入21世纪,神话学研究学者叶舒宪给出学术总结,认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从史前至远古时期的玉器形象谱系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器图像系统研究;萨满教信仰的艺术形态研究;新出土图像资料十分丰富的汉画像研究。它们均属神话学与艺术学研究相结合的理论范畴。
其实,如今学术界对神话图像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以至于关于神话学与艺术学相结合的学术成果逐渐丰富。通过艺术的视角和丰富的图像资料,神话学研究得以克服文字材料的局限,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同时,神话学与宗教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例如,有学者关注到要建构起神话学与叙事学交融的理论体系,需要对古代神话样本进行重新解读。如,2024年出版的宁稼雨等人所著的《涅槃:中国神话的文学之路》一书,即将神话与叙事故事进行分组归类,通过结合历史与地理,揭示出不同神话产生、流变、传播的各类规律。“该书寻求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微观的神话元素看宏观的中国文化,实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的多重跨界。”同时,书中强调的中国神话和神话文学对于承续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对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重视,并将中国神话研究从“溯源”拉回到“探流”,展现出古代神话原型在文学道路上的再生历程,强调了史学研究应具备的动态发展视野,这些方面都是神话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带来的成果。
可见,在探寻人类早期文明的演进轨迹中,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势在必行,特别是在神话与历史文化的脉络连接中,展现出跨学科互动和融合的趋势。这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又反过来推动了神话学学科定位的变革。就此意义来看,现代神话学研究正尝试采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专注于对文明起源时期的意识形态形成问题的探讨。因此,适应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成为不同学科间整合的桥梁,是时代赋予神话学的新角色和新任务,也是神话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在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神话作为方法——第三届艺术遗产国际论坛”上作《艺术史中的神话佐证意义》讲演,2024年9月28日
结 语
综上所述,神话学与艺术史的交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史学家们正在重新评估历史叙述,并探讨神话作为非理性表达形式中所隐含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真实性。因此,神话与历史研究的分界线变得逐渐模糊,况且这种二者并行的思想自古即有之,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在发展。像颛顼时代之前,神与人尚未明确区分,而颛顼之后则实现了天地的隔绝。至于商代重视巫术,西周时期重视《易经》,而楚国有巫女,齐地有八主,秦国又有《诅楚文》和墨家的明鬼之说,并随着道家的兴起,神话叙事再次流行开来。直至公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这是《史记》有准确纪年号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有年号,但缺乏文献且混乱,整理难度极大,再加上时代变化,最终很多文献都流失了,难以考证。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一年起往后的记载,中国史采用编年体体例,且有明确的记载,比较贴近史实。至于从商朝起我国历史开始从神话转变为神化,逐渐神化君主与事件,提供了统治的基础,但不可否认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补充。于是,艺术史研究出现了利用神话思维将零散的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整合的新方法,而这种跨学科的结合还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和信仰,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进行文史互证,其中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也展现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这些传承千年的古老传说所体现的爱国精神、民族大义、崇敬英雄、重亲重孝等核心主题,构成了中国神话的基本叙事框架和中华文化的根基。通过向公众阐释这些故事,我们能够强调神话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当然,在现如今的艺术创作领域,中国神话的现代表达也日益丰富,如动画、电影、游戏创作等,都开始从传统神话中汲取灵感,将古老的神话故事以现代的视角重新诠释,使其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而且推动着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深入传播与交融互鉴。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5年第4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