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强,历史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要:明初在西北地区通过设定不同的盐米比价,引导商人支盐于解池而运粮至边地。至永乐时,解盐开中成为明廷获取盐利的主要方式。明代中叶,河东解盐逐步实现了从尽数开中到半数开中、半数折银,再到尽数折银的转变,并形成固定税额,所获盐利主要用以抵补山西财政原本的支出项目。隆庆四年水灾之后,盐产骤降,资本有限的解商纷纷因“预纳”“包赔”或破产,或他徙,税源萎缩,河东盐官被迫招徕细商小贾充塞其中。晚明灾害频仍,盐产屡有不足,实力不济的解商们难以完纳税银,明廷被迫将部分盐税按户口摊派,这使得行销区内民户的税负较别处更重。
关键词:明代;河东;盐税;解盐;山西财政;开中法
山西解池产销食盐的历史十分悠久,历代王朝多榷盐于此,以资国用。唐宋以降,解池食盐产量和盐税数额虽登耗不定,均平有差,但对历代王朝的财政和北方的民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明代,中国盐业渐由官统制向商专卖制转型,河东解池盐税的征收也因之屡有变化。关于明代河东盐税的分配,隆庆年间户部尚书马森曾这样概括道:“内给宗粮,外佐边饷,而余皆贮之布政司,以备灾伤抵补之用。”【1】然而,明代河东盐税征收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总额几何?所给宗粮几何?所佐边饷几何?贮之藩司几何?关于河东盐税的变化情况,特别是那些具体而又不断变化的数字,无论是明人所修的“会典”、《万历会计录》以及清修诸“盐法志”【2】,乃至当下的著述,都未能详加厘清【3】。
河东解盐和明代其他盐区一样,盐税种类较为繁多,大体而言,明前期主要是盐课和盐税两大类,明中叶后又有盐课银、余盐银等新增名目,另外还包括各种杂税。为了行文简便,文中将其一并统称之为“盐税”。为了理清明代河东盐税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方搜求史料,聚焦于明代河东盐税的征收及其变迁问题,详细考察其征税形式、盐税总额、盐利分配、盐商聚散等问题,兼析河东盐税与山西财政的关系,讨论盐税变迁与民生苏困之间的关联,以期完整展现有明一代河东盐税征收的实态。
一
本色征收与开中法的实施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取山西。次年正月,明廷于解池之畔置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简称河东运司),管辖河东、陕西盐务【4】;又于年末确定河东池盐课额与盐课征收方式:“解盐东西二场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每引重二百斤。其法,每岁伏暑时月,于山西平阳府安邑等十县内起民夫捞办,毕日还家。”【5】河东运司每年办盐30.4万小引,即6080万斤,额课总量仅次于两淮运司和两浙运司【6】。与东南沿海等处不同的是,解盐的生产方式为捞办,而非东南沿海的煮盐或晒盐。
河东解盐之所以来自捞办,是因为解池拥有天时地利的原因。解池为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咸水湖,每年初夏五月间烈日高悬,应候而至的季风从南方吹来,“盐花因之以结”【7】,甚至会出现“盐花遍池生结,今日般[搬]尽,明日复生”【8】的情形。倘若阴雨连绵、南风爽期,抑或外水入池,那么盐花便会少结甚至不结。为了减少天气所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明廷要求河东盐务官员“遇盐花生结,务要尽力捞办,如法苫盖,以后[候]放支之时”【9】。
明初山西解盐的运销方式,是在宋元旧制的基础上改良而来。元代后期,解盐运销主要是按户摊派,由于民户在纳钱之后赴盐场支盐十分困难,“纵然引目到手也无力装运,’只从各处盐商勒价收买’”【10】,故而盐商仍然存在。明初推行“户口食盐”法,天下官吏、军民人等计口授盐,民众需要缴纳粮食以支付盐价,此举解决了元代按户摊派过程中民户因人口多寡不同而产生的税负不均问题。但百姓支盐依旧不易,特别是距离盐场较远地方的搬运耗费更是巨大,故而民间依旧有商人业盐。或是鉴于山西等省地处边境,每年有大量的军粮需求,明廷除了计口授盐之外,又仿效元代“出盐券,募民入粟”的做法【11】,于解盐行销区内执行开中法,即每纳粮若干便可换得食盐一引,于河东运司持引支盐后便可赴指定地方销售。普通百姓财力有限且支盐不便,所食之盐多半购自那些“入粟”的商人,而非“户口食盐”。
洪武七年(1374年),明廷对开中制度下商人的“中纳数额”做了具体规定,总体原则是:商人于边地纳粮换取盐引(称作中纳),其纳粮数额视与解池的距离由近及远而呈递减趋势。为鼓励粮食运输,明廷虽许可折色缴纳钱银,但在缺粮边地实行折收加价政策。如河州府纳粮0.8石可得1引,折色则需缴纳价值1.5石的银钱(基数0.8石+加价0.7石)【12】。其详情见图1。
图1 洪武七年拟定之西北各地每引食盐中纳数额图【13】
细审图1,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其一,明廷人为地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解池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盐价市场,距离解池越远,越是临近边境,中纳数额越低。其二,商人所缴纳的主要是粮食,以米麦、布绢中纳者均被视为本色。如果缴纳银钱则被视为折色,在解池附近地方可以按照规定数额缴纳折色,但在临近边境地区则需要加价缴纳,最高几近一倍。朝廷此举显然是为了促进物资,特别是粮食向边疆地区流动。在开中制度下,商人缴纳的米粮主要由地方的府卫州县接收,成为边军和边地财政的重要补充。通过这一制度,朝廷在边境地区获得米粮,商人获得利润,百姓获得便利,诚为良策。随着朝廷不断地开榜召中,明代的开中制度也愈加完善。
或因北方战乱初定,民户在授盐之余需求有限,以致盐价低廉,复因利薄而致商稀,“民间食盐商贩者少”【14】,河东运司“入粟给引”的收益一度不如预期。而同期的都城南京(应天府)有着巨大的支盐需求【15】,于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令原属解盐行销区的河南南阳、汝宁府等地改食他盐【16】,除少量食盐留与客商支领外,其余悉数转运南京。转运之路千里迢迢,明廷便于每百里设一站,每站设船十艘,“次第接运至京仓收贮”【17】,后又添设运判一人主其事,并规定,河东运司只运到淮安,再由直隶地方转运至南京【18】。是时,河东“盐课除客商以次支领外,其未支之数”,由户部“差官督同运司官运至各仓,转运淮扬。故当时盐价腾贵,人多愿中”【19】。即人为减少北方市场的食盐供应量以抬高食盐价格,促使商人更为积极地纳粮,但此举也让山西百姓负担了更多的运输劳役。
“靖难之役”中,解盐转运因战争终止。永乐二年(1404年)战乱平息,户部又要求河东运司继续转运食盐,但山西的一些官员则告称:“民贫路险,难以输运。宜令商人中盐,年久者量增引数,以为路费,使就关之,庶免劳民。”明廷最终废除了解盐南运的旧制,又通过优化盐米比价与增加支盐优惠,引导商人支盐于解池而运粮于边地,成功吸引到了更多的商人参与开中【20】。明廷通过“多给引价以偿其费,商人喜得厚利,乐输边饷”【21】,达到了不劳民而边仓充实的效果。
好景不长,永乐四年(1406年)之后河东盐池水灾频发【22】,频繁地出现“淫雨坏堤,淡水入池而盐不结,致亏岁额”【23】等情形。无论是商人支盐,还是计口授盐,都变得无以为继。直到宣宗继位后,朝廷先后于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七年征发十数县,乃至二十余县的民夫修筑堤堰、城垣、更铺【24】,终于使得外水不复入池,河东盐业产销得到恢复。这里面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永乐时期为何没有修复解池的水利以恢复盐业生产,一直拖到宣德时期才有行动?这应与明初的军饷供应来源变化有关。洪武时,明廷于边地推行军屯,不少军粮可以就地自给,若有不足再以民运作为补充。至永乐时,军屯“屯种者率怠惰不力”【25】等情形开始出现,军需粮草更加倚重民运。是时,工役繁兴,征伐不已,军屯乏人,每次出征漠北,征发山西等地的民丁更是动以十数万计【26】,山西等北方省份的百姓负担很重,甚至出现了“民苦挽运,负欠累年”【27】的情形。及至新君嗣位,面对边仓空虚、民力已困的状态,明廷唯有开辟新的财源才能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修水利,以期恢复解盐产量,复行开中,利用解盐之利供给边军。
解池盐产恢复之后,解盐被频繁地用于在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等处的开中,开中所获或为粮食,或为钱银,或为冶铁,或为草料,或为马匹,不一而足【28】,开中收益主要由负责此事的沿边卫所和各地有司使用。另外,在山西等地遭灾时,明廷也常开中解盐进行赈济。如景泰七年(1456年),晋南等地“连年荒旱,民饥”,朝廷令河东运司“于正盐课外再捞二十万引,令本布政司斟酌米价,定立斗数,出榜召中”【29】,即令河东运司临时增办20万引用以开中,开中所得归地方有司用于赈灾。频繁开中逐步加深了沿边军镇和山西等地对于解盐的依赖,以致成为日后解盐收益归属调整的背景。
盐税折银与盐利渐归山西
至明代中叶,九边军需日益倚重盐利:“各边初皆取给屯粮,后以屯田渐弛,屯军亦多掣[撤]回守城,边储始为民运是赖矣。而其派运之数又多逋负,故岁用往往不敷,乃以银盐济之。”【30】当时北方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有供应边镇的任务,但税粮屡有逋欠,民运每有不济,山西尤甚。成化三年(1467年),山西巡抚李侃坦言:“山西所属拖欠税粮,自天顺元年起至八年止,不下数十余万。”【31】山西民运不继的情况一时难以改善。与此同时,随着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边饷已由原来的交纳米粮逐步向交纳银两过渡”【32】,而边地开中过程中占中卖窝日益盛行,以致商人中纳者日渐减少,边储益乏。在此背景下,原有的不定时的开中已经不能满足边地的需要,边地各军镇急需获得稳定的军费供应,于是临近边地的河东解盐被重视起来。
成化四年(1468年)二月,户部尚书马昂建议改革河东运司的盐利获取方式,不再执行开中政策,直接将河东运司每年额办盐课30.4万引全部卖出,“可卖银一(十)七八万,尽可以供边储”。但执行过程中,由于河东运司疏于管理,解盐多被“偷捞”,以致“私盐盛行,官盐价贱,客商不肯中纳”【33】,被窃之盐四处流溢,甚至“越河南至襄阳,径往下江”【34】。
鉴于河东运司腐朽不堪和严重的私盐问题,明廷曾尝试以河东分巡道“兼巡视河东盐池”【35】、缉捕私贩,终因该道员“词讼繁浩,无暇巡视”而作罢【36】。至成化九年(1473年),河东运司官盐因久不畅销,“积聚八年以上盐课未经放支”【37】,合计达250万引,明廷被迫增差御史巡盐河东,加以禁治。首任河东巡盐御史是王臣,王臣到任后殚心经画,整肃吏治,修筑池垣,加强缉私,官盐由是畅销【38】。次年,王臣发现“各边开中河东盐每引价银伍分,而所定粮草价亦略等,今河东支出官盐每引就本城发卖,价亦几至二钱,视开中之价不啻三倍”【39】,于是建议河东运司就地卖引,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运司差委掌印官,将积聚盐课变卖银两,仍每一月官卖(按,即卖盐与运司的购盐商人),一月商卖(按,即支盐与开中商人)。候各年中纳客商后[依]次关支原中到引盐尽绝,河东运司额办盐课但遇开中,不必召商中纳,止令官卖价银……河东运司相去各边不远,每年预期该部行令山西布政司差委的当官员,将运司变卖、收贮盐价银两赍解榆林城等边运粮草郎中、主事等官交割【40】。
《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
自此之后,河东盐税征收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其一,改变了以米粮等实物为主的盐利形式,盐利收益逐渐统一为白银。其二,较之以往开中制度下盐利由府卫州县收取不同,“官卖价银”使得盐利征收开始改由运司负责。其三,“官卖价银”使得商人获取食盐更为便利,促进了解盐的兴旺,“巨商细贾竞聚池下,盐大售于时”【41】。大量盐银流入边镇,也促进了边境商业的发展。不久,王臣任满将去,“商人匍匐入都,愿借一年”,由是得以留任一年,后因过度劳累而卒于任上【42】。
需要说明的是,自王臣奏改税制以后,事态的发展并未像他生前预想的那样:开中逐步停止,河东解盐尽数出售,所得白银运解边镇。实际上,明廷并未立即停止开中解盐,解盐售引与开中同时存在了很长时间。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为了应对蒙古达延汗的崛起,边镇屡有增兵,军饷持续紧张,明廷不得不依旧开中解盐,不仅次数视宣宗、英宗之时未见减少,而且每次开中的数量更多,动辄数十万引。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至十八年的三年中,河东食盐计划开中之数竟达到155.4万引【43】,平均每年要开中51.8万引。除了开中之外,河东盐银还被随时调拨,或运至沿边军镇,或周济灾民,或供王府禄米,或存山西藩库,或解送太仓,不一而足【44】。由于河东的变卖盐引和支盐给开中商人是隔月进行的,运司售卖之盐本已不少,再加上频繁且大量的开中,导致开支的解盐远超产出的定额。
为解决这一问题,明廷逐步提高了河东运司每年办盐的数额。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增河东岁办盐课一十一万六千引,共为四十二万引”【45】。河东盐额虽增加至42万引,但仍不敷所需,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各商新旧开报未补之数”已经达到266万引【46】,盐商守支动辄数年。由于额课不敷所需,明廷曾多次下令河东运司于定额之外临时增加捞办,使得实际捞采的食盐时常远超定额,这种情形在弘治年间就开始了。弘治六年(1493年),山西巡抚杨澄因营建王府住宅和墓地的经费缺乏,请求朝廷令河东运司于额课之外捞办余盐十万引,“委官贸易价银,转输布政司”【47】。弘治七年(1494年),山西巡抚张敷华请求河东每年“除额办外,仍以三十万引充粮饷”,户部担心此举会造成盐价大幅降低而仅同意暂行一年【48】。正德八年(1513年),盐花盛生,户部复准河东运司于额办之外另捞20万引,“召商于偏头等处开中,以补王府禄粮之缺”【49】。正德十六年(1521年),山西巡抚张禬又请求在正额42万引之外,“捞采足二十万引之数以补给禄粮、军饷”【50】。不久世宗改元,裁革增课。嘉靖二十年(1541年),经山西抚按奏请,朝廷同意河东运司“每年捞办余盐二十万引,解补禄粮、边饷”【51】,再次令河东每年增办盐20万引。至此,河东盐额由成化二十二年的42万引增加至62万引。如果细审上引几则史料,不难发现,推动河东运司不断增加捞办数额的主要群体就是山西官员,特别是山西巡抚,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应与山西的财政状况有关。
明代山西财政在保障当地官府运转之外的主要负担,有三大项:其一,供应边储。其二,“借拨”给宣府镇。借拨山西民粮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年土木之变猝然发生,明廷紧急“借拨山西民粮二十七万三千六百石运赴宣府”【52】,此后年年“借拨”,山西财政难以承受,为此山西官员不断上疏。弘治十一年(1498年),户部议准山西供应宣府镇的粮草减半解运。由于各边每石粮食均折银1两上下,山西减半解运后的缺额便是13万两。起初是以京运5万两及河东盐银5万两抵补10万两,但剩下的3万两差额一直没有着落。正德八年,明廷令河东运司以后每年解送宣府的盐银由原5万两增加到8万两,才使这一缺额得以解决。此后虽屡有调整,但大致稳定【53】。其三,供应宗藩俸禄。山西境内“宗室独繁于他省”,宗藩俸禄开支巨大,致使山西财政一直都比较拮据,加之“频年被灾,军民疲敝已极”【54】。如何就近获得更多的河东盐利,是山西官员念兹在兹的目标。山西官员不断上奏,要求提高河东课额,并频繁索取盐银,进而引发山西官员与河东盐官的争执。
成化年间,解盐每引初定税银0.32两。至正德年间,因延绥镇兵饷不足,每引增税至0.5两,引发盐商们的不满。至嘉靖九年(1530年),河东巡盐御史杨东先是奏请每引盐税减作0.42两【55】,接着又在次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盐税分配方案:河东运司不再开中,每年将所产之盐尽数变卖,所得盐银“以八万两为宣府年例,以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两为王府禄粮,余则归之户部”。户部同意了这个提议【56】。当时河东额盐42万引,税银当为17.64万两,其中8万两为宣府年例,8.935万两为王府禄粮,上缴户部的约为0.7万两。杨东的方案可以视为先前王臣方案的改进,不再开中,所有解盐都售给盐商,河东盐商从运司购入盐引之后,直接赴解池支盐,经过掣盐便可运往销区发卖。继任巡盐御史方涯又“题请”将每引盐税“减作三钱二分”,并要求解盐“每年卖足四十二万引之数,除解宣府八万两外,余随多寡解布政司支用”【57】。即将每年所得盐银13.44万两,解宣府镇8万两,余下的5.44万两进入山西藩库。此举降低了河东盐区的负担,但造成山西得利的减少。
嘉靖二十年,山西“逋王府禄粮共一百二十一万余两,又逋宣大、三关粮银一百二万余两,无从措补”,朝廷命河东每年增办20万引以补其不足【58】,额盐总数达到了62万引。由于山西财政供养的宗藩众多,且繁衍日众,俨然已成“无底洞”,即便增加解池的盐额也不能长期维持。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向来依赖山西财政支援的大同镇又“欠王府禄粮银几三十万”两,户部被迫调拨河东运司盐银5万两,“再借”藩司官银5万两补给,并要求大同、山西巡抚商议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59】。与之同时,御史陈炌巡盐河东,其坐主徐阶(时任吏部侍郎)去信告诉他,朝廷准备于河东增加额课:“闻池盐近日颇多,似有加课之议。此等事恐增加则易,减免则难。”【60】不难猜测,朝廷此次加课的动议应起于大同、山西巡抚商议的结果,他们试图让河东运司再次提高盐额以解决财政缺口。陈炌在获知消息后随即上疏,称解池“盐引消折”,“商利益微而引盐日滞”,试图减少盐课。于是出现了“在藩司则请增,在运司则请减,相持不下”的局面【61】。争执持续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户部拟定了新的河东盐税分配方案:
本部复准:四十二万引系是正额,折以今价三钱二分,得银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两,内除解宣府八万两年例外,仍剩银五万四千四百两,当解布政司抵补民粮。其余二十万引之数,亦难议减,但以时价每引三钱二分计之,可得银六万四千两……合将六万四千两并正额剩银五万四千四百两,共一十万八千四百两,内将四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两八钱,径解大同府补王府欠禄,其余七万五千二百八十三两,俱解布政司抵补民粮及王府禄粮【62】。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按照新方案,河东盐额不增不减,仍然是62万引,包括正盐42万引、余盐20万引。无论正盐、余盐,引价均为0.32两,正盐折银13.44万两,余盐折银6.4万两,盐银合计19.84万两。正盐折银除了运解宣府的8万两之外,剩下的连同余盐折银分作两部分:王府岁俸约43 116两,存入山西藩库75 283两。宣府镇银、抵补民粮银和王府禄粮银三者的比例大体是4∶4∶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官吏的食俸盐、王府食盐等需要从解盐调拨,河东实际可售之盐是略少于62万引的,加之盐税的细微调整,同时又有杂项税收存在,故而《万历会计录》中所载万历初年的数字虽与嘉靖二十七年核准之数相近,但略有出入,并且有整有零,总数为198 546.46两,其中包括上交太仓的4395.9两的票税银【63】。票税银为隆庆二年(1568年)以后,河东运司于太原、汾州等产土盐之处,“查核州县户口食盐之数,计口定盐,给票收税”【64】所产生的税款,此项收入解运京师。
总的来说,成化至嘉靖年间,河东盐税征收大致发生了三种变化:盐税的征收形式由开中纳粟变为就司征银,盐利收入由边地的军卫收取变为运司直接收取,盐利的使用由多个去向逐渐向补充山西财政集中。解盐盐税逐渐补充了原由山西财政主要负担的边镇军饷、抵补民粮、藩王俸禄三大项,使得山西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职是之故,河东盐税之于山西财政更显重要,正如时人桂萼所言,山西“一切供输,自岁赋之外,皆仰给河东之盐课”【65】。实行运司纳银制度之后,河东运司的税款均由盐商缴纳,而盐商的盈利情况自然就与运司能否完成课额相挂钩。如前所述,河东解池盐产受天气影响极大,一旦持续减产,商人将无盐可支,无利可图,自然不肯购引,运司售引得银的模式便难以为继,这便成为河东运司在新税制下的巨大隐患。
商困税绌与税负转嫁至民户
河东盐商转运食盐与他处不同,“他处率多水运,晋省必由陆运,山路崎岖,骡头车辆脚费数倍”【66】。因无水运之利,运输成本偏高,解商的利润较之他处并不算丰厚,即便经年日久,所积累的资本一般也不是太多,远逊于两淮等处,明时便有“淮商富,解商贫”【67】之说。因而一些山西商人,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并不就近业盐于解池,反而选择客居扬州等地。资本有限,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快的资本周转速度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解商才能足额缴纳盐税,盐务官员才能顺利完成考成任务。河东盐官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未在支盐、掣盐环节过分刁难,解商在支盐、掣盐过程中大体上较为顺畅,并未出现如两淮、两浙等盐区累世候支、经年候掣等怪诞情形。然而,隆庆四年(1570年)河东的特大水灾,使得解盐的产销和税收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隆庆四年五月,“暴雨,河水涨,蒲堤溃渠决,水入盐池,则盐花不生”【68】,此后“节年水患频仍,盐池受害”【69】。解池频繁遭灾,盐花不生,盐产持续不足,而山西财政和宣府军需等早已严重依赖河东盐利,于是户部便不肯减少额课,“军饷、年例毫不可缺”。由于“盐花不生,捞采为艰”,河东盐官为了完成额课,“设法浇晒以求足数……晒盐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别项征银抵价,或抑勒铺里承买,而民间实用反取之私贩,而民病矣”【70】。如果说盐质下降、强迫承买、私盐盛行是因灾害而产生的暂时性问题的话,那么对河东盐税征收产生重大打击的则是盐商的大规模破产和他徙。
由于盐花不生而额课又丝毫不减,河东盐官为了足额缴纳盐税以完成考成,便组织原来的商人预先交纳盐银于运司,承诺等到盐花复盛时进行补给。然而解池盐产持续多年都没有恢复,解商每年所获得的补给之盐有限,他们资本原本就不多,没几年便不愿跟进投资了。河东盐官又强迫解商按原来所购引数继续购买,实行“包赔”。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河东盐商“预纳、包赔积至九十余万”【71】,几近河东五年盐税之和,实在无力再进行预纳了。在盐商“杖毙、自尽者已十余”【72】人之后,河东盐官被迫放弃了追缴。为了完成税额,河东盐官不仅降低了贩盐门槛,而且为了吸引新的商人加入,又创设“超支”之法。对此,御史刘士忠有清晰的记述:
旧时,商人中盐必先以千万金上纳运司,然后挨次领盐,转发各省鬻卖。乃永春创为超支之法,令民间但上银一二两、十数两者,准与先支。于是三省积贩神奸蚁屯运城图厚利,而宿商巨贾素日为国家出财力用者,反坐守十数年不得关领,自此盐法大坏,商人不至【73】。
刘士忠:《三巡奏议》
河东运司把每年所获之盐售给新纳银的小商人之后,便无力顾及此前预纳的商人,于“旧商压欠数十万者,置之不问”【74】,旧商因此纷纷破产。临近运司的平阳府百姓贩卖解盐者最多,破产者也最多,出生于蒲州盐商家庭的阁臣张四维曾向河东巡盐御史邢侗言:“隆庆间池盐不生……乃创为预责商办,待池盐盛生补给之说。迄今为河东大害,环中条数百里间,富家无故破产者十室九矣。”【75】
由于河东盐商大量破产,盐税征收无以为继。在一波三折的博弈后,万历十七年(1589年),原属解盐行销区的开封府、归德府改食芦盐和鲁盐,得益于河东盐官极力争取到了阁臣的支持,河东解盐的税负得以大幅降低【76】。开封、归德二府在解盐行销区时,每年食盐仅12万引【77】,但割出二府之后,解盐每年的盐额却减少了20万引,“不论盐花盛生、靳生,酌定税额四十二万”【78】,“山东、长芦盐二运司分认河东盐课银四万八千两,河东每年止该正课银十万二千四百两”【79】。对比前引《万历会计录》,不难发现:万历初河东盐场每年办盐62万引,纳银198 546两余,每引折银约0.32两,至万历十七年,河东办盐降至42万引,纳课102400两,此时河东盐额减少了约1/3,盐税却减少了48%,每引的税银降至0.24两左右,即每引税额约减少了1/4。可以说,河东运司食盐的总税额和税率都出现了大幅降低。至万历末,陕西凤翔府“改食花马小池,仍在河东纳课领引”【80】,河东运司每引食盐的税款进一步减少。
河东运司的税负虽然在万历年间是不断降低的,但盐商的境况并未改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由于解池发水之后,解盐生产开始采用“治畦浇晒”技术,虽稳定了产量,但其较之以往的捞采法需要更多的投入【81】,食盐成本提高了,商人获利相应降低。其二,先期预纳造成盐商压垫了巨额资本,他们已无力再“报中”纳银,而盐官为了完成考成,予以新加入的小商人“超支”之权,使得河东盐务陷入一个循环怪圈:“(盐)商不报中穷于压垫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穷于旧商之不报中。”【82】由于晚明灾害多发,解池不少年份的产量不足以完成税额,新加入的小商人即便执行“超支”也不能保证尽数支盐,复使一部分小商人也开始“穷于压垫”,并加入候支行列,盐法因此大坏。万历晚期之后,河东盐官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奏革超支,重整支盐秩序。令众商“挨支以封银时日为序,毫不容搀越”【83】,但商人缴税依旧早于支盐数年。另一方面,设法提高食盐产量。例如,河东运司允许商人募民捞采,特别是在天气好的年份尽量捞采,然而多数年份“盐不生花,惟以畦种为事,竭力浇晒,不能充额”【84】,个别丰收年景所增产量也不足以填补逋欠。又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向年压待,诸商万无补掣之望”而于女池开荒浇晒;天启六年(1626年),又于金井南北池等处开荒浇晒【85】。但诸小池池面最大不过亩余,产盐无几,铢两之获不足以扭转局面。其三,由于大量新商人,特别是那些资本不多的小商人涌入市场,在增加河东运司管理成本的同时,势必会造成解盐行销区内诸商竞争的加剧。细商小贾竞逐贩运,所获无几;大商无利,自然他徙,其中迁往长芦者最多。这种情况早在万历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如前举张四维在为其姻戚王海峰所作荣归序中提到,王海峰在长芦和山东盐区经营盐业多年,至万历初年,大量的同乡开始去投奔他,“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86】。张四维在给沧州盐商展玉泉的送序中又说道,近岁长芦盐商“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87】。两序结合,可以推知当时确实有很多河东盐商离开家乡,转赴长芦等地业盐,解盐的税源日渐萎缩。
盐税既然降低,河东盐利的分配势必也要重新调整。明末,河东岁征盐银124 932.1两,“内以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八两五钱六分解宣镇,以四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两八钱解大同,以五万三千三十六两七钱四分解山西”。根据最初的设计,解送山西的盐银中,有1万两“听代、晋、沈三府宗禄不敷之用”,但这仅有的1万两也常被改作他用【88】。这一分配方案,是在保证山西藩库收入没有大幅减少的前提下,由宣府、大同二镇和山西瓜分了原分配给诸藩王的俸禄款项,户部不再参与分成。也正因此,明末山西诸藩俸禄的拖欠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陷入绝境【89】。
天启以降,外患、内乱纷至,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河东解盐屡有增课。天启六年,明廷令“每引量加盐课以助大工”,河东增课8400两,即每引加银二分。但是完工之后,该税仍“照旧加征,以济军饷”【90】。崇祯五年(1632年)初,又令河东运司“增引一万两千五百,以充兵饷”【91】。每引按旧价0.32两征收,是为4000两。然而,是年解池又遭水灾,“雨经三旬,决池,无盐,商大困”【92】。至九月盐税解运之时,河东巡盐御史罗元宾被迫上疏请求缓征盐税。
内称……今春池水不涸,盐花不生,所望者夏秋之际耳。不意天雨连绵,洪波汪洋……河东诸商苦无雄资,又皆先纳课而后支盐,盐生不时,崇祯元年纳课者尚未支掣,今又一年无盐,又增一年预报矣……臣以国课所关……除每年边饷一十二万三千有奇,务必依期征解外,有近年加增助饷银八千四百两……又加课银四千两,恳祈皇上于中量行缓征一年,少[稍]苏其困……
奉圣旨:盐课,军饷急需,岂容延缓?还着依限解部,其考成仍照旧例行。钦此【93】。
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七
细审上引史料,可见罗元宾于奏疏中及时汇报了河东的灾情,如实陈述了河东盐商的困境,在保证能够完成额课的同时,希望加课部分能够“缓解一年”,舒缓商困。但被思宗直接拒绝。然而加课于大灾之年,催征于惶惶各商,盐官苦于考成,诸商每被杖责,“苦无雄资”的河东盐商已被逼入绝境,于是“商贾散亡”【94】,主要盐商从原来的五百余家“消乏至百余家,而额课渐次不敷”【95】。继任巡盐御史杨绳武虽“日以招商为事”【96】,但未能扭转局面。
崇祯九年(1636年),河东巡盐御史姜思睿鉴于运司缺盐、商人逃散、行盐地方相继动乱的情形,上疏奏请除票盐和花马池盐代征的小部分盐税之外,河东运司实行“商人浇晒之法及分派户口之议”,即由河东盐商与行销区内部分州县共同缴纳盐课,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河东运司允许盐商出资在解池内治畦晒盐,于运司“纳课领引”后“支盐出场”,食盐“听三省小贩接买,发卖行盐州县”【97】,百余盐商共认课78 768.3两。另一方面,在治安尚好的晋南、豫北行销区内按照人丁多寡分摊盐课,其中平阳、潞安、泽州、怀庆所属41县共认课银39 235.52两【98】,而黄河以西和以南的陕西、河南多数州县因“寇盗纵横,私盐充斥,官商裹足不前”基本不参与分摊【99】,所在地区民众食盐由小贩售卖。姜思睿的办法虽然解决了解商不能全额纳课的问题,但迭次引发了以下四个后果:其一,明代中叶之后,户口“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100】,官府并不能掌握各地确切的人口情况,照户籍摊派,势必造成各地食盐税负不均。另外,由于“行盐地方途生路迂”,商人根本无法做到“逐户散给”【101】。其二,灾害频仍造成的盐产不敷所需是河东盐区盐税问题的根源,单纯规定食盐分派户口,造成很多民众虽缴纳银钱,但不一定有盐可领。在摊派盐税之后,河东盐官只重视向民户征税,而不关心他们是否能获得食盐,也不关心解盐生产能否达到定额,产盐不多的盐池因而日渐荒废,如万历末年开辟的女池等“尽行荒废,积水汪洋而已”【102】,造成食盐产量进一步下滑。其三,在盐税派及户口之后不久,河东运城迭遭战事,解商逃散,“仅存寥寥三五十人,皮毛俱尽,课额征解不前”【103】,各地承销的小贩也裹足不前。产盐无人销售,盐课亦无人承办,于是明廷将盐税摊派至各州县,“令各属照人丁之多寡纳价领运,移不封课之商盐俵给人户,追户口之盐价,用抵商逋”【104】。“州县始则按人丁而受盐,继则计盐斤而缴引,按季比销,年终考成”【105】,销盐多寡成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其四,既然销引征课成为地方官员的任务,而各地承销食盐的店牙土商也多因战乱破产、逃亡殆尽,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成,就将盐银并入地丁田粮中一并征收。如山西翼城县,便是将盐银“于通县丁粮派征”【106】。如前所述,解盐所行销的晋、陕、豫三省有输边任务,民众负担本已十分沉重,启、祯之时年年灾荒,还有“三饷”相继加派,又复摊入盐课,使得民众税负极为沉重,彻底陷入绝境,以致相继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省之地成为晚明农民战争的渊薮。
结 语
明初河东盐税的征收是在前朝旧制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明廷通过开中法用解盐换取粮食、布匹等物资。成化十年(1474年),解盐半数于运司折银售卖,半数于各地开中。随着盐课折银的普遍推行,至嘉靖十年(1531年),解盐被全数折银,不再参与开中;嘉靖二十年,解盐的盐额和盐税都实现了定额化。盐利的最终形式由粮食变为白银,收取盐税的主体也变为盐司,这一进程与各盐区大抵是同步的。16世纪下半叶,河东的盐额基本稳定在62万引左右,盐税保持在19万两以上,就盐税总量而言,河东是当时仅次于两淮的第二大盐区【107】。万历十七年,解盐的盐额随着部分行销区的割出出现了大幅下调,但盐税下降得更多,每引税额也因此降低了不少。天启之后,盐税屡增,每引税额有了较大提高,民众盐税负担加重。兹据前文考证所得的岁办引盐与岁解盐银数额,制作折线图2。
图2 明代河东解盐岁办引盐和岁解盐银数额图
嘉靖朝之前,河东的盐利分配并不固定,嘉靖中叶盐课尽数折银之后,河东盐税并未像其他运司那样将盐银运解北京,而是将其中的绝大部分抵补原山西财政的支出项目,如是分配,则与山西财政困难和山西官员的极力争取有关。这一分配方式固然免去了盐银解运的烦琐,但减少了户部财政可支配的数额。另外,食盐尽数折银之后,盐商成为盐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盈利情况与盐税的完纳与否相挂钩。万历初期,商人或破产或他徙,新招徕的小商人人数虽多,但获利有限,抗风险能力差,难以承受明末的税负和灾害,最终迫使明廷将盐税转嫁给民户。其实,无论盐法怎么变革,增加的盐税最终都会以盐价上涨的形式落到每个人身上。在晚明北方各省灾害频仍、兵戈迭起、新税屡增的背景下,明廷又不断增加百姓的盐税负担,无疑使得百姓陷入绝境,进而加剧了地方的动荡。
清军入关之初,军需旁午,清廷除了下令将河东盐银尽解户部外,还要求解池盐税“仍旧例催征”【108】,即按照晚明的定额进行征收,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免除晚明的苛捐杂税。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又因“兵饷不敷”而于河东增加盐课3.2万两【109】,使得民众负担进一步加重。是时,解盐所行销的秦、晋、豫三省久经战乱,户口凋敝,商民无几,官吏惮于考成,百姓苦于摊销,以致三省官民交困,萧索万分。直到康熙中叶,随着全国的大抵安定,清廷才下调了河东的盐税。与此同时,北方人口逐渐恢复,官员考成也略有放松,加之盐商相继招徕,认引办课,社会的人均税负水平逐渐降低,民生方苏,北方地区才从明末大乱后的虚脱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这也预示着盛清时代的即将到来。然而,由于成本、转运等方面的劣势,清代河东盐商与明代一样,因无法积累起丰厚的财富,依旧多是商小利微的状态,河东盐商虽有纲商之名,但其实力远逊于两淮盐区,“或一家而有数十锭,或一家而止有数锭,甚且有一商名而数人朋充者”【110】。资本不足,导致河东盐商抵御风险的能力依旧较差。至清中叶,盐政渐坏,河东盐商每有不支,清廷不得不反复调整河东盐法,或推行纲商包运,或将盐课摊入地亩,或又招商转运,或改行留商行票之法,还有捐免充商之议【111】,终清一代,未得长策。盐商困绌,盐法屡更,盐税不充,盐官渐裁,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数千年的河东解盐也因之日渐式微。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在此致谢!)
【1】马森:《奏盐法事宜》,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8页。
【2】如清康熙朝所修《河东盐政汇纂》便误载了明代河东盐引之数,乾隆朝所修《河东盐法备览》一书虽指出前书关于盐引的部分错误,但对于不同时期的盐引数额仍未能明确(参见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七《引目》,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39页)。后人的相关研究常引用清修诸书,在讨论明代河东盐税的演变和总数时常有不同,甚至彼此矛盾。
【3】长期以来,寺田隆信(氏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佐伯富[《中国盐政史的研究》(『中国塩政史の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徐泓(《明代的盐务行政机构》,《台大历史学报》总第15期,1990年12月,第197~206页)、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前辈学者从整体上理清了明代盐政和盐税的演变趋势,对开中、占窝、纲盐法等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的研究日益聚焦于探讨各盐区的运作实态。关于河东盐区,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第25~30页)、孙晋浩(《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第68~73页)、黄壮钊(《明清山西解盐生产技术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3~122页)等学者探讨了明代河东解盐的盐政管理、生产方式、食盐产量、运销以及行销区域等问题。不过,关于明代河东盐税征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仍有置喙的余地。
【4】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戊申,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770页。按,本文所引“明实录”皆为此本。
【5】《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第946页。
【6】明初,两淮运司岁办大引盐35.2万余引,两浙运司岁办大引盐22万余引。每大引重400斤(参见《诸司职掌·户部》,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33~634页)。
【7】成化《山西通志》卷二《山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44页。
【8】《明英宗实录》卷八四,正统六年十月庚寅,第1682页。
【9】万历《明会典》卷三四《户部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602页。
【10】 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11】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12】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辛丑,第1643~1644页。
【13】此图中唯太原、朔州或因不甚缺粮,明廷特准其折收不加价。
【14】《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丙申,第1091页。
【15】明初都城南京食盐配给数目很大,即便永乐时都城北迁之后仍有不少。正统初年,侍郎何文渊称,仅“南京光禄寺并大军食盐,岁给一十万引有奇”(《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壬辰,第553页)。
【16】参见《条例全文·成化九年条例》,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719页。
【17】《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癸丑,第3240页。
【18】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壬午,第3403~3404页。
【1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督察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8册,第737页。
【20】《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甲申,第507页。
【21】章懋:《议处盐法事宜奏状》,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九五,第836页。
【22】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丙戌,第864页;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八《河渠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1页;《明宣宗实录》卷二九,宣德二年七月丁亥,第757页。
【23】《明宣宗实录》卷二九,宣德二年七月戊子,第757页。
【24】参见《明宣宗实录》卷一四,宣德元年二月壬午,第386页;卷二九,宣德二年七月戊子,第757页;卷八九,宣德七年四月己丑,第2037~2038页。
【25】《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一,永乐十三年二月癸酉,第1823页。
【26】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七《成祖三》,第93页。
【27】《明宣宗实录》卷七,洪熙元年八月癸酉,第193页。
【28】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226~227页。
【29】《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九,景泰七年八月乙巳,第5699~57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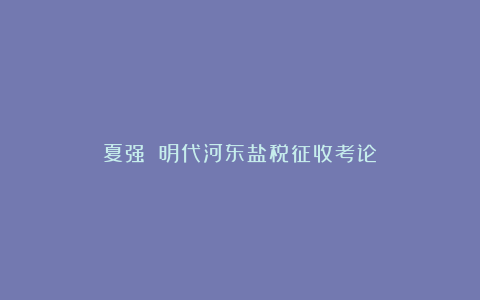
【30】《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戌,第876页。
【31】《明宪宗实录》卷四七,成化三年十月辛酉,第979页。
【32】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57页。
【33】戴金辑,蒋达涛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八《户部类·盐法》,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6、811页。
【34】朱廷立:《盐政志》卷七《疏议·左钰禁越境私贩疏》,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276页。
【35】万历《明会典》卷三四《户部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607页。
【36】戴金辑,蒋达涛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八《户部类·盐法》,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6、811页。
【37】《条例全文·成化九年条例》,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3册,第700、703~704页。
【38】参见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三《宦绩》,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570页。
【39】《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八,成化十年五月丁亥,第2434页。
【40】《条例全文·成化九年条例》,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3册,第700、703~704页。
【41】彭华:《重修解池垣堑记》,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一二《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5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572页。
【42】康熙《平阳府志》卷二〇《宦绩》,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1584页。
【43】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五,弘治十四年六月戊戌,第3196页。
【44】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初年,河东解盐的开中始终在频繁进行,售盐的盐银也被用于各种开支(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三,成化十八年正月辛卯,第3840页;《明孝宗实录》卷四三,弘治三年闰九月庚辰,第879页;《明武宗实录》卷一七〇,正德十四年正月庚子,第3283页;《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元年四月己卯,第453页)。
【45】万历《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576页。
【46】《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己亥,第3155页。
【47】《明孝宗实录》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戊子,第1372~1373页。
【48】《明孝宗实录》卷八五,弘治七年二月丁亥,第1594页。
【49】康熙《平阳府志》卷一五《盐法》,第942页。
【50】《明世宗实录》卷五,正德十六年八月庚寅,第219页。
【51】《明世宗实录》卷二五〇,嘉靖二十年六月壬申,第5022页。
【52】康熙《平阳府志》卷一五《盐法》,第943页。
【53】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三,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子,第2502页;《明武宗实录》卷一〇四,正德八年九月庚午,第2137页。
【54】《明孝宗实录》卷一〇〇,弘治八年五月己亥,第1839页。
【55】参见《巡盐御史王诤请复盐课旧额疏》,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七《疏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第641页。
【56】《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二,嘉靖十年十一月辛酉,第3127页。按,《明世宗实录》误将杨东记作山西巡按。
【57】《巡盐御史方涯额课常规疏》,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七《疏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第640~641页。
【58】《明世宗实录》卷二五〇,嘉靖二十年六月壬申,第5021~5022页。
【59】《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三,嘉靖二十六年五月甲寅,第5988页。
【60】徐阶:《世经堂集》卷二二《书一·与陈皆所侍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80页。
【61】《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七,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壬戌,第6160~6161页。
【62】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三九《盐法目录·河东盐运司》,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第118~119页。
【63】参见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6页。
【64】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六《户部十·盐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5册,第605页。
【65】桂萼:《序·大明舆地图序·山西图》,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二,第1862页。
【66】乾隆《陵川县志》卷一二《赋役二·附盐法》,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42册,第280页。
【67】嵇璜:《钦定文献通考》卷二〇《征榷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88~489页。
【68】康熙《夏县志》卷一《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63册,第90页。
【69】房寰:《护池官地疏》,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一一《奏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4册,第220页。
【70】萧彦:《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〇七,第4425页。
【71】《明神宗实录》卷一四〇,万历十一年八月庚戌,第2601页。
【72】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七《盐法议(代归德太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第219页。
【73】刘士忠:《三巡奏议》卷一《中台奏议·纠论阳和兵备险肆不法疏》,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影印本,第56~57页。按,引文中的“永春”,即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
【74】萧彦:《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〇七,第4425页。
【75】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一八《书三·复邢知吾》,续修四库全书第1351册,第556页。
【76】参见夏强:《由“随奏随行”到“动辄纷争”:明代解盐行销区的调整》,《学术研究》2022年第7期,第135~138页。
【77】参见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七《盐法议(代归德太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第219页。
【78】《明神宗实录》卷二〇四,万历十六年十月丙申,第3816页。
【79】《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九,万历十七年三月甲戌,第3927~3928页。
【80】觉罗石麟:《初修河东盐法志》卷三《引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4页。
【81】黄壮钊:《明清山西解盐生产技术的演变》,第115~116页。
【82】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七《盐法议(代归德太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第219页。
【83】《明熹宗实录》卷七五,天启六年八月丙寅,第3654页。
【84】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一《盐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第531页。
【85】顾炎武撰,黄坤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4页。
【86】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一《序二·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1册,第600页。
【87】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三《序四·送展玉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1册,第653页。
【88】毕自严:《度支奏议》山西司卷一《题覆乐昌王府补给宗藩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第444~445页。
【89】参见安介生:《从山西宗藩看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宗禄困境”》,《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太原:山西省历史学会2004年编印本,第49~61页。
【90】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一二《再议措饷未尽事宜三款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3册,第534~535页。
【91】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五《引目》,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626页。
【92】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一《解池》,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497页。
【93】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七《题覆河东盐院罗元宾议解池水灾仍照例督催捞盐征课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141~142页。
【94】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五《引目》,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643页。
【95】《户部尚书车克等为招商认课何以宽期五年事题本》(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河东盐务题本》,《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第6页。
【96】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三《宦绩》,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第573页。
【97】 康熙《平阳府志》卷一五《盐法》,第953页。
【98】参见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二《盐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第541页;《户部尚书车克等为招商认课何以宽期五年事题本》(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河东盐务题本》,第6~8页。
【99】康熙《平阳府志》卷一五《盐法》,第952~953页。
【100】万斯同:《明史》卷九六《食货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25册,第610页。
【101】觉罗石麟:《初修河东盐法志》卷六《盐法》,第497页。
【10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第1914页。
【103】《河东盐政朱鼎延为允准招商分引办课事题本》(顺治四年正月二十日),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河东盐务题本》,第3页。
【104】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五《商贩》,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643页。
【105】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二《行盐》,第544页。
【106】光绪《翼城县志》卷九《田赋·盐法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47册,第291页。
【107】参见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2118页。
【108】《河东盐政朱鼎延为允准招商分引办课事题本》(顺治四年正月二十日),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河东盐务题本》,第3页。
【109】冯达道:《重修河东运司志》卷二《盐法》,第542页。
【110】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六《运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4册,第101页。按,清代河东解盐每120引征税50两,谓之一锭。
【111】参见佚名:《河东盐务议略》(不分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第13~24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0期
编辑:阎浩华
审核:安 瑞
监制:苗书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