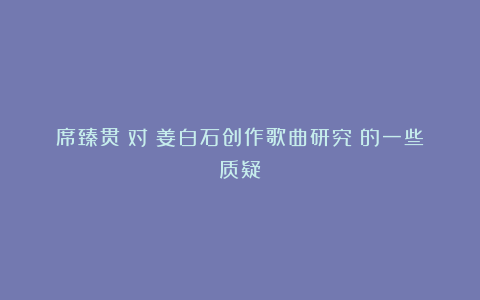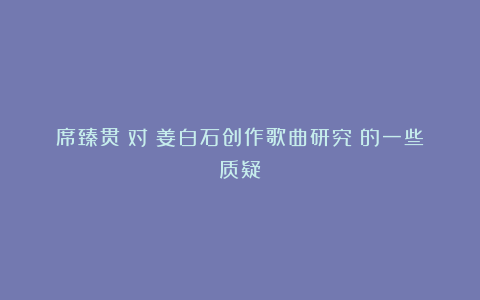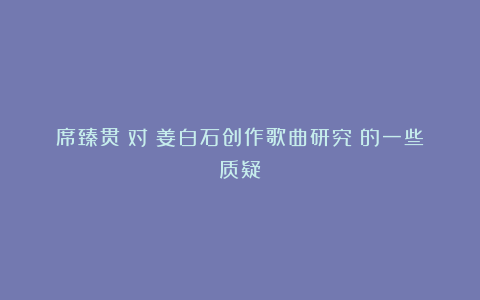 杨荫浏、阴法鲁合著之《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有论及宋代的箫,其中《从所用管乐器来推测姜白石所用音阶的准确程度》一节认为:“在箫上任何两孔之间,无论如何,是产生不出准确的增四度音程来的”。由于这个问题,不但涉及管色指法及乐器制作史,更直接影响白石歌曲的准确翻译,故笔者不揣谫陋,谈谈愚见。
杨荫浏、阴法鲁合著之《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有论及宋代的箫,其中《从所用管乐器来推测姜白石所用音阶的准确程度》一节认为:“在箫上任何两孔之间,无论如何,是产生不出准确的增四度音程来的”。由于这个问题,不但涉及管色指法及乐器制作史,更直接影响白石歌曲的准确翻译,故笔者不揣谫陋,谈谈愚见。
宋代歌曲作法,有一特点,即沈义父《乐府指迷》所谓:“按箫填谱”。白石也然,如其《角招》序云:“予每自度曲,吹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又如诗《过垂红》:“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可见姜白石自度曲,皆以箫音为准。
《研究》认为:“我们有理由推测,姜白石根据了他吹箫的经验而写出的增四度的曲调进行,实际不一定是增四度的进行。”于是“在《淡黄柳》曲中,我们降低了一些第七度音”。¹
对于姜白石这样一位在乐理律学上有极深造诣,而且又上书过列论古今乐制之《大乐议》的音乐家来说,居然会在增四度谱录中不辨一律之差异,恐怕有悖情理。而况《谈黄柳》被降的“变徵”音,是姜夔歌曲的音阶特征,即《大乐议》所云:“凡六十声为六十调,其变官十二在羽声之后、官声之前;变徵十二在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因而,角微间的“变徵”是降不得的。
那么,像《淡黄柳》那样从官到变徵的增四音程,在洞箫上是否能吹出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说,在洞箫正常音域内的任何增四度音程,都能运用各种指法及气息控制奏出。关键在于,宋代箫与现代箫在形制上是否一致。这又可从绝对音高、开孔方式及指法三点,分别予以探究。
关于绝对音高标准,《宋史·乐志》:“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可知黄钟比d¹略高一点。又据陈旸《乐书》载,筒音为黄钟,故而与现代箫音高大致相似。《研究》依据大晟乐尺,计算出黄钟频率“约为298,725 V.D”,其正确性毋容置疑。
关于开孔方式,据陈旸《乐书》记载,有两种:(1)二至三孔为半音关系。(2)三至四孔为半音关系(“中管”开孔法)。而其共同特点又是,五至六孔(后出音孔)为小三度关系。示意图如下:
姜白石在《湘月》序中说:“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隔指声也。”方成培《香研居词尘》曾这样解释:“……太簇当用’四’字住,仲吕当用’上’字住,箫管’上’’四’字中间只隔一孔,笛’四’’上’两孔相联,只在隔指之间。”这段文字曾使许多学者费解而困惑,如罗蔗园《读夏承焘君白石词乐说笺正书后》云:“如云箫管四上字中间只隔一孔,笛四上字两孔相联,只在隔指之间。其实古今箫管与笛,四上之间均隔一孔。岂方氏所见之笛,独有不同耶?”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的事实,戈载《七家词选》、陈沣《声律通考》、凌廷《梅边吹笛谱》都采用方说,可见其中必有道理。
这段文字的启示是,当时之横笛,亦应与洞箫一样,五六孔之间乃小三度。又因为笛与箫一般呈四度关系,据林谦三对正仓院藏几组尺八与横笛之考证,可知唐代已形成笛比箫(尺八)通常高四度的规律。于是,宋代横笛可作如下示意图:
与前边宋代箫图参较,不正如方说“箫管’上’’四’字中间只隔一孔,笛’四’’上’两孔相联”吗?
从演奏角度言,宋代的这种洞萧,第六孔吹低一律为应钟,反比现代箫更容易与第三孔仲吕形成准确的如《淡黄柳》宫至变徵的增四度进行。
关于洞箫指法,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姜白石上书《大乐议》之前九十多年,即崇宁二年陈旸献进的《乐书》中,就已详载了多种管色运用“半窍”的十二半音演奏法。运用这种指法,可十分准确奏出每一律音。因此也就告诉我们,姜白石所用的音阶,包括增四度进行,都可能准确到像他所暗示的程度,并非《研究》所云“不可能准确到像他的理论所暗示的程度”。
陈旸《乐书·雅部》载洞箫的半音指法为:“从下而上,一穴为太簇,半窍为大吕;次上一穴为姑洗,半窍为夹钟;次上一穴为仲吕;次上一穴为林钟,半窍为蕤宾;次上一穴为南吕,半窍为夷则;变声为应钟,谓用黄钟清与仲吕双发为变声,半窍为无射;后一穴为黄钟清。”
其中唯应钟叉口指法稍稍偏高,靠唇部及气息控制,或改用○●●●●○指法,都可达到准确程度。顺便提一句,包括西洋铜管、木管在内,管乐器的吹奏,都必须靠演奏者作一定程度的音准控制,不作任何控制而能完全音准的管乐演奏,实际在世界上并不存在。
虽然陈旸上述指法,能吹出十二律吕之每一音,但若在一器上“翻十二调”究非易事。就拿西洋管乐来说,升降号多了也不易演奏,于是出现诸如低一律的A调黑管等变调乐器。与此同工异曲之妙的是,陈旸《乐书》亦记载一种低一律的箫,谓之“中管”:“中管”起应钟为首为宫,其次上穴大吕为商,又次上穴夹钟为商,又次上穴仲吕为变徵,又次上穴蕤宾为正徵,又次上穴夷则为羽,变宫为无射,谓后穴与第三穴双发声也。如此即不用半窍,谓十二律用两笛成曲也。”
陈旸认为,两支分别以黄钟与应钟为筒音的箫,完全能应付十二均的演奏。其所谓“如此即不用半窍”,是指不在半窍上成均,并非每一宫调音阶中不出现用半窍的音。
以差一律而成对的箫,一直被保留至现代,不但历史悠久,且传播面甚广。譬如创于明代的玉屏箫,以高低分雌雄而成对;江南流行的凤凰箫,一镌凤,一镌凰,也取雌雄成对之意。一般来说,民间之对箫,与宋代洞箫、中管的音高相似,一支筒音为d¹,一支筒音为#C¹。但是,专门用来与古琴合奏的“雅萧”(又称琴箫),则以筒音为C¹谓“律箫”,筒音为#C¹谓“吕箫”,这是由于从调性指法及音色上,更适宜与古琴的谐合。记得岸边成雄先生几年前访问我国西北,听了一些民族乐器的独奏后,曾向笔者问起:“缘何中国乐器店卖箫,要两支一起出售?”盖原本于此矣!
再从姜白石标有旁谱歌曲所用宫调来看,如果连基本音阶中的增四度进行都不能准确奏出的乐器,要翻那么多调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姜白石的所有歌曲都可以在一支箫上演奏,不必求助于低一律的“中管”。十七首歌曲共用了六个均的指法:
(2)运用“闷工调”按孔法(全按作3 )的有四首:
(4)运用“小工调”按孔法(全按作1 )的有二首:
现代箫上实际应用于演奏的七种指法中,除“凡字调”外,姜白石歌曲都用到了。而且,上列之前五种按孔法,属“常用指法”,在传统箫独奏曲中不乏可见,如《薰风曲》《加花老六板》《高山流水》用的是“闷工调”;《佛上殿》用的是“六字调”;《三六》《阳关三叠》《平湖秋月》《塞上曲》用的是“尺字调”;《心中思友人》用的是“小工调”;《平沙落雁》《柳摇金》用的是“正宫调”。
再从另一方面讲,姜白石的“过腔”论,也是增四度必须准确的有力佐证之一。如果没有可靠的律吕固定音高为基础,“过腔”奏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这种“过腔”理论不可能在具有七平均律色彩的“平均开六孔”的笛箫上付诸现实。因此从乐器制作史角度探讨,宋代的笛箫应是按律吕之全音、半音关系开孔的。这一点,在陈旸《乐书》关于篪的十二半音指法记载中,同样可得到证实。
淳熙十三年(1186),姜白石与箫氏兄弟泛舟湘江作《湘月》,序中谓:“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隔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声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
这是一段关于吹箫技术很重要的论述,但是“过腔”究竟是怎么回事,古来词家说法不一。辄举其要如下:
方成培《香研居词尘》云:“盖念奴娇本大石调,即太簇商,双调为仲吕商,律虽异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过……又此调毕曲,当用’一’字’尺’字,亦鬲指之间,故日’鬲指声’。”
张文虎校姜词谓:“念奴娇有转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工大石。”
周之琦《心日斋词录》云:“今之吹笛者,六孔并用,即成北曲,隔第一孔第五孔吹之便成南曲,隔指过腔,义或如是。”
夏敬观《词调溯源》曰:“大石调与双调,谱字止’一’’凡’’勾’与’下一’’下凡’’上’三字不同……以有定之笛孔,配丝弦之谱字,终难准一,故笛中有过腔之法。”
冒广生校白石歌曲谓:“陈元龙白石词选此调住小石,小石即雅乐之仲吕商,用’尺’字住,白石用双调吹之,双调即夹钟商,用’上’字住,仲吕与夹钟隔一律,’上’与’尺’则隔一指,故云’鬲指声’,自来无明此理者。”
由于《湘月》谱已不存,故聚讼至今,无法用谱字验之耳。但是上述诸说中,已由夏承焘先生指出周说为“附会之谈”;由冯登府指出“陈元龙词选乃伪书”,因而我们可把参酌研究的范围缩小一圈。
正如罗蔗园所说:“至论鬲指过腔一语,当以方成培《香研居词尘》为最佳,然亦有未尽处……而又云此两调毕曲当用一字尺字,则又何所据而云然耶。此盖迷于蔡元定起调毕曲之说,而又不知段安节七运之用所致也。
其实,蔡元定起调毕曲之说并无不妥,段安节之“七运”即《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也无不妥,方成培之“未尽处”在于“之调式”与“为调式”的阴差阳错。我们知道,北宋大率用“为调式”系统政和七年起直至整个南宋咸用“之调式”系统,至元代又复用“为调式”系统。因而,作为南宋时代的姜白石,其“自度曲”所标宫调名,都是依“之调式”系统解释的。
但是,方成培解“鬲指”之谓:“大石调”,即太簇商,双调为仲吕商”。却说的是“为调式”,即“太簇为商”“仲吕为商”。如果仅此而止,也还不成大错,然而接下来谈到“此调毕曲”,不知缘何又把这两个调名当作“之调式”解,即变为“太簇之商”“仲吕之商”。这样一来,大石调、双调的主音就被错误地提高了二律。其谓“此调毕曲,当用’一’字’尺’字,自然令人如堕五里雾中。
此二调,正脗夏敬观云:“谱字止’一’’凡’’勾’与’下一’’下凡’’上’三字不同”。可观如下谱式:
从中可看出,大石调音阶只要把一、勾、凡三字降低半音,就变成了夹钟均。也就是说,在箫上运用大石调(全按作1 )的演奏指法,再把角、变徵、变宫三音通过“半竅”或“叉口”变为清商、清角、闰,便成了实际上的“双调”曲。
不难看出,在箫上运用吹越调(全按为作2 )的指法,同样也是把角、变徵、变宫三音降低一律,便成实际上的“高大石调”曲。
由此可见,“过腔”乃一种半固定概念之洞箫演奏技术,即运用熟习的一、二种(或几种)指法,把角、变徵、变宫吹低半音,使其“过入”到上方小三度的“第二关系”调上。这种方法,乃利用原有的指法,再增加出新的宫调来,以使在一支箫上产生更多的旋宫可能性。
晁无咎自号“归来子”卒于大观末年,因之证明北宋时已有“过腔”之法。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在萧上,无论演奏与理论,均臻相当水平。于是,又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既然箫之“过腔”所赖,必须是准确的十二律吕音程,那么类似《淡黄柳》那样的增四度进行,也必然可以,而且应该是准确的。
1 “第七音”所指乃应钟。姜白石自提《淡黄柳》为“正平调”,即之调式林钟均宫、商、角、变徵……排列论,此为“第四音”;若按羽调式音阶,此又是“第六音”。故“第七音”说法不妥。
2 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二七《白石道人歌曲四集》谱所译。“溪”字上比《研究》谱多一“フ”音。此乐思在《玉梅令》中共出现四次。
作者简介:席臻贯(1941—1994),男,甘肃敦煌艺术剧院原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