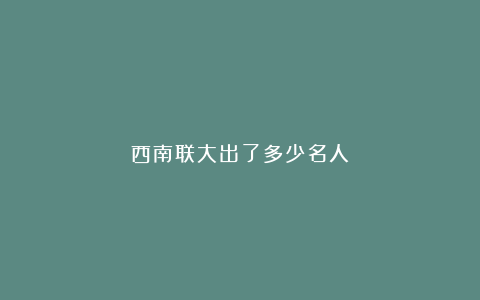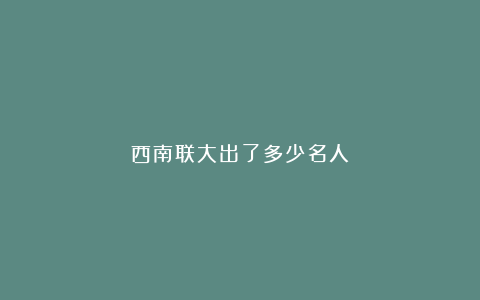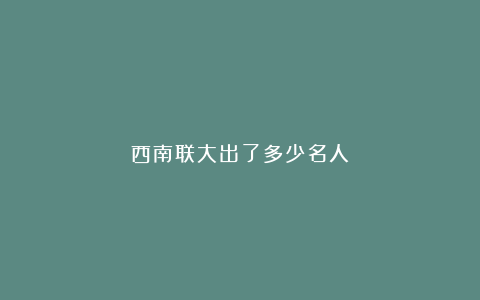很多年后,杨振宁回忆起西南联大,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求学时的学习环境:“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当然不是设计问题。西南联大新校区的设计出自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迫于校方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的设计方案只得一改再改。
我们先了解一下,西南联大当时成立的背景到底有多艰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由卢沟桥一路蔓延至整个华北。凶残的日寇烧杀抢掠,连大学也不放过,天津陷落后,位于城南的南开大学,惨遭日军毁灭性轰炸。校园多处建筑被毁,几十万册文献典籍灰飞烟灭。
南开大学的悲剧并非个例。抗战期间,日寇一方面以“东亚文化共荣圈”为名,竭力拉拢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破坏。据统计,到1938年8月底,我国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其中10所完全被毁,25所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锐减50%。
在民族存亡之际,为挽救中国教育,各界精英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名发表声明,请国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将部分高校内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其中,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并要求各校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主持大局。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若累卵。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余里才能抵达昆明。
西迁路上的盘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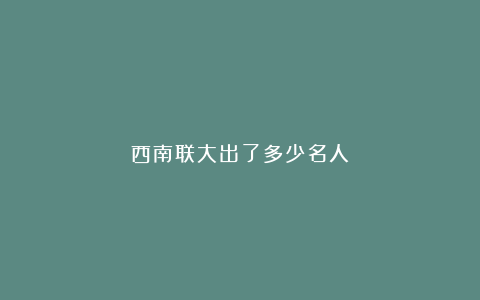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一开始,西南联大连校舍都没有,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也就在这一年,17岁的杨振宁随其父亲、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南迁至昆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杨振宁报考大学时选的是化学系,进入西南联大后,他切身感受到了物理学的魅力,于是转入物理系,师从赵忠尧、吴大猷、吴有训、周培源等物理学家。这一选择,改变了杨振宁的命运,也在多年后改变物理学界。
1937年北平沦陷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邓稼先一样从沦陷区逃亡的,还有李政道。李政道当时不到20岁,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同时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历经3年颠沛流离,李政道才进入西南联大,拜入物理学大师吴大猷门下,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美留学。
在美国,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做研究,发表论文,并在1957年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办学的九年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就读,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西南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西南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学生有90人。
当然,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也赫然列在西南联大校友录上。
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学子献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戴荣钜、王文、吴坚等西南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在空战中英勇殉国。翻译家许渊冲曾为飞虎队准确翻译日军情报,使昆明免遭一次空袭。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蔚然成风。三位校长的子女——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张伯苓之子张锡祜、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投身抗战。梅贻琦的四个女儿中,两个也在1944年从军运动中报了名。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西南联大在短短九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其精神可以概括为 “刚毅坚卓” 的校训,这四个字体现了联大人在民族危亡关头的精神风貌。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西南联大守护了中华文脉,延续了学术薪火,培养了复兴种子。这段历史,将永远激励后来者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一开始,西南联大连校舍都没有,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也就在这一年,17岁的杨振宁随其父亲、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南迁至昆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杨振宁报考大学时选的是化学系,进入西南联大后,他切身感受到了物理学的魅力,于是转入物理系,师从赵忠尧、吴大猷、吴有训、周培源等物理学家。这一选择,改变了杨振宁的命运,也在多年后改变物理学界。
1937年北平沦陷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邓稼先一样从沦陷区逃亡的,还有李政道。李政道当时不到20岁,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同时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历经3年颠沛流离,李政道才进入西南联大,拜入物理学大师吴大猷门下,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美留学。
在美国,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做研究,发表论文,并在1957年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办学的九年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就读,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西南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西南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学生有90人。
当然,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也赫然列在西南联大校友录上。
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学子献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戴荣钜、王文、吴坚等西南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在空战中英勇殉国。翻译家许渊冲曾为飞虎队准确翻译日军情报,使昆明免遭一次空袭。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蔚然成风。三位校长的子女——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张伯苓之子张锡祜、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投身抗战。梅贻琦的四个女儿中,两个也在1944年从军运动中报了名。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西南联大在短短九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其精神可以概括为 “刚毅坚卓” 的校训,这四个字体现了联大人在民族危亡关头的精神风貌。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西南联大守护了中华文脉,延续了学术薪火,培养了复兴种子。这段历史,将永远激励后来者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