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皇权旁落
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公元前48年1月10日,开创西汉“孝宣中兴”、将汉朝综合国力推到极盛43岁的汉宣帝,病逝于未央宫。
汉宣帝刘询在弥留之际,望着侍奉在旁,“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内心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然后无奈闭上沉重的双眼,含恨而去。
刘奭是汉宣帝和许平君的独子。
当年,汉宣帝因祖父戾太子刘据,刘询因巫蛊之祸事件而下狱。
皇子皇孙变成了阶下囚,刘询与宦者丞许广汉(昌邑哀王刘髆的侍从官,后犯罪被处以宫刑)同室而居。
当时,管理掖庭令张贺,原是刘据家吏。
刘据被诬害时,张贺也受了宫刑,以旧日恩情,对刘询十分照顾。
等到刘询长大,张贺想把自己孙女嫁给他,却被与霍光一同辅政的弟弟右将军张安世制止。
张安世估计也不会认为刘询会死灰复燃。
张贺是铁了心要牵红线,听说许广汉有女,便打定主意!
他就设宴相邀老许,酒兴浓时,就说:“皇曾孙是皇帝的近亲,即使地位卑贱,也可能当关内侯,可以择其为婿。”
许广汉看到自己这副模样,于是毫不犹豫便同意了。
于是,15岁二婚的许平君,就嫁给落难凤凰不如鸡的黄曾孙刘询,他们成为一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夫妻。
两人本以为会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没想到风云突变,21岁的汉昭帝去世,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由于不断挑战权臣霍光的权威,光速被霍光直接废掉。
刘询因无权无势,被拥立上台,和当年汉文帝被功臣派拥立上位,如出一辙。
刘询作为傀儡,霍光专权。
许皇后被霍光女儿霍贵人毒死,刘询一直隐忍不发,等霍光去世后,才把霍家连根拔起。
亲政后的他,开启了西汉最后一个盛世:“孝宣中兴” 。
经过26年的励精图治,他将西汉送上了巅峰。
不过,雄才大略的他,也为子孙埋下两颗炸弹:外戚专政,宦官专权。
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他的势力太弱,只能依靠祖母史家和老婆许家,依靠陪他安全渡过权臣霍光危险的宦官。
后世评价道:“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
如今他即将告别这个他亲手缔造的帝国。
他知道,眼前这个满脑子“纯任德教”、不得“以霸王道杂之”要领精髓的继承人,终将会把汉朝带上“独尊儒术”的道路,大汉帝国百年荣光也即将迎来日落黄昏。
可惜再也没机会了,贫贱夫妻感情深,念及“故剑情深”,加之有“好圣孙”(汉成帝,和后来的司马炎一样,看走眼),他才没废掉太子刘奭。
西汉初年,盛行黄老之术,崇尚无为而治;
汉武帝时期,虽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暗地里却是“以霸王道杂之”;
从汉元帝时期,西汉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
元帝上台后,很快应证了汉宣帝的担忧。
乱大汉天下,果然是太子。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舞台上角逐。
宣帝临终前,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史高是汉宣帝的表叔、是外戚,史家把汉宣帝养大;
萧望之、周堪是元帝的老师,是儒臣的代表;
中书令弘恭、石显,典领中枢(汉武帝开创),是中朝宦官的代表。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
于是,外戚的史高与儒臣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为首的儒臣,上书新任帝王,打算废掉中书宦官制度。
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
萧望之提出此动议,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
端掉别人的饭碗,与谋财害命无异。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都是汉宣帝的提拔的外戚集团)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的儒臣集团,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
出于身体欠佳,加之灵魂伴侣仙逝,对石显的信任,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
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
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
石显为人机灵聪明,能够参透汉元帝的心思,极其狡诈,常用诡辩陷害异己,对于违逆他的人,石显都睚眦必报,将其处以严刑峻法。
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
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
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
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诽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专权期间,结党营私,清除异己,谮杀宰辅萧望之、魏郡太守京房、待诏贾捐之、太中大夫张猛、郑地长官苏建,禁锢周堪、刘更生,废黜御史中丞陈咸,使得公卿百官无不畏惧。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谀奉承石显,不敢言。
石显前后得赏赐及贿赂多达一亿,名副其实的“二皇帝”,为后来宦官专政擅权,树立了“标杆”。
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汉元帝始终未能觉察。
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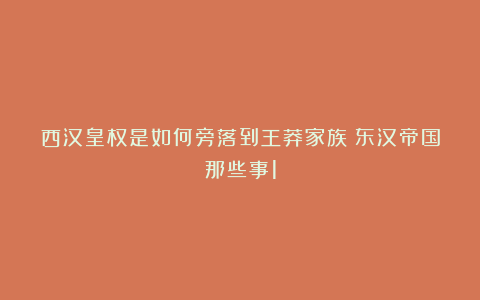
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太监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
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回顾汉元帝的时政,基本上乏善可陈,除了造就中国历史四大美女之一的昭君出塞,还是陈汤攻杀郅支单于,结束了匈奴南北分裂的局面。
只可惜,那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立下奇功,却被儒臣凿壁借光的丞相匡衡及中书令石显等,诋毁擅自假托皇帝命令兴师动众。
好在汉元帝硬气了一把,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给陈汤关内侯的爵位。
可以说在汉元帝时代,是西汉宦官的巅峰期,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很快权力开始易主。
这一切,来源于一个“三婚女”王政君的上台。
元帝虽然好糊弄,却是405年两汉中第一大痴情种帝王。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君心可否似我心?
当时,他深爱的司马良娣病逝。
临死前,司马良娣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
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史书: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因以过怒诸娣妾,莫得进见者。
汉宣帝怕太子忧伤过度,又考虑皇位的继承,于是令王皇后挑选五名宫女,供太子选妃,王政君位列于候选人中。
她穿着一件绣着红色花边的艳服,刚好坐在最靠近太子的位子上。
太子还陷于思念爱妃司马氏的悲痛之中,无心选妃。
皇后在旁边催促,刘奭随便指着靠近自己身边的一位宫女。
皇后看王政君长相还算说得过去,更何况皇太子点头,于是就忙命人将王政君送到东宫。
王政君是法官王禁之女,其母李氏是魏郡李家的长女。
史称:廷尉史王禁有大志,不修边幅,好酒色,多娶傍妻,一共有二女八子;
长女王君侠,次女王政君;
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王凤、王崇与王政君同母。
记住这些人,他们将是不久后西汉政坛的风云人物。
李氏本是王禁正妻,后因她妒忌诸妾,与王禁离异,改嫁给河内郡的苟宾为妻。
在未入宫前,王政君原先许嫁一户人家,可男方突然死了。
后来东平王纳她为妾,但还没入门东平王就死了,用后来的话说是天煞孤星、命里克夫。
太子原本已有姬妾十多人,但长年以来一直都没怀孕,而王政君成为太子妃后,一夜之间竟然怀孕了,这使汉宣帝非常高兴。
公元前51年,王政君分娩生下一子,汉宣帝亲自为皇孙命名为刘骜(骜即骏马),字太孙,时时带在身边。
四年后,刘骜被立为太子。
刘骜应该就是《世说新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型,和后来司马炎的孙子司马遹一样,幼年聪慧,长大则废。
青年时的刘骜,爱读经书,喜欢文辞,宽博谨慎。
有一次元帝急诏刘骜,他不敢横越驰道(皇帝专用道路),绕了一圈迟迟才面见元帝。
汉元帝知道了事情始末之后,非常的高兴,下令太子可以直接穿越驰道。
随着年龄增长,刘骜开始终日沉湎于玩乐,生母王皇后也不得元帝宠幸。
有一次,汉元帝的弟弟中山哀王刘竟去世,看到太子面无哀伤的表情。
汉元帝很恼火地说:“哪里会有一个人不慈和仁爱,却可以奉祀宗庙,作百姓父母的呢!”
于是,他一意孤行要废掉这个冷血的太子。
幸好汉元帝的首席托孤大臣史高的儿子史丹帮忙周旋,加之石显的拥护,捡回太子的帽子。
汉元帝以史丹是旧臣,而且还是父亲外戚,因此很亲信他,诏令史丹护卫太子家。
当时,汉元帝的妃子傅昭仪生子定陶王刘康,刘康有才艺,子母都受到汉元帝爱幸。
而太子刘骜有酒色过失,其母皇后王政君亦无宠幸,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公元前33年,体弱多病的汉元帝,即将迎来人生的黄昏。
这时的他,终于体会到当年父王内心的各种滋味。
汉元帝卧病,傅昭仪和定陶王刘康常在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却很少进见。
汉元帝病情渐重,思想迷惑不清,多次拿汉景帝时立胶东王刘彻旧事,询问尚书。
当时刘骜的长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尉卫、侍中,与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忧愁,不知计从何出。
史丹以亲密之臣,得到侍奉探病的机会,等候汉元帝单独睡着时,直入卧内,顿首伏在青蒲席上,以死劝服。
汉元帝一向仁慈,不忍心见史丹涕泣,谈话真切至诚,汉元帝大为感动,喟然叹息说:
“我一天天精力不济,而太子、两王幼少,思想中恋恋,又怎么不念叨呢?但无动摇之议。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我岂敢违旨!驸马都尉从何处听到此语?”
史丹即后退,顿首说:“愚臣妄闻,罪当死!”
汉元帝便纳史丹之言,对史丹说:“我病渐重,恐不能再愈,君好好地辅导太子,不要违背我的意思!”
太子刘骜由此便成为继承人。
前33年5月,汉元帝刘奭崩。
6月,皇太子刘骜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
刘骜的母亲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侯。
首先是自己的一母同胞获益,以太后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同母弟王崇为安成侯。
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是西汉中后期的首席大臣、实际上的宰相,始于汉昭帝。
当年,大将军霍光柄政,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是为此官之始。
后来,又同日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世称“五侯”,王氏权势大炽。
就连王政君的生母李氏改嫁生的苟参,也打算封侯,被汉成帝拒担任任侍中、水衡都尉。
王莽的父亲王曼,因早死而没有被封侯,而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等人多称赞王曼之子王莽,便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王莽嗣侯位,并任命为大司马。
老大王凤官位高至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其大司马职位先后由王音、王商(成都侯)、王根继承,最后传至王政君的侄子王莽。
皇权旁落,王氏家族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王莽也开启了他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