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细胞因子风暴(CS)是一种严重的系统性炎症综合征,特征为免疫细胞过度激活及循环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与多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密切相关,包括FM、ARDS、HLH、CAR-T疗法相关的CRS以及III-IV级aGVHD。该综述深入探讨了CS的病理生理机制,聚焦于关键信号通路(如JAK-STAT、TLRs、NLRP3炎症体和NETs)及其引发的免疫失调和多器官损伤。文章系统回顾了CS在FM、ARDS、SIRS、HLH、aGVHD及CRS等疾病中的特征与管理策略,强调多学科协作、免疫调节、器官支持及靶向治疗的重要性。针对不同疾病中CS的独特信号通路与细胞因子,研究者提出了定制化治疗方案,并展望了通过组学技术、人工智能、靶向药物传递及基因编辑等前沿手段实现更精准的CS管理前景。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科汪道文/隗佳/魏双团队于2025年4月16日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发表题为“Deep insight into cytokine storm: from pathogenesis to treatment”的系统综述。该综述系统概述了CS相关的关键信号通路和免疫细胞,阐明了CS导致器官损伤的机制,以及在多种内科危重症疾病中CS的作用机制和治疗策略。聂佳丽、周灵、田卫伟、刘先胜为本文的第一作者,汪道文、隗佳、魏双教授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图1 细胞因子风暴的洞察时间线
CS涉及的关键信号通路及相关细胞因子的作用
图2 细胞因子信号通路
JAK/STAT通路
JAKs与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s)是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CS中发挥重要作用。该通路由三个主要结构组成:跨膜受体、受体相关的JAKs和STATs。JAK家族包括四种亚型:JAK1、JAK2、JAK3和TYK2,而STAT家族包括七种亚型:STAT1、STAT2、STAT3、STAT4、STAT5A、STAT5B和STAT6。多种细胞因子,包括IL(ILs)、干扰素(IFNs)和生长因子,已被证明参与JAK/STAT信号传导,调控细胞分化、代谢、造血、稳态和免疫调节等关键生理过程。特别是IL-6作为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通过经典顺式信号、跨信号和跨呈递机制触发JAK/STAT3通路。IL-6可与免疫细胞上的膜结合IL-6受体(mIL-6R)以及sIL-6R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触发gp130激活并随后启动JAK/STAT3信号通路。这种IL-6/IL-6R/JAK/STAT3的激活级联导致系统性过度炎症反应,引起IL-1β、IL-8、趋化因子配体2(CCL2)、CCL3、CCL5、GM-CSF和VEGF等介质的分泌。此外,TNF和IFN-γ是两种重要的促炎细胞因子,可激活JAK家族激酶,特别是JAK1,导致STAT蛋白的磷酸化和激活,从而促进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这一过程在CRS的病理生理中起关键作用。JAK/STAT通路的过度激活被认为是HLH、aGVHD、CAR-T、COVID-19和FM相关CS等多种疾病中诱导细胞因子释放和炎症紊乱的关键因素。
在HLH患者血清中检测到多种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包括IL-1、IL-2、IL-6、IL-10、IL-12、IL-18、TNF、IFN-γ和GM-CSF。这些细胞因子主要激活JAK/STAT通路,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常作为不良预后指标。特别是IL-2和IL-12是诱导CD8 T细胞中STAT5激活的关键细胞因子。JAK/STAT通路在aGVHD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介导NK细胞的促GVHD效应。STAT1和STAT3在调控aGVHD中细胞因子生成、激活、扩增和Tregs命运中至关重要。
在CAR-T疗法相关的CRS中,JAK/STAT通路发挥重要作用,适当激活可增强CAR-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而过度激活则导致CRS。抑制JAK1已被证明可减轻CAR-T疗法相关的CRS。在COVID-19中,CS与ARDS和多器官衰竭相关。抑制JAK在COVID-19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疗效。JAK/STAT通路在病毒性心肌炎的启动中起重要作用,影响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STAT3间接调节肥厚重塑和心力衰竭的进展。STAT3的过度激活在小鼠心肌梗死模型中加重了预后。此外,STAT3对Th17细胞的分化至关重要,对心肌炎的发展和进展有重大影响。这些发现强调了不同细胞因子和JAK/STAT通路在CRS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表明靶向JAK/STAT通路作为CRS治疗策略的潜在有效性。
Toll样受体
Toll样受体(TLRs)是一类原始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可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s)。这些受体存在于多种免疫细胞和组织细胞上,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Cs),作为病原入侵的探测器。TLRs的激活在感染性疾病发展和CS进程中起关键作用。TLRs识别PAMPs后,启动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并协调适当的免疫反应以保护细胞免受伤害。TLRs激活导致抗病毒细胞因子(如I型干扰素、IL-1β和IL-6)的产生,直接抑制病毒复制。然而,TLRs释放的促炎因子和细胞因子也可能产生有害效应。促炎介质的过度产生可能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TLRs通过两条不同的信号通路促进CS:经典TLRs-MyD88-MAPK通路,触发TNF、IL-1β和IL-6等促炎因子和细胞因子的转录;以及非经典TLRs-TRIF-IRF3通路,诱导I型干扰素(IFN-α和β)的产生。
TLRs的激活在多种炎症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与临床结局密切相关。研究表明,TLR3、TLR4、TLR7和TLR8等在COVID-19的免疫失调中发挥作用。SARS-CoV-2的突触蛋白与细胞表面TLRs(特别是TLR4)相互作用。气管内吸出物、全血和血浆样本分析显示,重症COVID-19患者中TLR3、TLR4、TLR7和TLR9的激活增强。使用核酸结合微纤维治疗显示出减轻TLRs过度激活及后续NF-κB通路的潜力,通过移除受损相关分子模式(DAMPs)/PAMPs。在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机制中,TLRs也发挥作用,TLRs的遗传变异影响疾病易感性。在经活检证实的肠道病毒性心肌炎患者中,52.63%存在TLR3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其中21.05%为SNP纯合子,而对照人群中该SNP纯合子率仅为4%。此外,TLR4 SNP与心肌炎症易感性相关。在经典的柯萨奇病毒B3(CVB3)诱导的病毒性心肌炎小鼠模型中,CVB3感染导致所有TLRs上调,进而触发细胞因子产生和免疫细胞向心肌募集。心肌内浸润的免疫细胞与受损心肌细胞共同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IL-1、IL-6、TNF和干扰素,导致进一步的组织损伤和细胞因子释放,形成有害的正反馈循环。TLRs的不当激活可能导致自身免疫反应。例如,由于与特定PAMPs的结构相似性,心肌肌球蛋白暴露可直接刺激TLR2和TLR8,启动下游信号通路。
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
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是由中性粒细胞形成的胞外网状结构,包含中性粒细胞弹性酶、髓过氧化物酶、组织蛋白酶G、组蛋白和DNA等成分。NETs具有捕获病原体和限制感染扩散的强大能力。炎症刺激可通过中性粒细胞的网状增殖过程(称为NETosis,一种新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诱导NETs的产生。NETs的内容物可通过促进IL-8释放增强中性粒细胞的促炎活性。此外,NETs通过炎症体信号促进CD4+ T细胞的激活和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在动脉粥样硬化中,NETs通过TLR2和TLR4通路增加巨噬细胞IL-6和pro-IL-1β的表达。促炎细胞因子的升高促进Th17细胞分化和髓系细胞募集。
NETs可能加剧SARS-CoV-2诱导的CS和巨噬细胞激活综合征(MAS)。在COVID-19中,NETs的过度形成与急性肺损伤(ALI)、ARDS和免疫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相关。NETs加剧病毒性心肌炎的进展。抑制NETs改善了实验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结局。调控NETs释放和NETosis的一个已知机制是midkine-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轴。
NLRP3炎症体
NLR家族含吡啶结构域3(NLRP3)炎症体是一种多聚体细胞质蛋白复合物,在细胞刺激下形成。NLRP3炎症体的激活导致胱天蛋白酶-1的激活,进而促进IL-1β、IL-18和gasdermin D(GSDMD)的成熟。NLRP3炎症体的激活需要两个信号:首先通过PRRs激活NF-κB,NF-κB转移到细胞核,启动胱天蛋白酶-1、NLRP3、pro-IL-1β和pro-IL-18的转录。随后,细胞应激信号刺激NLRP3炎症体复合物的组装和激活。NLRP3炎症体随后促进胱天蛋白酶-1的二聚化和激活,导致pro-IL-1β、pro-IL-18和GSDMD裂解为活性形式。IL-1β促进中性粒细胞和T细胞向感染部位募集,导致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释放IL-6和TNF等次级细胞因子。IL-18的升高刺激T细胞和NK细胞产生IFN-γ。此外,GSDMD作为促炎介质触发焦亡性细胞死亡。IL-1β与IL-1R1和IL-18与IL-18R的结合激活NF-κB信号通路,形成放大炎症反应的正反馈循环。
NLRP3炎症体的持续激活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相关,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哮喘和过敏性气道炎症、糖尿病、炎症性肠病、动脉粥样硬化、痛风性关节炎等。此外,NLRP3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导致一组自身炎症性疾病,称为冷炎素相关周期性综合征(CAPS),包括新生儿多系统炎症病、家族性冷自身炎症综合征和Muckle-Wells综合征。INFEVER数据库报告了超过200种与CAPS相关的NLRP3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导致在无应激信号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炎症体和IL-1β、IL-18产生以及细胞焦亡。CAPS患者表现为发热、血液中性粒细胞增多以及皮肤、关节和结膜的组织特异性炎症。携带CAPS相关NLRP3变体的小鼠表现出系统性、致命性炎症。NLRP3炎症体的激活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相关。在病毒性心肌炎中,CVB3感染在体内外均触发炎症体激活。类似地,在SARS-CoV和MERS-Co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肺炎中,NLRP3炎症体在过度炎症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在COVID-19中,NLRP3炎症体的激活不仅导致严重呼吸系统并发症,还引发神经系统综合征。
CS中的细胞死亡与免疫细胞激活作用
图3 细胞死亡与细胞因子风暴
CS中的细胞死亡
细胞因子风暴(CS)是由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和大批量细胞因子释放引起的病理状态,可能导致多种细胞死亡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坏死性凋亡、凋亡、焦亡和PANoptosis。坏死性凋亡是一种涉及病毒感染免疫反应和严重炎症损伤的程序性坏死。抑制胱天蛋白酶-8足以减少坏死性凋亡并释放抗炎细胞因子IL-10,IL-10参与脓毒症的免疫抑制阶段。凋亡在病原体清除和稳态维持中起关键作用。SARS-CoV-2感染触发胱天蛋白酶-8依赖性凋亡,导致COVID-19患者肺损伤。焦亡是一种促炎的程序性细胞死亡,作为宿主对抗感染的防御机制。SARS-CoV-2编码的冠状病毒产物调控焦亡途径中的关键成分,包括炎症体、胱天蛋白酶和gasdermins。
PANoptosis是一种独特的先天免疫炎症调控细胞死亡(RCD)途径,由PANoptosome复合物调控,整合了其他RCD途径的元素。PANoptosis的发生与多种疾病相关,如感染性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自身免疫病。不同信号激活特定的感测蛋白,启动不同PANoptosome复合物的组装。ZBP1、AIM2和RIPK1是常见的PANoptosome触发因子,可被不同病原体或刺激物激活,引发一系列生物反应,包括凋亡和CS。例如,ZBP1在流感病毒感染和IFN治疗期间的CoV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AIM2参与疱疹病毒1型感染和细菌感染的病理过程。IFN信号在病毒感染中发挥多重作用。在SARS-CoV-2感染中,先天免疫细胞产生的多种炎症细胞因子中,TNF和IFN-γ的共同产生独特地触发PANoptosis。研究发现,只有TNF和IFN-γ的组合诱导了以PANoptosis为特征的炎症性细胞死亡。使用针对TNF和IFN-γ的中和抗体可保护小鼠免受SARS-CoV-2感染、脓毒症、HLH和细胞因子休克相关的死亡。强烈的细胞因子释放被认为与肺损伤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相关。
T细胞
T细胞激活是炎症反应和CS诱导的重要组成部分。T细胞可分为两大亚型:CD4+辅助T细胞(Th)和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CD4+ T细胞主要参与免疫调节,而CD8+ CTL是促炎因子产生和组织损伤的直接效应细胞。
CD8+ CTL选择性靶向感染或恶性细胞,通过分泌促炎细胞因子、与Fas配体受体相互作用以及释放细胞溶解颗粒导致其死亡。CTL功能障碍可能导致CRS。一个显著因素是穿孔素介导的细胞溶解。穿孔素包含在CTL释放的细胞溶解颗粒中,形成通道使细胞毒性介质进入靶细胞,导致细胞溶解。多个基因产物参与颗粒形成和穿孔素与靶细胞融合的过程。这些基因的遗传缺陷导致CTL无法杀死靶细胞,持续存在DAMPs/PAMPs。CTL与APCs的长期交互导致大量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这是原发性和继发性HLH中CS的关键机制。
CD8+ T细胞的细胞靶向和细胞毒性能力已被广泛研究用于潜在治疗应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过继细胞疗法,其中从患者获得的CD8+ T细胞在体外扩增和激活后重新注入患者体内。CAR-T疗法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是一种基因修饰的CD8+ T细胞被重新注入患者以特异性靶向和对抗癌细胞的治疗方式。
NK细胞
NK细胞主要发挥抗病毒和抗肿瘤反应并产生促炎细胞因子。然而,NK细胞功能障碍导致无法消除感染或恶性细胞,造成持续的免疫激活和CS。一个机制与穿孔素缺乏有关,类似于CD8+ CTL。此外,NK细胞根据周围炎症环境表现出细胞因子产生的可塑性。遇到肿瘤配体和细胞内病原体时,NK细胞分泌Th1型细胞因子,如IFN-γ、TNF和GM-CSF,进而刺激T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DCs的激活。此外,NK细胞释放趋化因子,如MIP-1α、MIP-1β、CCL5、淋巴毒素和IL-8,吸引髓系细胞和效应淋巴细胞到炎症组织。IL-2和IL-15在激活NK细胞中起关键作用,重组IL-15可扩增NK细胞群并促进肿瘤消退,同时减少转移。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的过度激活直接导致炎症放大和CS,如MAS所示。巨噬细胞通常根据其激活模式和炎症能力分为M1和M2亚型。M1巨噬细胞主要由T细胞反应(特别是CD4+ Th1细胞)激活,表现出强大的抗原呈递和促炎功能。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清除病原体的主要效应细胞,由IFN-γ和TNF激活,释放包括IL-1β、IL-6、IL-12、IL-15、IL-23、TNF和MIP-1在内的炎症细胞因子。M1巨噬细胞通过分泌炎症趋化因子(如MCP-1、CXCL10、CCL2、CCL5、CXCL8和CXCL9)募集粒细胞、NK细胞、Th细胞和其他巨噬细胞到感染部位。此外,还促进CD4+ T细胞分化为Th1和Th17细胞,在清除侵入性病原体中起关键作用。这些机制共同促成了M1巨噬细胞的强大抗感染和炎症功能。
M2巨噬细胞以其抗炎特性而闻名,是炎症消退和组织纤维化愈合的主要巨噬细胞亚型。M2巨噬细胞可进一步分为M2a、M2b、M2c和M2d亚型。M2a巨噬细胞是最常研究的亚型,由IL-4和IL-10调控,具有抗炎潜力。在感染或损伤部位,巨噬细胞通过感知凋亡细胞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而被激活。巨噬细胞上的IL-4R和IL-13R由2型细胞因子IL-4和IL-13激活。凋亡细胞感知与IL-4/IL-13信号的协作促进巨噬细胞极化为M2a表型并消退炎症。IL-4信号缺陷抑制巨噬细胞的DNA修复功能,使巨噬细胞处于促炎状态,促进炎症扩展和机体老化。M2b巨噬细胞(也称为调节性巨噬细胞)由免疫复合物和TLR配体激活,产生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以发挥免疫调节功能。M2c巨噬细胞由糖皮质激素或IL-10激活,促进组织再生。M2d巨噬细胞(也称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由TLR配体和A2腺苷受体激动剂激活,促进肿瘤进展和转移。
M2巨噬细胞产生的主要抗炎细胞因子包括IL-10和TGF-β,IL-10通过抑制IL-12和IL-23合成直接抑制APCs并干扰Th1和Th17细胞的分化。M2巨噬细胞的过度极化导致病原体清除受损和T细胞调节功能受损。这种T细胞功能受损随后削弱巨噬细胞的杀菌能力和B细胞的抗体产生。此外,无法有效清除病原体导致其持续增殖和免疫系统持续刺激,导致炎症因子不受控分泌,最终触发CS。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是损伤、感染和炎症部位的第一反应者,通过趋化作用到达这些部位。在识别PAMPs或DAMPs或响应炎症信号时,中性粒细胞通过募集和激活其他白细胞以及信号通知骨髓产生和成熟更多中性粒细胞来启动免疫反应。中性粒细胞通过三种主要机制清除病原体:吞噬作用、NETosis和脱颗粒。吞噬作用涉及中性粒细胞对病原体的吞噬、内化和降解,而NETosis是病原体的胞外捕获过程。脱颗粒是中性粒细胞从其颗粒中释放多种细胞因子的过程,包括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α、IL-1β、IL-6、IL-16、IL-18和MIF。中性粒细胞不仅释放炎症介质,还在调节其他免疫细胞(特别是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功能中发挥作用。例如,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涉及中性粒细胞分泌azurocidin,进而增强吞噬活性和促炎细胞因子(如TNF和IFN-γ)的释放。中性粒细胞还释放CXCL10通过CXCR3信号促进巨噬细胞增殖。此外,在炎症后期阶段,中性粒细胞通过巨噬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被清除。
中性粒细胞在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在病毒性心肌炎中,早期中性粒细胞消融导致单核细胞向心肌的流入减少。此外,抑制NETs形成显著减少炎症并维持小鼠心肌炎的收缩功能。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肺部观察到大量中性粒细胞存在。在COVID-19的初始阶段,中性粒细胞被激活并迁移到肺部对抗SARS-CoV-2病毒。然而,中性粒细胞的过度激活与COVID-19患者中严重CS的发展相关。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循环中性粒细胞水平升高与COVID-19患者的氧合受损相关。此外,易于发生NETosis的低密度中性粒细胞与COVID-19患者血管内微血栓形成和ARDS的发展密切相关。
B细胞
B细胞的主要作用是产生抗体,以及参与抗原传递和调控T细胞活性。在CAR-T细胞疗法中,B细胞缺乏抗体产生导致无法有效清除病原体,PAMPs反复触发炎症级联,最终导致CS。此外,B细胞针对病毒抗原产生的抗体可能与自身抗原发生交叉反应,可能导致自身免疫反应。
肥大细胞
肥大细胞以其在过敏反应和寄生虫感染中的作用而闻名,也在炎症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肥大细胞是心肌中TNF释放的主要来源,在CVB3感染期间,心脏肥大细胞分泌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如TNF、IL-1β和IL-10。肥大细胞的积累与CCL2介导的Ly6Chigh巨噬细胞向心脏的浸润增加有关,加剧病毒性心肌炎中的心脏功能障碍和纤维化。来源于驻留心脏成纤维细胞的早期干细胞因子刺激肥大细胞积累和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这些细胞因子反过来激活成纤维细胞表达TGF-β、沉积胶原并产生额外的细胞因子。肥大细胞通过加剧炎症和纤维化共同促成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机制。
嗜酸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通过合成多种毒性颗粒蛋白维持免疫稳态。受刺激时,嗜酸性粒细胞释放这些蛋白,包括主要碱性蛋白、过氧化物酶、神经毒素和细胞因子。嗜酸性粒细胞对寄生虫、细菌和病毒具有抗感染特性,同时也促成心肌炎、哮喘和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等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在高嗜酸性粒细胞疾病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持续激活导致颗粒蛋白和化学介质的释放,引起组织损伤。嗜酸性粒细胞的增殖、成熟和募集受IL-5、IL-4和IL-13等细胞因子的调控。糖皮质激素传统上用于治疗嗜酸性粒细胞疾病,通过非特异性减弱嗜酸性粒细胞。最近,几种新型生物疗法已被批准用于临床,特异性靶向嗜酸性粒细胞成熟相关因子,包括IL-5、IL-5受体或IL-4/IL-13。
细胞因子风暴(CS)中的靶器官损伤及不同疾病的应对策略
图4 致命性心肌炎的诊断与治疗
靶器官损伤
CS常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包括心脏、肺、肾等器官的损伤。尽管器官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继发性损伤,而非CS的根本病理生理机制,但却反映了CS的严重程度,并且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了解CS如何影响这些器官有助于研究者更早识别CS并提供及时治疗。
血管内皮
在CS中,血管系统主要受到血管通透性增加和内皮功能障碍的影响。这种现象主要由细胞因子(如IL-1、IL-6和TNF)的过度释放驱动。这些细胞因子激活并损伤内皮细胞,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从而引发组织水肿和液体积聚。此外,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可能损害内皮功能,表现为内皮细胞收缩和血管舒张功能受损,进而导致低血压和组织灌注不足。细胞因子诱导的血管舒张可进一步降低血压,严重时可能导致器官灌注不足甚至休克。此外,IL-6、IL-1β和TNF等细胞因子可激活凝血系统,促进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激活,从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补体系统的激活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的形成进一步加剧血管损伤和血栓形成。补体系统激活导致内皮损伤和血小板激活,而NETs促进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激活,增加血栓风险。
心脏
CS导致的心脏损伤主要表现为FM,伴随快速的血流动力学恶化和严重心律失常。细胞因子诱导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液体渗漏至心肌组织。超声心动图、MRI和心内膜心肌活检(EMB)显示明显的心肌水肿。此外,细胞因子直接损害心脏收缩功能,导致心源性休克,并可能因组织灌注不足引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例如,促炎细胞因子IL-1已被证明具有负性肌力作用,直接降低心肌收缩力。阻断IL-1受体(如使用阿那白滞素)可有效改善FM患者的心脏收缩功能和预后。此外,细胞因子抑制线粒体功能,导致能量生成受损,产生过量活性氧(ROS),引发氧化应激和心肌细胞死亡。受损细胞释放的自身抗原进一步加剧炎症紊乱,促进细胞因子释放。因此,由于能量供应不足、组织水肿和细胞损伤,心脏收缩功能显著下降。
除收缩功能受损外,CS还破坏心脏电传导的协调性和收缩同步性,导致心律失常。常见的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和难治性室颤。在FM的急性期,CS通过三种主要机制诱发或加重心律失常:首先,细胞因子(如TNF、IL-1β和IL-6)通过改变ryanodine受体和L型电压门控钙通道Cav1.2的功能,直接干扰Ca2+稳态。由于Ca2+在动作电位生成和兴奋-收缩耦联中至关重要,其信号紊乱可促进心律失常。其次,细胞因子通过诱导膜裂解和减少细胞间连接,直接损伤心肌细胞膜,导致电不稳定和传导受损。在小鼠心肌炎模型中,柯萨奇病毒B3(CVB3)被发现降低心肌连接蛋白表达并破坏间隙连接功能。第三,炎症细胞浸润和组织水肿也被观察到。电解剖电压映射显示,淋巴细胞显著浸润的局灶部位电位较低。心律失常是FM的常见临床表现,与预后不良相关。除了FM,多种炎症性疾病的细胞因子级联反应也可导致心脏损伤。例如,CS与CAR-T疗法和COVID-19中的心脏损伤及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CS的心血管表现包括心肌损伤、心肌炎、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病和心力衰竭。
肺
多种炎症细胞因子可靶向肺部,导致肺泡塌陷、肺顺应性降低、肺血管阻力增加和气体交换障碍。肺损伤是CS中的常见现象,源于基础疾病(如FM和呼吸道感染)以及治疗相关并发症(如CAR-T疗法诱导的炎症和移植后GVHD)。此外,病原体通过与肺泡上皮细胞受体相互作用可触发ARDS。肺实质中细胞因子的积聚受到小血管丰富的影响。这些细胞因子刺激炎症反应,导致肺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损害。这种炎症级联反应导致低氧血症、肺泡上皮细胞钠泵活性降低、细胞代谢紊乱,并最终加剧肺损伤。NF-κB的释放进一步放大炎症反应,最终导致肺功能恶化和ARDS的发生。
IL-6在肺损伤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IL-6可诱导免疫细胞在肺部积聚,触发自由基和蛋白酶释放,导致肺上皮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IL-6还通过与炎症体复合物协同作用促进肺泡细胞焦亡。此外,IL-6减少纤维连接蛋白生成,导致细胞间连接减弱。随着肺泡和血管上皮细胞发生水肿和焦亡,呼吸膜通透性增加。此外,IL-6在Th17细胞分化和成熟中发挥作用,Th17细胞产生IL-17和IL-22等细胞因子,从而促进包括成纤维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类型产生炎症细胞因子。
骨髓
在CS中,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导致骨髓功能广泛紊乱。细胞因子可抑制骨髓功能,导致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关键血细胞生成减少。这种紊乱可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造血干细胞(HSC)功能障碍和骨髓微环境损伤。
炎症细胞因子(如TNF、IFN-γ和IL-6)损害HSC的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导致HSC池的加速衰老并耗竭。TNF通过ERK-ETS1途径诱导IL-27Ra,促进炎症并进一步损害HSC功能。IFN-γ也对HSC自我更新产生负面影响。持续的炎症暴露导致进行性和不可逆的造血抑制,表现为贫血、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长期细胞因子暴露耗竭HSC池,导致骨髓衰竭和感染风险增加。
除了直接影响HSC,细胞因子驱动的炎症还破坏骨髓微环境,其中基质细胞在支持造血中起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L-1β是微环境炎症的核心介导者,驱动造血老化并改变支持性微环境的功能。然而这些微环境损伤无法通过全身性干预逆转,凸显其不可逆性。在aGVHD等病理状态中,T细胞过度激活和细胞因子生成失调导致骨髓微环境严重损伤,造成显著的骨髓抑制。类似地,在HLH中,TNF和IFN-γ驱动的激活巨噬细胞促进造血细胞吞噬,进一步导致骨髓衰竭。
肾脏
CS导致的肾损伤主要表现为急性肾功能障碍或损伤,导致肾衰竭。患者可能出现氮质血症、少尿和无尿等症状。损伤的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免疫细胞募集、微血栓形成和其他器官功能障碍。IL-6通过促进Th17细胞分化和成熟发挥作用,Th17细胞分泌IL-17和TNF,共同减少血管内皮NO生成并增加血管收缩。IFN-γ在肾局部血管紧张素原生成中的调节作用导致AngII-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过度激活,增加醛固酮生成、水和钠重吸收,最终导致高血压。这一系列事件可损伤肾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并促进肾动脉粥样硬化。此外,细胞因子趋化作用吸引的T细胞沉积在肾毛细血管中,浸润毛细血管外膜和周围脂肪,产生ROS,最终导致肾损伤和纤维化。严重的凝血亢进可导致DIC,在毛细血管网中形成肾微血栓,导致肾微纤维化、急性肾小管坏死和皮质功能受损。在CS晚期,心脏输出量减少导致的肾灌注不足、肺损伤引起的低氧血症以及肝肾综合征均可导致肾损伤。CS与肾损伤中的补体系统密切相关。CS相关的先天免疫失调反应集中于IFN和补体功能障碍。肾小管上皮细胞、肾小球内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均可合成和分泌补体成分,并与肾局部免疫细胞和内皮细胞膜上的激活补体受体结合。补体功能障碍与急性病变(如肾小球肾炎、急性肾损伤和急性移植物排斥)以及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病、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纤维化)相关。
肝脏和胃肠道
CS导致的肝损伤包括肝大、肝损伤和可能致命的肝衰竭。患者可能表现为转氨酶升高、高胆红素血症、低白蛋白血症和胆汁淤积。胃肠道损伤可能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腹水和结肠炎。IL-1、IL-6、TNF和IFN等细胞因子均与肝损伤相关。IL-6与sIL-6R相互作用,刺激急性期蛋白(如血清淀粉样蛋白A、CRP和纤维连接蛋白)的生成。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可能导致肝淀粉样变性,进而引发肝衰竭,并影响肾和胃肠道功能,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此外,急性期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可激活补体系统并启动凝血级联,导致循环系统中持续的凝血亢进状态。免疫细胞浸润、补体系统和促凝途径的相互作用促进微血栓形成。肝功能障碍破坏凝血与抗凝平衡,严重时可能导致DIC。炎症体激活触发IL-1诱导的IL-1β生成,导致肝细胞焦亡和其他肝脏细胞因子的激活。这种正反馈反应加剧炎症损伤,炎症体和IL-1在肝细胞损伤和肝衰竭中起重要作用。此外,肝脏含有高浓度的NK细胞,过度激活时可通过IFN-γ依赖的STAT1信号通路抑制肝细胞增殖,阻碍肝再生。TNF在肝功能中发挥双重作用,通过NF-κB途径防止细胞死亡,同时通过ROS-JNK途径诱导肝细胞凋亡和坏死。
中枢神经系统
CS在中枢神经系统(CNS)中较为常见,与脓毒症相关脑病、脑型疟疾和CNS感染等多种疾病的神经功能障碍相关。在接受CNS肿瘤细胞疗法和其他免疫疗法的患者中,CS可能导致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或肿瘤炎症相关神经毒性。脑脊液中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与预后较差相关。CNS受累的CS患者可能表现为脑水肿、认知障碍、构音障碍、头痛、幻觉、失语、偏瘫、颅神经功能障碍、癫痫和嗜睡。脑CS可能导致血管渗漏、补体激活和凝血异常,增加患者卒中和脑组织缺血性坏死的风险。IL-6和TNF水平升高诱导的内皮损伤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促进血流中多种细胞因子进入脑实质。CNS内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可释放多种炎症因子,对神经元和胶质细胞产生有害影响,最终表现为神经症状。IFN-γ和TNF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效应,恶化神经表现。此外,病毒更容易渗透并直接损伤脑组织。虽然CAR-T细胞通常不直接损伤脑组织,但BCMA相关的CAR-T疗法例外,与帕金森样现象相关。但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的病因尚不清楚。IL-1及其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有表达,基线水平较低,但在多种病理条件下,IL-1加剧多系统炎症性疾病相关的神经退行性变。IL-1受体拮抗剂(如阿那白滞素)具有CNS渗透能力,可对CNS CS发挥保护作用。
CS在不同疾病中的应对策略
CS的病因众多,包括FM、病毒性肺炎、严重感染和噬血细胞综合征(HLH)等基础疾病。此外,CS还可能作为某些治疗的并发症,如CAR-T疗法和allo-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研究团队积累了宝贵的临床前数据和临床经验,致力于降低这些疾病中CS相关死亡率。
FM
FM中CS的发病机制
心肌炎是一种影响心肌的炎症性疾病,可由感染、免疫治疗毒性或自身免疫病等多种因素引起,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病因。FM是其最严重形式,特征为临床状况迅速恶化,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循环功能障碍和可能致命的心律失常。尽管FM较为罕见,但其死亡率和发病率较高,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在中国,估计每年有3–5万例FM病例。由于其前驱症状非特异性和极快的进展速度,大多数关于FM的知识来自尸检。近年来,随着治疗和EMB技术的进步,对FM的认识加深。CS在FM中的有害作用通过三方面证据得以确认:首先,FM中多种炎症标志物和细胞因子显著升高,包括IL-1、IL-10、可溶性肿瘤发生抑制因子-2(sST2)、TNF、IFN-γ、MIP-1α、MIP-2等;其次,大量促炎免疫细胞浸润心肌,伴随肝衰竭、肾衰竭和呼吸衰竭等多器官功能障碍;第三,免疫调节疗法(包括糖皮质激素、静脉丙球(IVIG)或细胞因子阻断)对FM治疗有效。研究者此前对FM队列进行了122种炎症细胞因子的全面分析,与对照组相比,FM样本中39种细胞因子显著变化,支持CS的存在。此外,EMB样本分析显示,FM患者退行性或坏死心肌中有大量免疫细胞浸润,包括T细胞、巨噬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尽管存在细胞因子释放。在针对178种人类病毒基因组(包括SARS-CoV和诱导心肌炎的病毒)的多重病毒PCR检测中,FM样本未检测到病毒基因组,强调免疫反应在FM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而非病毒直接损伤心脏。
病毒感染被认为是FM的主要病因。先天免疫在病毒性FM中起主导作用,TLRs、NETs和炎症体在信号通路、免疫细胞激活和细胞因子分泌中至关重要。中性粒细胞在急性心肌炎中迅速被募集至心肌,是最早响应的免疫细胞之一。Carai等进一步证明,在急性CVB3心肌炎小鼠中存在显著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和NETs存在。研究者近期研究发现,FM中中性粒细胞在迁移至心脏后具有独特的发育轨迹,通过Cxcl2/Cxcl3-Cxcr2轴持续募集外周中性粒细胞,导致心肌中性粒细胞急性积聚。此外,这些心脏分化的中性粒细胞募集并激活促炎巨噬细胞,加剧心脏CS。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自我调节募集机制显著缓解小鼠FM。使用抗Ly6G抗体早期耗竭中性粒细胞可减少单核细胞向心脏流入,抑制促炎巨噬细胞分化,阻止趋化因子CXCL1和CXCL2(相当于人类IL-8)上调,最终改善心肌炎中的心脏坏死。此外,通过敲除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4(PAD4)阻断NETs形成也被证明可缓解CVB3感染小鼠的心肌炎症和坏死。
巨噬细胞被认为是FM中的主要浸润细胞,作为清除者、杀菌效应细胞和调节细胞在心脏炎症中发挥作用。抑制心脏巨噬细胞积聚或其募集其他炎症细胞已被证明有益于急性心肌炎的管理。CCR2缺陷小鼠(缺乏巨噬细胞募集能力)显示促炎IL-1和IL-4生成减少,保护性IFN-γ和IL-10水平增加,炎症消退后心脏功能改善。巨噬细胞分泌的趋化因子IL-8及其小鼠对应物MIP-2对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具有强大趋化作用。心肌炎小鼠中观察到MIP-2水平升高,删除MIP-2受体与心肌炎严重程度降低相关。
在病毒性心肌炎中,CD4+ T细胞激活并分化为Th1、Th2、Th17和Tregs四种不同亚型。Th1和Th17细胞释放IL-17、IL-21、TNF和IFN-γ等细胞因子,加剧病毒性心肌炎的进展,而Th2和Treg细胞对疾病具有保护作用。多项研究显示CD4+ Th细胞比例与病毒性心肌炎的发展相关。此外,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通过选择性靶向和消除病毒感染细胞在抗病毒性心肌炎中起关键作用。
嗜酸性粒细胞心肌炎(EM)是心肌炎的重要形式,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特征,常伴随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然而,部分患者可能无外周嗜酸性粒细胞增多。EM需通过EMB明确诊断,通常表现为暴发性心肌炎,死亡率高。其病因尚未完全阐明,与感染、过敏反应、免疫紊乱和恶性肿瘤相关。心肌损伤的最终效应细胞主要是嗜酸性粒细胞及其毒性颗粒,而发病机制受T细胞调控。IL17A和IFN-γ双敲除导致小鼠出现Th2偏向免疫状态,易发生致命性嗜酸性粒细胞心肌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相关的FM已成为重要的ICI相关毒性。ICIs是靶向T细胞调节途径(如PD-1)的单克隆抗体,增强T细胞对恶性细胞的细胞毒性能力,可能挽救生命。但这些药物诱导的免疫失调可导致多器官炎症和功能障碍。FM是ICI治疗的严重不良反应,但其发病机制相对病毒性心肌炎而言未完全阐明。当前研究表明,T细胞介导的免疫在该病发展中起关键作用。EMB分析显示,ICI心肌炎患者心脏中有淋巴细胞浸润,支持T细胞免疫的参与。人类和动物研究观察到,ICI心肌炎患者心脏中CD8+ T细胞较CD4+ T细胞的淋巴细胞浸润更为显著。近期研究显示,ICI心肌炎患者外周血中CD8+细胞毒性效应细胞显著增加,与PD-1缺陷心肌炎小鼠血中和心脏中效应细胞毒性CD8+ T细胞的增加一致。这些增殖的效应CD8+ T细胞具有独特转录特征,包括心肌趋向性趋化因子CCL5、CCL4和CCL4L2的上调。此前研究显示,自身免疫性心肌炎小鼠心脏组织中CCL3、CCL4和CCL5及其对应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增加,提示T细胞向心肌浸润的潜在途径。
血管痉挛性心绞痛(VSA)现被认为是心肌炎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表现为静息时心绞痛,短期硝酸酯可缓解,由冠状动脉痉挛引起。VSA的症状范围从无症状和心绞痛发作至严重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和心脏骤停。尸检研究显示,VSA患者心肌中有炎症细胞浸润,特别是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近期研究表明,VSA患者血浆和心肌中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显著增加,提示心肌炎状态。VSA患者中IL-6、IL-12p70、IL-15、IL-13、IL-10、PD-L1、MIP-1α和MIP-1β水平较正常参与者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升高。研究者的观察显示,EMB证明的轻度心肌炎和FM诱导的冠状动脉痉挛,冠状动脉造影显示硝酸酯给药后冠状动脉狭窄消失。此外,心肌炎诱导的VSA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显示积极反应,提示糖皮质激素和炎症失调在VSA中的重要作用。
FM的救援和治疗策略
FM是致命的疾病。但能成功度过这一危急期并在1个月内完全恢复心脏功能的患者通常具有良好的长期预后。因此,管理急性期是FM治疗的最大挑战。研究者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研究,建立了“基于生命支持的综合治疗方案”,包括(i)机械生命支持、(ii)免疫调节治疗和(iii)抗病毒治疗。该治疗方案的基本原则涉及免疫调节、控制CS和通过使用机械循环支持(MCS)设备(如IABP和ECMO)以及其他生命支持设备(如呼吸机和血液透析器)为受损的血流动力学提供支持。机械生命支持有助于循环和呼吸功能,减轻心脏负荷。立即实施IABP为FM患者提供有效的循环支持,降低院内死亡率。通常,IABP给药使收缩压升高超过20 mmHg,同时心率降低20-30次/分钟。如果IABP无法维持循环稳定,建议使用ECMO。ECMO作为支持全身血流灌注的替代方法,同时减轻正性肌力药物和血管加压素的潜在心脏毒性作用。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ECMO的使用挽救了许多生命。然而,有报道称ECMO应用可能诱发CS。这种炎症反应是有害还是潜在有益尚不清楚。因此,必须注意这一可能的并发症并提供必要的治疗。
除了机械支持功能外,MCS有助于减少心肌炎症,恢复正常代谢功能并调节心脏重塑,所有这些对恢复心脏结构和功能至关重要。机械呼吸支持在FM治疗中也起重要作用。除纠正低氧血症外,该治疗还处理成人ARDS并减轻心脏负荷。根据需要,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如临时心脏起搏器和持续肾替代治疗。机械生命支持通过减轻器官负荷为FM患者提供恢复期,强调及时管理心源性休克以防止进一步组织损伤、器官衰竭或死亡的重要性。
建议立即并充分应用糖皮质激素(通常每日200-400mg甲龙,持续数天)和IVIG(20g/d,持续3-5天)进行FM的免疫调节。糖皮质激素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生成和下游信号通路,是急性炎症反应阶段的强效炎症调节剂。具体而言,糖皮质激素阻断TLR信号下游转录因子并诱导TLR信号抑制因子的基因表达。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改变巨噬细胞的线粒体代谢,导致代谢物衣康酸的生成增加。衣康酸具有抗炎、抗病毒和抗菌特性。尽管最初担心糖皮质激素可能促进病毒复制,但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给药可降低病毒性FM小鼠的死亡率并减少组织病毒滴度。人类数据表明,糖皮质激素对经EMB确诊的淋巴细胞性心肌炎患者具有潜在治疗益处,无论病毒状态如何。此外,近期研究显示,糖皮质激素通过增加EETs增强IFN-γ生成,发挥抗病毒效应。临床研究进一步支持糖皮质激素在管理CS和促进心肌功能恢复中的有效性。
在儿科人群中,IVIG最初用于治疗急性心肌炎。其治疗机制涉及中和促炎细胞因子、调节免疫反应并通过IVIG Fc片段促进巨噬细胞M2极化。此外,IVIG抑制DC抗原启动并改善FM大鼠的预后。高剂量IVIG还被证明可增强FM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向急性心肌炎患者给予高剂量IVIG(1-2g/kg,持续数天)与炎症细胞因子减少、心脏收缩功能改善和死亡率降低等临床结果改善相关。
相反,不建议使用纯免疫抑制剂或靶向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药物(如硫唑嘌呤和CsA)治疗FM。研究者在FM小鼠模型中的研究显示,CsA给药未改善心肌炎小鼠的生存率。此外,心肌炎治疗试验确认,细胞毒性药物未改善FM患者的生存率。
“基于生命支持的综合治疗方案”的另一个概念是抗病毒治疗。研究中,奥司他韦作为抗病毒药物显著改善FM患者的治疗效果,无论病毒状态如何。奥司他韦治疗FM的疗效部分归因于其对流感A和B病毒的抗病毒活性及其作为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的功能。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心肌炎导致受损心肌组织释放神经氨酸酶,导致血浆N-乙酰神经氨酸水平升高并加剧心脏损伤。奥司他韦通过保护心脏和全身免受神经氨酸酶的酶促损伤,阐明了其在病毒阴性FM患者中的治疗效果。鉴于病毒感染被认为是FM众多潜在原因中的主要触发因素,一旦检测到病原体,可使用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
病毒性肺炎相关ARDS
图5 病毒性肺炎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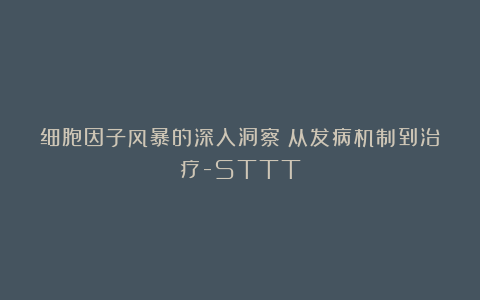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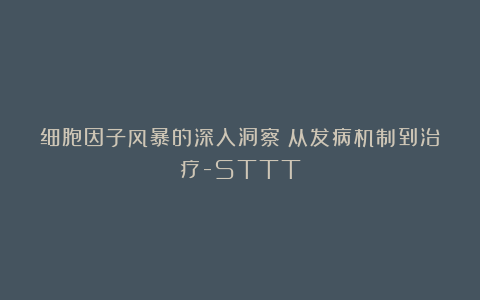
病毒性肺炎相关ARDS中CS的发病机制
ARDS是一种严重的医学状况,特征为肺部炎症和损伤迅速发生,导致氧合受损。ARDS可分为肺外和肺内亚型,取决于损伤的根本原因。肺外ARDS通常与脓毒症或创伤等系统性疾病相关,间接影响肺部;而肺内ARDS由肺炎或吸入性损伤等直接肺损伤引起。ARDS常因CS的发展而复杂化,某些病毒性肺炎已知会触发这些免疫反应并加重ARDS的严重程度。冠状病毒疾病,特别是COVID-19和SARS,以其引发过度免疫反应的能力而闻名。类似,流感病毒如H1N1和H5N1株在大流行期间也引发类似反应。因此,应对这些反应对于减轻病毒诱导肺炎中ARDS的严重后果至关重要。冠状病毒分为α、β、γ和δ四类,COVID-19、MERS和SARS属于β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被证明导致不同程度的严重肺炎甚至ARDS。COVID-19死亡患者的尸检报告证实存在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和细胞因子水平升高,提示发生类似于SARS和MERS的CS。CS是由病毒触发的免疫反应,多种细胞因子的协同作用导致持续强化和放大,最终导致对自我攻击,造成显著的组织和细胞损伤,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因此,在ARDS晚期,病毒载量仅是影响疾病进展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CS诱导的免疫激活加剧系统性器官损伤。及时干预抑制CS是防止疾病从轻度或中度恶化为重度的关键。
肺炎中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可导致显著的病理改变。在肺炎相关CS中,JAK信号通路在传递细胞内信号中起关键作用。不同细胞因子受体与特定JAK相关,提示可靶向抑制特定JAK功能,同时保留其他JAK途径的正常功能。IL-2/IL-2R/JAK(JAK1和JAK3)/STAT5信号通路对NK细胞、CD8+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至关重要。IFN-γ在aGVHD和CAR-T细胞疗法诱导的CRS中发挥类似作用。
CS是流感重症病例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流感病毒感染以其诱导肺损伤相关死亡的倾向而闻名,特别是在大流行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流感病毒感染的预后受病毒载量影响,但宿主对病毒的炎症反应与流感诱导的肺损伤发展密切相关。流感病毒首先通过内吞作用侵入上呼吸道上皮细胞。随着感染进展,可能导致下呼吸道感染。病毒特异性靶向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诱导初始细胞因子释放以清除病毒。这种早期细胞因子反应旨在帮助病毒清除,随后激活适应性免疫系统,导致二次细胞因子反应。称为CS的夸大免疫反应在流感病毒感染病例中,尤其是严重疫情期间,死亡率增加中起关键作用。这种免疫过度反应可导致显著的免疫病理损害,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且恶化其总体疾病预后。在严重病例中,CS可诱导ARDS。流感病毒肺炎的特征性肺泡变化包括毛细血管血栓形成、局部坏死、肺泡壁充血、炎症细胞浸润、透明膜形成和肺水肿。这些变化共同对肺部产生深远的免疫病理效应影响。严重流行性肺炎可能导致小血管血栓形成、出血和弥漫性肺泡损伤,提示凝血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相关疾病已被证明通过诱导CS增强免疫反应,表现为肺内皮细胞激活、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管渗漏和肺微栓塞。此外,严重CS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系统性炎症和潜在死亡。
细胞因子在免疫系统内介导细胞间通讯至关重要,对协调针对感染病原体的有效防御至关重要。病毒RNA可通过激活MAVS和NLR炎症体诱导IL-1β和IL-18释放。在适应性免疫反应阶段,T细胞和2型先天淋巴细胞的各种亚群被激活和调节。这些免疫反应共同促进病毒清除。然而,过度免疫反应可能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过度产生,导致不受控的CS、系统性炎症、器官功能障碍和潜在致命后果。过量IL-1β已被证明加剧H1N1、H3N2和H7N9病毒感染者的疾病并导致严重后果。靶向抗IL-1β抗体治疗在H1N1或H3N2感染的早期和晚期均显示出减少肺部炎症和提高生存率的疗效。在H7N9病毒感染中,NLRP3-/-和caspase-1-/-小鼠较野生型小鼠显示更高生存率,这归因于NLRP3-/-和caspase-1-/-小鼠中IL-1β水平较低,H7N9感染期间caspase-1缺失导致促炎细胞向肺部募集减少。ASC-/-和IL-1R1-/-小鼠在H7N9感染后显示肺部炎症减少和生存率增加。在流感病毒诱导的CS中,IL-1β和IL-18在TNF和IL-6生成中发挥调节作用。H3N2感染导致sIL-6R表达升高,流感病毒感染期间IL-6表达依赖于sIL-6R。流感病毒激活的γδ T细胞产生的IL-17可加剧病毒感染期间的炎症反应。Th-17诱导的高细胞因子血症被认为是2009年H1N1感染重症病例的初始宿主反应。在缺乏IL-17RA的流感病毒感染小鼠中,观察到中性粒细胞迁移减少、炎症轻微、肺实质保存、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病毒性肺炎相关ARDS中CS的预防和治疗
病毒性肺炎的治疗策略是综合性的。糖皮质激素在SARS和MERS中的作用已广泛研究。糖皮质激素用于抑制CS症状和改善ARDS。然而,Russel等的评论发现,糖皮质激素治疗未改善患者的90天死亡率。免疫系统在个体间显示明显异质性,免疫细胞的基因表达也因个体而异。这些差异导致个体对免疫相关疾病的易感性差异很大。研究发现,感染SARS-CoV-2后,与单核细胞和干扰素相关的早期免疫细胞反应在不同人群(如中非、西欧和东亚)中有所不同。受环境、遗传和进化选择压力的影响,这些人群产生不同的免疫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种族对SARS-CoV-2不同易感性的遗传和免疫机制。性别对CS的易感性也有报道,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激素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睾酮和雌激素水平影响抗病毒IFN-1和促炎信号(如TNF)之间的平衡。单核细胞对睾酮的促炎反应增加,解释了男性重症感染中CS更频繁发生。
在COVID-19病毒性肺炎患者中,糖皮质激素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患者更有益。地塞米松具有广泛的免疫抑制作用,可通过抑制SARS-CoV-2诱导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体外细胞因子表达改善COVID-19患者的生存率。另一项涉及住院患者的临床试验显示,地塞米松降低接受侵入性机械通气或单独氧疗的COVID-19患者的28天死亡率。总体而言,基于地塞米松的联合治疗在COVID-19中取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IL-6和CD8+ T细胞计数作为评估患者风险和预测COVID-19死亡率的可靠预后标志物。托珠单抗是一种重组人IL-6单克隆抗体,有效抑制IL-6信号并调节炎症反应。托珠单抗的给药对需要重症监护室器官支持的重症COVID-19患者显示出积极效果。托珠单抗治疗在重症COVID-19患者中可改善结果。但在无机械通气的情况下,托珠单抗可降低进展至机械通气或死亡的复合结局发生率,却未改善总体生存率。其他研究发现,托珠单抗和系统性糖皮质激素改善了住院COVID-19患者的生存率和其他临床结果。JAK2抑制剂菲卓替尼(fedratinib)被提出可抑制Th17细胞因子。JAK2通过STAT3介导Th17细胞中的IL-6和IL-23信号。JAK1和酪氨酸激酶2受体通过STAT1和STAT2起作用,对抗病毒免疫功能重要。菲卓替尼目前获FDA批准用于利用JAK2途径的骨髓增生性肿瘤。在2009年H1N1病毒大流行期间,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了恢复期血浆疗法对H1N1肺炎患者的效果。结果显示,病毒载量、IL-6、IL-10和TNF等细胞因子在治疗组显著降低,且血浆疗法未记录不良事件,但在COVID-19患者中,高滴度恢复期血浆未改善生存率。
SIRS
SIRS中CS的发病机制与机制
自1991年以来,脓毒症通常被定义为对微生物感染的系统性炎症反应,表现为至少两种症状:呼吸急促、心动过速、发热或低体温、白细胞增多或减少以及中性粒细胞减少。这一定义强调了机体过度炎症反应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然而,SIRS的临床表现可能无法准确捕捉重症患者脓毒症的复杂性。2016年脓毒症3.0的重新定义强调,脓毒症是由感染引发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源于宿主对感染的失调反应。这一更新定义突出了感染后免疫失衡作为脓毒症的主要驱动因素,导致严重器官损伤和潜在死亡。虽然传统上依赖SIRS的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已被摒弃,但CS和免疫失调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革兰氏阴性菌内毒素脂多糖(LPS)通过识别PAMPs或DAMPs触发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主导的免疫细胞释放大量TNF。脓毒症的传统进展涉及炎症介质的级联反应,导致不受控的炎症反应、免疫功能障碍、代谢活动升高和多器官功能损伤。这一过程由TNF启动,通过其下游受体TNFR1激活炎症反应,并与其他炎症因子(如IL-6)协同作用,通过炎症介质的自动放大迅速放大级联效应,最终诱导SIRS。在炎症存在下,IL-6诱导内皮细胞上C5a受体的上调,从而增强对C5a的敏感性并增加血管通透性。此外,IL-6已被证明诱导心肌功能障碍。因此,IL-6的多种效应导致组织低氧、低血压、心肌功能障碍、DIC和多器官功能障碍,这些都是SIRS和脓毒性休克的标志特征。IL-1和TNF的大量释放可能通过上调一氧化氮合成、心肌细胞收缩、促进免疫细胞粘附和激活以及启动外源性凝血途径,诱导心肌抑制、血管舒张、组织损伤和死亡。
SIRS中CS的预防、救援和治疗策略
优先识别SIRS高危人群对于有效预防和治疗该病至关重要。特别是老年人、营养不良者、存在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应及时评估感染部位和潜在病原体。此外,对于严重感染患者,建议及时筛查细胞因子水平。
感染控制主要包括识别病原微生物、给予抗感染治疗和消除感染源。当前快速检测技术包括肺炎链球菌抗原检测和多种细菌检测平台,如G试验和GM试验。此外,抗原和核酸检测以及实时PCR检测用于真菌检测。NGS技术的进步显著,使其在临床环境中广泛应用于多种病原体检测,降低假阴性可能性,成为病原体诊断的宝贵工具。抗菌治疗应在诊断后1小时内迅速启动,抗生素在4小时内给药。此外,建议在开始抗生素治疗前收集病原体标本。在有明确病因的SIRS病例中,单独抗生素治疗可能具有挑战性,难以获得有效结果,因此需要结合快速干预和感染灶的局部治疗。缓解CS是预防和拦截脓毒症的关键策略。应在疑似脓毒症且有CS迹象的患者中进行细胞因子水平筛查,以确定SIRS的程度。当代研究表明,脓毒症相关CS涉及多种细胞因子。SIRS和CARS的主要因素包括促炎细胞因子(如TNF、IL-1、IL-6、IL-12、MIF、sCD74、HMGB-1)以及抗炎细胞因子(如IL-4、IL-10、IL-35、IL-37、TGF-β和IL-13)。证据表明,当促炎因子水平显著升高或炎症反应失调时,应开始炎症管理。因此,对于高危脓毒症感染患者,建议定期监测细胞因子水平,以迅速识别疑似脓毒症的个体。Tregs对维持免疫耐受至关重要。这一过程涉及抑制体内T细胞激活和增殖,产生IL-10和TGF-β等抗炎因子,并通过激活TNFR2受体促进Treg细胞增殖。这些机制共同有助于维持免疫稳态、清除病原体和防止免疫超载。当前针对炎症介质(如TNF、IL-1和抗内毒素LPS抗体)的特异性抗体研究显示,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可缓解脓毒症。
在感染患者出现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或炎症失衡时,建议及时干预以调节炎症,恢复体内稳定和协调的炎症反应。早期给予糖皮质激素已被证明可有效抑制脓毒症患者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和释放。然而,在缺乏可靠SIRS检测方法的情况下,准确确定糖皮质激素治疗开始时间的挑战依然存在。此外,乌司他丁(一种非甾体抗炎药)已被证明可阻止溶酶体酶释放、抑制心肌抑制因子生成、消除氧自由基和抑制细胞因子释放。在细胞因子升高的初始阶段,给予低剂量乌司他丁可能对细胞因子发挥调节作用。然而,在细胞因子失调的情况下,促炎细胞和抗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被破坏,导致器官功能受损。给予高剂量乌司他丁已被证明可有效抑制脓毒症相关指标的进展。
噬血细胞综合征(HLH)
图6 病毒性肺炎系统性治疗
HLH的发病机制
图7 HLH相关CRS的机制和临床表现
HLH是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特征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NK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失调激活,导致高位水平细胞因子血症和免疫介导的多种器官系统损伤。根据病因,HLH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形式。原发性HLH通常有家族史和/或基因异常,主要在儿童期表现。原发性HLH(pHLH)与PRF1、Unc13D、Syntaxin-11、STXBP2和UNC18B等基因异常相关,SH2D1A/SAP和BIRC4也促进pHLH的发展。这些基因影响CTL和NK细胞中依赖穿孔素的颗粒酶外排、运输和装载等过程。因此,原发性HLH的发病机制以高免疫激活为特征,源于NK细胞和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功能减少或缺失。多种免疫细胞持续激活,持续分泌IFN-γ、TNF、IL-1β、IL-2、IL-6、IL-12、IL-16和IL-18等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导致严重CS。穿孔素缺陷小鼠模型证实,CD8+ T细胞分泌的IFN-γ升高在疾病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Syntaxin-11缺陷小鼠模型表明,T细胞耗竭是决定HLH疾病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
近期进展,约有30个基因与HLH相关,主要亚型包括家族性HLH(FHL)家族类、免疫缺陷综合征类和EBV驱动类。此外,HLH已从单纯的隐性遗传病转变为可通过隐性和显性遗传模式表现的疾病。此外,EBV感染个体可能存在固有免疫缺陷,不仅易患HLH,还增加EBV相关淋巴瘤的风险。年龄传统上被用作区分原发性和继发性HLH的因素。但近年来青少年和成人中识别的遗传病例数量增加,挑战了这一假设。国内外学者正在研究遗传突变与成人HLH患者的相关性,目前尚无成熟理论阐明成人原发性HLH的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成人原发性HLH的延迟发病可能与基因突变的具体位置、突变方式以及触发因素的存在与否有关。例如,错义突变和剪切位点突变可能在较晚年龄表现,而复杂杂合子突变通常比纯杂合子突变具有更晚的发病。此外,特定亚等位基因通常保持静止,但可被感染等外部刺激激活,导致其发展。
继发性或获得性HLH(sHLH)以感染、恶性肿瘤、风湿病、移植、药物过敏反应或其他潜在原因引发的突变为特征。其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可能涉及感染或自身免疫触发导致的持续TLR激活。EBV是HLH最常见的感染相关因子。慢性活动性EBV感染(CAEBV)在东亚尤为常见。此前研究显示,CAEBV与HLA-A26显著相关,这是在东亚裔个体中常见的遗传标记。在中国,EBV被确定为31个地区1445例HLH病例中44.01%的主要病因,是最常见的HLH原因。EBV触发的HLH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更常见,伴随家族性HLH和原发性免疫紊乱相关基因突变,如X连锁淋巴增生综合征1型和2型。在成人中,EBV相关HLH主要由免疫抑制导致的病毒再激活诱导。CAEBV此前被认为通过系统性炎症和EBV感染T或NK细胞的克隆增殖诱导淋巴细胞毒性,如HLH。但近期有研究显示CAEBV患者造血系统中包括淋巴系和髓系以及造血干细胞的多种细胞被EBV感染,提示CAEBV疾病可能源于造血干细胞感染(Blood近期已发表该观点)。先前研究显示,非免疫抑制患者EBV+T/NK-淋巴增殖性疾病的淋巴细胞毒性与基因突变相关,且有基因缺陷的患者与无突变患者相比临床预后较差。
sHLH已记录与Allo/Auto-HSCT后的GVHD相关。一旦确诊,死亡率很高,强调及时识别和处理过度炎症的重要性。有证据表明,铁蛋白水平可能与GVHD关联不强,但却与HLH显著相关。移植后铁蛋白水平升高可能提示患者发生继发性HLH,是区分sHLH/MAS的潜在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建议在疑似HLH病例中首先检测血清铁蛋白水平,但在成人和儿童中,血清铁蛋白水平<500 μg/L可作为HLH的阴性诊断指标。近期研究发现,allo-HSCT后继发性sHLH/MAS中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升高,提示GVHD中的异基因反应状态可能促进sHLH/MAS的发展。此外,接受CD22 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显示CAR-T细胞相关HLH(CAR HLH)发生率较高,可视为CRS的一种形式,与HLH作为T细胞介导的炎症过程的提议病理生理以及关键细胞因子与HLH的已知关联一致。CAR HLH患者中与HLH相关的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包括IFN-γ、IL-6、IL-1β、IL-18、IL-18结合蛋白(IL18bp)、IL-8、MIP-1α、CXCL9和CXCL10)较无CAR HLH患者持续且显著升高。相反,CAR-T相关严重CRS患者的细胞因子升高虽达到类似峰值水平,但为短暂且迅速下降,提示更严重的CRS与CAR HLH可能相关。近期研究发现,在穿孔素缺陷的同源小鼠模型中,抗原非依赖性CAR-T细胞扩增与HLH样毒性相关。穿孔素缺陷CAR-T细胞的扩增伴随野生型T细胞的同时扩增,提示T细胞驱动的扩增促成继发性炎症反应。
HLH的识别、监测和治疗策略
HLH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系统性过度炎症综合征。早期识别和迅速管理对于防止器官衰竭和降低死亡率至关重要。根据EULAR/ACR指南,当以下未解释或显著异常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同时出现时,应怀疑HLH,特别是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包括持续发热、铁蛋白升高及其他炎症或损伤标志物(如CRP、LDH)升高;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或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ALT、AST、胆红素升高);凝血异常(如低纤维蛋白原、高PT/INR、D-二聚体);脾大;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见HLH-04/24、OHI等诊断标准)。诊断评估应包括检测铁蛋白、纤维蛋白原、NK细胞活性、IL-2Rα(CD25)和其他炎症生物标志物。对于疑似HLH的患者,应根据临床表现、年龄和实验室结果仔细考虑基因检测的需要,这些因素显著影响诊断和治疗决策。早期识别高危患者至关重要。利用血清标志物和临床特征开发的各种评分系统和建模研究用于预测HLH的严重程度和预后。HLH的两个关键预后因素:总胆固醇水平≤3.11 mmol/L和BUN水平≥7.14 mmol/L,均与不良预后相关。此外,有研究预测儿童患者疾病进展高危的预后评分系统,有助于确定是否需要二线治疗,包括allo-HSCT。Zoref-Lorenz等显示,优化HLH炎症(OHI)指数结合可溶性CD25(>3900 U/mL)和铁蛋白(>1000 ng/mL)升高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相关HLH不良预后的强有力预测因子。此外,研究表明,诱导治疗后铁蛋白/血小板比率可可靠反映成人HLH患者的治疗反应。Cheng等建立了基于治疗前白蛋白和胆红素水平的白蛋白-胆红素(ALBI)评分和分类系统,ALBI 3级被确定为30天死亡率和总体生存率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提示受影响患者死亡风险较高。Zhang等提出了包括深部器官出血、初始诱导治疗反应和诱导后8周血清钙水平等因素的早期预后模型,有助于识别该时间段内死亡风险升高的患者。此外,Cui等开发了整合年龄、EBV-DNA水平、BUN、sCD25和PCT等因素的柱线图模型,以预测诱导治疗期间的高死亡风险。另一项利用机器学习的研究发现,低总胆固醇、高尿素氮和胆红素以及凝血酶时间延长与儿童HLH患者早期死亡高度相关(另王旖旎教授团队在Blood去年发表的EBV-HLH需不需要移植也很值得临床借鉴)。
HLH的管理首先集中于控制过度炎症反应以阻止疾病进展,随后处理潜在免疫缺陷并管理原发性疾病以防止复发。HLH-94和HLH-2004方案是最广泛使用的初始治疗方案。HLH-2004方案在诱导阶段纳入CsA以增强免疫抑制,但早期临床研究显示在该阶段纳入CsA无显著临床优势。因此,大多数中心继续遵循HLH-94方案。对于原发性HLH患者,allo-HSCT是唯一治愈选择。对于不适合立即进行allo-HSCT的原发性HLH患者,维持治疗对防止复发至关重要。HLH-94方案建议使用依托泊苷联合地塞米松进行维持治疗,根据患者耐受性调整治疗强度,以尽量减少毒性同时维持疾病控制。继发性HLH更复杂,通常需要偏离HLH-94/2004方案的个体化方法。例如,CAR-T细胞疗法相关的免疫效应细胞噬血综合征最初以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免疫抑制治疗。然而,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损害CAR-T细胞功能。难治性或复发性HLH需要及时的挽救治疗,可能与初始诱导方案不同。复发病例也可通过重复原始治疗方案进行管理。然而,医学界对复发或难治性HLH的最佳挽救治疗方案尚无共识。DEP方案(脂质体阿霉素、依托泊苷和甲泼尼龙的组合,伴或不伴门冬酰胺)在成人难治性HLH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近年来,几种靶向疗法用于HLH治疗。Emapalumab于2018年获FDA批准,是目前唯一用于儿童(包括新生儿)和成人难治或复发原发性HLH的药物。其他有前景的药物包括JAK1/2抑制剂ruxolitinib、CD52单克隆抗体alemtuzumab、IL-6抑制剂、IL-1Ra阿那白滞素、IL-18抑制剂和TNF抑制剂。此外,针对XLP1、FHL2和FHL3相关缺陷基因的基因治疗在临床前小鼠模型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为未来治愈性治疗提供了潜在途径。
图7 CAR-T和GVHD相关CRS的机制和临床表现
CAR-T疗法相关CRS
CAR-T疗法相关CRS的发病机制
CAR-T细胞相关CRS是一种系统性疾病,特征为免疫效应细胞的过度激活和多种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该综合征的细胞因子升高模式与HLH相似,IL-6、IFN-γ和IL-1起关键作用。CAR-T是一种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新型疗法,显示出绕过宿主免疫耐受、选择性靶向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约束内的肿瘤细胞的能力。此外,它具有强大的靶向能力、广谱肿瘤细胞杀伤和持久治疗效果的显著优势。因此,CAR-T已有效用于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管理。然而,CRS和ICANS已成为阻碍CAR-T细胞疗法在癌症治疗中更广泛应用的重大障碍,表现为免疫系统过度激活以及与CAR-T细胞增殖相关的血清细胞因子和促炎分子水平升高。严重CRS和ICANS对患者健康构成重大风险。
髓源性巨噬细胞在CRS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研究表明,CRS相关毒性可能主要涉及以巨噬细胞为中心的病理生理机制,特征为CAR-T细胞肿瘤微环境中通过CD40L-CD40相互作用初始激活巨噬细胞,CRS期间关键细胞因子(如IL-6、IL-1和IFN-γ)的释放,以及巨噬细胞中儿茶酚胺自我放大循环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IL-6及其下游效应因子在CRS临床症状表现中至关重要。IL-6主要由激活的T细胞合成,血管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谱系在CRS中也有贡献。IL-6水平升高与血管通透性、补体激活、DIC和心肌功能障碍相关。近期研究强调了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作为M1巨噬细胞表达的促炎细胞因子在CR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IL-1β已被证明刺激iNOS的表达和合成。此外,GM-CSF在炎症复杂网络中发挥作用,主要源于CAR-T细胞。其在神经元细胞中的高表达有助于神经毒性症状的表现。IFN刺激或与病原体共同诱导触发巨噬细胞激活,导致铁蛋白释放增加和随后严重CRS的发展。研究表明,CRS期间CAR-T细胞上CD40L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谱系上CD40的相互作用加剧综合征的严重性。巨噬细胞通过激活肾上腺素能受体可响应并分泌儿茶酚胺,导致巨噬细胞内细胞因子(IL-2、TNF、IFN-γ和MIP-1α)生成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儿茶酚胺的自体分泌循环。这种事件级联可加剧CRS相关的炎症损伤。
CAR-T疗法相关CRS的识别、监测和治疗策略
CRS的严重程度与患者生存率显著相关。严重CRS与残疾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影响患者管理进程。CRS的分级标准通常基于美国移植和细胞治疗协会(ASTCT)建立的标准。该系统将CRS严重程度分为1至4级,3级或以上表示严重CRS。准确分级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及时识别和管理CRS,可能改善患者预后。然而,预测CRS风险的能力,特别是早期检测严重病例,对于优化治疗策略至关重要。多项研究探讨了识别和监测高危CRS患者的方法,以在严重症状出现前进行干预,最终减轻CRS严重程度和死亡率。这些模型通常结合输注前实验室标志物和/或给药后血清细胞因子或其他免疫蛋白水平,包括但不限于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血红蛋白、CRP、ALP、BNP、APTT、PCT和铁蛋白。此外,细胞因子谱(如IFN-γ、可溶性IL-2受体、IL-4、IL-6、IL-8、IL-10、IL-15、MCP-1、TNFRp55、CX3CL1、GZMB、PDGFAA等)也被使用。此外,输注后24-48小时内ST2、Ang-2、NETs水平以及可溶性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sVCAM-1)或细胞间粘附分子1(sICAM-1)的早期变化已被用于早期识别严重CRS患者。考虑到内皮细胞激活在CRS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结合基线血肌酐、乳酸脱氢酶和血小板水平的内皮激活和应激指数(EASIX)评分以及改良EASIX公式已被用于严重CRS风险的分层。当前关于预测CRS的研究显示,缺乏针对不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识别和监测CRS的标准化系统。密切监测和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特别是CAR-T细胞治疗后高危CRS患者的各种血清生物标志物或细胞因子至关重要。
已提出多种预防CRS的策略,如优化剂量方案、创建毒性较低的嵌合抗原受体(CARs)和实施可逆开关。然而,这些策略在应用于临床环境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主要干预方法涉及药理治疗。CRS预防可通过使用托珠单抗(IL-6受体拮抗剂)抑制IL-6受体或通过单核细胞耗竭实现。尽管最初对托珠单抗相关ICANS风险的不确定性,研究现已表明,接受多次托珠单抗剂量的患者与接受较少剂量的患者相比,低级别和高等级ICANS风险均升高。相反,IL-1Ra(阿那白滞素)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预防CRS和神经毒性的疗效。
托珠单抗的早期给药和糖皮质激素的及时使用在管理严重CRS(sCRS)中至关重要。研究显示,风险适应的预防性托珠单抗有效预防儿童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TL019治疗后的4级CRS,且不影响CTL019的抗肿瘤疗效或安全性。当前研究文献普遍主张实施分级治疗方法。对于出现sCRS症状的患者,初始治疗通常包括托珠单抗和糖皮质激素。具体而言,托珠单抗以8 mg/kg剂量通过静脉输注给药,最大剂量800 mg,1-2次给药,24小时内不超过三次,最大四次。此外,地塞米松以10 mg剂量每6小时静脉输注,治疗持续1至3天。或者,甲泼尼龙可每日1000 mg静脉给药,持续3天,随后逐渐减量;然而,糖皮质激素的最佳剂量和给药时机尚不清楚。如果甲泼尼龙无效,某些医疗中心使用抗IL-6抗体siltuximab和IL-1Ra阿那白滞素管理CRS。阿那白滞素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可缓解CRS症状,且不损害CAR-T细胞疗法的疗效。临床报告表明,阿那白滞素对糖皮质激素耐药的CRS有效。糖皮质激素难治性严重CRS的额外治疗选择包括JAK途径抑制剂、GM-CSF抑制剂、TNF阻断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mTOR抑制剂、血液过滤、血浆置换、机械通气和手术干预。在多器官功能障碍情况下,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可有效消除多余液体和炎症介质,稳定内部环境并促进受损器官的恢复。可能需要额外的临床试验来确认这些治疗的有效性。
尽管当前治疗和预防CRS的方法有所进展,但进一步研究和临床试验对于增强这些策略并保证其安全性和疗效至关重要。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aGVHD
HSCT相关CRS的发病机制
aGVHD是allo-HSCT后的重要并发症,特征为移植受者和供者之间抗原差异导致的过度炎症反应。它是移植后非复发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与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该病影响多个器官,包括皮肤、肝脏、胃肠道、肺、肾、胸腺、淋巴结、骨髓和中枢神经系统,根据其严重程度分为I-IV级,通常在HSCT后数周至数月表现。该病的临床症状源于一系列复杂事件,首先是宿主APCs对预处理引起的组织损伤的激活。随后,供者T细胞被激活的宿主APCs刺激以识别宿主抗原,迁移至受累组织并触发凋亡。在初始阶段,预处理化疗或放疗产生的PAMPs和DAMPs被TLRs等先天免疫受体检测,导致促炎细胞因子(如TNF、IL-1β和IL-6)的分泌和宿主APCs的随后激活。在第二阶段,供者T细胞与激活的APCs的接触触发T细胞的激活和增殖。在第三效应阶段,激活的供者T细胞和单核细胞迁移至aGVHD影响的靶器官,包括皮肤、肝脏、脾脏和肠道。这些细胞刺激额外效应细胞(如细胞毒性T细胞和NK细胞)的募集,通过直接细胞毒性或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TNF、IL-1β、IL-2、IL-12、IL-17、IFN-γ、CCL2、CCL3、CCL4和CCL5)导致组织损伤。这加剧aGVHD的严重程度并可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此外,研究表明,aGVHD患者中的T细胞主要依赖糖酵解作为主要代谢途径,提示T细胞糖酵解失调可能是aGVHD发展的一个新机制。
HSCT相关CRS的识别、监测和治疗策略
严重aGVHD患者通常对治疗反应不佳,移植后死亡率升高,强调及时识别和监测风险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开发了利用血清生物标志物、细胞因子和合并症的多种预测模型。例如,国内研究者提出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第7天使用SA/PA比率(<0.731)作为预测严重aGVHD的手段。在国际研究领域,肠道微生物群评分、HCT-CI评分和DeltaAlb≥0.9等评分系统被用于评估III-IV级aGVHD的可能性。此外,通过MAGIC算法识别的生物标志物(如IL-2Rα、TNFR1、IL-6和ST-2以及REG3a)在移植后前2周内显示出预测严重和致命GVHD的潜力。此外,内皮损伤标志物(如Ang-II)在aGVHD病例中显著升高,与严重aGVHD患者的较低生存率相关。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临床变量和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模型在预测严重GVHD中显示出疗效。此外,炎症性CD4/CD8双阳性T细胞和Tim-3CD8 T细胞的比例显示出早期识别高危患者的潜力。关于aGVHD的特定预测研究显示了预测方法的多样性。然而,这些研究可能并非通用的,因为它们针对不同患者群体。因此,临床医生必须对不同人群进行个性化评估,并对高危患者实施主动预防干预或立即干预。
GVHD的常规预防方案通常涉及CNI(如CsA或他克莫司)和抗代谢药物(如甲氨蝶呤或霉酚酸酯),偶尔辅以ATG。北京方案(包括ATG和G-CSF)以及基于移植后环磷酰胺的T细胞耗竭策略已显示出降低aGVHD发生率的疗效。在减强度预处理和匹配无关供者allo-HSCT中,添加西罗莫司到标准治疗方案与GVHD和非复发死亡率降低相关,最终改善总体生存率。阿巴西普(一种T细胞共刺激抑制剂)在美国获批用于预防GVHD,与CNI和甲氨蝶呤联合使用时效果显著,特别是在HLA匹配或不匹配无关供者移植中。维多利单抗(靶向α4β7整合素)通过干扰T细胞向肠道相关淋巴组织的迁移,有潜力预防急性胃肠道GVHD。
aGVHD的初始治疗方法通常涉及使用糖皮质激素。对于糖皮质激素反应不佳的患者(称为糖皮质激素难治性aGVHD,SR-aGVHD),ruxolitinib已获FDA批准作为可行治疗选择。aGVHD的其他治疗策略包括alemtuzumab、α1-抗胰蛋白酶、basiliximab、细胞疗法(如间充质干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daclizumab、体外光化学疗法、粪便菌群移植、其他JAK抑制剂、霉酚酸酯、甲氨蝶呤、喷司他丁、兔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西罗莫司和维多利单抗。在低风险aGVHD病例中,目前正在研究如itacitinib等替代药物的单药治疗。在高危患者中,由于其抗炎和组织保护特性,正在探索新型药物与糖皮质激素的组合。近期研究发现,MHC不匹配小鼠模型中同时抑制促炎细胞因子IL-6R和TNF显示出潜力,可挽救糖皮质激素耐药和致命性肠道GVHD的受者,同时保持移植物抗肿瘤效应。此外,泛素特异性蛋白酶11(USP11)的表达水平与allo-HSCT患者aGVHD的发展相关,提示USP11抑制可能是预防和治疗aGVHD的可行策略。此外,通过将糖皮质激素与糖酵解抑制剂联合,协同增强aGVHD患者的T细胞功能,在小鼠模型中显示出减少疾病严重程度同时保持移植物抗肿瘤效应的潜力,为aGVHD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有前景的途径。
细胞因子风暴(CS)的治疗前景
图8 与细胞因子风暴相关疾病的未来治疗靶点和新治疗方法
快速诊断与靶向治疗
鉴于细胞因子风暴(CS)对疾病病理的重大影响,研究人员持续探索快速诊断和靶向治疗CS的策略。快速诊断工具正在开发中,例如,基于血清sST2水平与FM进展相关的发现,开发了sST2检测工具以实现FM的快速诊断。此外,已开发出多种细胞因子抗体或类似物,用于中和促炎细胞因子或抑制下游信号级联。例如,IL-1(包括IL-1α和IL-1β)是一种关键的促炎细胞因子,会引发破坏性炎症。阿那白滞素(Anakinra)是一种重组IL-1受体拮抗剂(IL-1Ra),专为阻断IL-1α和IL-1β的活性而设计。研究表明,阿那白滞素给药可显著且迅速缓解发热,并降低与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相关的炎症细胞因子和生物标志物水平。这种治疗在风湿性疾病相关的CS患者中也显示出疗效。类似地,IL-1β中和抗体卡那单抗(Canakinumab)表现出抗炎特性。在CVB3诱导的急性心肌炎小鼠模型中,使用IL-1β中和剂的组别显示心肌损伤和炎症显著改善。与IL-1Ra类似,托珠单抗(Tocilizumab,一种IL-6受体抗体)在治疗系统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严重类风湿关节炎、Castleman病以及CAR-T疗法诱导的CRS中显示出疗效。此外,IFN-γ是控制CS的潜在靶点。最近,FDA批准了IFN-γ抗体Emapalumab用于治疗复发性/难治性噬血细胞综合征(HLH),基于一项单臂、开放标签的2/3期试验(NCT01818492; NCT02069899)的积极结果。此外,IFN-γ中和抗体在LPS诱导的脓毒症小鼠模型中显示可提高存活率。其他有前景的治疗靶点包括IL-18和TNF抗体或类似物。
除了抗细胞因子疗法外,利用小分子抑制细胞因子生成和信号传导也是一种有前景的方法。例如,JAK抑制剂(如巴瑞替尼、托法替尼、乌帕替尼和芦可替尼)在临床环境中对管理aGVHD、类风湿关节炎、sJIA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中的CS显示出疗效。芦可替尼在原发性和继发性HLH小鼠模型中显示出改善疾病症状的潜力。此外,巴瑞替尼已被证明可促进COVID-19感染的恢复。尽管这些抗体已获批用于某些疾病,但其在更广泛疾病中的疗效仍在研究中。
新兴CS控制策略
除了药物研究外,开发了多种控制CS的新策略,并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这些包括细胞因子纳米海绵、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以及使用细胞因子吸附柱进行血液净化,均提供了改善细胞因子控制的潜力(图9)。
细胞因子纳米海绵
生物中和是一种有前景的策略,可通过使用治疗剂与炎症介质或感染病原体结合并抑制其生物活性来减轻破坏性CS的影响。细胞纳米海绵由细胞膜包覆的纳米颗粒组成,被设计为用于生物中和的诱捕剂。细胞因子纳米海绵通过呈现与靶细胞相同的抗原表位,模拟源细胞并中和细胞因子,从而破坏炎症性疾病中的细胞因子级联反应。
巨噬细胞具有高浓度的细胞因子结合受体,因此巨噬细胞膜包覆的纳米颗粒成为抗炎治疗的广泛研究对象。研究表明,LPS刺激的巨噬细胞膜包覆纳米颗粒(LMNP)能够减轻HLH中的CS。通过有效结合多种细胞因子,LMNP可通过抑制CS和防止过度巨噬细胞激活来缓解HLH症状。LMNP在小鼠模型和人类患者中显示出作为致命性HLH治疗选择的潜力。类似地,中性粒细胞膜包覆的纳米颗粒也被设计用于中和炎症细胞因子。
间充质干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MSCs)是一类具有造血能力的多能祖细胞,可分化为多种中胚层谱系。MSCs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特性,可控制多种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炎症反应。MSCs能够改变CD4+ T细胞的炎症环境,从效应T细胞主导的微环境转变为富含调节性T细胞的微环境。此外,MSCs抑制树突状细胞的成熟,促进更耐受的调节表型,并诱导巨噬细胞向抗炎M2表型极化。
由于其强大的免疫调节特性,间充质干细胞移植(MSCT)用于治疗免疫和炎症性疾病是当前研究的热点。2004年,记录了一例儿科患者使用MSCT治疗allo-HSCT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严重aGVHD的案例。该病例的积极结果引发了对MSCT在免疫疾病中应用的广泛兴趣。随后启动了两项大规模试验,研究MSCT在治疗aGVHD中的疗效,进一步探索其在其他炎症性疾病中的潜力。虽然有报告表明MSCT在治疗重症COVID-19病例中有效,但不同临床试验的结果存在差异。截至目前,NIH临床试验数据库记录了超过1000项研究MSC治疗的临床试验,涵盖肺部炎症、aGVHD、风湿性疾病和其他炎症性疾病。此外,胚胎干细胞和诱导性人多能干细胞等新产品的开发进一步扩展了MSC免疫调节的潜在临床应用。
细胞因子吸附柱血液净化
血液净化疗法已被用于治疗细胞因子相关疾病,其中β2微球蛋白吸附柱是研究高细胞因子血症(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主要方法。动物研究显示,使用β2微球蛋白吸附柱治疗脓毒症小鼠可显著降低IL-6和TNF水平。类似地,人类脓毒症患者研究显示,接受β2微球蛋白吸附柱治疗的患者血浆中IL-1β、IL-6、IL-8和TNF水平呈时间依赖性降低。
除了β2微球蛋白吸附柱外,还开发了多种其他吸附柱以靶向新型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例如,多黏菌素B固定纤维柱已被用于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内毒素吸附治疗。最近,Sekiya等介绍了一种新型吸附柱(NOA-001),设计用于在兔急性肺损伤(ALI)模型中消除细胞因子和活性中性粒细胞。在ARDS和ALI的发病机制中,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毒性颗粒、形成NETs、在组织中沉积血小板-中性粒细胞复合物以及激活其他免疫细胞等多种机制促进炎症,最终导致CS。因此,同时靶向细胞因子和活性中性粒细胞可能有效阻止ARDS和ALI的进展。鉴于NOA-001在动物模型中改善肺功能的疗效,它显示出作为人类ARDS潜在治疗的潜力。
结论与展望
CS的主要特征包括由循环细胞因子、急性全身炎症和继发性器官功能障碍引起的原发性疾病及其并发症,这些超出了身体的代偿能力,最终导致不可逆损伤。预防CS的发生和提高存活率仍是持续挑战。随着对CS潜在机制和靶向疗法的深入研究,CS的治疗已有改善。然而,CS的总体死亡率仍较高。为更好地控制CS及其后续器官损伤,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综合整合治疗、靶向不同疾病的关键介质以及选择更具选择性、减少脱靶效应的治疗。
综合整合治疗
由于CS的病理生理涵盖了分子、细胞、器官和系统水平的紊乱,综合整合治疗尤为必要。
1.多种CS信号阻断剂或调节剂的组合:一个典型例子是HLH的治疗,其中通过多种方式靶向CS信号。HLH的治疗通常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化疗消除活化T细胞并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生成以控制过度CS,随后通过allo-HSCT替换缺陷免疫系统。此外,IFN-γ抗体(如Emapalumab)也被用于HLH治疗。其他靶向疗法,如JAK抑制剂和CD20抗体,也在研究中用于HLH治疗。
2.多种医疗干预形式的组合:包括药物治疗、机械通气呼吸支持、IABP/ECMO循环支持、CRRT肾支持等。这适用于所有临床情况下的CS控制,如FM、ARDS、HLH、aGVHD和CAR-T相关CRS。
3.多学科合作:由于CS是全身炎症状态,多个器官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学科团队合作有助于早期识别和更好地保护器官功能。
靶向关键介质
识别特定疾病的关键介质为诊断生物标志物和靶向疗法提供了信息。多种常见通路(如TLRs、JAK/STAT、NLRP3炎症体和NETs)在不同CS场景中被激活,产生大量炎症细胞因子。每种疾病的主导信号通路和关键炎症介质不同。使用不当的靶向疗法可能导致治疗无效甚至有害。例如,在风湿性疾病和MAS中,TNF阻断有效,但在HLH中,TNF阻断的效果尚不确定,甚至有报告提示抗TNF治疗可能间接诱发HLH或加重炎症。因此,识别关键介质至关重要。
更具选择性的治疗
药理学的发展使得更具选择性、减少脱靶效应的治疗更加安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JAK抑制剂。第一代JAK抑制剂已获批用于控制aGVHD和风湿性疾病中的CS,并在治疗ARDS中显示出疗效。然而,由于选择性不足,这些抑制剂也存在脱靶效应,增加严重和机会性感染风险,并导致贫血及淋巴细胞、NK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减少。因此,下一代更具选择性的JAK抑制剂正在探索中,其疗效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CS管理的未来展望
CS管理的未来在于结合尖端技术(如组学、人工智能、靶向药物传递、基因编辑和生物材料)与先进生命支持系统和器官替代疗法的多方面方法。这些创新将带来更有效、精准和个性化的治疗,为改善CS患者的预后提供希望。
组学技术
组学技术的进步将为CS复杂分子网络提供前所未有的视角。高通量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可识别参与炎症反应起始和升级的特定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和细胞过程。结合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研究人员可绘制CS的单细胞图谱。这些技术的详细分子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驱动炎症的免疫细胞群及其作用,从而发现更精准干预的新型治疗靶点。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AI)和深度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CS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通过分析电子健康记录、生物标志物和临床影像的庞大数据集,AI模型可在CS进展至危及生命阶段前识别其早期迹象。这些预测模型可整合到早期预警系统中,使临床医生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此外,机器学习算法可根据患者发展严重CS的可能性进行分层,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方案。
靶向药物传递
靶向药物传递系统有潜力革新CS治疗。脂质体、纳米颗粒和微球等技术可被设计为将抗细胞因子药物直接传递至炎症组织或免疫细胞,确保药物在局部高浓度,同时减少全身毒性。这些传递系统可通过炎症微环境特有的刺激(如pH或温度变化)激活,实现对CS涉及细胞因子的精准靶向。
基因编辑
利用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为治疗CS提供了巨大潜力。一个有前景的方法是基因编辑MSCT以增强其抗炎特性。通过基因编辑,MSCT可被改造为表达细胞因子抑制剂或抑制炎症通路,从而减轻CS的严重程度。
先进生命支持与器官替代
在严重CS病例中,先进生命支持技术和器官替代对于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基于现有技术(如ECMO、通气和CRRT),新一代生命支持系统旨在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副作用。结合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实时监测将实现更个性化和响应性护理。对于伴有严重CS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器官替代可能是救命措施。为克服人类供体器官的短缺,探索了异种器官移植(如猪心脏移植)和人工器官。器官芯片技术和生物打印的整合最终可能实现功能性器官的创建,用于移植或作为临时支持直到供体器官可用。
注意治疗诱发的CS风险
尽管CS新疗法的发展令人振奋,但需保持警惕,防止治疗诱发的CS。某些治疗,特别是免疫调节疗法或CAR-T细胞疗法,可能在某些个体中无意触发过度CS。在接受这些治疗的患者中监测CS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以防止伤害并确保新型疗法的安全给药。随着这些领域研究的进展,研究者有望在管理这一危及生命的炎症反应方面取得显著改善。
https://www./articles/s41392-025-0217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