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习武者清晨在公园里缓缓推手,与同好交流劲路变化时;当一位少年在武馆中认真练习基本功,为强健体魄而挥汗如雨时;当一位老者在夕阳下打一套太极拳,享受身心合一的宁静时——这些场景构成了当代中国武术的多元图景。
然而,关于’武术能否打’的争论却始终如影随形,甚至演变为对传统武术价值的根本性质疑。京武以为,必须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重新审视武术中’打’的辩证意义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多元价值。
传统武术的’打’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技击术,而是整体生命修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一代宗师孙禄堂提出’拳与道合’的至高境界,将武术提升至性命双修的层面。太极拳名家杨澄甫在《太极拳术十要》中强调:’太极拳本是武当内功,非徒作技艺之末也。’
这些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事实:传统武术的终极追求从来不只是克敌制胜的技巧,而是通过技击训练达到身心和谐、人格完善的道路。
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虽详细记载了各种实战技法,却同样重视武德修养,认为’武艺精熟,尤贵乎德性纯全’。这种’打’与’养’的辩证统一,正是传统武术最珍贵的文化基因。
当代擂台搏击与民间武术的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不同语境下’打’的价值取向。
那位批评’擂台上的打是伤害对手或让对手伤害自己,成为有钱人娱乐的一种方式’的观点虽有偏颇,却也道出了职业搏击商业化带来的异化现象。
职业格斗运动员为生存而战,其训练体系自然围绕最大化杀伤效率展开;而传统武术习练者多以健身修心为目的,两者的目标差异决定了技术路径的分野。
正如推手大师所言:’推手不能有打人的念头,连’打’字都不能想’,这种’不争之争’的智慧,恰恰体现了传统武术对暴力手段的超越性思考。
民国时期,太极拳家吴图南曾告诫弟子:‘练拳不是为了打人,而是为了不打人。’这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哲学,使传统武术在本质上区别于单纯的格斗技艺。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过度强调武术的’打’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杨班侯之子杨兆鹏因推手胜人而被暗杀,孙禄堂在上海险遭毒手,武汇川因发劲过猛遭人报复致死——这些并非孤例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高超的武技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灾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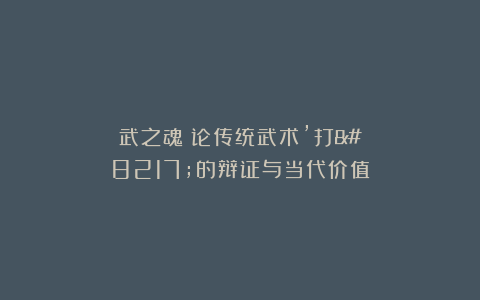
清代武术家甘凤池曾告诫弟子:‘艺成而下,德成而上。’传统武术界素有’宁可失传,不可轻传’的保守传统,正是基于对武术社会风险的深刻认知。
当代社会法律秩序完善,暴力解决问题的成本极高,武术的技击功能自然应当回归其本位——作为特殊职业人群的专业技能,而非大众普及的内容。这种差异化定位,恰是对习武者生命安全的负责态度。
传统武术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对’打’的超越与升华。
当太极拳从战场杀伐之术演变为’延年益寿不老春’的养生之道,当八卦掌从战场步法发展为调节身心的运动方式,武术完成了从’杀人技’到’活人术’的伟大转型。
这种转型不是对武术本质的背叛,而是对其更深刻的理解——真正的武学大师,往往最先领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
当代太极拳名家陈发科曾说:‘我教拳是为了让大家都健康,不是为了培养打手。’这种以人为本的武学理念,使传统武术在失去冷兵器时代实用价值后,依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面向未来,传统武术的发展应当遵循’各得其所’的多元路径。
对于少数专业从事搏击运动的人士,应当鼓励其借鉴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开放精神,科学系统地提升实战能力;而对于广大武术爱好者,则应侧重武术的健身、修身价值,通过站桩、盘架、推手等练习获得身心和谐。
正如一位老拳师所言:’练武先练心,练心先做人。’传统武术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它能打倒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塑造怎样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推手运动作为’文明的格斗’,既保留了武术的核心智慧,又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取向,或许正是传统武术在当代最富生命力的传承形式。
武之魂,不在拳脚之利,而在精神之高。
当我们超越’武术能否打’的简单追问,方能窥见传统武术’止戈为武’的深刻智慧。在当代社会,传统武术的价值不在于固守’打’的原始功能,而在于通过’打’的辩证思考,引导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身心和谐与人文修养。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武术大师往往谦和低调——因为他们深知,武术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不战而胜’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