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阮元《儒林传稿》,学界几乎都依据南京图书馆藏本进行研究,但对其版本系统则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根据该藏本无印记、牌记以及文中避讳字使用情况,再结合阮元致黄奭书札所言,推断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极有可能就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甘泉黄氏刻本。如果此判断不误,南京图书馆藏本是初刻本、单刻本,也是家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关键词:南京图书馆藏本 《儒林传稿》 版本 阮元 清代学术史
《儒林传稿》是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1810—1812)阮元任国史馆总纂时主持辑纂的第一部官修学者类传体清代学术史。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四卷刻本(以下简称南图藏本)影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后,[1]学界几乎都据此从事研究,影响很大。南图藏本“书版框高一二九毫米,宽一八八毫米”;[2]版式为黑口,四周单边;行款为半叶10行,每行21字,注文双行;版心上记儒林传稿,儒林传稿下右记序、例、录或卷数,版心下右记叶数;卷首为序、凡例、目录。
以往学者对南图藏本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否为清嘉庆刻本。王汎森指出:“关于这个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者注明是嘉庆刊本,但查考南京清凉山《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原本(分为线装两册,第一册是卷一、二,第二册是卷三、四),并没有任何出版资料及收藏印记,只有一’南京图书馆藏’朱印,并无任何确证可以判定为嘉庆刊本,编者极可能是根据该书序于嘉庆十七年(1812),故遽定为嘉庆刊本。”[3]黄圣修也曾赴南京图书馆调阅该本,他的判断与王汎森相同:“该书并无任何印记、牌记可供辨识,故南京图书馆馆员当是据阮元之序而径将此本著录为嘉庆年间刊本。”[4]黄圣修还赴上海图书馆考察,发现“与此本相同之版本,上海图书馆亦有收藏,不过装订则略有差异,南京图书馆之藏本,为一、二卷一册,三、四卷一册,共分为两册,至于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则四卷装订为一册,并于封面上注明’一册全’。两者除装订不同外,其余内容与刊刻样式则完全相同,当为同一版本不同装订。此外,上海图书馆所藏本上有’同治戊辰(同治七年,1868)八月寻于京师’字样,则此版本之刊刻,最迟当不晚于同治年间”。[5]其二,是否为阮元辑纂。戚学民推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嘉庆刻本《儒林传稿》,……判断它出于阮元的授意,大约不错”。[6]马延炜认为,《儒林传稿》四卷,嘉庆十七年刻本,藏南京、上海,“确为阮元主持拟订之初稿”。[7]总之,南图藏本为阮元辑纂,不是嘉庆刻本,刻印“不晚于同治年间”。那么,南图藏本的刻者是谁,刻于何时,为何刻印?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梳理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推测其刻印时期;分析阮元致黄奭信札,确定刻者;揣摩刻印《儒林传稿》之因,供治清代学术史者参考,并请读者指正。
阮元《儒林传序》
一、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
南图藏本无印记、牌记,在此情形下,探讨成书于何时,考察避讳是常用的方法。通过避讳的线索,可以大致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而南图藏本确有避讳。因此,本文从梳理其避讳入手。
(一)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
1. 避孔子名讳,改“丘”为“邱”。《薛凤祚传》“盖祖邱濬旧说也”,卷三第654页上;[8]《刘源渌传》“安邱人”,卷三第659页下;《阎循观传》“安邱张贞”,卷三第660页上;《武忆传》“比邱尼”,卷四第672下;《孔广森传》“城楚邱之不嫌于内邑”,卷四第676页上。
2. 避明光宗名讳,改“洛”为“雒”。《耿介传》“寻予假归,卒。《雒学编续》”,卷一第624页上;《张夏传》“又著《雒闽源流录》”,卷一第629页下。
3. 避明熹宗名讳,改“校”为“较”。《王懋竑传》“较定《朱文公年谱》”,卷三第655页下。
4. 避康熙帝名讳,“玄”缺末笔。《序》“两晋玄学盛兴”,卷首第617页上。避康熙帝名讳,“弦”缺末笔。《薛凤祚传》“所列止正弦、余弦”,卷三第653页下;《戴震传》“然用余弦折平为中数,……震则谓用余弦者……盖余弦者……八线法:弧小则余弦大,弧大则余弦小。弧若大过象限九十度,则余弦反由小而渐大,……不似余弦之参差”,卷四第 670页下、671页上。避康熙帝名讳,改“玄”为“元”。《王夫之传》“而亦不空谈元妙”,卷一第627页下;《惠栋传》“而参以郑元,……辨郑元所传之二十四篇”,卷二第636页下;《臧琳传》“琳之元孙庸学于卢文弨”,卷三第659上;《李光坡传》“兼取扬雄太元”,卷三第662页下。
5. 避雍正帝名讳,改“胤”为“嗣”。《阎若璩传》“《五子之歌》《嗣征》”,卷二第637页下。
6. 避雍正帝名讳,改“禛”为“正”“稹”。《阎若璩传》“《博湖掌录》,王士正《居易录》”,卷二第639页下;《李铠传》“王士稹称其为有本之学,……王士稹撰《传》”,卷二第640页上;《范镐鼎传》“讲濂、洛,王士正《居易录》”,卷三第 660 页上。
7. 避乾隆帝名讳,改“弘”为“宏”。《凡例》“宏文馆”,卷首第619上;《王心敬传》“陈宏谋”,卷一第625页下;《高愈传》“朱宏”,卷一第628下;《顾炎武传》“王宏撰”,卷一第633页上;《阎若璩传》“陶宏景”,卷二第637页上;《严衍传》“欲树宏猷”,卷二第644页上。
8. 避乾隆帝名讳,空“历”字。《黄宗羲传》“《大统法辨》四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勿庵算书目》”,卷一第626页下、627页下,“大统”“授时”“西洋”“回”“勿庵”下,均空“历”字。
避乾隆帝名讳,改“历”为“天”。《梅文鼎传》“著《天学骈枝》六卷,值天学书之难读者,……所著天算之书八十余种,……作《元史天经补注》二卷,……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余卷”,卷二第649页上。
避乾隆帝名讳,改“历”为“法”。《梅文鼎传》“读《元史》授时法经,……作《庚午元法考》一卷。……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经立法之根,拈其义之精微者,为《郭太史法草补注》二卷。……作《回回法补注》三卷”,卷二第649页上下。
9. 避嘉庆帝名讳,改“颙”为“容”。《序》“如孙奇逢、李容等”,卷首第617页下;《目录》“李容”,卷首第620页上;《孙奇逢传》“与李容、黄宗羲鼎足行谊”,卷一第623页下;《李颙传》“李容”,卷一第624页下、625页上下;《王心敬传》“容学”,卷一第625页下;《李因笃传》“李容”,卷一第 625 页下;《顾炎武传》“李容”,卷一第632页上;《陆世仪传》“李容”,卷二第 642页下;《梅文鼎传》“李容”,卷二651页上。
10. 避嘉庆帝名讳,改“琰”为“琬”。《吴鼎传》“俞琬”,卷一第 622 下。
综上,南图藏本避孔子和明清帝名讳,避讳字有:丘、洛、校、玄、胤、禛、弘、历、颙、琰等 10 字;避讳方法有:(1)改字,加偏旁代替避讳字,改“丘”为“邱”;用同义字或义近字代替避讳字,改“胤”为“嗣”,改“历”为“天”“法”,改“琰”为“琬”;用形似字代替避讳字,改“校”为“较”;(2)谐音,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避讳字,改“洛”为“雒”,改“玄”为“元”,改“禛”为“正”“稹”,改“颙”为“容”,改“弘”为“宏”;(3)缺笔,以缺笔示避讳,“玄”“弦”缺末笔;(4)空字,空其字而不书,以示避讳,空“历”字。
(二)南图藏本避讳不一致
南图藏本避明光宗名“洛”讳仅两例,但其不避者竟有20例。例如:《孙奇逢传》“奇逢早年潜心濂、洛之书,……奇逢命斌辑《洛学编》”,卷一第623页上、624页上;《胡渭传》“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以当洛书,……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渭则于河图、洛书,……《洛书》本文”,卷二第633页下、634页上下。
南图藏本避明熹宗名“校”讳仅1例,但其不避者竟有38例。例如:《阎若璩传》“以今孔书校之,……今以《史记》《说文》与晚出《书》相校,……手校《困学纪闻》”,卷二第 638页上、639页下;《毛奇龄传》“学校诸问答”,卷二第 640 页下。
南图藏本避康熙帝名“玄”讳,含“玄”的“弦”字亦避。但避雍正帝名“禛”讳,而含“真”的“慎”字不避。例如:《孙奇逢传》“以存诚慎独为持要。……惟是慎独而已”,卷一第623页上。
南图藏本避雍正帝名“禛”讳,而不避“真”字。例如:《胡渭传》“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渭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卷二第 634页上。
南图藏本避讳不一致,是由于其史源不同。南图藏本文本源于近 200种文献,而各文献的避讳方法不同。另外,各传记辑纂者的避讳方法也不尽一致。
众所周知,文本避讳至什么时期,可大体判断其为何时版本。南图藏本避嘉庆帝名颙琰讳,不避道光帝名旻宁及其后诸帝名讳且与成书于嘉庆朝一致,说明其版本可能为嘉庆刻本。但是,南图藏本中全部使用“上书房”,而无“尚书房”。《王懋竑传》“在上书房行走”,卷三第 655页上;《钱大昕传》“上书房行走”,卷四第 667页上;《卢文弨传》“上书房”,卷四第 672页上。上书房是清代皇子读书之地,道光前叫“尚书房”或“上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称“上书房”,据此,南图藏本可能是道光刻本。
二、阮元致黄奭信札分析
阮元致黄奭(1809—1853)信札是研究《儒林传稿》版本的重要史料。
阮元是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致仕的。阮元回到扬州后,刘文淇(1789—1854)时常前往拜见。道光二十三年春,阮元招刘文淇居其宅校勘《旧唐书》。据刘文淇观察,致仕后,阮元在扬州接触较多的客居扬州有名望者是沈歧(1773—1862)和梁章钜(1775—1849),而对黄奭则时常称赞。刘文淇云:“窃见太傅门墙高峻,平日所与往还者,一二名德寓公外,谓总宪沈饴原、中丞梁芷邻两先生。大率皆寒畯请业之人,若当途冠盖及里闬绅富,绝无宴会酬唱之事,而独于右原比部称道不置。比部每来,讲学必历一两时。太傅间至比部宅,亦坐谈良久甫回。比部每来假书,属文淇检书目,令人往选楼取出,即行赍送。……以耄年犹及见之为幸,其倾许也,可谓至矣。”[9]在刘文淇印象中,阮元对黄奭厚爱有加,且交往颇密。
黄奭编《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黄奭字右原,原名黄锡麟,江苏甘泉人。父至筠(1770—1838)为两淮盐商总商且两任首总(1804—1805、1818—1822)。[10]虽家资雄厚,而黄奭独好于学,尤笃郑学。道光二十三年,阮元在《高密遗书序》中称,黄奭“以赀为刑部郎,又因大京兆吴梅梁杰(1783—1836)为举主,得赐举人。京兆,余门生也。右原以门下晚学生来谒,己亥(1839)后,屡问学。予见其所言《四库》诸书,大略皆能言之,与讲汉学,知其专于郑高密一家,元元本本,有《高密遗书》之辑。余诧之,以为其家以赀殖为事,柳子厚所云’为世所嫌’,安能知所谓高密郑公者?诘其所学,必有所来。右原乃言幼读书为举业,入安定书院,曾宾谷先生(曾燠,1759—1830)异之,曰:’尔勿为时下学。余荐老师宿儒一人,与尔为师。’乃甘泉江郑堂子屏藩(1761—1830[11]也。右原以重脩礼延之,馆其家,从之学。右原质本明敏,又专诚受教,四年,子屏老病卒,独学又十馀年,日事搜讨,从汉唐以来各书中得《高密遗书》盈尺之稿,稿本有已刻者:《六执论》……吾于是慨然高密之学矣”。[12]阮元、江藩、黄奭均主汉学,可谓志同道合。阮元称黄奭“高密之学”,评价甚高。是年,阮元已80岁,而黄奭才34岁。此后,阮元与黄奭,看芍药、互和诗、赠古砖、送端砚、致信札、书匾额、讲学、作书序等等,交游甚笃。黄奭是清代著名辑佚家,所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215种,[13]数量巨大,厥功甚伟。黄奭辑《端绮集》卷二一收录阮元致黄奭信札一组,迻录如下:
《儒林传稿》奉存贵处,可雇人抄一分,原书秋间见还不迟。如能似前刻列传手,刻成小本,为万幸。
王氏横云山人《明史稿》不碍刊之,以此例,似乎可以不必说出谁刻即妙矣。
《儒林传》前须缀行,若曰:阮某稿,某抄得一分。阮底稿及正副稿尚有三分,乃上巳夜皆为六丁取去。是以某幸抄存。因照横云山人《史稿》之例,付之剞劂云云。
昨闻有人见《儒林传》板,不知是不佳者,抑重刻者,即不佳者,到底多一分,亦不必毁之也。
贵处剞劂氏总不见完工,若字字必亲看,虑汗青无日也。
《儒林传》三十部收到,欣谢之至。昔元在定香亭有句云“修书最乐书成后,望雨翻惊雨到时”,书成后之乐,惟自喻耳。京中如何子贞、张石州想皆由贵处给之矣。
锦套《传稿》本付上,若改,自然就小板改,改后必又多印,乞再付与,其前未改者已送人,只好任之矣。[14]
阮元这组信札作于道光二十三年。黄奭在《端绮集序》中称:“数十年同人之诗、古文为天所留者,不分体,而编年以先后之,虽有断烂显然,亦仍之。年各一卷,而卷留空白,以待他处、他日踪迹得之,或本人之存者自补之,不数年更续之。”[15]《端绮集》各卷卷端记端绮集卷几,下记清颂堂丛书,次行记干支,版心记端绮集,端绮集下右记干支及序号。阮元这组信札收录于《端绮集》卷二一癸卯十六,据此,可以确定其作于道光二十三年。
这组信札是当事人阮元所作,当事人黄奭所辑、所刻,且刻印时,两当事人均在世,故为宝贵的原始史料,它证明:
第一,是阮元让黄奭刻印《儒林传稿》的。阮元把抄本给黄奭,让其刻成小本。
第二,阮元对刻印《儒林传稿》很重视。从交付抄本、雇人抄写、抄写时间、刻本大小、刻印理由、不置印记及牌记、加缀行说明其来历及刻印原因,到跟踪刻版、催促进度,总之,阮元对刻印《儒林传稿》的各个环节,既细心,又期盼。
第三,《儒林传稿》印数不多。阮元收到30部,后有部分锦套本。
第四,《儒林传稿》刻印不久,就流传至北京等地。阮元让黄奭送给在北京的何绍基(1799—1873)和张穆(1805—1849)。
第五,黄奭刻印《儒林传稿》非常用心,亲自字字校对。
第六,《儒林传稿》有两种封面,部分加锦套。
那么,南图藏本是否就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为论证这一关键问题,以下将南图藏本与阮元致黄奭信札所言进行比较:
第一,南图藏本“原书版框高一二九毫米,宽一八八毫米”,[16]与阮元所言“小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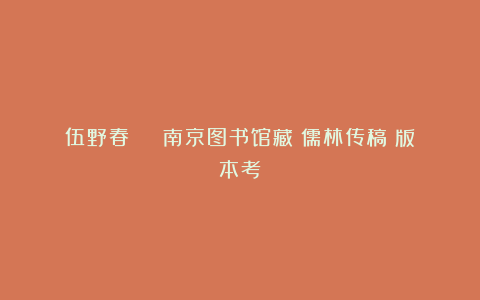
第二,南图藏本无刻者、无刊行时间,与阮元所言“不必说出谁刻”一致。
第三,南图藏本全部使用“上书房”,与道光二十三年刻印时间一致。
第四,南图藏本前无“缀行”,与阮元的要求不同。
第五,南图藏本无锦套,与阮元所言封面之一加锦套者不同。
上述第四可能另有其因,第五因阮元让黄奭所刻有两种封面,故可忽略。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存世《儒林传稿》四卷刻本只有两种,一为南图藏本,一为榕园丛书本,后者系张丙炎(1826—1905)刻、张允 (生卒年不详)刊行,故前者可能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
三、阮元刻印《儒林传稿》之因
阮元刻书无数,刻印一部仅五万馀字的小书,可谓易如反掌,但其完稿于嘉庆十七年的《儒林传稿》,31年后才刻印,且不置印记、牌记,为什么?
阮元《揅经室集》
其一,忌惮国史馆对史稿的管理。清国史馆对史稿的管理较为严格。王汎森指出,“清代国史馆成稿一向存档,并不刊刻,……嘉庆年间的钱仪吉(1783— 1850)……因为参与《会典》的修纂而得以见到国史馆的传记,却未敢抄录向外流传。同治年间,李元度(1821—1887)编《国朝先正事略》,序上也抱怨草野之士无由获睹国史馆传。……史馆列传一般不能得见,史官也不可携回私寓,但是可以就馆抄录”。[17]
其二,对《儒林传稿》被修改非常不满。黄圣修认为,“嘉庆十七年阮元署漕运总督后,便将所纂办之《儒林传稿》交呈国史馆。然而国史馆对于阮元之稿有著不同意见,因此才有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的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总裁曹振镛(1755—1835)曾与翁方纲(1733—1818)有过讨论,自此改变了阮元传稿的学术原则与去取标准”。[18]马延炜指出,“此稿原有的沈国模、谈泰、桂馥、钱澄之、方中通、朱鹤龄、臧庸、阎循观、汪绂、金榜、王鸣盛、丁杰、任大椿、孔广森、张惠言、孔兴燮的传记被删去,毛奇龄改入《文苑传》”。[19]道光十年(1830),阮元将沈国模、毛奇龄等传以《集传录存》为篇名,收入《揅经室续二集》卷二中,并刊行。[20]
其三,英军侵入,局势骤变。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阮元致函钦差大臣伊里布(1775— 1843),提以美国人制英国人之策,未果;七月,英军犯江浙,阮元与卞光河等议防堵诸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扬州筹办防堵事宜,阮元命长孙恩海捐输制钱壹仟缗钱。六月十四日,英军攻占镇江,阮元避居公道桥。
其四,80 岁后文稿每年刻印。以《揅经室集》为例,道光二十三年前,间隔多年才刻印一次:道光三年(1823)刻四十五卷本,道光十年(1830)刻五十四卷本,道光十九年(1839)刻五十六卷本。道光二十三年及其后则每年刻印:道光二十三年刻六十卷本,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六十二卷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再续集》增加若干文章及诗,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六十三卷本。[21]
其五,底稿及正副稿毁于大火。阮元说“上巳夜皆为六丁取去”,是指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三夜,其扬州大东门北第的大火,被烧书含《儒林传稿》底稿及正副稿三份。阮元云:“大东门北第,祁门张氏造,以板包拱把之木,伪为方柱,本不坚壮,方愧难奉御笔,余又积书连屋,时虞傾折。是以邻火骤来,癸巳(1833)、癸卯(1843)两次,御赉皆得护出,其馀书物皆烬。……上巳城中几处夜火,幸而在乡,否则老夫跛卧,将困郁攸。”[22]
第六,刻印国史馆史稿有先例。王汎森指出,“清代从史馆抄辑列传成稿并加刊刻的例子并不在少,乾隆、嘉庆间《满汉名臣传》等书即是。这类书的出版者往往并不明显,有时不具名或是安上一个化名,而出版者亦多不挂名,或挂上厂甸铺的名字”。[23]
四、小 结
通过避讳研究版本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有时仅仅依据避讳研究版本,其结论可能有误,南图藏本就是如此。根据避讳及其方法,南图藏本可能为嘉庆刻本,但根据全部使用“上书房”,则可能是道光刻本。道光二十三年,阮元致黄奭信札是刻印《儒林传稿》重要的证据。将南图藏本与阮元致黄奭信札所言比较,南图藏本可能就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
道光二十三年,阮元刻印《儒林传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对国史馆史稿不得刻印的规矩,阮元心知肚明,处事谨慎的风格,使其在任上不便刻印。阮元对《儒林传稿》颇为自负,[24]对其被修改,且改变“学术原则与去取标准”非常不满。道光十年,阮元将沈国模、毛奇龄等传以《集传录存》为篇名,收入《揅经室集》,以表不满。但《集传录存》只是《儒林传稿》的部分内容,不足以由此评判《儒林传稿》之优劣,只有将其全部刻印,才能供世人鉴别。这是隐藏阮元心中31年的无奈,既想刻且能刻但不便刻。英军侵入镇江,阮元避居公道桥,这对八十高龄且“跛卧”的阮元,刺激颇大,时局莫测,来日不多。《儒林传稿》底稿及正副稿毁于大火,促使阮元尽快刻印。至于阮元说,仿王鸣盛刻印《明史稿》之例,只是给自己理由,授黄奭证据。阮元刻印《儒林传稿》是为了证明其价值,而非盈利,故其印数极少。因此,光绪七年(1881)主持辑纂《清国史·儒林传》、1914年主持辑纂《清史稿·儒林传》的缪荃孙(1844—1919)也未见过《儒林传稿》。[25]
南图藏本极有可能就是《儒林传稿》清道光二十三年甘泉黄氏刻本。如果此判断不误,南图藏本是初刻本、单刻本、也是家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注释
上下滑动阅览
[1] 〔清〕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本。
[2] 〔清〕阮元《儒林传稿》扉页,《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
[3]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版,第72页。
[4] 黄圣修《清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考述──兼论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传〉稿本之变化》,(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民国一百一年夏季),2012年版,第238页。
[5] 同2
[6] 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8页。
[7] 马延炜《〈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64页。
[8] 〔清〕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本,下同。
[9] 〔清〕刘文淇《授砚图》,黄奭辑《端绮集》卷二四丙午十六,《扬州文库》第五辑第79册,广陵书社2016 年影印黄奭《清颂堂丛书》清道光中甘泉黄氏刊本,第518页上;又见顾廷龙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0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9 年影印本,第521页。
[10] 参见明光《清代两淮盐业首总考》,《两淮盐业与扬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40页。
[11] 高明峰《江藩生平探研》,《江藩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1-5页。
[12] 〔清〕阮元《高密遗书序》,沈莹莹校点《揅经室再续三集》卷三,《儒藏》精华编277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6-1197页。
[13] 《汉学堂知足斋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4] 阮元致黄奭信札,黄奭辑《端绮集》卷二一癸卯一五,《扬州文库》第五辑第79册,第509页上下;又见顾廷龙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05册,第512页。
[15] 〔清〕黄奭《端绮集序》,《端绮集》卷首,《扬州文库》第五辑第79册,第433页上;又见顾廷龙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05册,第431页。
[16] 〔清〕阮元《儒林传稿》扉页,《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
[17]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第84-85页。
[18] 黄圣修《清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考述──兼论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传〉稿本之变化》,(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民国一百一年夏季),第237页。
[19] 马延炜《〈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第42页。
[20] 〔清〕阮元《集传录存》,沈莹莹校点《揅经室续二集》卷二,《儒藏》精华编 277下,第930-954页。
[21] 〔清〕沈莹莹《校点说明》,阮元撰、沈莹莹校点《揅经室集》卷首,《儒藏》精华编277上。
[22] 〔清〕阮元《小暑前坐宗舫船游北湖南万柳堂宿别业用庚午年雨后游京师万柳堂五律韵为七律》,沈莹莹校点《揅经室集再续集》卷六,《儒藏》精华编277下,第1226页。
[23]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第84-85页。
[24] 汪喜荀(原名汪喜孙,1786—1847)说,阮元曾将原稿本给他,请他藏诸名山,“昔阮相公撰《儒林传》未成,迁漕运总督,以其稿嘱喜荀藏之名山”。汪喜孙《尚友录叙》,杨晋龙编《汪喜孙著作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713 页,转引自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第248 页。
[25] 1915年9月,缪荃孙致吴士鉴(1868—1934)信云:“阮文达之旧稿,弟仅得九篇。……阮文达旧稿未见。”见陈东辉、程惠新《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文献》2017年第1期,第122页。
载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23辑,
广陵书社2019年7月出版。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作者简介
伍野春(1955-),江苏扬州人,历史学硕士。曾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研部,现为扬州文化研究会会员。在《民国档案》《民俗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扬州文化研究论丛》《扬州学研究》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裴松之评传》,参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点校阮元《儒林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