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
2025年第2期
熔古铸今
守正出新
阮元《揅经室集》原刻、覆刻考
吴雪菡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
作者简介
吴雪菡,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研究生,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提要:清嘉道间学术领袖阮元的《揅经室集》是极具代表性的清人别集。学界此前已注意到阮元《揅经室集》版本混乱的现象,却未发现乱象产生的实质性原因是《揅经室集》存在扬州藏版、广州藏版,且两种版本存在初刻、覆刻关系,其内部又分别存在增改现象。本文从“实物版本”角度出发,重新梳理《揅经室集》的版本源流,分析两种版本的生成路径,以期为完善整理《揅经室集》提供参考。而分析《揅经室集》的文本演变,也为认识阮元“雅正为宗”的文学观念、“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阮元 《揅经室集》 《文选楼丛书》 富文斋 覆刻
阮元《揅经室集》包括《正集》《外集》《续集》《再续集》,是极具代表性的清人别集,目前已有整理本多种。(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邓经元整理本,以《四部丛刊》影印 54卷本为底本;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沈莹莹整理本,收入《儒藏(精华编) 》第277册,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63卷本为底本;2023年广陵书社出版张鑫龙整理本,以陕西省图书馆藏64卷本为底本。)《揅经室集》的版刻情况尤其复杂,已吸引学人多次讨论。沙志利最先探析《揅经室集》多次结集的现象,归纳出 45卷本、54卷本、60卷本、62卷本、63卷本,提出“从全书卷数上比较众本,情况比较复杂,又因为《揅经室集》各部分有其独立性,因此比较各版本之异同,最好不要就全书来比较”。(沙志利《〈揅经室集〉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 期,第49-54页。) 沈莹莹从此思路出发,发现《揅经室集》的《正集》有2个版本、《续集》有3个版本、《再续集》有4个版本、《外集》有2个版本。( 沈莹莹《〈揅经室集〉版本续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2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1-362页。)张鑫龙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再续集》的第5个版本。(张鑫龙《新见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八卷本及其增多诗文八篇辑考》,《历史文献研究》第47 辑,扬州:广陵书社,2021年,第319-330页。)相关研究虽渐趋完善,但仍值得反思。如前人仅就分集发论,缺少整体性的研讨;多从文本对勘的角度分析,缺乏“实物版本学”的关照。本文尝试重新探析《揅经室集》的版本问题,谨备学界参考。
一、《揅经室集》扬州藏版、广州藏版及其关系考
传统版本学对“文本版本”的关注较多,一般通过校勘字句梳理版本谱系,对“实物版本”瞩目甚少。但文本内容相合不完全代表版本相同,譬如原刻、覆刻,单纯离析文本所获结论难称准确。而“实物版本”强调观察版本实物特征,从刊记、序跋、字体、版式、纸张等方面入手探析版本问题(陈正宏《实物版本、文本版本与古籍稿本的整理——-以陈三立早年诗集稿本〈诗录〉的整理为例》(《文本形态与文学阐释(论文集) 》,2015年,第387页) 较早提出“实物版本学”概念,后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第17页) 亦有阐发。),可为研究《揅经室集》版本提供新的视角,呈现新的结论。
(一)两种《揅经室集》版本的发现
阮元具有强烈的立言意识、极大的学术影响力,其诗文集《揅经室集》迭经增刻,目前影印及保存在各大图书馆的版本众多,谨胪列如下:(《揅经室集》尚有 2 种 64卷本,张鑫龙文已详细讨论,故本小节暂不列入,待下小节讨论刊刻过程时再采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78-14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中《揅经室集》为拼合版本,其中《正集》《续集》《再续集》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外集》据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亦未列入。)
甲本。54卷。《四部丛刊》影印本。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9卷。书前墨围题“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初印本”。(《四部丛刊》影印古籍存在描润、改字现象,参见封树芬《略论〈四部丛刊〉影印本的描润改字等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8 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284-293页)。检《四部丛刊》影印之《揅经室集》,尚未发现此类情况。)
乙本。54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 X/810. 78/7110. 1)。二函十六册。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9卷。前人鉴定乙本全同甲本,实稍有差异,如乙本《续集》卷一末较甲本多《释有》一文。
丙本。5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 X/081. 17/7100. 2)。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11卷。此本汇印入《文选楼丛书》28 种本,载该丛书第一、二、三函,凡 23册。前有《文选楼丛书总目录》:“《揅经室全集》四十五卷。《揅经室续集》十一卷。”《文选楼丛书》乃汇印扬州阮氏所藏书版而成,曾多次刷印,每次都重新遴选书版、编刻目录。故今存《文选楼丛书》收书种数、种类不一,笔者所见已有 28 种本、31 种本、32 种本,皆附《文选楼丛书总目录》。
丁本。60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 PG48/26)(此本沈莹莹文著录为 62卷本,误。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登记及笔者检阅,实为 60卷本。)。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9卷、《再续集》6卷。《再续集》卷六末有“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承接刊印”刊记。
戊本。62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 X/810. 78/7110. 2)。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11卷、《再续集》6卷。内封钤“广州熔经铸史斋印行”朱记。
己本。62卷。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 8515)。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11卷、《再续集》6卷。此本汇印入《文选楼丛书》32种本,《正集》《外集》《续集》载该丛书第一至三函,凡 22册,《再续集》载该丛书第七函,凡 2册。前有《文选楼丛书总目录》:“《揅经室全集》四十五卷。《揅经室续集》十一卷……《研经室再续集》六卷(附增)。”需要注意的是,此套《文选楼丛书》中《再续集》未与《正集》《续集》《外集》连排。
庚本。63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 X/081. 17/7100. 1)。包括《正集》40卷、《外集》5卷、《续集》11卷、《再续集》7卷。此本汇印入《文选楼丛书》31 种本,载该丛书第一至五函,凡 34册。前有《文选楼丛书总目录》:“《揅经室正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揅经室续集》十一卷、《揅经室再续集》七卷、《揅经室外集》五卷。”
对勘上述七本的高广、板式、行款、字体等版刻信息,能从蛛丝马迹中探知,此七本分属两套《揅经室集》版片。今以《正集·一集》卷一第1页a为例说明,结果见表一:
分析版刻细节发现:甲本、乙本、丙本、己本、庚本属同一种版片,“揅”字左上版框有缺口、“意”字上方有断版、“或”字右上点靠外;丁本、戊本同属另一种版片,“揅”字左上版框无缺口、“尽”字正中有断版、“或”字右上点靠内。且经过对比发现,甲本(54卷)、乙本(54卷)、丙本(56卷)、己本(62卷)、庚本(63卷) 重合部分的版刻细节完全一致,多出卷数为增刻所致。丁本(60卷)、戊本(62卷) 之间也是相同的情况。足见甲本、乙本、丙本、己本、庚本属于经过增刻的一套书版,丁本、戊本属于递经增刻的另一套书版。
考察史实发现,确实存在两套《揅经室集》书版,一套在扬州,一套在广州。
扬州有《揅经室集》书版的证据是:《文选楼丛书总目录》后附阮亨识语云:“余于文选楼、积古斋诸处所贮书板皆加收检,其中家兄所刊者为多,亦有门下士暨余侄辈所刊者,久不墨印,恐渐零落,印书人请以各小种汇为丛书而印之,亦可行也。”这就说明汇印入《文选楼丛书》的书版,包括《揅经室集》,曾收藏在扬州文选楼或积古斋中。
广州有《揅经室集》书版的证据是:《南海县志》云:“学海堂。咸丰丁巳(七年,1857)为蛮酋分踞,学长等以山堂多藏书板,募有能取出者厚赏之。有通事某甲取出,然缺失者大半矣……先是,山堂外门之内有藏书之室,屯卒毁其书,屋亦摧坏。乃其址拓而大之,增筑山坡,与旧址平高。其外垣为室三间,以藏《经解》板。《揅经室集》《学海堂正集》《二集》板亦有缺失,皆补之。”(郑梦玉等修,梁绍献等纂《(同治)南海县志》卷四,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12叶a。) 学海堂是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办的书院。据《南海县志》可知,咸丰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学海堂所藏书版如《皇清经解》《揅经室集》《学海堂集》等皆遭毁坏。足见广州也保存有一套《揅经室集》书版。
上述两套《揅经室集》版片恰好能与扬州、广州二地相对应:甲本、乙本、丙本、己本、庚本皆同《文选楼丛书》所收版本,当是据扬州藏版刷印;至于丁本、戊本,则与广州关系密切。丁本《再续集》卷六末有“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承接刊印”刊记,“富文斋”是广州规模较大的书坊,位于西湖街,经营时间自嘉庆至民国,历经百余年。(刘淑萍《清代广东书坊的新型经营模式——-以富文斋为例》,《新世纪图书馆》2008年第1 期,第99-100页。) 戊本内封钤有“广州熔经铸史斋印行”朱记,而“熔经铸史斋”是陶福祥的图书发兑处。陶福祥,字春海,广东番禺人,曾任学海堂学长、禺山书院院长,管理过学海堂的版片。(徐信符《广东版片纪略》,《广东文物》,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860页。)丁本、戊本既然属于同一套书版,可见该版片是学海堂委托富文斋刻版的,版藏学海堂,后学海堂学长陶福祥又以“熔经铸史斋”的名义刷印发行。
图一 丁本刊记
图二 戊本朱记(广州藏版内封)
综上所述,扬州、广州各存有一套《揅经室集》书版。甲本、乙本、丙本、己本、庚本即用收贮于扬州的书版刷印的,可称为“扬州藏版”,为便于讨论,下文分别称作扬54卷本a、扬54卷本b、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丁本、戊本则用收藏在广州学海堂的书版刷印,可称为“广州藏版”,下文分别称为广60卷本、广62卷本。
(二)两套《揅经室集》版片关系考
上文已证,《揅经室集》存在扬州藏版、广州藏版,且两个版本面貌高度相似,仅存在微小区别。将古籍依照原样翻刻,版本学上有“仿刻”“影刻”“覆刻”之别,姚伯岳区分云:“用’临’的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应称之为’仿刻本’,而用’摹’的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应称之为’影刻本’……将原本之书叶拆散,然后作为版样直接粘贴于版片上,照原本的版式、字画原样雕镌。用这种复制方法刻印而成的刻本即可称之为覆刻本。”(姚伯岳《中国图书馆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可见覆刻与原刻相似度最高,影刻次之,仿刻又次之。反观《揅经室集》扬州藏版、广州藏版的版刻细节若合符契,如不仔细甄别,完全会混为同版。而且《揅经室集》在当时并非珍稀版本,影刻、仿刻写样成本又高,显然直接使用原书覆刻上板更符合实际情况。综上所述,《揅经室集》扬州藏版、广州藏版之间当存在原刻、覆刻关系。那么二者孰先孰后?可从史实、文本两个角度来观察。考虑到《揅经室集》之《正集》《外集》《续集》《再续集》并非刻于一时一地,因此扬州藏版、广州藏版的原刻、覆刻关系不可一概而论,各分集的情况应当分别讨论。
《揅经室集》之《正集》40卷、《外集》5卷初刻于道光三年(1823),时阮元任两广总督。广州雕版印刷业兴盛,又有学海堂协助校理文稿,为阮元出版图籍提供了便利,如《皇清经解》《雕菰楼集》《江苏诗征》《国朝汉学师承记》《广东通志》皆刊刻于广州。于情于理,《正集》《外集》当初刻并顺势藏版于广州。也就是说,《正集》《外集》的广州藏版为原刻本,扬州藏版为覆刻本。版本实物亦能印证此推论。版本学上鉴定原刻、覆刻最常用的方法即比较“刊雕的工拙”,毕竟覆刻本以原刻本为写样稿雕造,难免出现变形走样的情况,细节亦不如原刻本丰富,因此一般来说“刊刻工者当为原本,拙者应是翻刻”。(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0页。) 今观察《正集》内封的书名题写,可发现广州藏版的笔锋、飞白刻画较扬州藏版更生动细腻(参图二、图三),如“集”字下方有明显的出锋、“室”字右下方有形象的飞白,更符合原刻特征。
图三 扬州藏版(扬54卷本b)内封
《揅经室集》之《续集》9卷初刻于道光十年,时阮元任云贵总督,《续集》9卷即于云南镂版。那么后来书版被移贮何处呢?如果云南雕版被运往扬州,说明扬州藏版为原刻,广州藏版为覆刻;如果被运往广州,则广州藏版为原刻,扬州藏版为覆刻。由于文献不足征,姑且通过比勘字形的方法尝试解答此疑问。对勘发现,扬州藏版文字较广州藏版更显规范、整饬。兹以《续集·一集》卷一第1 叶a 为例,对照扬州藏版(扬54卷本a)、广州藏版(广62卷本)进行说明,校例见表二。如表二所示,“曰”字扬州藏版左上角有缺口,此缺口在广州藏版中被忽略;扬州藏版中“易”字长撇是独立的,有明显的起笔,而在广州藏版中这条长撇与横折钩相连,起笔细节被模糊处理了。综上所述,在云南雕造的《续集》9卷书版当运归扬州,即《续集》9卷的扬州藏版当为初刻本,广州藏版为覆刻本。
阮元自道光十八年致仕至道光二十九年去世,始终栖居在家乡扬州,而据序跋、校勘识语、收录诗文的创作时间推知:《揅经室集》的《续集》卷十至十一、《再续集》卷一至六、《再续集》卷七至八分别编成于道光十九年、道光二十四年和道光二十六年(详见下文)。可见在《揅经室集》后期结集过程中,阮元一直身居扬州。且编纂《揅经室集》始终是阮元关注且亲身参与的。如《再续集》卷七后附阮元识语:“自乙巳之后,经史之属亦少作,而杂记之笔时时有之,随笔录之,此实集也,故抄之于《再续集》之后。丙午(道光二十六年) 冬至颐性老人。”如此来看,道光十八年后,扬州是《揅经室集》编刻的先导阵地,故《续集》卷十至十一、《再续集》8卷的扬州藏版为原刻本,广州藏版为覆刻本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所述,《揅经室集》存在扬州藏版、广州藏版两套版本,伴随主要编刻阵地的转变,使得二者之间存在交错的原刻、覆刻关系。从史实、文本两个角度观察发现,《揅经室集》的《正集》《外集》之初刻本为广州藏版,覆刻本为扬州藏版;而《续集》《再续集》之初刻本为扬州藏版,覆刻本为广州藏版。
二、两套《揅经室集》版片的生成路径
经上文探析知《揅经室集》存在两种版本,即扬州藏板、广州藏板,且其内部存在原刻、覆刻关系。学界此前认为《揅经室集》的刊刻“并不是遵循一个线性的、后出转精的过程”( 张鑫龙《揅经室集·整理前言》,《揅经室集》,扬州:广陵书社,2023年,第13页。),这其实是混淆两条版本脉络导致的结论。进一步对勘扬州藏版、广州藏版发现,其内部实则分别存在着清晰的增刻、修改路径。
(一)扬州藏版
现以扬54卷本a、扬54卷本b、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为例,结合序跋、题识、诗文内容等,尝试还原《揅经室集》扬州藏版的刊刻过程。
1. 迭经增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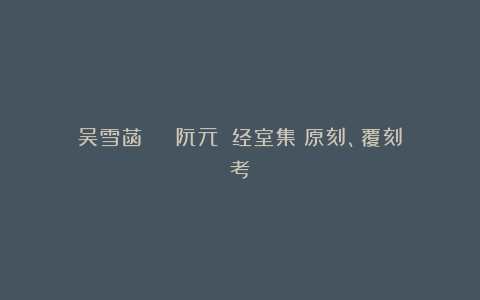
对勘上述五种印本的篇卷异同,将结果汇总为表三(无此卷以“/”标识。前后版本篇数相同,书“同左”;篇数有差异,则括注增几题、删几题,具体情况见小注)。
注释:
① 增文 1 题:《释有》。
② 增文 8 题:《诗书古训序》《孝经先王即文王说》《六宗解》《与曾勉士钊论日月为易书》《诗有馥其馨馥误椒记》《武进张氏谐声谱序》《齐侯罍铭释》《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按:《释有》改题《日有食之不宜有解》,移置《六宗解》后。
③ 增文 8 题:《一切经音义跋》《石画记序》《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罗茗香四元玉鉴细草九式序》《重修滇省诸葛武侯庙记》《汪容甫先生手书跋》《阙里孔氏诗抄序》《梁中丞文选旁证序》。
④ 增文 7 题:《谢赐回疆方略折》《谢授协办大学士折》《谢赐七十寿折》《谢授大学士折》《教习庶吉士谢折》《缅甸进奇异花象赋》《纸赋》。
续表① 增文 1 题:《晋赠荣禄大夫郑公墓表》。
分析上表可知,从扬54卷本a 到扬54卷本b、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扬州藏版的卷数、篇数都处于清晰且持续的增刻状态中。已知的扬州藏版,尚有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两种 64卷本(张鑫龙整理《揅经室集》所据底本即陕西省图书馆藏 64卷本,将其文本对照表二观察,皆与扬州本相合,可见陕西省图书馆藏《揅经室集》64卷本属扬州本。),兹称为扬64卷本a、扬64卷本b。除此以外,其实扬州藏版的增刻过程,远比我们所见更为复杂,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推测,还应当存在扬56卷本a、扬62卷本a、扬62卷b(详见下文)。现梳理扬州藏版的增刻过程如下:
其一,道光十年 (1830) 刻《续集》9卷于云南,后书版移藏扬州。扬州阮氏文选楼据广州藏版覆刻《正集》40卷、《外集》5卷,与《续集》9卷合为扬54卷本a。检《续集》目录后阮常生识语:“以上癸未至庚寅八年文笔,仍以经史子集分为四卷,以后再各续于每卷之后,篇页积多再分中、下卷,诗则接四卷之后列为五六七八九卷。庚寅冬刻于滇南。”知《续集》9卷刻于道光十年(庚寅),增道光三年(癸未) 以来诗文。
其二,道光十四年后《续集》卷一末增刻《释有》,成扬54卷本b。检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有阮元致王引之书札:“《说文》’有’字之说,前接大意,诚为要论。今另又叙成一则,抄以奉览,以为何如?”( 陈鸿森《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8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知阮元曾将《释有》初稿抄寄王引之。陈鸿森考证此札作于道光十三年冬,论证可靠,则《释有》定稿于此后,扬54卷本b 亦形成于是后。
其三,道光十九年增刻《续集》卷十、卷十一,成扬56卷本。此外《续集》卷一末增刻文 8 题、卷三末增刻文 8 题、卷四末增刻文 7 题,为道光十年以来文笔。如《续集》卷三末增刻《重修滇省诸葛武侯庙记》署“乙未二月工毕”,知作于道光十五年春;《汪容甫先生手书跋》署“丁酉九月”,知作于道光十七年。此时阮元已致仕回乡。《续集》前增刻阮元《自序》:“又十数年,积若干篇。至七十六岁,予告归田,以所积者刻为《续集》……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节性斋老人阮元自识。”此次增刻,采用道光十年阮常生识语提及的方案,即于《续集》卷一、二、三、四末分别增刻经、史、子、集相关文章。又因卷二增刻较多,析出卷二下。值得注意的是《释有》改题《日有食之不宜有解》,移置《六宗解》后。
其四,道光二十四年增刻《再续集》6卷,成扬62卷本。《再续集》卷六收录诗歌截止于甲辰,当编刻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此外,广60卷本、广62卷本《再续集》6卷作为覆刻本,分别较扬62卷本少文2题(《再续集·一集》卷一少文 1 题:《释谓》;《再续集·二集》卷二少文 1 题:《程节母秋镫课子图记》。)、文 1 题(《再续集·二集》卷二少文 1 题:《程节母秋镫课子图记》。)。可见广60卷本据以覆刻的《再续集》6卷出现时间要早于扬62卷本,推测存在扬62卷本a;广62卷本据以覆刻的《再续集》6卷出现时间亦早于扬62卷本,又晚于扬62卷本a,推测存在扬62卷b(参见下文)。
其五,道光二十六年增刻《再续集》卷七,成扬63卷本。又于《再续集》卷二末增刻文 1 题。(增文 1 题:《晋赠荣禄大夫郑公墓表》。)《再续集》卷七末有阮元识语:“自乙巳之后,经史之属亦少作,而杂记之笔时时有之,随笔录之,此实集也。故抄之于《再续集》之后。丙午冬至颐性老人。”知编刻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冬,收录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以来所作诗文。同年又增刻《再续集》卷八,成扬64卷本a。此据陕西省图书馆藏《揅经室集》(索书号 0013996),64卷,其《再续集》卷八收文 2 篇 (《释真后篇》《桐城刘少涂乞其父孟涂广列女传序》),末有阮元识语:“道光丙午年冬十一月,颐性老人年八十三岁。”
其六,道光二十六年后,《再续集》卷八末增刻文 6 题,成扬64卷本b。陕西省图书馆藏有另一部《揅经室集》(索书号 0009060) 64卷,其《再续集》卷八末补刻文 6 篇(增文 6 题:《罗氏始迁扬两世先茔碣铭》《林茮生印稿序》《辛丑冬日小支方丈于建国寺西南隅梅竹中分屋立五代李招讨龛位绘图征诗因题识之》《建隆寺志略跋尾》《兵部车架司主事许君宗彦配梁恭人传》《艾湖春泛图题句》。),既有道光二十六年及此后所作诗文,也有部分早年诗文,此即扬64卷本b。钤有“扬州阮氏著礼堂珍藏金石书画之印记”“阮充私印”白文方印,知为阮元弟阮充旧藏(张鑫龙《新见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八卷本及其增多诗文八篇辑考》,第319-330页。),张鑫龙推测“当年家刻试印时所留存,故流传不广”。(张鑫龙《揅经室集·整理前言》,第12页。)此即目前所知编刻最晚、内容最全的《揅经室集》。
2. 挖改换版
扬州藏版在持续增刻的同时,也对部分先期刊刻的板片进行修改。此现象前人未揭示,今以《正集》40卷《续集》9卷为例,对勘扬54卷本a、扬54卷本b、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具体情况见表四(无此内容以“/”标识,前后版本无差异书“同左”)。
从上表可以看出,扬州藏版《揅经室集》在持续增刻的同时,也对部分早期板片进行剜改、换版。修改内容少者,一般剜改修版 (如《正集·一集》卷一第1 叶b,扬54卷本a “大室,盖皆谓清庙中央之室”,扬56卷本剜改 “谓清”作 “僭谓”);修改内容多者,则通过整体替换相关板片的方式实现 (如《正集·一集》卷十第28叶a),但不影响其他板片。而这些变动,全部发生在54卷本增刻为56卷本的过程中。据案语、题名知,当时参与校改的有阮福、阮亨、阮恩浩等。关于这个问题,扬54卷本b 最能说明问题。如上表所示,扬54卷本b 大部分文本与扬54卷本a 相同,又有少部分文本与扬56卷本相同 (如《续集·四集》卷七第10叶a)。不过还有部分文本,既不与扬州54卷本a 相同,也不与扬56卷本相同,体现了两者间的过渡状态。如《正集·一集》卷一第1叶b (见表五),扬54卷本a “皆出八卦益明矣”,在56卷本中剜改为“皆出于易卦也”,而扬54卷本b “皆出”下作空白,体现出板片剜改后尚未填补的面貌。
笔者所见《文选楼丛书》数种,其中收录的《揅经室集》有 56卷本、62卷本、63卷本,但从未发现有 54卷本,可见最早收入《文选楼丛书》的《揅经室集》即 56卷本。可能在《揅经室集》收入《文选楼丛书》时,曾裒理旧稿,作过一番增补、校改,同时还添加按语,严谨地阐明校阅情况。如扬56卷本《中庸说》后添加阮福按语:“福谨按:家大人另有《塔性说》一篇,因其言似近于谐,故不刻入此卷之内,然发明 ‘ 性’ 字误入老释之故,明则畅之,至后刻入《续三集》内,近于子部也。”《塔性说》推崇将佛典“窣堵波”译为“塔”,同时讨论将佛典中“有物焉,具于人未生之初,虚灵圆净,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为嗜欲所昏”翻译为“性”并不合理,提出自己对释家之“性”的理解。因此阮富解释《塔性说》之所以刻入《续集·三集》卷三,是因为它更近于子部。如此细致的校改、系统的编刻,也体现出阮元乃至扬州阮氏家族对作品集的费心经营。
(二)广州藏版
具有原刻、覆刻关系的广州藏版、扬州藏版关系密切,广州藏版的生成路径亦可尝试还原。目前能看到的广州藏版有广60卷本、广62卷本,据上文推论,其中《正集》45卷《外集》5卷为道光三年 (1823) 广州初刻,《续集》《再续集》则属于据扬州藏版覆刻的。既然扬州藏版迭经增刻、修改,那么广州藏版之《续集》《再续集》又是据何种扬州藏版覆刻的呢?对勘篇卷发现,广60卷本、广62卷本与扬54卷本a、扬62卷本关系尤近,兹将对勘结果汇总如表六(因《正集》《外集》无差异,仅列《续集》《再续集》;若前后版本篇数相同,书“同左”;若篇数有差异,则括注增几题、删几题,具体篇题见小注)。
注释:
① 增文9题:《诗书古训序》《孝经先王即文王说》《六宗解》《日有食之不宜有解》《与曾勉士钊论日月为易书》《诗有馥其馨馥误椒记》《武进张氏谐声谱序》《齐侯罍铭释》《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
② 增文8题:《一切经音义跋》《石画记序》《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罗茗香四元玉鉴细草九式序》《重修滇省诸葛武侯庙记》《汪容甫先生手书跋》《阙里孔氏诗抄序》《梁中丞文选旁证序》。
③ 增文6题:《谢赐回疆方略折》《谢授协办大学士折》《谢赐七十寿折》《谢授大学士折》《教习庶吉士谢折》《纸赋》。
④ 增文1题:《缅甸进奇异花象赋》。
⑤ 删诗1题:《悲长子常生》。
⑥ 增文1题:《释谓》。
⑦ 删文1题:《道桥别业爱吾草堂八韵序1文;增文1题:《程节母秋镫课子图记1文。
⑧ 沈莹莹文著录为15篇,误。经笔者核查实物,实为 18 篇。
⑨ 增诗1题:《道桥别业爱吾草庐诗并序》。
⑩ 增诗10题:甲辰诗10题。
如上表所示,广60卷本《续集》所收诗文数量、题目皆同扬54卷本a。对比表三所列扬54卷本a 与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的相异文本,广60卷本皆同扬54卷本a,知广60卷本《续集》覆刻所据底本即扬54卷本a。有趣的是,广60卷本包括《再续集》6卷,但《续集》只有9卷,缺少《续集》卷十、卷十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上文已述,扬62卷本汇印入《文选楼丛书》时《续集》载该丛书第三函,而《再续集》载该丛书第七函。《再续集》未与《续集》排在同处。推测刊刻广60卷本时,只得到了单行的《再续集》6卷,因此《续集》卷十、卷十一未能及时补刻。(今见上海图书馆藏《揅经室再续集》六卷(索书号:线善 764294) 末有张文虎跋云:“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 中夏归自京师,道次淮扬,天中前一日谒仪征相国于徐林门新第之揅经室……日过午矣,旋遣八公子鲁卿孔厚答拜,携赠《揅经室再续集》……《再续集》为扬州毕蕴斋光绮所校,凡文四卷诗一卷。”张文虎拜访阮元,阮元遣阮孔厚答拜,并赠以《揅经室再续集》,也说明《再续集》确实曾单行于世。对校上图本《再续集》与广60卷本《再续集》,发现篇目完全一致,当类广60卷本《再续集》覆刻所据版本。《再续集》尚有其他的单行本传世,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四卷本(书签题“揅经室再续集,道光二十三年春正月门下士毕光琦谨校”)、南京图书馆藏《再续集》五卷本(索书号:89902),因非完整成套的《揅经室集》,暂不列入讨论范围。但据张文虎跋推测,这些单行的《再续集》版本皆为毕光琦持续编校的成果。)那么广60卷本《再续集》6卷的底本是什么呢?如表五所示,广60卷本《再续集》6卷与扬62卷本并非完全相同。相较而言,广60卷本《再续集》尚少文 2 题(卷一少《释谓》,卷二少《程节母秋镫课子图记》)、诗11题(卷五少《道桥别业爱吾草庐诗》1题、卷六少甲辰诗10题)。可见广60卷本刊刻所据《再续集》6卷,是较扬62卷本《再续集》6卷更早结集的版本,故收录诗文不及后期完整,兹称之为“扬62卷本a”。目前虽未见扬62卷本a实物,但扬州藏版迭经增刻,当有不少或历久湮没、或目力未及的版本,扬62卷本a即为其中之一。
广62卷本在广60卷本的基础上增刻《续集》卷二下、卷十、卷十一等整卷,又零散增刻了部分诗文:《续集》卷一、卷三、卷四末分别增刻文9题、文8题、文6题;《再续集》卷一末增刻文1题,卷六末增刻诗10题。据广62卷本《续集》卷一补刻部分版心所署“甲戌续刊”,推测这次补刻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检广62卷本《续集》11卷较扬56卷本少文1题(卷四少《缅甸进奇异花象赋》),依据的应当是较扬56卷本稍早的版本,兹称之为 “扬56卷本a”。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广62卷本《续集》卷十“癸巳”下多诗 1 题 (《悲长子常生》),推测其底本扬56卷本a 中亦有此诗。而扬56卷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癸巳”下都没有收录此诗,取而代之的是“是年有两期丧,无韵语”双行小注。说明这首诗很快在后期版本中被刊落了,至于被刊落的原因,则颇引人遐思(详见下文)。广62卷本《再续集》6卷较扬62卷本少文1题(卷二《程节母秋镫课子图记》)、诗1题(卷五《道桥别业爱吾草庐诗》)(扬62卷本将《道桥别业爱吾草堂八韵序》(《再续集·二集》卷二) 移至《道桥别业爱吾草庐诗》(《再续集·四集》卷五)前,两相抵消,不增不减。),故其底本当是较扬62卷本稍早的版本。而这个版本比广60卷本《再续集》6卷的底本——扬62卷本a 更全,出现时间更晚,兹称之为“扬62卷本b”。
《揅经室集》在广州的覆刻是持之以恒的。我们能明确获知的一次覆刻时间,是同治十三年,此时距阮元卸任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 已近五十年,距《揅经室集》的最终结集也过去了十余年。《揅经室集》的广州覆刻本,体现出岭南士人对阮元的深切追忆。
三、廓清《揅经室集》刊刻过程的意义
经过以上查考,《揅经室集》的刊刻过程较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兹以图四标识《揅经室集》的版本源流(发现实物存世的版本,用实线框标识;推测存在的版本,用虚线框标识)。我们不得不惊异于《揅经室集》结集的频繁。自道光三年(1823) 首次结集,至道光二十九年阮元去世,二十余年间《揅经室集》至少增刻过十次,篇幅从 54卷发展为 64卷。仅就道光二十六年而言,就至少两次增补,形成了扬63卷本、扬64卷本a。《揅经室集》的增刊全面、细致,单篇文章亦及时补刻,投射出阮元对名山事业的重视。版本源流的厘定有助于我们在整理或阅读《揅经室集》时更好地选择底本。在古籍整理实践中,当以相应分集的原刻为底本、覆刻为参校本,同时也要留心各版本间迭经增刻、剜改的现象。与此同时,亦可将《揅经室集》作为窥探清代学术领袖阮元文学、学术思想的一个窗口,使版本学与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互动,加深对阮元人物形象的理解。
前人论述阮元的诗学观念,一般从具体诗文发论。而通过对比不同版次的《揅经室集》,可为理解阮元的文学思想提供一个新视角。阮元在《群雅集序》中表达过自己的诗学观念:“近今诗家辈出,选录亦繁,终以宗伯去淫滥以归雅正为正宗。”提倡诗歌应当“雅正为宗”,秉承“真厚和雅”的儒家诗教(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5页。),从而“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阮元《揅经室集·正集·三集》卷五,第734页。)这与阮元在官场备受赏识、仕途得意的人生经历有关,故于诗歌创作时亦维持作为政客的沉稳形象,追求“中正平和”的审美意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这种文学倾向,恰体现在《揅经室集》被刊落的情愫中。如道光十三年,阮元的妻子孔璐华、长子阮常生先后辞世。阮元当时的悲恸心情,可从哀婉动人的《悲长子常生》(《续集·四集》卷十) 一诗中窥见。诗云:
惟妻与长子,礼皆三年丧见《左传》《仪礼》。余兼二丧,三年不与丝竹之宴。可怜诸孙子,倏已将大祥。观察兼臬事,畿辅称其良常生官清河道,裁陋规,清驿路。殁后永平府士民请祀名宦祠,格于父官三品以上不准举之例。至尊甚怜惜,谓其材尚长余以妻及长子丧面奏,上为动容曰:“尔夫人自然年老也,是人家常事。尔儿子可惜,他是个材料。”并问病状。因奏是癍疹,误于参黄之故。太傅为我劝,谓勿太感伤曹太傅前年失长子,因劝余曰:“入内阁多损长子。”历数满汉诸公皆然。此亦奇矣。骨肉归乡土,命也不克长延陵季子葬子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只可读此自宽。昔余命其名曰“常生”,岂即不常之兆耶。
《悲长子常生》将丧妻、丧子的伤感之情诉诸笔端,追念长子阮常生的才华,记叙皇帝的惋惜,细说同僚对自己的宽慰,字字泣血。耐人寻味的是,这首诗很快在后期版本(扬62卷本、扬63卷本、扬64卷本a、扬64卷本b) 中删去,被替换为“是年有两期丧,无韵语”小注一行。《悲长子常生》在《揅经室集》中保存的时间极短,较为稀见,目前只能在覆刻自扬56卷本a 的广62卷本《续集》卷十中看到。至于这首诗被刊落的原因,大抵是情感过于悲戚,实在有违阮元以往展现出的沉稳内敛形象,亦不符合“雅正为宗”文学审美倾向。此外,清代士人有丁忧不诗的提法,如《随园诗话》云:“诗乃有韵之文,在衰毁时,何暇挥毫拈韵?况父母恩如天地。”(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袁枚全集新编》第十九册,王志英编纂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但士人仅在父母去世时有禁忌,而阮元丧妻、丧子时亦恪守此规则,也能体现出其严格的自我道德规范。
阮元对《揅经室集》的部分修改,目的是剔除僭越因素,能表现阮元身为清廷重臣的谨慎。如扬54卷本a“大室,盖皆谓清庙中央之室”,扬56卷本及其以后版本改作“大室,盖皆僭谓庙中央之室”。此文出自《明堂论》(《正集·一集》卷三),附于《乐记》“武王伐殷,俘馘于京大室”句下,通过姬鼎师、毛父敦、牧敦等铭文“大室”,说明诸侯亦于大室祭祀祖先、奉献俘虏。但从礼制上看,明堂大室为天子专有,诸侯拥有是僭越的表现。故阮元虽援之为例,却不能不对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加以批判,增“僭”字表明态度。
《揅经室集》还有部分改动的目的是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展现出阮元严谨的学者形象。如扬54卷本a“后世之言语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扬56卷本及其以后版本改作“后世之言语文字皆出于易卦也”。此文出自《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正集·一集》卷一),讨论易卦为语言文字生成的源头,并举夬卦为例:“书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后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后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后有夬书,先有夬书而后有夬辞也。”而八卦仅包括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显然将“八卦”改作“易卦”更准确。又如扬54卷本a“公于经未有成书,仅成《类篇》小学一书”,扬56卷本及其以后版本改作“公于经未多成书,又成《书仪》《切韵》等书”。此节出自《通鉴训纂序》(《正集·二集》卷七),首先讲论司马光的治学旨趣,说司马光完全没有与经学相关的著作显然不够严谨,改动后的表达更准确。《揅经室集》亦收录阮元的学术论著,体现其学术观念。对勘《揅经室集》历次版本发现,阮元对早期文章仍有修正,而这些修正往往是对自己学说的审视、完善。透过这些文本变化,能够体会阮元“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阮元《揅经室集·正集·一集》卷二,第45页。)的学说,即提倡集合宋学义理与汉学考据之优长的学术思想。阮元《性命古训》(《正集·一集》卷十) 的宗旨是通过网罗《尚书》《孟子》等古籍对“性命”的阐释,来探寻“性命”的原始意义。扬56卷本及其后各版本的《性命古训》增加 “《孟子》:孟子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忍性者,忍食色等欲也,忍性比节性更为用力坚苦也,岂静复乎”二则内容,可见阮元对此论题持续思考,不仅补充作为考据依据的《孟子》经文,亦添加相关义理分析,体现出“汉宋兼采”的治学特点。
笔者在调查《揅经室集》版本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朱小梅、北京大学出版社沈莹莹、北京大学图书馆赵兵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丰子翔等师友的热心帮助,谨致谢忱!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