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武汉出版社2021年版
编者按
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依托丰富的一手史料,深入考察了现代长篇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面貌与接受状况,堪称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吴晓东教授以陈著提供的详实史料与论述框架为基础,通过专题片论的形式,勾勒出1940年代长篇小说的整体图景。文章立体呈现了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如何深刻回应时代巨变,在艺术与思想上开拓新境,为理解现代文学的关键转型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初刊《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感谢吴晓东教授授权发表。
经过战火的洗礼,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小说家无论在历史经验、社会阅历,还是文学体验、艺术感受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进入一个丰富的收获季。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更是生成了新的小说理念和艺术模式,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陈思广教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以下简称《编年史》)中也获得了充分的印证。本文试图基于《编年史》提供的丰富史料和论述图景,粗略谈谈40年代长篇小说的观念视野及艺术探索问题。在形式上,本文尝试采取片论的方式,以期更多元地展现40年代的长篇小说图景。
丰富性和探索性
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在观念视野、结构方式、艺术风格和小说文体等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探索性。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冯至的《伍子胥》,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师陀的《结婚》,巴金的《憩园》,梁山丁的《绿色的谷》,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沈从文的《雪晴》,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标志着新的小说艺术图景的生成,也更深刻地昭示了长篇小说与时代语境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从而要求研究者既要从小说理念和艺术的维度加以考察,同时也要把小说放置于40年代的大历史中去深入探讨,进而打通文本内外的阐释渠道。
20世纪40年代长篇小说的政治性空前强化,小说家们的创作与团结御侮、民族独立、抗战建国等时代的重大议题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小说也表现出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譬如《马伯乐》、《伍子胥》、《山山水水》、《果园城记》、《围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都把战时深切的民族关怀与关于远景的思考,蕴藉于历史、记忆与战时日常经验的书写之中。政治性维度也以渐趋曲折和隐微的方式显影在小说形式中。
在艺术思维和美学风格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也突破了前两个十年的现实主义主流模式,在创作资源方面,显示出空前的兼容性。尤其对现代主义生存哲学和小说理念的吸纳,在《伍子胥》、《围城》、《山山水水》以及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等作品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作家们所获得的现代主义滋养,既有助于直面与呈现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也拓展了小说的观念视野。
萧红:《马伯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世纪40年代也体现出长篇小说体式的多样化以及文体跨界的诗学特征。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废名在《桥》中就追求兼容散文和诗化文体,到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则让小说囊括了经史、杂感、政论、哲学、传记,塑造了空前的集大成或者说大杂烩文体。萧红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也都别具一格,语言兼有诗化以及散文化的特质,风格上则杂糅了抒情体和讽喻体。《马伯乐》尤其使讽喻体成为40年代渐趋成熟的小说文体,而《呼兰河传》在戏谑之外还展现出茅盾所谓的“歌谣”风,是此前现代文学中难得一见的文体风格,而其第一人称追溯式回忆结构,既有助于诗性文体的生成,也内化了个体生命成长史和地方风物志,“将其中蕴含的巨大的文化含量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诗意地写出”(685页)。回忆体也由此成为40年代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类型[2]。骆宾基的《幼年》“是一部充满诗意性的、散文化的长篇小说”(824页),在诗性文体以及追忆结构方面受到萧红的影响,同时也涵容了史诗诉求,使40年代的史诗性小说,在茅盾《子夜》的基础上,呈现出别异的探索性。
新范式的诞生
20世纪40年代也创生了一些新的长篇小说范式,这些范式即或在前两个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隐约闪现,也未成为主流。它们因应了40年代总体性战争情境,也构成了对战争年代的直观反映。
相当一部分小说家战时都有流徙经历,这一经历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小说创作的题材与结构,如《马伯乐》、《围城》、《伍子胥》、《山山水水》、《引力》、《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都处理了诸如流亡、漂泊、迁徙、逃离和旅行的主题,也催生了漂泊和旅行的叙事线索和故事框架,在战时成为一个普泛的结构模式。
20世纪40年代还生成了归乡模式,《果园城记》、《还乡记》、《憩园》、《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是典型的归乡题材[3]。如果说早在鲁迅的《故乡》、《祝福》中就奠定了这一模式,但毕竟是短篇形制,而40年代的小说家们则为归乡模式赋予了更丰富的情节容量和历史内涵。赵树理则在《李家庄的变迁》、《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建构了离乡-归乡的结构模式[4]。
沙汀《淘金记》(1943)、《困兽记》(1945)、《还乡记》(1948)初版本书影
40年代也出现了书写地方史的长卷,沙汀的“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沈从文的《长河》以及《雪晴》,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艾芜的《丰饶的原野》,骆宾基的《幼年》,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使地方性作为战时中国的一种社会力量,也为这一类小说赋予了乡土社会学的动力机制,贡献了不同于30年代左翼视野下的乡土图景和地方史观。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
而在延安和解放区,新的政治蓝图和历史远景的出现,也为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长篇小说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视野和结构图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范式的诞生,代表了“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5],而《暴风骤雨》在描写了“农民怎样在斗争中克服自己思想中的弱点而发展和成长起来”[6]的同时,也为革命中国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正如周立波在1949年自述的那样:“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一般的说,典型化的程度越高,艺术的价值就越大。”(1234页)周立波既概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范式,也凸显了艺术手法和创作原则。而针对“革命现实主义”在创造性与模式化之间的得与失,《编年史》有精彩的总结:“人物的描写开始从阶级的视野予以审视,人性的展现也被框进相对固定的模式中,出现了大量类型化人物”;“在结构上,作家的创作重心从表现人转移到表现事件上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二元对立的’矛盾——斗争——胜利’结构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选择。”(1227页)
对既有模式的突破
李泽厚指出,与五四时代相比,30年代才有了“小说领域内的真正的模式的创造”[7]。叶圣陶的《倪焕之》(成长小说框架),茅盾的《子夜》(全景式史诗),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长河小说”结构),巴金的《家》(家族叙事),都为长篇小说奠立了相对成熟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在40年代得到延续的同时,也被新的探索突破。
《财主底儿女们》尤其具有一种综合性和集大成性,难以用单一图式进行阐释。似乎路翎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企图囊括所有的长篇小说模式,其中对他最具吸引力的或许是史诗模式。而评论界也正是用“史诗”范畴去界定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大史诗”,“是现代中国底百科全书,因为它所包含的是现代精神的一些主要的倾向;横可以通向全体,直可以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倾向,这是光明和斗争的大交响”(902页)。胡风在《青春底诗—<财主底儿女们>序》中更是为这部小说定了调子:“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份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1109页)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但对既有模式的突破,或许更是路翎的自觉追求。《财主底儿女们》虽然称得上是卢卡契总体性意义上的史诗,但其实也以蒋纯祖的死,预示了“史诗性”的根本性欠缺。而从结构上看,《财主底儿女们》即使涵容了“成长小说”模式,也被研究者更多地解读为“反成长体”[8]。蒋纯祖的成长历程在凸显40年代的“成长模式”所能囊括的历史图景和思想容量的同时,也突出表现了人物主体的不稳定性。蒋纯祖与其说在“成长”,不如说在“挣扎”和“矛盾”,尤其在各种“主义”之间,在各种思想和观念之间难以选择的矛盾性,更是把主体心灵史臻于巅峰,其成长模式的复杂性也是“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无法全部容括的。正如王璞所说:“中国的成长小说孜孜以求的是成长,最终却成为’反成长’的小说,因为历史没有给出关于个人’成熟’的叙事可能性。”[9]路翎忠实地表明,在战乱年代,自我遭遇的往往是历史的困局,而马伯乐、方鸿渐一类的反成长形象显然更具有时代性。而“反成长”模式的生成,也提供了对成长小说这一经典模式的反讽式重建。
尽管“历史没有给出关于个人’成熟’的叙事可能性”,但路翎却在小说学的意义上提供了新的叙事的可能性视野,即对既有模式的突破。路翎曾这样评论《财主底儿女们》:“它也许并不像一篇小说(我简直越来越不懂什么是’小说’了,或者说,我从来不曾懂得它)。——或许是一篇拙劣之中最拙劣的小说。”[10]“拙劣”的说法,或许是出于自谦,但路翎所谓“不像一篇小说”的体认,则意味着对经典意义上的小说的突破,是模式的超越,也由此创生了一部现代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精神现象学”。尽管无名氏在其构想更为宏大的《无名书初稿》中立志写一部“心灵的史诗”,“决心反叛现实主义”,“写出精神”[11],但就“心灵辩证法”所呈现的力度和深度,《财主底儿女们》显然更胜一筹。
长篇小说的观念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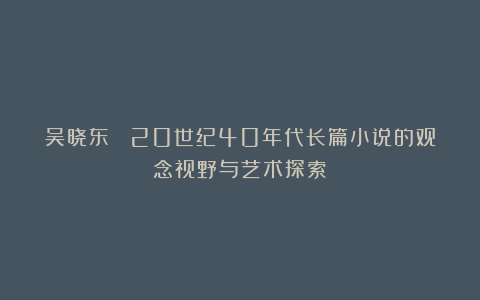
相比于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更需要小说家在文本中提供相对完整的观念图式,从中也能见出作家对社会历史、人生情境乃至世界结构的体系化的理解。
这种观念图式之所以重要,也关涉了长篇小说的叙述动力学问题。如果一部长篇缺乏整体图式,也往往欠缺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叙事动力。
仅以家族(家庭)小说为例。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家族(家庭)小说艺术成就相对较高,一方面源于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念以及家族制度的深厚土壤,源于传统家族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作家在家族叙事中往往有着观念图式的支撑。譬如状写封建家族走向没落的必然性,以及家中青年一代的蜕变与新生,构成了《家》的基本叙事动力,既有作者的情感力量的推进,也有观念形态的加持。“青春是美丽的”,即是为家中新生代设计的观念图景。
巴金“激流三部曲”书影
但《春》和《秋》在观念上只是《家》的惯性延续,在40年代语境中则多少丧失了历史动力。正如巴人在《略论巴金<家>的三部曲》中指出的那样:“巴金把这世界划分为两个壁垒。这边是旧的,那边是新的。对立着。形而上学的绝对地对立着。……然而旧和新之间,没有连续,也没有嬗递与关联。”“同样,巴金在人物的塑铸上,给予新的一种定型,给予旧的一种定型,给予不新不旧的,又是一种定型。”“却没有典型的情势和典型的性格。”“巴金是只把他们代表一种势力,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存在着,没有把他们代表一种势力,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在各别不同的形象下面活动起来。”(685-686页)巴人所期待的小说化的“思想体系”不是静态的形而上学的“定型”,而是行动中的人、运行中的社会和发展变化中的历史。而激流三部曲,尤其在后两部中,多少表现出理念图式的定型化,叙事模式化重复化的问题。巴金长篇小说观念和艺术上的真正突破,是在《憩园》和《寒夜》中。《憩园》的第一人称叙事格局,连同嵌套的叙事设计(在“我”的总体性叙事框架中嵌入人物“杨家小孩”的第一人称叙事),都使小说在结构上摇曳多姿,同时对杨梦痴这类放在激流三部曲中属于被鞭挞的对象,也赋予了理解的同情,反更具人性深度。《寒夜》的格局算不上宏大,但炉火纯青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使小说人物获得了心理分析和解剖学意义上的叙事动机,而“寒夜”作为具有总体性的氛围象征,也使小说生成了浓郁的时代感。
而40年代在家族(家庭)叙事方面更有突破性的是《四世同堂》和《京华烟云》,也因为两部小说真正把战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图景内化到小说观念结构之中[12]。作者对家族制度的正面评价和歌颂,也与战争年代对家国一体性的强调密不可分。同时,老舍和林语堂借助书写家族制度渲染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尽管折射了战时意识形态,却也提供了理解中华民族和历史赓续的正能量。
诗化小说的叙事动力
《桥》缔造了30年代绝无仅有的长篇诗化文体,也奠立了现代诗化小说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废名在《桥》中并没有找到长篇诗化小说的结构模式,只能如李健吾所说“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13]。借用鲁迅评价《儒林外史》结构特征的著名判断,则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14],暴露的是诗化小说叙事动力的结构性欠缺,《桥》也因此无法收束,终成断尾之作。
到了40年代,《呼兰河传》、《果园城记》、《伍子胥》、《幼年》、《山山水水》等作品的问世,使长篇诗化小说在延续抒情性因素以及诗学特质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叙事动力,抒情和诗意也内化为一种情动机制。而茅盾把《呼兰河传》首先看成是“一篇叙事诗”,然后才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998页),也看重的是小说叙事性与诗性的熔铸。《呼兰河传》也表现了萧红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的匠心,前两章对小城的总体描述,第三章先对后花园空间进行营造然后引入“我”和爷爷的故事,此后逐章讲述其他人物(小团圆媳妇、有二伯以及冯歪嘴子)的故事,都体现了对结构的精心设计。《伍子胥》借助于流亡框架以及成长主题,不断书写伍子胥逃亡过程中的启悟时刻,小说也成为在精彩叙事中兼容诗化哲理的不可多得的佳构。《幼年》则试图以儿童视角统摄回溯型叙事,相对完美地统一了回忆体与家族史。
卞之琳:《山山水水》,香港山边社1983年版
更值得讨论的诗化鸿篇巨制则是《山山水水》,借助于题词“行行复行行”所昭示的“反复行进”[15]的旅行模式以及纪德式的“螺旋式上升”的理念,卞之琳实现了自己的宏大企图:“用形象表现,在文化上,精神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16]而支撑起小说叙事结构的,则是卞之琳精心设计的旅行和迁徙的框架:“《山山水水》背景设置的转移,第一卷随未匀从敌占区边缘乡下出来,所到的战区中心城市是武汉,第三卷随纶年从敌后抗敌根据地回来,所到的地区中心城市却是延安了;第二卷未匀重见到纶年的’大后方’城市是成都,第四卷纶年再见到未匀的’大后方’城市则是昆明了。延安固然大大不同于武汉,昆明也多少不同于成都。三年内的背景设置,也标志了螺旋式。”[17]这里的“螺旋式”既是小说的诗化哲理,也是理念图式,同时也是叙事结构,诚如李松睿所说:“卞之琳以’螺旋式的进步’观念结构小说文本,使得小说中的时代、战争成了主人公磨砺自我的工具。”[18]因此,卞之琳堪称匠心独运地创建了一个长篇小说的诗化结构,“《山山水水》中的’诗化’首先是结构上的,具有整体性的内在视景。卞之琳希望借助这种’诗化’结构所带来的’推涌’力量来展现人物的成长,并将之与’山水’的’相隔与相接’联动起来,这成为卞之琳在战时所建构的包含了’人的发展’的独特’山水’图景”[19]。
世界视野
《编年史》的丰富性,还体现在为读者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世界视野。
40年代的中国作家,体验到的是中国与世界的空前的一体化图景。在长篇小说观念领域,也与世界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同步性。卢卡契著名的理论文章《叙述与描写》在战时被翻译进中国文坛,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文学理念迅速介入到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观念之中。《山山水水》更是接受了西方长篇小说结构观的影响,如果说卞之琳所借鉴的亨利·詹姆斯的“视点”[20]理论还是比较传统的小说叙事技巧,但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当红作家纪德“螺旋式进步”的思想和观念,则创造性地转化为《山山水水》的内景,并决定了长篇小说的结构,是卞之琳与西方文学理念同步运行的结果。
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当研究者关注西方的流浪汉体影响了《围城》的时候,存在主义则对这部小说内在的哲理视野有着更为决定性的制约。这一点尽管早有研究者指出[21],但《编年史》呈现给读者的是确凿的史料证明:钱锺书在1947年《观察》杂志第3卷第5期发表《补评英文新字辞典》一文,对辞典里的“存在主义”词条加以了辨析:“’Existentialism:现代法国文学里的一种哲学。’这不大确切,只能说一派现代哲学,战前在德国流行,战后在法国成风气。我有Karl Jaspers:Existenzphilosophie,就是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比法国Sartre:L’Etre et le nean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要早四五年。近来Kierkgaard,Heidegger 的著作有了英译本,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本辞典为’存在主义’下的定义,也不甚了了。”(1084页)陈思广在接下来的“按”语里指出:“这是钱锺书为竞文书局1947年7月出版的《英文新字辞典》所写的一篇书评。……这小段材料很重要,它表明钱锺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是了如指掌的。”“也表明钱锺书从存在主义的视野去观照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是有意为之的,它表明,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揭示《围城》的意涵或许更接近钱锺书的本意。”(1085页)《围城》因此是一部“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意识同步构建的名著”(1063页)。
《编年史》所钩沉的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坛的互动材料中,中国文坛对老舍《骆驼祥子》英译的持续关注,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精彩而难得的个案。
1946年5月15日,署名“铮”的一位作者在《文章》上发表消息《<骆驼祥子>的英译》:“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经译成英文,于去年(一九四五)夏季在美国出版后,传诵一时。在出版后的两星期内,即销去五万本。……由美国’每月新书推荐会’选定为一九四五年八月份的最佳文艺书籍。该书的题名被译成’Rickshaw Boy’(洋车夫);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译名,’祥子’为Happy Boy,’虎姑娘’为 Tiger Girl,’小福子’为 Little Lucky。全书译文大体尚不错,但有许多地方,似乎尚见英译者未能完全了解原作,因而颇有文不对题处。”(970-971页)
Evan King翻译版本Rickshaw Boy
倘若这位作者读了英译本的结尾,恐怕其感受就不仅仅是“文不对题”这么简单了。到了1946年6月29日,夏燕在《华北日报》发表《谈“生意眼”作祟下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在指出了美国译者各种离谱的翻译之后,照录了英译本所擅自篡改了的结尾:“祥子找到了白面口袋,白面口袋带他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福子,祥子趁白面口袋出去给小福子找东西吃的当口把小福子抱起来,逃跑到树林子里——”“在夏暮的温柔的冷风中,他臂中的负担轻轻地转动,紧靠在他身上,他抱着。她还活着,他也活着,他们已经自由了!”(981页)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揣测译者何以让在老舍笔下自杀了的小福子死而复生:“也许是为了迎合美国与战时盟友加强团结的需要,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求乐的愿望。”[22]但英译者大刀阔斧的改译,也折射出世界性的战争带来的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式的影响,《骆驼祥子》英译本以及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英文写作在美国形成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助于增强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也同时昭示着跨语际误读是文学互译和传播过程中永远的宿命。
未完成性
20世纪40年代小说家一方面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呈现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但另一方面,时代依然在行进中,天地玄黄未定,因此作家们对历史长河的走向,也依然在摸索中。而长篇小说则表现出一种“现象级”的未完成性,也是一个巨变时代在小说形式层面的症候性体现。
此间相当一批长篇小说或者在设计上是多卷本的格局,但只写出第一卷(《霜叶红似二月花》、《长河》、《第一阶段的故事》),或者只写出一部分(《刘二和与王继圣》、《雪晴》),或者无法收尾(《马伯乐》、《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此外,诸如丘东平的《茅山下》,李慧英的《松花江上》,黄谷柳的《虾球传》等,都是未完成之作。除了丘东平因为已牺牲在战场上,《茅山下》的五章成为永远的残稿,其他小说的未完成则各有各的原因。但总体上似乎都可以归因于战乱的时代背景。
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表面上看,是作家在动荡的时局中难有稳定的时间和心态去完成长篇构架,但更内在的原因则是作家的创作蓝图本来就缺乏完整规划,或者长篇小说内部本来就匮缺一个历史远景。《围城》并非一部“未完成”之作,甚至可以说小说的结尾相当精妙:“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但方家祖传的这个慢了五个小时的“老钟”,恰恰意味着小说缺少一种未来的向度和矢量,正是倒退的历史观的微妙的体现——作者的时间观是向后看的。而巴金的《秋》虽然在形式上给出了一个结尾:“对于那些爱好’大团圆’收场的读者,这样的结束自然使他们失望,也许还有人会抗议地说:’高家的故事还没有完呢!’”但这种勉为其难的收束,其实也是一种未完成性的表征,堪称是长篇小说无法收尾的一种“元指涉”。
在远景缺失的同时,则是作家主体塑造的未完成性,也充分影响了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视野,呈现为小说结构的未完成性。即便如《财主底儿女们》似乎有个确凿的结局,但蒋纯祖的死去,并不意味着历史划上一个句号,时代依旧正在进行中,只是主人公被甩出了历史进程而已。路翎无法状写出一个西方经典比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意义上的大写主体,蒋纯祖的死,恰是40年代主体未完成性的表征。这大概因为当路翎在小说中为蒋纯祖寻路时,他自己也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也就意味着小说难以生成一个明确的历史远景,而远景的匮乏,则直接影响了一个坚定的大写的主体的诞生。长篇小说在结构形式上的未完成性也是主体的未完成性的表征。因此,在40年代的小说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路翎塑造的那种正在形成中的主体。如果说小说的形式即是主体的形式,那么40年代的小说中呈现出一种“嵌入的主体性”:主体是被嵌入作家正在塑造的形式之中的,在结构和形式之外没有先在的主体性。而主体和形式也都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形态。因此,1940年代长篇小说的未完成性,就与一代作家主体的未完成性之间具有一种同构性。
注释
[1]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武汉出版社2021年10月版。本文引用该书的文字,如果没有特别标注,则仅在行文中列出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