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及其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关系的讨论
吴寒啸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普遍认为史前欧亚大陆只有东亚和西亚这两个彩陶源发中心,其他地区在两地的影响下才陆续出现彩陶文化。然而,南亚次大陆的考古发现表明,印度河流域也是欧亚大陆彩陶源发中心之一,即便彩陶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我国和西亚两河流域。概括来说,在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之前,印度河流域还拥有着长达约4500年的文化时期,如本努盆地(Bannu Basin)、戈马尔平原(Gomal Plain)等地均发现有史前彩陶文化遗址,但尤以印度河中下游流域的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地区数量最多。在过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很少关注南亚地区的彩陶,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印度河流域彩陶文化发展序列,进而讨论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之间彩陶文化的关系。
一、印度河流域史前与文明时代的两大坐标
(一)前印度河文明的坐标:梅尔伽赫(Mehrgarh)遗址
梅尔伽赫遗址(图1—1)位于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卡其平原(Kachi Plain)的博兰山口 (Bolan Pass)脚下。1974年,法国考古使团在著名考古学家贾立基(Jean-François Jarrige)的带领下发现了梅尔伽赫遗址。
梅尔伽赫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其一,梅尔伽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印度河文明的起源具有本土性根源。在发现梅尔伽赫之前,南亚的考古研究建立在文化和文明非融合理论的基础之上,并认为印度河流域的人群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徙过来的。然而,梅尔伽赫的发现直接改变了过往的谬误,它是南亚次大陆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将南亚文化史向前推进了近3000年,更为南亚土著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 ;其二,梅尔伽赫遗址的时间跨度巨大,它拥八个连续的文化层。梅尔伽赫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2500年间持续被占领,这一时期也可称为“前印度河文明”文化时期。 这也就意味着,梅尔伽赫遗址不同文化层出现了印度河流域不同文化类型的彩陶。因此,梅尔伽赫不仅是大型文化集合体 ,更是前印度河文明时代的区域性生产中心。
图1 印度河流域史前与文明时代的两大核心遗存
1.梅尔伽赫遗存一角;2.哈拉帕遗存粮仓和大厅景象
(二)印度河文明的坐标:哈拉帕与摩亨焦·达罗城址
印度河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哈拉帕(Harappa)与摩亨焦·达罗(Mohenjo-daro)这两座孪生城市的出现。遵循考古学文化命名传统,印度河文明又可称之为“哈拉帕文明”。其中,哈拉帕城址(图1—2)位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Punjab)萨希瓦尔市(Sahiwal)西南约35公里处。城址的发掘工作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考古学家达亚·拉姆·萨尼(Daya Ram Sahni)的监督下发掘了哈拉帕城址的两个土墩;后来,沿着印度河的干流南下,又在今巴基斯坦信德省(Sindh)的拉尔卡纳县(Larkana)南20公里处发现了同类型的摩亨焦·达罗城址,并由印度考古学家迪克希特(K. N. Dikshit)于1924—1925年间进行了首次发掘。
在时间序列上,哈拉帕文明虽繁盛于公元前2600至前1900年间(=哈拉帕Ⅲ期),但哈拉帕文明从初生到落幕共分为五期。梅尔伽赫文化的Ⅱ至Ⅵ期(约5500BC—3300BC)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前哈拉帕时期”,而作为早期哈拉帕文明的哈拉帕Ⅰ期和Ⅱ期,又可分别称之拉维(Ravi)阶段和科特·迪吉(Kot Diji)阶段与瑙沙罗Ⅰ期(Nausharo)阶段。可以说,梅尔伽赫文化与哈拉帕文明是一脉相成的,哈拉帕文明的诞生必然建立在“前印度河文明”的基础之上。
二、印度河流域史前文化及其彩陶的发展历程
南亚印度河流域从梅尔伽赫文化的问世到哈拉帕文明的正式生成,其间长达约4500年的岁月在印度河流域周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文化 ,这些文化接续构建出了印度河流域彩陶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外学者对印度河流域,特别是对俾路支斯坦地区彩陶文化的相关研究,本文对印度河流域彩陶文化发展序列作如下阶段划分:
(一)第一阶段(约7000BC—5500BC)——南亚陶器从无到有的突破
梅尔伽赫文化虽然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但梅尔伽赫Ⅰ期所在的MR3区文化堆积层并没有发现原始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原始农业已经出现,考古人员在建筑的泥砖内发现了大麦和小麦的种子,证实了西亚原始农业向南亚地区的传播。
南亚原始陶器出现在梅尔伽赫Ⅱ期(约5500BC—5000BC),即在MR4区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一件器物内部印有篮纹的陶器,这说明梅尔伽赫先民开始以编织篮子为模具,并采用泥质板坯(Sequential slab)的方法制作陶器。 虽然此时的制陶技术不成熟,但南亚先民的大胆尝试实现了南亚陶器从无到有的突破,既证实了印度河流域陶器生产的独立性,又为彩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阶段:KGM文化彩陶(约5000BC—4000BC)——南亚彩陶的问世
乞力·古尔·默罕默德(Kili Ghul Muhammad,简称KGM)文化在时间线上紧接梅尔伽赫Ⅰ期,遗址本体位于梅尔伽赫不远的奎达山谷之中。KGM文化共分为四个时期:第Ⅰ、Ⅱ期无彩陶,第Ⅲ期是典型KGM风格彩陶(=蒙迪加克(Mundigak)Ⅰ期、托高(Togau)A段),第Ⅳ期则出现凯奇·贝格(Kechi-Beg)文化彩色风格的陶器 。
典型KGM文化彩陶主要为碗、鼓腹罐等简单器皿,以红衣黑彩为主要特征,并实现了几何纹饰(图2)和自然题材纹饰(图3)的分野。KGM遗存本体出土的主要是一些简单几何纹饰彩陶,如折线交叉纹、平行线纹、三角网格纹、大圆点纹、虚线玫瑰花结纹(Dotted rosettes)、大环纹(Large loops)等 ;自然题材纹饰被认为出自梅尔伽赫Ⅲ期,以细长造型的大角鹿形象为标志。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细长式大角鹿、羚羊等动物形象在中亚地区也有发现, 说明印度河流域在KGM文化时期就已经与中亚地区存在文化互动关系。
图2 KGM文化几何纹饰彩陶
1.折线交叉纹罐(KGM遗址出土);2—4.圆点纹罐、方块纹罐、垂弧纹与玫瑰花结纹碗(日本爱知博物馆藏);5.KGM文化几何纹彩陶片 [皮尔·海达尔·莎尔(Pir Haider Shar)遗址出土]
图3 KGM文化自然题材纹饰彩陶片(梅尔伽赫Ⅲ期出土)
(三)第三阶段:托高文化彩陶(约4000BC—3600BC)——KGM彩陶的延续与发展
托高遗址本体离梅尔伽赫也不远,它是萨拉旺(Sarawan)查帕尔山谷(Chhappar Vally)的一个大型土丘。1948年英国考古学家德·卡迪(Beatrice de Cardi)发现了托高遗址,只是一直没有发掘。 相反,其附近安吉拉(Anjira)和西亚·丹布(Siah Damb)遗址出土的彩陶在1965年被德·卡迪将定义为托高式彩陶。
德·卡迪认为托高式彩陶可按鹿角的形象变化划分为托高A式、B式、C式和D式。 其中,托高A式以完整的长角鹿形象为标志(图4—1);托高B式则舍弃鹿的身体,仅保留完整的鹿角;托高C式和D式分别将简化的鹿角朝左或朝右刻画(图4—2)。当然,各式角之间可相互搭配组合(图4—3),甚至继续简化为拱形纹饰(图4—4)。因此,这种角状纹饰被称为“托高之角”(Togau horns)。托高文化彩陶以碗类为大宗,故动物纹饰常绘于器物的内外边缘。纹饰色彩在继承KGM文化红衣黑彩的基础之上,新出现了白色、红色和深棕色等配色,有学者认为托高彩陶和KGM彩陶是同一陶器制作体系下的两种变体 。
“托高之角”的出现奠定了印度河流域彩陶流行角状动物纹饰的传统,如本努盆地的谢里·汗·塔拉凯(Sheri Khan Tarakai,以下简称SKT)遗址出土的大角鹿纹陶碗 (图4—6),佐布(Zhob)地区拉纳·贡代(Rana Ghundai )Ⅱ期出土的拉长式大角瘤牛纹(humped bulls)碗(图4-5)等 ,特别是瘤牛形象的出现成为后来印度河流域彩陶上的传统纹饰之一。
图4 托高文化彩陶以及同时期印度河流域角状动物纹饰彩陶
1. 托高“A式角”陶片(①、②梅尔伽赫Ⅲ期出土、③、④、⑤蒙迪加克Ⅰ期出土);2.“托高之角”B式、C式、D式角(笔者根据德·卡迪整理自绘);3.鸟纹与“C式角”碗(日本爱知博物馆藏);4.垂弧线纹碗(俾路支斯坦中部地区出土);5.大角公牛纹碗(拉纳·贡代遗址出土);6.“A式角”碗(SKT遗址出土)
(四)第四阶段:凯奇·贝格文化至纳尔文化彩陶(约3600BC—3200BC)
凯奇·贝格(Kechi Beg)文化与纳尔(Nal)文化虽然在时间序列上相互重叠,但两种文化的彩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面貌,故分而述之:
1.凯奇·贝格文化彩陶:复杂多变的几何纹饰
凯奇·贝格遗址本体南距首府奎达市约8公里,目前奎达山谷有20个地点拥有凯奇·贝格文化的证据。 除KGM文化Ⅳ期以外,梅尔伽赫Ⅳ至Ⅴ期,丹布·萨达特(Damb Sadaat)Ⅰ期、苏拉布(Surab)Ⅲ期、苏尔·贾加尔(Sur Jhangal)Ⅲ期,拉纳·贡代Ⅲ期4段以及佩里亚诺·贡代(Periano Ghundai)等遗址都确定有凯奇·贝格文化的占领层。
方块化的几何纹饰是凯奇·贝格文化彩陶的标志之一,这种方块几何纹饰的流行可能与彩陶的器型有关。凯奇·贝格式彩陶以直壁式器型为主,特别流行长壁烧杯(图5—1)、圆柱形小底碗(图5—2)、小圆锥形碗等。直壁式陶器的表面也更容易表现方块结构的纹饰,而在方块结构纹饰的内部还装饰有三角纹、梯状纹饰(Ladder Pattern)、半圆形纹、圆圈纹、鱼鳞纹、叶片纹等其他纹样(图5—3至图5—7)。器表饰浅黄色或白色陶衣是凯奇·贝格文化彩陶的另一大标志,纹饰喜用黑色粗线描绘轮廓,并配以红色、深红色、橙色等暖色充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色彩涂绘方式也延续到了纳尔文化彩陶当中。
图5 凯奇·贝格文化彩陶
1.长壁烧杯(分别出土于梅尔伽赫Ⅳ期和Ⅴ期);2.方格棋盘纹直壁碗(KGM遗址Ⅳ期出土);3—6.方格对顶三角纹直壁碗、方块梯状纹直壁碗、方块与半圆形纹敞口碗、圆圈纹直壁碗(俾路支斯坦中部地区出土);5—7.凯奇·贝格彩陶装饰纹样展开图(笔者自行整理)
2.纳尔文化彩陶:妙趣横生的动/植物纹饰
纳尔文化遗址本体是苏尔·丹布/纳尔(Sohr Damb/Nal)遗址,它位于俾路支斯坦库兹达尔地区(Khuzdar)西部的基尔塔尔(Kirthar)山谷之中。1925年,时任印度考古调查局主任J·马歇尔(J·Marshall)爵士对该遗址进行的发掘。 苏尔·丹布/纳尔遗址共分为四期,但只有第Ⅱ、Ⅲ期属于纳尔文化层。
纳尔文化彩陶拥有三大特点:第一,除继承凯奇·贝格文化彩陶的器型外,独创的一种平顶小口罐成为纳尔彩陶的标志性器物;第二,纳尔文化彩陶拥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纹饰系统。动物纹饰包括狮子、豹、山羊、水牛、野猪、蝎子、鸟类、鱼类等 (图6—1、图6—2、图6—3),甚至出现了鸟头兽身、长翅膀的山羊等幻想中的神兽(图6—4)。植物纹饰则首次出现了南亚地区常见的菩提树(叶)与柏树形象,且纳尔文化彩陶上的菩提树叶(Pipal tree leaf)仅为单片(图6—5)。菩提树叶的出现也意味着继瘤牛形象以后,印度河流域彩陶上的两大传统纹饰至此全部诞生。几何纹饰则创新出十字相连环形纹、“几”字形纹(图6—6)、鱼鳞片纹(图6—7)等特色纹饰;第三,纳尔文化彩陶拥有极为丰富的色彩体系,特别是出现了蓝色这种罕见色彩。当然,有的彩陶纹饰仅绘轮廓而不施彩,倒也显得简单质朴(图6—8)。
整体来看,纳尔文化彩陶纹饰天真活泼,线条也不重视粗细变化。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划分,即两者不会同时并置于同一画面空间当中。独树一帜的彩陶风格宣告印度河流域彩陶正式进入繁盛阶段。
图6 纳尔文化彩陶
1.狮子纹多彩罐;2.蝎子纹、鸟纹陶片;3.梯状纹、鱼纹陶片;4.鸟头马身带翅膀神兽多彩平顶小口罐(平视与俯视视角);5.菩提树叶纹罐;6.十字相连环形纹与“几”字纹多彩直壁碗;7.鱼鳞纹罐;8.绘有带翅膀山羊的单色陶片 [1.由美国东海岸私人收藏,3.出土于尼埃·布蒂(Niai Buthi)遗址,其余出土于苏尔·丹布遗址]
3.其他文化类型的彩陶
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定居点的大规模涌现,印度河流域还确认有其他文化类型的彩陶。例如围绕着戈马尔和本努地区的托奇·戈马尔(Tochi -Gomal)类型彩陶,其特点是流行环状类纹饰,出现了圆圈纹、垂幛纹、鱼鳞纹(图7—1)等纹饰,另见波浪纹、梯状纹、三角纹以及鹤纹 (图7—2)等其他类纹饰;佐布地区的彩陶也进入繁盛时期,以拉纳·贡代、佩里亚诺·贡代和莫卧儿·贡代(Moghul Ghundai)三个遗址最具代表性,彩陶流行线型纹饰,以弧线纹最为常见(图7—3、7—4)。与此同时,拉纳·贡代彩陶上的瘤牛形象则呈现出拉长变形的趋势(图7—5)。当然,最代表性的莫过于被考古学界认定为阿姆里—纳尔文化体系当中的阿姆里(Amri)彩陶,一种彩陶素体大多属于灰色陶系下的文化类型。 阿姆里类型彩陶以深碗或浅碗为主,纹饰多施黑彩,偶见红棕、浅黄彩等。自然题材纹饰包括棕榈树(图7-6)、树叶、山羊、猫科动物、公牛、鱼类和鸟类等 ;几何纹饰包括梳状纹、三角纹、菱形纹、折线纹等。由于碗类器物较多,故阿姆里类型彩陶纹饰常绘于碗内,并以大型“卍”字纹为标志(图7—7至图7—9),其间偶尔会穿插程式化的山羊纹(图7—10)、树叶纹等。
图7 托奇·戈马尔、拉纳·贡代与阿姆里类型彩陶
1.托奇·戈马尔类型垂幛纹陶片 [詹迪·巴巴尔(Jhandi·babar)遗址出土];2.托奇·戈马尔类型鹤纹陶片(詹迪·巴巴尔遗址出土);3、4.拉纳·贡代遗址出土线型纹饰陶片;5.变形瘤牛纹饰(笔者收集整理);6.棕榈树陶碗(俾路支斯坦西南地区出土);7—9.大型“卍”字符陶碗(俾路支斯坦西南地区出土);10.“卍”字符与羊纹陶碗(日本爱知博物馆藏)
(五)第五阶段:奎达文化彩陶(约3200BC—2600BC)——动/植物纹饰的整合
奎达文化是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而并非根据某一特定遗址命名。该文化以卡奇平原及奎达山谷为核心,向北可延伸至阿富汗南部,向西能达包括马克兰在内的伊朗东南片区,因此,部分学者认为伊朗地区发现的奎达式彩陶可能是从俾路支地区输送过来的。
奎达文化彩陶的素体更加多样,既有浅黄色或红色素体,更有从阿姆里类型继承下来的灰陶。彩陶器型主要包括碗和碗架、小口罐、开口罐、鼓腹杯、高脚杯等。纹饰色彩以红棕彩和黑彩为主,并继承了印度河流域传统动植物题材纹饰,较纳尔文化时期更为写实。例如奎达文化彩陶的菩提树叶有完整的花和果实,鱼纹也摆脱了纯真质朴的形态(图8—1、图8—2)。几何纹饰也变得细密繁复起来,出现如太阳纹、星形纹、同心圆纹、折线纹、梯状纹等,更主要的是实现了不同几何纹饰的搭配组合,装饰意味明显增强(图8—3)。
印度河流域彩陶在奎达文化阶段走向成熟,精美程度远超以往。笔者认为奎达文化彩陶的特点如下:第一,彩陶保留了纹饰分层刻画的传统,层次感强烈;第二,彩陶更加重视器物边缘的装饰性效果,常用细致的几何纹与程式化的动物纹进行装饰(图8—4);第三,彩陶纹饰实现了动物和植物纹饰的画面整合,几何纹饰的搭配组合更加多样;第四,锯齿纹成为奎达文化彩陶的标志性纹饰,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广泛流行(图8—5、图8—6)。
图8 奎达文化风格彩陶
1.菩提树叶与鱼纹陶碗;2.鱼儿嬉戏主题陶碗;3.万花筒纹陶碗;4.程式化羊纹陶碗;5.锯齿纹陶杯;6.多彩锯齿纹陶罐(4.出土于梅尔伽赫Ⅶ期,6.出土于沙赫里索克塔,其余由日本爱知博物馆藏)
(六)第六阶段:哈拉帕文明彩陶(约2600BC—1900BC)——从前哈拉帕阶段谈起
1.哈拉帕Ⅰ期:拉维(Ravi)阶段彩陶(约3300BC—2800BC)
1986年,哈拉帕考古小组在哈拉帕遗存A和B丘西部边缘发现了早期哈拉帕文化陶器。后来,A 丘、B 丘和E丘都出土了若干彩陶碎片,这些彩陶碎片被认定为拉维期彩陶。 从出土情况来看,拉维期彩陶数量虽不多,但统一为泥质夹砂红陶,主要器型包括豆、浅底碗、鼓腹短颈罐、鼓腹圜底罐等。彩陶以黑彩为主,辅之白彩、红棕色彩等进行点缀, 与我国仰韶文化的彩陶色彩搭配方式较为接近。几何纹有网格纹、波浪纹、三角纹、平行线纹、拱形线纹等(图9—1至图9—4);具象纹饰有鱼鳞纹、花瓣纹、蝎子纹、鸟纹和叶片纹等(图9—5至图9—8)。鸟纹和网格叶片纹还同时出现在一件折腹罐上(图9-9),所绘画面可能是拉维河附近的自然场景。虽然拉维阶段彩陶大部分纹饰在科特·迪吉阶段都消失了,但相交式花瓣纹、鱼鳞纹和叶片纹都被保留了下来,并在科特·迪吉阶段和成熟哈拉帕阶段大量出现。
图9 拉维阶段彩陶
1—4.几何纹彩陶(拉维阶段-1A出土);5.鱼鳞纹陶片(拉维阶段-1出土);6、7.叶片纹与花瓣纹陶片(拉维阶段出土);8.花瓣纹折腹罐(拉维阶段出土);9.鸟纹与网格叶片纹折腹罐(拉维阶段出土)
2.哈拉帕Ⅱ期:科特·迪吉(Kot Diji)阶段彩陶(约2800BC——2600BC)
科特·迪吉遗址本体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凯尔布尔市(Khairpur)以南25公里处,与印度河西岸的摩亨焦·达罗城址隔河相望。据不完全统计,在基尔塔尔山脉、信德省北部冲击区、旁遮普省、西北边境和焦里斯坦(Cholistan)等地发现属科特·迪吉阶段的遗址多达111个。
科特·迪吉阶段的彩陶素体也以夹砂红陶为主,鼓腹罐是科特·迪吉彩陶的典型器型,另见碗、盆、盘和盘架等 。彩陶多为红衣黑彩,几何纹饰特别流行线型纹饰,出现波浪纹、交叉线纹、绞索纹等(图10—1至图10—3);自然题材纹饰则发展了拉维阶段的花瓣纹(图10—4至图10—7)和鱼鳞纹(图10—8)。值得一提的是,科特·迪吉阶段出土了一件红衣牛角纹鼓腹罐,而克什米尔地区的扎霍姆遗址(Burzhom)也出土过一件同类型的牛角纹罐(图10—9至图10—10),这表明哈拉帕文明早期阶段与印度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存在联系。
图10 科特·迪吉阶段彩陶
1—3.几何纹彩陶 [巴基斯坦莱万(Lewan)地区出土];4—7.花瓣纹彩陶或碎片(科特·迪吉遗址出土);8.鱼鳞纹喇叭口罐(科特·迪吉遗址出土);9.牛角纹鼓腹罐(布尔扎霍姆遗址出土);10.红衣牛角纹陶罐(科特·迪吉遗址出土)
3、成熟哈拉帕阶段彩陶(约2600BC—1900BC)
到了文明阶段,哈拉帕先民并没有停止制作彩陶,反而继续优化了制作工艺,因此,成熟哈拉帕阶段的彩陶完成度极高。彩陶由极细的粘土制成,几乎没有其他杂质,烧制十分均匀。 另外,轮制技术的成熟也极大丰富了器型种类,主要器型有碟架、圆柱形穿孔罐(cylindrical perforated jars)、圆柱形瓶(cylindrical vases,图11—1)与纽盖、烧杯、高脚杯、盆以及一种大型侈口平边诸物罐等。 彩陶多为红衣黑彩,纹饰艺术则集印度河流域各阶段的精华于一体,自然题材纹饰有孔雀、鹿、瘤牛、蛇、鱼类、鸟类、人物、大焦树、菩提树(叶),以及花瓣纹、鱼鳞纹、太阳纹等;几何纹饰不多但较难概括,出现最多的是三角类纹饰,另见圆点纹、矩形纹、直线纹、“之”字纹等。
在笔者看来,成熟哈拉帕阶段的彩陶有三大特点:第一、彩陶创造出了花与叶的世界。在继承原有花瓣纹的基础之上,哈拉帕先民继续丰富了叶状类纹饰,特别是菩提树叶还出现了环状式结构(图11—2、图11—3);第二、纹饰组合方式比奎达文化阶段更自由。不同类型的植物纹实现自由组合,植物纹中又穿插动物纹(图11—4),俨然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作;第三、彩陶器形较大。有些彩陶的体积甚至大于人体,猜测可能作为礼器之用。
图11 成熟哈拉帕阶段彩陶
1.圆柱形瓶(德里国家博物馆藏);2、3.环形菩提树叶纹小底鼓腹罐 [印度西北部加加尔平原(Ghaggar Plains)法尔马纳地区(Farmana area)出土];4.成熟哈拉帕阶段小底鼓腹罐 [查胡达罗(Chanhu-daro)遗址出土]
(七)第七阶段:库里文化彩陶(约2600BC—1900BC)——与哈拉帕文明同行
在哈拉帕文明未能波及到的地方,库里(Kulli)文化在俾路支斯坦西南部的马克兰山区兴起。 库里文化之所以能成为独立的文化类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彩陶存在自身的个性。库里文化彩陶器型也很丰富,包括敞口浅底碗、直壁碗、敞口罐、喇叭口短颈罐、鼓腹球形罐、矮底罐、盘、盘架、杯架、盆等 。表面上看,库里文化彩陶的纹饰种类都是印度河流域的传统纹饰,如瘤牛、大角羊、猫科动物、鸟类、菩提树(叶)、柏树等,但仔细看来,纹饰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动物纹必然拥有环形大眼(图12—1),且眼睛占据整个头部空间;第二,纹饰拥有固定的组合方式。具体来说,库里文化彩陶纹饰在一个单元画面内必须同时包含大眼动物纹、植物纹和装饰性纹饰,即动物是主体,植物是次主体,而后再搭配“M”形纹和梳子形纹等装饰纹样 (图12—3),三者缺一不可(图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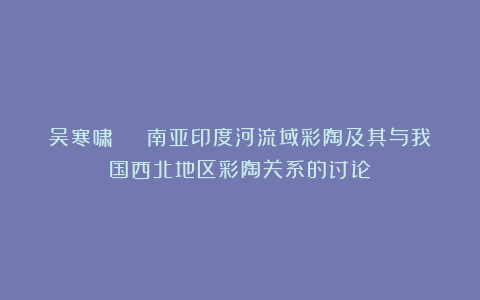
当然,库里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也并非全部同时拥有以上三类纹饰,有的只刻画了梳子纹和山羊纹(图12-4、12-5),有的仅绘环形大眼动物纹,有的则仅有植物纹(图12-6)。这些部分拥有典型库里式彩陶纹饰的陶器称之为“库里相关式”(Kulli-related)彩陶。
图12 库里文化彩陶
1.库里式环形大眼瘤牛与大眼鸟;2.典型库里式彩陶鼓腹罐;3.库里式彩陶上的装饰性纹饰;4—6.“库里相关式”彩陶(以上彩陶均由日本爱知博物馆藏)
三、印度河流域彩陶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关系的讨论
在史前“彩陶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上,国内鲜有学者深入讨论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仅见韩建业和俞方洁在其相关研究中部分涉及。在梳理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列后,笔者拟通过以下四种共有的彩陶纹饰浅谈两地彩陶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可能性,以为后续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
(一)从几何纹饰看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交流互动的可能性
1.垂幛纹
垂幛纹因波线连续下垂如倒挂的帷幕而得名,是南亚印度河流域和我国西北地区彩陶上的常见纹饰。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两个地区拥有完全不同的垂幛纹演化路径。其中,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垂幛纹的演化路径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4000BC—3300BC)至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约3300BC—2850BC)初期;二是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中后期至马厂类型时期(约2350BC—2050BC)。
第一阶段是彩陶垂幛纹的发端期。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最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垂幛形态的纹饰,其源头十分明晰,即由侧身飞翔的具象鸟纹演化而来(图13—1、图13—2),随后逐步简化成“圆点纹+弧线纹”(+)的固定组合样式(图13—3);到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初期,这套固定组合样式仍得以延续,只是在纹饰的细节上稍有改动,马家窑文化先民弱化了“圆点”,而突出了“弧线”的描绘,并开始趋于程式化(图13—4、图13—5)。严格来说,由于这一时期的波线并非为多重连续性下垂,故只能算作是垂弧纹。
第二阶段是彩陶垂幛纹的生成期。随着线型纹饰的盛行,以“水”为主题的纹饰成为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的主旋律,随后不久便抛弃了鸟纹形态的垂弧纹。马家窑类型中后期,彩陶开始盛行一种以圆圈为中心,波浪相互勾连的旋涡纹(图13—6),并在半山类型时期(约2650BC—2350BC)发展出了标志性的“四大圈纹”。不过此时的线型波浪纹仍互相勾连,只是线条变得更加粗犷且黑红相间,有的甚至还装饰有锯齿纹(图13-7、图13-8)。来了马厂类型时期,流动的“旋涡”突然稳定了下来,波浪纹不再相互勾连,锯齿纹也趋于消失(图13—9)。正因为如此,马厂式“四大圈纹+垂幛纹”(+ )的纹饰组合样式开始出现,多重波线连续下垂的“大垂幛纹”自此生成(图13—10)。
图13 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垂幛纹演化图
1.仰韶文化彩陶鸟纹演变路径(采自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第159页);2.具象鸟纹钵(陕西渭南泉护村遗址出土);3.抽象鸟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4.垂弧纹钵(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5.人手柄彩陶盆(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6.马家窑类型旋涡纹罐(甘肃陇西小堡子出土);7.半山类型四大圈锯齿波浪纹罐(甘肃广河地巴坪遗址出土);8.半山类型圆圈方格网纹壶(甘肃东乡锁南镇征收);9.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壶(甘肃临夏民主乡征集);10.马厂类型四大圈网格纹罐(2024年意大利归还)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彩陶垂幛纹也有自身的演化路径,只是没有我国西北地区复杂。早在KGM文化时期,垂幛形态的彩陶纹饰就已经出现了,只是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绘制传统,可能是纯审美的。到了托高文化时期,印度河流域先民才开始有意识的反复绘制垂幛形态的纹饰(图14—1)。与我国西北地区早期情况类似,此时也并非为真正的垂幛纹,而仅作为一种连弧式装饰性纹样绘于陶器的内部。西方有学者曾对器内的纹饰做过内涵释读,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纹饰(包括连弧纹在内)可能是对当地自然景观的描绘,例如山川、河流、动物等等(图14—2)。纹饰的布局也有讲究,陶器的内部空间被刻意划分成三等分,并让各单元纹饰围绕着陶器中心点做永恒地旋转运动。结合彩陶作为随葬品的性质,该观点认为“三等分”象征着人生的三阶段,即出生、成长和死亡,以此来表明逝者已经走过了前两个阶段,正式步入第三个阶段。通过无始无终的循环运动,他们将再次重生,生命将循环往复。 在笔者看来,这种内涵的释读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有的陶器内部空间也会被划分成四等份及以上(图14—3)。
回归到纹饰的形态,不难发现印度河流域早期的垂幛纹虽然不一定向下垂挂,但纹饰的构成方式已经形成,即逐步固定为“竖条纹+弧线纹”(+)的组合样式(图14—4至图14—6)。进入凯奇·贝格文化阶段(约3600BC—3200BC)之后,彩陶垂幛纹在奎达地区、佐布地区大规模流行开来,且纹饰构成方式再无任何改变。特别是奎达地区的阿姆里类型彩陶,佐布地区的拉纳·贡代、佩里亚诺·贡代和莫卧儿·贡代三大遗址出土的彩陶常以垂幛纹为主题(图14—7、图14—8),只是器形一般都不大,且垂幛纹的走线较细。直到奎达文化时期 [包括费兹·默罕默德(Faiz Mohammad)],才出现了大垂幛纹侈口鼓腹罐(图14—9)。
图14 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垂幛纹演化图
1.连弧纹盘(苏尔·丹布遗址出土);2.阿姆里类型鱼纹碗(沙赫里索克塔遗址出土);3.阿姆里类型四重垂弧纹钵(沙赫里索克塔遗址出土);4.垂弧纹陶片(凯奇·贝格遗址出土);5.大角羊鼓腹罐(俾路支斯坦西南地区出土);6—8.垂弧纹陶片(分别出土于撒拉兹姆、佩里亚诺·贡代和费兹·默罕默德遗址);9.大垂幛纹鼓腹罐(瑙沙罗遗址出土)
在厘清两地彩陶垂幛纹的演化路径后,我们发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奎达文化时期的垂幛纹彩陶确实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一是器型接近,都为大型鼓腹罐;二是纹饰特征接近,垂幛纹走线较粗且不富于变化。然笔者认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并不是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两地彩陶垂幛纹的演化路径各有传统,相似性仅在个别,而非一般。我国西北地区彩陶从仰韶文化鸟纹形态的垂弧纹,到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勾连水波纹,再到后来大垂幛纹的生成,前后虽无确切的继承关系,但一直拥有绘制垂弧形态纹饰的传统;印度河流域彩陶垂幛纹的形态更加稳定,只是到奎达文化时期才出现大型垂幛纹。只能说,两地彩陶垂幛纹的演化过程都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而垂幛形态的纹饰本身应为人类审美自然选择的结果。
第二,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垂幛纹的搭配纹饰更为多样,印度河流域彩陶垂幛纹的纹饰搭配则更为固定。马厂类型彩陶垂幛纹的出现源于水波纹不再互相勾连,但与其搭配的“四大圈纹”,其内装饰纹样种类极为丰富,可内填网格纹、圆圈纹、棋盘格纹、十字纹、太阳纹、“卍”字纹等;印度河流域彩陶垂幛纹的搭配纹饰极为固定,有且仅有“竖条纹”一种,算得上是南亚彩陶的经典纹饰组合。
第三,在时间序列上,两地彩陶大垂幛纹的出现存在近千年的时间缺环。马厂类型时期约为公元前2350年至前2050年,即意味着大垂幛纹的盛行至多不过三百年;印度河流域彩陶垂幛纹的构成方式在凯奇·贝格文化阶段(约3600BC—3200BC)就已开始固化。除非我国西北地区先民过往并无绘制垂幛形态纹饰的传统,并在奎达文化末期与南亚先民发生文化互动,不然其间近千年的时间缺环根本无法填补。
2.锯齿纹
在所有的彩陶几何纹饰当中,唯独锯齿纹曾在两地文化的彩陶上大规模长时间流行过。李水城、韩建业两位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试图探究马家窑文化彩陶锯齿纹的来源问题。李水城将视野投放到了内蒙古地区,因为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红台坡、准格尔旗南壕、周家壕等遗址出土了一批时间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晚期的锯齿纹彩陶。他认为在讨论半山类型彩陶锯齿纹的来源时,应对鄂尔多斯高原一带给予关注。 韩建业则提出了我国西北地区彩陶锯齿纹受中亚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Namazga)Ⅱ至Ⅳ期文化(约3500BC—2600BC)影响的可能性。 两位先生各执己见,但仍无法明晰我国西北地区彩陶锯齿纹的来源问题。笔者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锯齿纹出现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对鲵鱼纹的抽象化。
其实,在马家窑文化之前,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属于仰韶文化泉护类型(约4000BC—3500BC)末期的锯齿纹彩陶盆(图15—1) ,这应该是我国西北地区时间最早的锯齿纹彩陶。值得注意的是,其上“十字交叉式”的纹饰结构在形态上的确与中亚吉奥克修尔类型(Geoksyur)晚段(约3300BC—3000BC)锯齿纹彩陶有几分相似(图16-8),故韩建业认为受纳马兹加Ⅱ至Ⅳ期文化影响的遗存可能曾分布在临近青海东部的地区。 然而,此件锯齿纹彩陶盆注定是特殊的,因为仰韶文化彩陶根本不流行锯齿纹,它的出现十分突兀,似为一件孤品彩陶,故锯齿纹的来源问题很难考证。
我国西北地区彩陶锯齿纹的真正长时间流行应该始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石岭下类型彩陶以鲵鱼纹著称,并且拥有一套完整的具象鲵鱼纹向抽象鲵鱼纹演进的过程。开始时,鲵鱼纹较为写实,头部圆润,身体细长,五官特征与身体肌理刻画清晰(图15—2),后来鲵鱼的身体被网格纹取代,鲵鱼的四肢开始有了三角化的迹象(图15—3);到了大地湾遗址三期,鲵鱼纹基本实现抽象化,鲵鱼头部消失,仅保留鲵鱼的身体(图15—4)。正是在此时,锯齿纹出现了,可能被用来表现鲵鱼的脚部或者背鳍;再后来,鲵鱼纹更加抽象,身体愈发扭曲(图15—5),随着长边弧线三角纹的加入,纹饰构成方式趋于稳定,形成了椭圆形网格纹()+长边弧线三角()+带状锯齿()+草叶纹()的固定纹饰组合样式(图15—6)。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彩陶锯齿纹至少在鲵鱼纹身上有完整的演化轨迹,让锯齿纹的出现有迹可循。
进入马家窑类型之后,鲵鱼纹虽然不再流行,但带状锯齿纹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一种装饰性纹饰。不过在马家窑类型时期,锯齿纹并不受重视,表现的也较为稀疏(图15—7)。彩陶锯齿纹的彻底爆发应该始于边家林类型时期(约2850BC—2650BC),繁盛于半山类型时期(约2650BC—2350BC)。虽然锯齿纹在这两个时期体积开始变小,但更加细密化了,并使得它成为了这两个时期彩陶上的标识性纹饰,任何纹饰似乎都可与其搭配组合(图15—8)。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半山类型时期,彩陶又重新开始出现“十字交叉式”的纹饰结构(图15—9、图15—10),这就意味着继仰韶文化泉护类型之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的纹饰形态又再一次接近中亚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的彩陶。到了马家窑文化最后一个时期,即马厂类型时期,彩陶锯齿纹则更加细小(图15—11),甚至趋于消失,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图15 我国西北地区彩陶锯齿纹演化图
1.十字交叉锯齿纹陶片(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出土);2.鲵鱼纹瓶(甘肃甘谷王家坪遗址出土);3.鲵鱼纹瓶(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4.抽象鲵鱼纹瓶(定西博物馆藏);5.抽象鲵鱼纹罐(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6.锯齿网格纹罐(甘肃通渭李家坪遗址出土);7.马家窑类型弧线锯齿纹瓶(甘肃通渭碧玉镇出土);8.边家林类型弧线锯齿纹壶(甘肃康乐附城镇张寨征集);9.半山类型锯齿菱形纹罐(兰州市博物馆藏);10.马厂类型十字交叉锯齿纹罐(甘肃临夏枹罕镇征收);11.马厂类型十字交叉纹罐(甘肃兰州永登杜家台遗址出土)
如果说我国西北地区彩陶锯齿纹的源头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那么南亚和中亚地区彩陶锯齿纹的源头则更加清晰。国外学者多认为,南亚和中亚地区彩陶锯齿纹的前身是应“梯状纹”。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是后来两地彩陶锯齿纹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
起初,南亚和中亚地区在个别文化遗址,如纳尔文化苏尔·丹布遗址、纳马兹加文化阿尔丁特佩(Altyn-Depe)中出现了梯状纹彩陶(图16—1、图16—2),倘若我们将视线转移到由梯状纹勾勒出来的纹饰轮廓则会发现,所谓梯状纹实际上是想表现一种凹凸有致的“城墙状”()纹样,国内学者一般称其为“垛口纹”或“雉堞纹”,并认为可能是对当时建筑形态的描绘, 此类纹饰还延续至中亚青铜时代,在后来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综合体(BMAC)的金属器上极为常见 ,其源头就是彩陶上的“梯状纹”。
公元前3500年左右,梯状纹演变成大锯齿纹,并以折线式的纹饰结构在彩陶上展开。大锯齿纹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阳绘锯齿纹,那么中间留白的部分则形成“雉堞纹”(图16—3);二是阴绘锯齿纹,即阳绘“雉堞纹”,那么折线内留白的部分则为锯齿纹(图16—4)。这两种表现形式的大锯齿纹彩陶在南亚阿姆里类型、奎达文化和中亚纳马兹加文化二期晚段(吉奥克修尔类型早段)中都曾见出 (图16—6),只是尚无法厘清两个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南亚和中亚地区曾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中晚期形成了以“大锯齿纹—雉堞纹”为标志的彩陶文化圈。
约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末期(约3000BC),南亚和中亚的彩陶文化分别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大锯齿纹—雉堞纹”彩陶文化圈迅速瓦解。南亚奎达文化脱离了纳马兹加文化的束缚,转而融入进当地的哈拉帕文化当中,故锯齿纹的流行戛然而止了;中亚则继续发展出纳马兹加文化三期(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和四期,彩陶锯齿纹的表现形式又在折线式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出“十字交叉式”结构(图16—7至图16—9),加之锯齿纹体积的缩小,这才导致其纹饰特征近似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锯齿纹彩陶。纳马兹加文化四期以后,锯齿纹进一步退化(图16—10),青铜时代则随着彩陶的衰弱而消失。
既然中亚、南亚和我国西北地区都曾广泛且长时间流行过锯齿纹彩陶,那么锯齿纹是否能够说明三地之间存在文化互动关系呢?笔者认为,南亚和中亚地区一定存在文化互动关系,但与我国西北地区发生文化互动的可能性较小,只是不能完全排除。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与彩陶垂幛纹情况类似,纹饰形式上的差异性远胜于相似性。诚然三地都流行过锯齿纹彩陶,但南亚与中亚地区之间似互通有无,或曾属于同一文化圈。我国西北地区锯齿纹彩陶主要是与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的锯齿纹彩陶存在相似之处:一是纹饰结构相似,即都出现了“十字交叉式”结构;二是锯齿纹都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趋势。然而,锯齿纹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因为这种相似性仅留于纹饰的表现形式,而非艺术风格本身。其实,最大的区别不再于锯齿纹,而在于雉堞纹,我国西北地区彩陶纹饰从未见已经符号化了的雉堞纹;
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相似纹饰结构的锯齿纹彩陶时间上互不对应,存在“错时同构”的情况。一方面,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出现“十字交叉式”锯齿纹彩陶的时间要早于吉奥克修尔类型早段,此时中亚和南亚地区才开始出现梯状纹;另一方面,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流行“十字交叉式”锯齿纹彩陶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3000年左右,而同时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仅偶见锯齿纹彩陶。当我国西北地区再一次出现“十字交叉式”锯齿纹彩陶时已是半山—马厂类型(约2650BC—2050BC)时期,与之对应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早已不见彩陶。
第三,从空间上维度上看,以“雉堞纹”为标志的锯齿纹彩陶曾靠近过我国南疆地区,只是当前的考古发现缺少新疆这个重要的地理缺环。正如韩建业所言,吉奥克修尔类型早段流行的“大锯齿纹—雉堞纹”彩陶曾在靠近我国南疆地区的撒拉兹姆(Sarazm)遗址中出现过(图16—5),与塔里木盆地仅一山之隔。 遗憾的是,锯齿纹彩陶似乎没有进疆。倘若要填补缺环,势必要加强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柴达木盆地的考古挖掘工作。
图16 中亚和南亚地区锯齿纹彩陶分布图
1.梯状纹陶片(苏尔·丹布遗址出土);2.梯状纹陶片(阿尔丁特佩早期出土);3.阿姆里类型锯齿纹罐(沙赫里索克塔遗址出土);4.奎达文化雉堞纹罐(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5.锯齿纹陶片(撒拉兹姆遗址出土);6.折线锯齿纹罐(蒙迪加克遗址出土);7.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锯齿纹罐(乌鲁德佩(Ulug-Depe)出土);8、9.十字交叉式锯齿纹钵(阿尔丁特佩出土);10.折线小锯齿纹钵(阿尔丁特佩出土)
(二)从具象纹饰看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交流互动的可能性
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曾说:“有关几何母题在全世界若干不同地方自发生成的表述,既不能明确地得以证实,也不能明确的遭到反驳……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几何风格是从单一地方传播开来的观点。”的确,彩陶几何纹饰很难说明南亚和我国西北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互动的关系。在此,我们以花瓣纹和舞蹈纹为例,从具象纹饰进一步讨论两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可能性。
1.花瓣纹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爱花,我国仰韶文化先民就对“花”情有独钟。他们以陶器为载体,创造出庞大的花纹体系,其中尤以花瓣纹最具代表性(图17—2)。关于仰韶文化彩陶花瓣纹的源头问题,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即花瓣纹由半坡类型时期的“鱼纹”一步步演化而来。(图17—1、图17—3)。纵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彩陶文化,唯独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出现过与仰韶文化类似的由黑色弧边三角阴绘而成的四方连续式花瓣纹(图17—5、17—6)。从拉维阶段到科特·迪吉阶段,再到成熟哈拉帕阶段,哈拉帕文化先民始终保持着对花的热爱。
西方学者也曾探讨过哈拉帕文化彩陶花瓣纹的源头问题,只是一直未有明晰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哈拉帕文化与阿姆里—纳尔文化联系紧密, 哈拉帕文化很多彩陶纹饰都继承自阿姆里—纳尔文化彩陶,如菩提树(叶)、公牛、大角山羊、“M”形纹等。虽然阿姆里—纳尔文化也发现有花瓣纹彩陶的踪迹(图17—4),但是绘制风格明显不同。例如纳尔文化的彩陶花瓣纹并非由黑彩弧边三角阴绘而成,而是用线条直接描绘,甚至还内填红彩,可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姆里—纳尔文化的彩陶花瓣纹又源于何处呢?西方考古学者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俄国美学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对19世纪仍存世的原始狩猎部落,即布须曼人(Bushmen)和澳洲土人(Aboriginal Australians)做过调查,指出他们从不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他赞成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anst Grosse)的观点,认为原始狩猎部落从自然界获取的题材完全是动物和人的形态,他们挑选的正是那些对他们有最大实际趣味的现象。意思是说,狩猎部落只对动物感兴趣,在农业生产到来之前,植物完全没有地位。因此,普氏最终做出结论:“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的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 普氏的观点十分契合我国仰韶文化的实际情况,即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仰韶先民从半坡类型时期对“鱼”的偏爱 ,逐步转变为庙底沟类型时期对“花”的钟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南亚彩陶花瓣纹的出现十分直接,并不存在从动物纹演变为植物纹的过程,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前哈拉帕阶段出现的黑色弧边三角花瓣纹是否受到了来自东方文化审美因素的影响?这就必须从一处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即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遗址谈起。
图17 仰韶文化与哈拉帕文化彩陶花瓣纹对比
1.半坡类型抽象鱼纹盆(陕西西安鱼化寨遗址出土);2.庙底沟类型典型花瓣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3.仰韶文化彩陶鱼身纹分解、复合演变推测图(采自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第154页);4.纳尔文化花瓣纹盆(苏尔·丹布遗址出土);5.哈拉帕文化花瓣纹罐(查胡达罗(chanhu-daro )遗址出土);6.哈拉帕文化花瓣纹样式(笔者自行整理)
布尔扎霍姆遗址之所以被认为是连接印度河流域与我国西北地区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它含有太多东方文化的因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布尔扎霍姆遗址出土了一件50岁左右男性的头盖骨,根据体质人类学判断,属于蒙古人种 。除此之外,布尔扎霍姆先民早期房屋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这种建筑形式仅见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基本承袭了我国仰韶—龙山文化先民的建筑传统。再加上布尔扎霍姆遗址出土的双孔石刀和长体斧、锛、凿等器物清楚地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存在接触。 布尔扎霍姆遗址虽少见彩陶,但一期乙段出土素陶却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卡若文化陶器相似,而卡若文化本身就与我国黄河上游更早期的陶器文化存在联系。 霍巍则进一步指出,卡若遗址所在的昌都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从昌都发出,一路向西沿着雅鲁藏布江上行到达西藏阿里地区后,可由日土进入克什米尔境内。原始先民可能在几千年前就踩出了一条连通克什米尔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羊肠小道。
以上这些考古证据表明,东方人种曾长距离西迁至克什米尔地区。笔者认为,如果要证实前哈拉帕阶段黑色弧边三角花瓣纹的出现受到了东方文化审美因素的影响至少需满足三大基本条件:一是布尔扎霍姆遗址所处年代需与拉维阶段大致同期;二是布尔扎霍姆先民与南亚地区先民要有互动的证据;三是布尔扎霍姆与拉维阶段遗址均出土花瓣纹彩陶。首先,在时间上,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即新石器文化遗存有三个文化层,分别是一期甲段(3000BC—2850BC)、一期乙段(2850BC—2550BC)和一期丙段(2550BC—1700BC)。 这就意味着,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甲段大致与拉维阶段同期或稍晚;其次,从出土器物来看,两地交流与互动的痕迹客观存在,上文所述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丙段出土的一件与科特·迪吉阶段同类型的牛头纹陶罐就是最好的实证(图10—9),足以说明两地之间有过直接性交流;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条,但遗憾的是当前的考古发现尚未在布尔扎霍姆及其周边遗址中发现花瓣纹彩陶。
以上三大基本条件虽然仅满足两条,但我们仍不能排除东方审美下的花瓣纹传统西传至印度河流域的可能性。因为布尔扎霍姆先民直到一期乙段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制陶传统。从一期甲段到一期乙段,近五百年的时间也足够让布尔扎霍姆先民与前哈拉帕阶段的先民发生文化互动,并将自己的审美观传递出去。
2.舞蹈纹
舞蹈纹是彩陶上为数不多描绘人类具体活动的纹样,在欧亚大陆多个彩陶文化中都有出现。在我国,彩陶舞蹈纹仅见于西北大地,抑或更准确的说,彩陶舞蹈纹仅流行于马家窑文化时期。马家窑文化出土过多件舞蹈纹彩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舞蹈纹彩陶盆,以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一件最具代表性(图18—1)。笔者通过整理发现,马家窑文化当前至少存世有6件同类型的舞蹈纹盆(图18—1至图18—6),只是有的流失于日本东京,有的则在私人藏家手中,很少有清晰的图像流出。不过根据彩陶纹饰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判断,这6件舞蹈纹盆应该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即出自马家窑文化石岭下至马家窑类型时期。这些舞者被安排在陶盆的内壁,他们或五人一组,或十人一排,手拉着手跳圈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舞者形象基本延续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的人物纹造像传统(图18—10),即圆脸,不见五官,身体细长甚至有些许溜肩,戴或不戴头饰和尾饰,舞姿单一且体态轻盈,围绕着陶盆中心旋转而舞。
除此之外,马家窑文化出还出土有其他类型的舞蹈纹彩陶,只是过往很少被人提及。兰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马家窑类型时期的长羽舞蹈纹壶(图18—7),壶肩外壁绘九位舞者,有学者认为这些舞者穿着长羽毛类的服饰,跳着模仿鸟类动作的舞蹈。 与拉手式舞者形象不同,这些舞者形象表现的更为抽象,不见头部和身体。在笔者看来,他们有可能是在做甩发一类的动作,因为“甩发舞”在欧亚大陆其他彩陶文化中极为常见。马家窑类型之后,舞蹈纹彩陶则渐少,不过在近六百年后马厂类型时期(约2350BC—2050BC)的永昌鸳鸯池墓地出土了一件意义非凡的舞蹈纹双耳罐(图18-8)。一方面,它是河西走廊上地理位置最偏西的拉手圈舞式彩陶;另一方面,经过时间的洗礼,舞者的造型特征已不同从前,即舞者的躯干结构由原先的“细长溜肩式”( )转变为“对顶三角式”( )。对顶三角式结构的出现意义重大,有学者认为它是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史前纹饰体系中的基础图像元素,西亚、中亚、南亚和我国新疆地区的彩陶和岩画上均发现有对顶三角式躯干结构的人物纹或动物纹。 马家窑文化之后,拉手圈舞式彩陶虽然消失,但对顶三角式躯干结构的人物纹得以保留,如陇西安家门村出土的一件辛店文化(约前1400BC—前800BC)人物双钩纹罐,其上人物躯干结构仍为对顶三角式(图18—9)。
图18 我国西北地区人物纹(舞蹈纹)彩陶分布图
1—6.人物舞蹈纹盆(1—4.分别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青海同德宗日、甘肃武威磨咀子、(传)甘肃会宁牛门洞遗址,5.流失于日本东京,6.为私人收藏,出土地不详);7.长羽舞蹈纹壶(兰州市博物馆藏);8.人物舞蹈纹双耳罐(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出土);9.人物双钩纹双耳罐(甘肃陇西安家门村出土);10.人物纹盆(陕西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相比于彩陶花瓣纹起源的不确定性,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舞蹈纹的出现有着明确的源头,即由西亚两河流域一路向东传播而来。两河流域的萨马拉文化(Samarra Culture:约5600BC—5000BC) 与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约5500BC—4500BC) 是欧亚大陆上最早出现舞蹈纹彩陶的两支文化,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具象和抽象舞蹈纹的分化。其中,具象舞蹈纹的描绘较为夸张,或突出舞者甩发的动作,或突出舞者的五官特征(图19—1至图19—4);抽象舞蹈纹则首次出现了拉手式圈舞,并逐渐用对顶三角式结构来表现舞者躯干(图19—5至图19—9)。
图19 两河流域舞蹈纹彩陶分布
1.长发人物纹陶片 [哈鲁拉丘(Tell Haluna)出土];2.长发人物舞蹈纹陶片 [萨比·阿卜耶德丘(Tell Sabi Abyad)出土];3.束发人物舞蹈纹陶片(哈拉夫丘出土);4.甩发舞女与蝎纹盘(柏林博物馆藏);5.甩发舞女陶片(伊拉克境内出土);6.对顶三角式人物舞蹈纹陶片(哈拉夫丘出土);7.抽象人物舞蹈纹盘(哈拉夫丘出土);8.半具象半抽象对顶三角结构人物舞蹈纹(出土地不详);9.抽象人物舞蹈纹(出土地不详)
继西亚两河流域之后,伊朗地区也开始出现舞蹈纹彩陶。代表性的彩陶文化或遗址包括里海沿岸的切什梅阿里遗址(Tepe Cheshmeh Ali),卡尚地区(Kashan)的锡亚尔克文化(Sialk Culture,约4500BC—2500BC)(图20—1至图20—4),以及西部山区与低地的扎里丘(Tall-i Jari)、巴昆丘(Tall-i Bakun)、奇加萨布兹遗址(Chigha Sabz)、克哈兹尼遗址(Khazineh)等(图20—5至图20—9)。各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舞蹈纹形象虽略有差异,但舞者躯干则继续发展了对顶三角式结构。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以巴昆遗址为代表伊朗西南山部片区还实现了对舞蹈纹的变形,纹饰结构朝着方块化的方向发展了(图20—7),甚至还出现了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相似的“蛙神纹”(图20—6、图20—10)。应该来说,彩陶舞蹈纹从西亚到伊朗高原演化出各式各样的形态,并直接影响了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舞蹈纹的出现。
图20 伊朗地区舞蹈纹彩陶分布
1.束发舞女陶片(切什梅阿里遗址出土);2—4.人物纹或舞蹈纹陶片(锡亚尔克遗址三期出土);5.弯腰搭肩人物舞蹈纹盘(扎里丘出土);6.蛙神纹陶片(巴昆遗址出土);7.蹲踞状人物舞蹈纹碗(巴昆遗址出土);8.锯齿纹与人物舞蹈纹碗(奇加萨布兹遗址出土);9.人物堆叠舞蹈纹陶片(克哈兹尼遗址出土);10.蛙纹陶片(叶海亚遗址出土)
印度河流域的舞蹈纹彩陶大多数出现在奎达片区的文化当中,如托高文化A段(梅尔伽赫Ⅲ期C段)、安吉拉遗址Ⅲ期、纳尔文化Ⅰ期等(图21—1至图21—4)。以色列学者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认为,舞蹈纹从伊朗向东扩散,最东部就是到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 其实,舞蹈纹彩陶还深入到了印度腹地,我们不仅在梅尔伽赫东北方向的哈拉帕文化H墓地(约1900BC—1300BC)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片(图21—5),更在印度内陆马尔瓦文化(Malwa Culture,约1900BC—1300BC) 的纳格达(Nagda)遗址中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片(图21—6),只是时间相对较晚。与伊朗与西亚地区的彩陶舞蹈纹相比,笔者认为南亚地区的彩陶舞蹈纹有三大变化:第一,彩陶舞蹈纹的数量开始变少,仅个别遗址见单件舞蹈纹彩陶碎片;第二,舞蹈种类变得单调,仅见拉手式圈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哈拉帕文化及以后,舞者躯干开始摆脱对顶三角式结构,变得圆润化和纤细化。
图21 南亚地区舞蹈纹彩陶分布
1.对顶三角式人物舞蹈纹陶片(托高文化A 段/梅尔伽赫ⅢC段出土);2.对顶三角式人物舞蹈纹陶片(安吉拉遗址三期出土);3.人物舞蹈纹陶片(苏尔·丹布/纳尔一期出土);4.(疑似)人物舞蹈纹陶片(蒙迪加克遗址出土);5.人物舞蹈纹陶片(哈拉帕H墓地出土);6.抽象人物舞蹈纹陶片(马尔瓦文化纳格达一期出土)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即我国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舞者躯干逐渐发展出对顶三角式结构,而南亚哈拉帕文化及以后彩陶上的舞者身躯则呈现出纤细化的趋势,直至用“竖线条”来表示。这种文化现象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不过舞蹈纹与其他彩陶纹饰不同,因为它涉及到人类舞蹈的起源问题。学界曾提出过多种假说来解释人类舞蹈的起源,代表性的假说包括本能说、模仿说、巫术说、宗教说和象征符号说等。这些假说虽各有其理,但出发点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建立在人性需求的基础之上,是生产力低下年代史前先民的共通选择,因而舞蹈具有全球性。笔者认为,即使这些假说对文化传播论造成一定程度地冲击,但都不足以解释两地彩陶舞蹈纹人物造型发生转向的问题,彩陶舞蹈纹双向传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从时间维度上看,彩陶舞蹈纹一路向东传播的时间线一环扣一环。西亚两河流域的萨马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时期是彩陶舞蹈纹的奠基期,彩陶舞蹈纹的基本特征,如剪影式表现形式、拉手式圈舞形态和对顶三角式躯干结构等都是在这两个文化时期形成的。彩陶舞蹈纹大约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早期来到靠近两河流域的伊朗西南地区,如扎里丘、盖普丘(Tall-i Gap)等,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晚期(约4500BC—4000BC)则遍及整个伊朗高原,并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早期到达印度河流域。梅尔伽赫Ⅲ期C段(约3600BC—3500BC)出土的舞蹈纹陶片应为南亚次大陆上最早的一件,此后,彩陶舞蹈纹在纳尔文化和奎达文化时期得以延续,舞者对顶三角式躯干结构已完全程式化。虽然约瑟夫·加芬克尔的研究只论及梅尔伽赫,但实际上我国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时期(约3300BC—2850BC)基本与奎达文化同期,这就意味着理论上彩陶舞蹈纹存在继续向东传播的可能性。
从空间维度上看,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文化互动的痕迹客观存在,只是新疆和西藏两地存在彩陶舞蹈纹的缺环。上文中我们谈及了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遗址与西藏昌都卡若文化之间的联系,而后来韩建业所述卡若文化又与早期黄河流域陶器文化存在着的联系,实际上指的就是与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存在诸多相似性特征。例如,在陶器方面,卡若文化早期的高领罐和敞口盆与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态较为接近,还同样流行假圈足,彩陶图案出现类似的折线纹、网格纹和附加堆纹等 ,更重要的是宗日遗址恰好就出土过一件舞蹈纹盆。在陶器之外,两者还出土有形制相似的骨牌饰,而宗日遗址、卡若遗址和布尔扎霍姆遗址三地更是都出现了同类型的珠子和项饰,汤惠生认为其源头完全可以追溯到南亚地区,由泛喜马拉雅廊道传播而来。 这样以来,三地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
若我们将视线扩展至器物以外,其他考古发现也表明南亚与我国西北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互动的迹象,如新疆与河西地区的岩画上刻画有对顶三角式躯干结构的人物形象,艺术载体上弥补了彩陶的缺失,但由于岩画的年代难以测定,故暂不清楚其时间的早晚。同时,我们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源自西亚地区的碳化小麦和大麦,更发现数枚被证实原产于印度洋的子安贝。 相反,南亚次大陆最早的水稻种植出现在印度中部的温迪亚山脉(Vindhya Range),而非印度河流域,源自中国的亚洲稻有可能最早通过泛喜马拉雅廊道来到南亚次大陆。
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舞蹈纹彩陶虽然存在地理缺环,但陶器终究不过是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之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舞者的躯干结构,若舞蹈纹继续向东传播至我国西北地区,原则上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彩陶舞蹈纹应该也会出现对顶三角式的躯干结构,可实际情况却是晚至马厂类型时期才出现。对于这种文化现象,文化变迁理论似乎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当一种文化物质或文化丛仅仅在观念上被借取,而缺乏实际内容,这时接受者的文化会依据这种观念发展其实际内容。 因此,基于该理论说辞,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马家窑文化早期只接受到舞蹈背后所藏观念的影响,属于间接性接触,故舞者的造型开始时仍保持着东方式的审美传统。后来,舞者的造型则直接受到影响,故躯干转变为对顶三角式结构。相反的,东方造型的舞者形象也可通过“西藏—喜马拉雅”通道来到南亚次大陆,并最终导致后哈拉帕时代舞者的造型发生审美转向。
结语
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在史前时代应该还存在着一条“彩陶之路” ,只是史前时代的文化互动关系很难考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字尚未诞生,故我们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弥补不能言说的缺憾。碍于现实情况的条件限制,当前的图像学研究也只能结合现有考古发现提出中西彩陶文化交流互动可能性,不过好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大多都承认在汉代“丝绸之路”凿穿之前,中西方文化在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和思想等诸方面都存在着交流。 本文通过梳理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文化发展序列,在对比与论证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如下认识:第一,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的诞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传统与特点;第二,南亚印度河流域彩陶文化与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彩陶纹饰互通互融;第三,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成长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创造出属于东方世界的史前彩陶艺术体系;第四,中西彩陶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潜移默化之间,可能并非为直接性交流,而是以“中间站”的形式缓慢推进逐步实现的,故中国彩陶文化的发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第五,我国新疆与西藏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就属于中华文化圈的范畴,这两个地区既为中国彩陶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屏障,阻绝了大部分外来彩陶文化的强势东进,又为中西彩陶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通道。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5年春之卷(总第33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