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6 00:22
1957年,在郭沫若和吴晗的坚持下,万历皇帝的定陵被打开。
谁能想到,那道石门一推开,等来的不是满堂喝彩,而是一连串心慌。人啊,总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真到临头才发现袖子空空。后来每次提起这事,吴晗的眉眼,大概都要沉一下。
其实,故事要往前倒一点。1955年秋天,几位学界大佬把一份长长的请示摆到了总理桌上,说白了,就是想动明十三陵里最“轴”的那座——朱棣的长陵。那阵子大家的心情像打了鸡血,谁不想“直捣黄龙”,翻出一手材料,把书里那些靠传抄的段子,换成墓砖上的真东西。
偏偏有人泼凉水。郑振铎和夏鼐从办公室一路急走到吴晗家,开门见山就劝:现在的技术,真不够用。这种庞然大物,一旦撬开,后面接着的是保存、修复、记录、管理,一环扣一环,没有一步是轻松的。说到后来,郑振铎都有些上火,茶水都凉了,还是不肯放软。
吴晗的脾气大家都知道,骨子里有股硬劲。他说,我们不缺人,先生有先生的本事,学生也蹦跶出来了,国家都搞起来了,怎么还不敢动几块石头?站在他的位置上看,是有道理的——研究明史的人,能碰到完整皇陵,是一场天大的机缘,谁想错过。
夏鼐就出来劝和。他不是不懂考古的甜头,只是知道全国还在大建设,今天这边修路,明天那边要水电,人手像被拔河一样两头拉。他说话不硬,意思却笃定:别只从书房里看问题,得看看整个盘子怎么转。
争到最后,事还是成了。批文下来了,长陵准备开场。1956年春,吴晗拿着红头文件找到郑振铎,笑里有股子得意,也有点把重担又推回去的味道:你当初不同意,现在批了,还得你来主持啊。郑振铎接过纸,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石。反对归反对,事既然开了,他也只有咬牙把自己这口锅背好。
长陵不好开。那是一座沉睡的山,转来转去找入口,像是在摸一头老牛的鼻子,摸了半天,连牛影都没见着。郑振铎最后只好松口:先从小一点的试刀。也巧,定陵那边传来消息,说围墙一处裂缝里露出了条石,有点像墓道。于是整个队伍一转向,目标锁在了万历皇帝。
从动土到倒扣最后一层砖,整整折腾了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为稳妥,他们把摄影师请来了,架着笨重的相机,跟着每一步挪动。胶片一卷一卷地装,心也一阵一阵地提。你说那时的人,不紧张?紧张。民间故事里讲的“机关暗器”,谁不怕。但翻开石门那一刻,黑洞洞的甬道里安静得出奇,没有飞箭,也没有暗井,倒是从地底慢慢飘上来一股老土味。
问题是,空气。几百年没见过风的丝绸、画轴,一旦见了阳光,就像被人突然掀开棉被,身子打了个冷战。黑色顺着纤维蔓延,像谁在布面上泼了一碗墨。那年冬天,站在墓室里的人,目睹了“时间”和“氧气”如何联手,把轻柔的东西变成脆屑。有人试图把一片龙袍挪进箱子,只不过一抖,边角就化成小黑末,飘到手背上,不敢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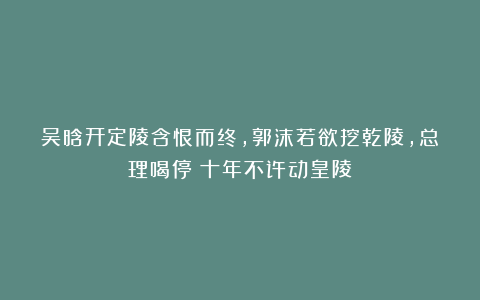
这万事都需要手,把东西一个个搬出去,先堆在地面的小瓦房里。小瓦房,说好听点是临时库房,说直白点,就是几间不透风不隔潮的屋子。三千多件出土物,在那里挤作一团。夏天闷到墙皮出汗,冬天冷得玻璃起霜,丝绸像烘干的荷叶,轻轻一碰,碎成鱼鳞片。那几年风向变得很快,很多参与一线的人突然被调离、下放,桌上的记录本停在半页,铅笔夹在纸缝里,就那么静静躺着,没人翻。
更重的事还在后头。万历和皇后的棺木被抬出,骨骸被摆进烈日和口号里。那场景,我不知道谁能描述得恰当。有人在怒喊,有人在拍手,有人把柴点着,火噼里啪啦地钻上来。三具骨,最后化作一滩灰,随风走了。你说“保皇派”的纸帽子能扣到几百年后的死人身上?荒诞到可笑,但它真实发生过。
吴晗的命运,从某个节点开始,和定陵的那些遗物一样,变脆。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在开一扇通往历史的门,后来才发现,门后不止有文本,还有风暴。他至死都没能好好读完那批一手材料。想来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会想问自己:换一个时间,会不会更好?这不是后人替他下结论,只是人在困局里自然冒出的念头。
定陵的教训并不立马被当回事儿。很多地方还燃着一股热,想掘汉陵,动唐陵,清陵也跃跃欲试。谁都觉得自己能把活儿干漂亮,没顾上问一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郑振铎和夏鼐坐不住了。上一次劝没劝住,酿成这场不忍细看的局面,他们不敢再看着风越刮越大。于是往上递,直说——不能再这么动。
上面很快拍板。该停的停,该收的收。像是有人把手从旋钮上拿下来,屋里终于安静了一些。事情到了1965年,郭沫若又提起乾陵,说想看看武则天的地下世界。周总理这回干脆回绝,大意是这十年,不动帝王陵。简短的一句,后来成了行当里的“红线”。
时间兜了个大圈子。那些堆在小瓦房的物件,等到正式的发掘报告问世,已经是1990年。换算一下,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年轻人都不在,有些细节只剩下含糊的讲法。这段空白,是实打实的损失。研究本该紧紧相扣,有了断口,后面的绳子就系得不那么牢。
后来的日子,情况总算好一点。为了给那些物件一个像样的家,2012年,地下建起恒温恒湿的大库房。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小床”,透明的箱子套着,规矩得很。别小看从地上搬到地下这段路,九个月,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拧,一层一层地往下移。这才是真正的“与时间赛跑”。何况我们吃过亏,谁还敢拿原物到处奔波?外展用复刻。万历的皇冠,皇后的凤冠、凤袍,你在各地展厅里看到的那件件华美,大多是高手按照原样做出来的。这样既能让人感受工艺之美,又不会让老东西在路上遭殃——说句闲话,那回古剑出国“生病”,到现在还让行内人心里一紧。
如今再回头看定陵这一段,心里是很复杂的。一边是学问的渴望——谁不想直面历史?一边是技术、制度、气候、时代的千条万缕。人总有一种少年感的急躁,以为踹一脚就能把门踹开,里面就亮堂堂地等着自己。可门后是暗渠,是湿气,是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是被耽误的报告,是忽然就上了火的柴。
当然,事情也在往好的方向动。非遗的手艺被看见了,考古的规范越来越细,文保的设备越来越不吝成本。我们开始懂得“有些门可以等”,不是不去,是要准备到位再去。人到中年,才学会慢一点,这道理放在学问上,也一样。
我一直在想,如果1957年那次没开,是不是六十年后,或者再往后一点,等我们把“怎么开、怎么保、怎么管”都练熟了,再开,结局会不一样?这问题不会有标准答案。历史不肯倒退,遗憾也不会原路返回。我们能做的,大概是把那次的错、那种急,把它们留在记忆里,当作绳上的死结,提醒后来的人,打结要打在合适的位置上。至于那些在地底沉睡的王朝、那些柔软的衣物、那些已经化成灰的骨头——它们也许并不需要我们立刻去惊扰。等吧,等我们真的拿得稳了再去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