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18.2025
▽
▽
刚看完《浪浪山的小妖怪》的时候,我用石塑黏土捏了大结局出现的石像。由于特别喜欢“浪浪山”这个题材,于是捏的时候心里也特别雀跃。我对着图片一点点琢磨。那几日,我所有的空闲都耗在这事上。指尖感受着黏土的细腻变化,看着那小妖怪的轮廓从无到有,眉眼渐渐清晰,心里有种奇异的平静。完工那刻,我将它们放在窗台,午后的阳光斜斜照在石像微仰的脸上,仿佛真能望见山外的天空。我拍了张照片,满心欢喜地发给挚友。
朋友很快回复:“手真巧!细节处理得好生动。”
屏幕这头的我,嘴角不自觉上扬。然而紧接着,下一条消息跳出来:“你可以做一个系列啊,把这些受欢迎的角色都捏出来。放到网上去卖,肯定有人喜欢。”
卖出去?我盯着那行字,先前盘踞心头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创作喜悦,像退潮般倏忽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盘算:哪些角色会更受欢迎?定价多少合适?包装和邮寄会不会很麻烦?我的“手艺”,真的能转换为“利益”么?
那天之后,我的确想了很多“赚钱”的方式,我质疑为什么自己坚持了很久的写作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我懊恼自己的“才艺”没有换取利益……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重读《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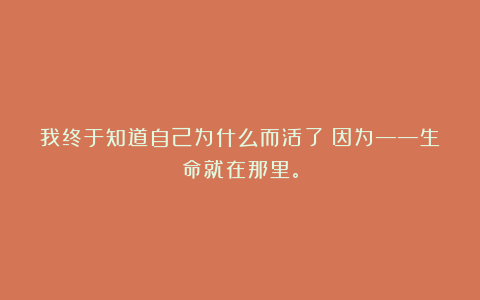
那是一部何等波澜壮阔的史诗,权力、谋略、战争、治世,无数英雄豪杰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争的是不世之功,求的是青史留名。可当全书即将落幕时,作者竟笔锋一转,抛开了所有这些宏大的叙事,用最后的篇幅,去讲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徐霞客。
这个没有功名的书生,没有去追求那些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他只是听从内心的呼唤,用一生的时间行走在路上,看山、看水、记录风物。他什么也没有建立,什么也没有改变,他的游记在当时看来,于国于民似乎并无大用。然而,作者在书的最后写道:“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这句话,像一道光,毫无预兆地劈开了我心中那片被功利笼罩的迷雾。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目光不自觉地落到窗台上那个落了些灰的浪浪山小妖怪石像上。
徐霞客的“成功”,在于他行走的本身,在于他体验了、感受了、投入了。他的人生价值,由他每一步坚实的脚印所定义,而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勋章来加冕。那么,我捏那个小妖怪时的快乐,不也正在于那个“捏”的过程本身么?在于指尖与黏土触碰时的专注,在于心无旁骛创造一个小世界时的宁静。那份快乐,是完整的,自足的。它本不需要“卖出好价钱”来赋予其意义。
朋友的建议自然是出于好心,是在用这个时代通行的价值标尺来肯定我的劳动。可一旦将那份初始的、纯粹的欢喜,迅速捆绑上“变现”的期待,乐趣本身便被异化了。它从一种自由的表达,变成了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从一种心灵的休憩,变成了一种绩效的考核。其实浪浪山这部电影本身也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当个体的成就无法被社会认可,社会也无法给个体提供普遍意义时,按照心里的声音去活,就成了最好的方式。
最近在读星野道夫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他写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棕熊开始感兴趣”时,何曾想过这兴趣能带来什么利益?他只是单纯地被那种强大的生命所吸引,最终将全部的热情与生命都献给了那片冰原。他的选择,源于生命内在的驱动,而非外在的计量。
我轻轻拂去小妖怪石像上的灰尘。它依然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神望着远方。我忽然理解了它那份怅惘与希望交织的神情——那是对“山那边”的纯粹向往,不是为了攫取什么,仅仅是为了“看见”。
我再次坐回桌前,掰下一块新的黏土。这一次,我不再去想它未来会成为什么“产品”,不再考虑它的市场前景。我只是感受着黏土在掌心的湿润与柔软,听从手指的意愿,让它慢慢形成一个也许只有我自己才懂的形状。那份久违的、专注于创造本身的平静与喜悦,又一点点地,回到了我的心里。
人生的丰盈,或许正在于这些“无用”之事。它们像散落在时间河流里的珍珠,不为了串成一条可供展示的项链,其本身温润的光泽,便已照亮了我们平凡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