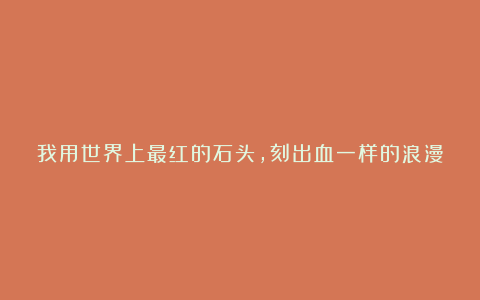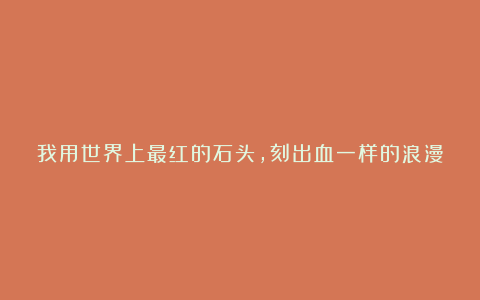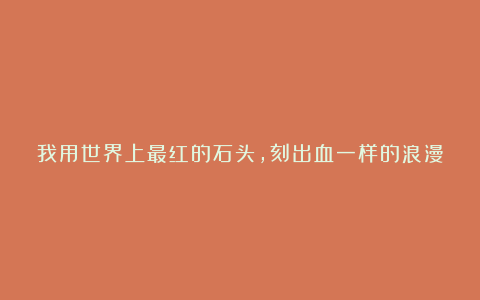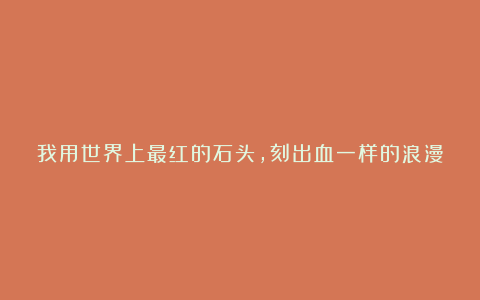
我用世界上最红的石头,刻出血一样的浪漫;也用最娇艳的玉,描摹心中的难抑的沸腾。
当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工作台时,我是最专注的匠人,每一道纹路都凝结着对完美的偏执;
当暮色笼罩长街,我又化身最风流的情种,衣袂翻飞间既不负佛陀的慈悲,亦不负佳人的缱绻。
我痴迷南红玛瑙那抹摄人心魄的绛色,就像迷恋美人颊边醉人的酡红。
它娇贵得如同深闺少女,稍不留神便会绽开细密的冰裂纹,甚至碎掉成渣,
可我宁愿守着它破碎的尊严,也绝不施以注胶的虚饰——即便最终只能磨成一枚孤品戒面,也要让它带着与生俱来的傲骨。
这赤玉啊,是大地血脉凝结的瑰宝,从鸽血红到柿子黄,层层叠叠的绛色里藏着万千气象。
再精妙的浮雕也刻不尽它云霞般的纹理,再灵动的俏色雕也难现其魂魄,唯有以心为镜,方能在流转的光影中窥见它未诉的传奇。
深夜的作坊里,钨丝灯在南红原石上投下蜂蜜色的光晕。
我握着金刚砂磨头的手突然一顿——石心处那缕火焰纹正随着角度变换舒展蜷缩,宛如敦煌壁画里飞天的飘带。
这分明是大地在亿万年沉寂中,为有缘人预留的一封朱砂情书。
当刻刀游走时,我常想起苏州评弹里那句”玲珑骰子安红豆”。
南红最动人的不是无瑕,而是那些天然形成的朱砂点,像美人眼角将落未落的泪痣。
他们不懂每块玉料都在用纹理低语:荔枝冻的莹润是西子湖畔的晨雾,冰飘料的嫣红是雪地里冻僵的胭脂。
尤其是那些包浆老料,表皮灰褐如僧衣,剖开后却现出满堂红——原来最炽烈的魂魄,往往藏在最沉默的皮壳之下。
突然明白祖师爷为什么说”玉雕到极致要能呼吸”,这哪是在琢玉,分明是帮沉睡的石头,把亿万年的月光咳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