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被“古希腊”教洗脑的
(下)
(一)地理移植术:“古希腊教”被如此编织
(二)身份重构术:为什么“古希腊”的先哲们多来自亚洲,而不是欧洲的希腊本土?
(三)调包术:被劫持的“欧罗巴”公主、“金发碧眼”的耶稣、特洛伊木马
(四)痴人说梦:“希腊文字历史最悠久”、“所有语言中最有效”
(五)黑白颠倒术:“中国人没有自然法概念” 、古希腊“逻辑”/“理性”的“独特优越性”
(六)变色龙的“理性”,催眠师的绝技
(五)黑白颠倒术:“中国人没有自然法概念”、古希腊“逻辑”/“理性”的“独特优越性”
“西方中心主义”用来催眠现代中国人的系列神话之一,是声称中国文化缺失“逻辑”、“理性”、“自然法”等理念。事实是,这些理念不仅在华夏文明中与生俱来,而且都是从华夏文明剥离后,几经西方人的曲解与误读、被扭曲异化完全变形后又被粘贴到“古希腊”身上。
“中国人没有自然法的概念”这个说法不过是在二十世纪才崛起,起先被一些欧美的现代法律学者宣传推广,继而通过对教育及信息流通话语权的垄断而得以在中国传播维持。它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与精神殖民这个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就如同声称“中国发明了火药,但仅知用来制作烟花,而西方则用来制造火器”等诸如此类的历史谎言一样,都首先出自欧美的一些学者、传教士、妖魔化宣传战机器之口后,又继而在中国本土被鹦鹉学舌地复制,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最终由神话化身成事实,并逐渐成为主流正统教育的一部分。
要谈论“古希腊”所谓的“自然法”、“逻辑”与“理性”,就需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等“前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家说起,因为他们为古希腊乃至西方思想史奠定了“自然法”、“逻辑”/“理性”等重要理念基石。
“万物都在变化,无一保持静止……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这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他阐述了长期被古希腊人及后来的西方人感到难以理解并严重误读的对立统一辩证思想,即:万物始终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是在两个不同的对立面之间进行的,而这两个面是对立中有统一的。
“万物归宗”、“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华夏文明的哲学思想精髓。赫拉克利特思想与华夏传统理念如响随声,但对古希腊人乃至后来的西方人来说却不可理喻,难以捉摸。自古及今,他的思想也被严重曲解。就如同西方对华夏文明阴/阳对立统一辩证哲学的误解一样,西方主流学者往往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视为“二元论”,认定他主张事物的“对立性”。
赫拉克利特被视为古希腊“最具独创精神”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说他“最具独创精神”,正是因为他的理念对于古希腊及西方文化来说十分陌生,所以才不被理解,甚至长期在西方遭到曲解和嘲笑。这也很自然,因为赫拉克利特并不是欧洲的希腊人,而是亚洲的米利都人。
赫拉克利特的主要关注是万物的“自然”本质属性,即他所称的“φῠ́σῐς ”。他奠定“自然法”理念基石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这个“φῠ́σῐς ”。
如同华夏文明的阴阳哲学一样,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所谓的“对立”不过是一个整体统一的两个方面,世界万物的不断变化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互相作用而生成的,即华夏文明所说的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转化,但又遵循同一个贯穿万物的法则,即华夏传统理念中的“道”。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它是万物的精髓与本质,万物源自“一”,也回归 “一”,所有的人间法律既被这个统一的法则“一”规范着也必须遵循之。这就是“自然法”的本质含义及其来历,与深受曾在东方文明古国周游拜师的色诺芬尼影响的巴门尼德的著名理念“统一而永恒的一”同出一辙。
他们的这些思想与华夏等东方文明一脉相承,用大家都能懂的通俗汉语概括,“自然法”就是基于“天人合一”宇宙法则的“天道”。
黄帝传授“恒无之初,迥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的奥秘,并透彻而明确地阐述自然法在人间的规范角色:“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虚无(刑)形,其寂冥冥,万物之所从生”(《道法》)
老子讲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对自然法的诠释也简洁深邃:“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并阐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然而这些华夏哲学思想精髓对于严重缺乏抽象思维的古希腊人来说如同天书。赫拉克利特试图向希腊人解释这个万物的“自然本质属性”(φῠ́σῐς ):它不是人用眼睛就可随意看到的,“自然”隐而不显,并向古希腊社会引入了一个新概念来解释这个无形之“道”。这个新概念就是“λόγος”,也有“言语”/“解释”/“理由”等意思。这个新概念就是后来的英文等欧洲语言中普遍翻译成“逻辑”的这个词。
但“λόγος”(“逻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古希腊人懂吗?
如同老子言“道”,赫拉克利特也指出,对这个万物的自然本质属性——即他说的“λόγος”(“逻辑”),大多数人是无知的,尽管万物都遵循它而产生:“有关这个λόγος(逻辑),人们总是不能理解,听到它之前人们不会明白,听了之后仍不会明白。”
的确,对“古希腊”人来说,这完全如同天外来客一般云里雾里:“统一而永恒的一”是什么?“一”怎么会“统一而永恒”?两个对立面又怎么会相互依存并转化,甚至还会有统一?简直是无稽之谈!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也因此长期被“古希腊”人及后来的西方人嘲笑。正如老子有教:“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逻辑”如此,“理性”同样如此。实际上,现代英文中使用“理性”(reason)与“逻辑”(logic)两个不同用词,最初的词源都是这同一个希腊语“λόγος”(“逻辑”)。在现代语言中这两个词之所以被分别使用、独立存在,只是源于在翻译赫拉克利特为释“道”而引入的这个难懂的概念时,许多使用法语和拉丁语的作者及思想家都对希腊文的“λόγος”有多种不同理解和翻译。最早用英语出版作品的著名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人,也使用当时比英语更通用的拉丁语和法语写作,他们都将“逻辑”、“理性”视为具有完全相同意义的可互换词。
换句话说,“逻辑”/“理性”这两个用词,最初被引入希腊社会,不过是赫拉克利特等与巴门尼德等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在试图向古希腊人解释“道”这个万物的“自然本质属性 ”时引入的新概念“λόγος”(“逻辑”),经过历史上一系列哲学思想家的猜测、曲解、误译,后人把这个神秘的“λόγος”翻译成“理性”或“逻辑”,并严重曲解了其本意。
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前苏格拉底”的先哲们在西方历史上多被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格拉底及“后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西方思想史上的巨人自己的误解和曲解。而这些西方思想史上的泰斗,作为西方知识界、思想领域的权威与大诠释家的地位,也确保了一点:他们自己的曲解与误解被叠加到甚至凌驾于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等先哲的真正思想精髓之上。
希腊哲学家的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曾有一段记载,描述“欧里庇得斯有一次向苏格拉底询问对赫拉克利哲学思想的看法。苏格拉底回答道:那些我明白的部分挺好的,我想我不明白的部分也会挺好的。但要彻底理解之,则需要一个能潜到德洛斯河底的潜水员”。苏格拉底是以此来说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如此之深,要彻底明白,就如潜至海底之难。
亚里士多德也因为自己理解不了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辩证哲学思想,曾著名地抱怨说,赫拉克利特的文章“前后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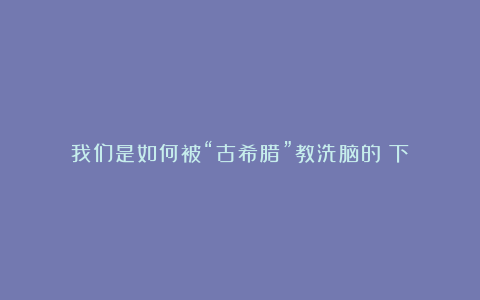
同样,这些西方的思想泰斗们也对巴门尼德的核心思想云里雾里,试图用所谓的逻辑论证甚至语法分析的方法肢解其思想精髓。
亚里士多德曾试图使用“理性/逻辑”的手术刀去解剖切割巴门尼德的“是”与“非” /“无”与“有”,他绞尽脑汁地分析却始终不得其解,最终诉诸语法的单、复数,以一种盛气凌人的权威口气,断然评判自己难以理解的巴门尼德思想是“语法错误”,声称巴门尼德把本应使用复数表达方式的用词用了单数表达方式,才导致人们无法理解。
柏拉图也试图用“逻辑/理性”将巴门尼德的“智慧之路”(道)切割解剖成“是”与“非” /“无”与“有”——柏拉图对这类概念十分迷惑,苦于搞明白,巴门尼德到底在指什么,甚至认定这是巴门尼德本人的错误——把这些概念“杂乱堆放在一起”是多么的 “粗糙而简陋”。(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 :《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Presocraic Philosophers”)
柏拉图被众多西方哲人尊为西方思想史金字塔顶峰的人物,就如哲学家怀特海德曾高度评价的:整个西方的思想史不过是一系列对柏拉图的脚注而已。即使如此,这位泰斗也同样难以逃脱自己所处的文化土壤所带来的思维局限。如果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这些西方思想史上的泰斗人物能明白东方文明对“万物归宗”原则、阴/阳辩证哲学的精髓阐述,就会轻易领悟巴门尼德的思想。包含阴/阳、是/非、有/无同时又超越这二元关系、无处不在又隐而不显、永恒存在又时刻运动的,是不可用语言描述的“道”,或印度传统哲学阐述的“梵门”。
抛除世界文明史的“重构”神话,古希腊人严重缺乏抽象思维,难以理解“无”、“有”、“无穷”、“无极”等这些概念都是什么,古希腊文化基本上没有 “天人合一”、“万物归宗” 这些理念,难以想象一个贯穿宇宙万物的统一自然规律。这一切文化与思维的局限,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古希腊思想家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如此,巴门尼德试图向同人们描述一个博大深邃的生命与自然奥秘,却被奚落成“语法错误”,并被切割成文明幼童们用来堆砌积木的拼图碎片。
如此,苏格拉底十分敬重巴门尼德,称之为“伟大的智者”,却搞不懂他究竟在说什么;毕达哥拉斯的“天人感应”、生死轮回与术数让希腊国人乃至后来的西方人莫名其妙;赫拉克利特被视为西方文明中最具“独创性”却又“最难懂”的哲学家之一;皮浪被误解为“怀疑一切”;亚里士多德对先哲们指手画脚;尼采又称柏拉图的理念太“非希腊化”……
西方文化的思维局限使他们难以想像到,隐藏在看似矛盾的万物表象下,存在着一种贯穿万物的本质属性。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表面的“对立”、“不断变化”层面上,看不到赫拉克利特强调的“变化中的永恒”、“对立中的统一”,也未能真正捕捉到赫拉克利特试图解释的“自然”/“逻辑”之本质:贯穿于宇宙万物的永恒的自然法则——“道”与阴阳的关系。但作为华夏等东方文明的根基,“自然法”在社会生活及个人思维意识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却又隐而不显。也只有在一个像华夏这样的“天人合一”、“万物归宗” 文化土壤里,才会产生真正的“自然法”理念,才会真正地理解这个贯穿于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才会真正将其融入社会及日常生活中。
不可思议的是,在最近一个多世纪西方对人类文明史的大规模重构中,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黑白颠倒,“自然法” ,就如同 “逻辑”、“理性” 、“哲学” 等概念一样,摇身一变,反倒成为“优越先进”的西方专利独有的文明标志。
(六)变色龙的“理性”,催眠师的绝技
“没有一个人是石头;人是动物;因此动物不是石头。我几乎忍不住要尖叫,难道你曾听过有什么人这样争论过吗,你这一群疯子的国度!?”
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发出的一句著名抨击。他抨击的,是几乎处于文化荒漠的中世纪欧洲僵化的经院主义学术及教育体制。当时,在教会牢牢控制的学术教育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占据着核心的垄断地位,但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就如洛伦佐·瓦拉抨击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中荒谬无稽的思维方式、窒息人大脑的学术体制是在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人性。亚里士多德也如此成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抨击与反抗教会经院主义学术的象征符号之一。
对欧洲“人文主义”运动施加了深远影响的伊拉谟斯、十七世纪的著名哲学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甚至培根等人,都对亚里士多德发出了尖利抨击,认为学者的才智“被囚禁在几个作者(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首要独裁者)的牢房中,就如同他们本人被囚禁在僧院与学院的牢房中”、“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是在那里唯一流行的,因而学习研究的,并不是正确的哲学,而是亚里士多德。”
不可思议的是,约十九世纪开始,伴随西方对全球殖民进入一个高潮,曾遭到人文主义者们抨击的“逻辑”、“理性”却摇身一变,成为“古希腊”、欧洲-西方“优越于”东方的一个标志。
更不可思议的是,“理性”,俨然一个变色龙,也在某些宣传认知战大师的手下随心所欲地变身,以适应“西方优越”这个永恒主题的需要。
明朝后期,当基督教的圣战武士——“耶稣会”的利玛窦及其战友们在中国执行“曲线同化”中国的圣战使命时,西方还普遍将中国人作为地球上“最理性”的民族;即使在利玛窦时代的数个世纪后,“启蒙运动”也仍将中国文化奉为“理性哲学”的典范,将孔子尊为理性的圣贤与楷模;但到了十九世纪,伴随西方对全球殖民进入高潮,“西方中心主义”对人类文明史的编织与重构开始盛行于世,东方被妖魔化成了“迷信、非理性的”,是一种“原始文明”、“朴素文化”、“小农经济社会”,华夏文明也被180 度大翻转——被反称为 “非理性的”文化体系、“封闭、专制独裁”的社会。
更荒唐可笑的是,二十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与与社会再次遭遇180度大脑翻筋斗——起于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开始的新一代思想运动。当时在交叉科学、生命科学、基因科学、量子物理学等领域的一些前卫科学家发现,不仅《易》、道家、佛教、印度教等东方文明的智慧体系中蕴藏现代科学最前沿的奥秘,而且在获取知识与信息方面,与“逻辑”、“理性”相比,东方文明强调的“悟”、“直觉灵感”是一种更优越、更有效的途径。于是,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又被指责“太过于理性”。
总之,黑的也是白的,白的也是黑的,只要需要,随时打造形象,不断化身。不变的,是结论:西方是永恒的“先天优越”,中国等东方则是不可救药的“先天落后”。
在对“理性”一词的历史重构、编织剪裁中,许多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事实:撇开“理性”这个用词被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引入古希腊时的本原含义不说,即使按照现代人对它的理解,古希腊、西方社会也并不具备养育“理性”的自然文化土壤。古希腊的本土文化相信的是人与神是对立的,人不具备获取真正知识的能力,只有神才有。在这样一个文化意识中,人的“理性” 究竟会达到一个什么高度?
如此也就不奇怪,西方“理性与启蒙时代”的典范之一牛顿,当他对万有引力的来源难以解释时,会以一句话了事,称这神秘的力量“来自上帝”,因而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探索这个来源;
一个多世纪后,在经受了“理性与启蒙时代” 洗礼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漏洞百出,他本人同样会以一句“令人讨厌的谜团”(an abominable mystery)而把自己难以解释的物种进化论漏洞一堵了事;
二十世纪的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也一直固执地拒绝接受当时已走在物理学发展最前沿的“量子力学”有关“不确定性”等理论,因为他相信 “上帝是不和宇宙玩掷骰子的”。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如何?宇宙“大爆炸”理论是被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引入并长期被作为科普知识,在全球许多课堂上传授。但霍金提出的这个宇宙模式有一个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虚无前提条件:在他假定的“大爆炸”发生之前,发生或存在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超出“科学”研究范畴,所以不予考虑。霍金及其科学家同伴们似乎不屑向“愚痴的”公众解释一个理性的逻辑问题:既然在那之前发生或存在的一切都不是“科学”所能研究的,人又如何得出一个“科学结论”,说在那一个时点之前什么也不存在?即使有什么存在,科学对这一切不也会一无所知吗?!
但这毫不妨碍霍金宣布: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的一切,对他及其科学家同行们的研究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而这一切也不应构成针对宇宙研究的科学模型的一部分。
这同样毫不妨碍宇宙“大爆炸”理论如今依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界定位成板上钉钉的“科学知识”、毫无谬误的“真理”,在课堂里传播。
科学领域如此,社会领域就更不必说了。可让我们窥一斑见全豹的“小事”:美国小布什总统在解释自己为何要下令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曾著名地称,因为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而他在大西洋另一端的同伴——英国首相布莱尔,面对公众斥责他通过谎言把英国带入这场战争时,则称只有上帝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没听到西方学术界或主流媒体对此有什么微词的。
西方版式的“理性”、“逻辑”,究竟有多“优越”?相信读者朋友们远比某些知识权威更有理性与独立的大脑思辨力,完全有能力得出自己的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文人热衷于长篇大论一系列伪命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科学”、“为什么中国没有逻辑、没有理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哲学”、“为什么中国没有自然法”、“没有牛顿”、“没有爱迪生”、“没有爱因斯坦”、“没有诺贝尔奖得主”……。诸如此类问题千变万化却不离其宗:都是处于精神殖民或催眠状态下被喂养的伪命题。
人处于精神奴役或催眠状态下会发生什么?不知大家是否见过这样一个催眠术表演:催眠师向被催眠者手里塞了一只臭气熏天的球鞋,告诉他,那是香甜可口的西瓜。被催眠者于是把那臭鞋捧到嘴边、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吃那“香甜的西瓜”,旁观者则笑得前仰后合。近日拜读一文,不觉想起这催眠术表演一幕。某大V致力于为中国人进行“科普”教育,如此对中国公众进行有关“古希腊”的开悟教化:
“古希腊文明绝无可能是对其他文明的简单抄袭,因为他的文明基因在全球范围是极其独特的”;
“古希腊文明是太过独特的,它有大量在全球范围内完全独有,其他古国都没有的文明基因。我们提到古希腊文明并且看重它的科学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古希腊的陶器、雕刻、葡萄酒、橄榄油、天文、医学等等,而是古希腊创造的数学与逻辑。它是如此地独特,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因不仅非常不同,而且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
“古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起来,必须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文明基因差异太大了”;
“说’古希腊文明是直接抄袭中国古代文明成就’,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猜测与探讨的空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