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的终南山浮着淡雾,云游子用鹿皮擦拭道德经碑。第四十九次描摹 “道可道,非常道” 时,指尖被碑石的裂纹划破,血珠坠在 “常” 字中央,像粒被晨露浸胀的朱砂。
他忽然听见洛阳城的争执。三年前太学的讲经会上,白发博士念尹喜手札 “道在瓦甓”,穿紫袍的学士将竹简掷在地上:“道若藏在砖瓦里,为何孔圣人要韦编三绝?” 满座的附和声中,云游子也摇头 —— 那时他认定,道该在泛黄的竹简里,怎会混在市井的尘埃中?
山风掀起他的衣角,碑上的字迹忽然模糊。云游子望着指尖的血珠晕开,猛地惊觉:世人总在经卷里搜寻 “道” 的影子,却从未低头看看,它或许早顺着指温,渗进了脚下的泥土。
云游子的原名,记在长安西市的税册上。咸亨二年的商籍写着:“孟砚,刻碑匠,居布政坊,年三十二。” 他的铺子挨着染坊,墙角堆着浸了靛蓝的青石板,案头的刻刀却亮得能照见檐角的铜铃。
铺子里总弥漫着松烟墨的清香。孟砚刻碑有个规矩,必得选终南山的青石,说那里的石头吸够了日月精华。有回西域商人出百两黄金求块 “富贵永昌” 碑,他嫌石料带着沙砾,硬是拒了这笔生意。
“孟先生还在跟石头怄气?” 送浆水的张婆放下粗瓷碗,围裙上沾着面粉,“崇业坊的王御史家,用两匹锦缎求块’孝悌’碑,你倒守着这破碑喝冷风?”
孟砚的刻刀在青石上顿了顿。刀锋下的 “道” 字刚刻到走之旁,他总嫌这笔画不够舒展。七岁时先生在他掌心写 “道” 字,说读懂《道德经》能腾云驾雾。可十年刻碑,他能背出百二十家注疏,却修不好漏雨的屋顶 —— 去年秋雨,他踩着梯子补茅草,反倒摔断了腿,躺了整月。
立秋那日,西市来了个卖卜老道。灰袍沾着茯苓香,手里摇着柄断齿的木梳。见孟砚对着残碑发怔,老道径直走到案前,用木梳敲了敲碑上的 “道” 字:“走之旁刻得比扁担还直,可知流水从不会直着奔?”
“大道当如绳墨,怎容曲折?” 孟砚摩挲碑上的纹路,语气比青石还硬。他曾访遍名山,见青城山道士炼丹必按八卦方位,武当道长打坐须对北斗星,便以为道藏在玄机里,藏在那些常人看不懂的阵图中。
老道弯腰捡起块碎瓷片,在地上画了条蜿蜒的线:“你看这雨水冲出来的沟,从不走直线,却能流到河里。” 他用木梳指着孟砚的刻刀,“你刻字总逼着石头听话,就像用绳子捆住河水,能成吗?”
孟砚喉头发紧。他想起那些被凿崩的石料,十块里倒有四块毁在自己手里。总觉得天然的纹路碍眼,非要凿成四方柱,结果往往是崩裂的碎石溅满铺子。
那晚暴雨如擂鼓,豆大的雨珠砸在铺面上,像无数人在外面敲门。孟砚蹲在水里抢碑片,忽见老道撑着桐木伞站在巷口。伞沿的水珠串成线,落在青石板上漫开,顺着砖缝绕开青苔,从不像他刻碑时那般执拗。
“水入方缸成方,入圆瓮成圆。” 老道的声音混着雨声飘过来,伞柄在泥里戳出个小坑,“世人总给道画框子,却不知它本就像雨水,遇啥形显啥形,从不用谁来教。”
孟砚望着游走的水痕,忽然想起自己刻 “上善若水” 时,非要把三点水刻得一般长短,间距不差分毫。此刻雨水漫过碑片,那三个字的水渍竟蜿蜒出天然的弧度,比他刻的不知灵动多少。
次日卯时,案头多了卷竹简。竹片泛着新削的白,“终南山阴有古观,溪水流处是道根” 的墨迹还润着。孟砚摸了摸磨秃的刻刀,刀背上的反光映出他眼下的青黑 —— 十年了,他总在石头上刻 “道”,却不知刀与石的碰撞里,早藏着道的真意。
锁铺门时,檐角铜铃被朝阳晒得发烫,摇晃声里,“孟砚” 二字像被风吹散了。他背着半袋干粮往南走,走到灞桥时,听见赶车的老汉唱:“溪水弯弯绕山走,不跟石头争短长……”
终南山的茅庐是云游子亲手筑的。溪里的卵石砌墙,不用灰浆,让石头顺着天然的弧度咬合,像老人互相搀扶的胳膊;屋顶铺松针,每年霜降后换新,针脚里能藏住过冬的瓢虫。他特意选了块向阳的坡地,门前有棵歪脖子松,风过时能听见松针的轻响。
每日辰时,他提着木桶去溪边汲水。看溪水撞在褐红礁石上,碎成银珠又聚成绸带,绕着礁石的褶皱游走。礁石三年没变样,溪水的姿态却天天不同 —— 有时像顽童蹦跳着躲闪,有时像老者拄着拐杖慢行,从没有重样的。
有回他蹲在溪边看了整日,发现水流过圆石时会绕个圈,遇到尖角就分开,从不用蛮力冲撞。傍晚打水时,木桶在水里打了个转,他忽然想起老道的话,原来水从不是在 “流”,是在 “顺应”。
起初他仍抱竹简诵读。坐在崖边念 “道法自然” 时,心总像被山风刮得站不稳。直到雪夜见松鼠踩出的脚印被新雪盖平,才懂 “自然” 原是不留痕迹的自在 —— 就像松鼠从没想过要留下足迹,雪也没想过要掩盖什么。
“先生对着草木发呆,能当饭吃?” 送米的樵夫把布袋放石桌上,粗手摸着崖缝里的松树,“这树长在石缝里,做不了栋梁,结不出松果,图啥?”
云游子捏起松针上的雪团,雪珠在掌心慢慢化了:“它从没想过做栋梁,也没想过结果子。” 他指着树干上的伤痕,“去年被雷劈了道缝,今年不照样发新芽?”
樵夫咧开缺牙的嘴笑,扛起柴下山。他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上画的歪线,比云游子案头刻意写的隶书更有灵气。云游子望着那串脚印被落雪慢慢填满,忽然明白 “无为” 不是啥都不做,是像这雪一样,该来的时候来,该盖的时候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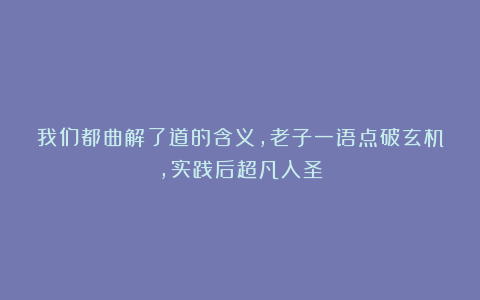
入夏的黄昏,云游子在溪边洗衣。上游漂来片卷边荷叶,托着颗莲子像绿色小船。他伸手去接,荷叶却顺着水流转了个弯,轻轻撞在他的草鞋上。
“原来你早知道要去哪。” 他喃喃自语,把莲子埋在茅庐后的土里。想起老道说的 “流水不争先”,这三年,他不再死记经文,看云卷云舒懂了 “无为”—— 云从不会为了变样子而使劲;观草木枯荣悟了 “不争”—— 草从不会和花比谁开得艳。
七月初七,山下药农送茱萸来。见他用枯藤补篱笆,药农蹲在旁边帮忙,手里的藤条却总被扯断:“用麻绳多结实,偏用这软藤子?”
云游子把藤子在竹桩上绕个圈,藤子遇风轻轻晃:“你看它弯而不折,山风再大也刮不断。” 他指着篱笆边的牵牛花,“藤蔓不和竹子比高,顺着竹架倒爬得更高,这就是老子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药农挠头走了,留下句:“洛阳来的道士带罗盘找’龙脉’呢,说找到就能白日飞升。” 云游子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从前刻碑总用朱砂画八卦,仿佛那样能引来道的灵气,现在才觉得好笑。
七月十五的夜,山风扯碎了茅庐的窗纸。云游子起身修补,忽见月下立着老道,灰袍在风里飘得像枯叶。“你可知为何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麟角?” 老道指尖划过崖下云海,云涛中突然浮出万千人影,都在伸手抓什么,抓得越紧,坠得越快。云游子浑身发冷,那些人影的模样渐渐清晰,竟有几个像极了当年访过的道士 —— 难道老子说的 “道”,竟是诱人坠渊的诱饵?
云游子追到崖边时,残月已躲进鹰嘴峰的阴影里。崖下的云海翻涌,那些人影早没了踪迹。他扶着松树喘气,忽然想起刻碑时的蠢事:总把边角磨得光滑,非要顽石符合心中的方圆,结果往往是崩裂的碎石扎破手指。
那些坠渊的人影,不正是和从前的自己一样?总想着抓住道的形状,抓住那些玄奥的词句,抓住别人说的飞升妙法,却不知手里攥得越紧,道就像沙粒般漏得越快。
天快亮时,他在溪畔青苔里摸到片竹简。竹片带着露水的湿凉,“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的墨迹还润着。指尖抚过 “瓦甓” 二字,忽然想起长安西市的砖瓦 —— 那些被他瞧不起的泥土块,经窑火一烧,却能撑起遮风挡雨的屋顶,这不就是老子说的 “道在万物”?
“原来道从不用找。” 指腹被竹片毛刺扎了下,这点尖锐的疼让他心头一亮。就像此刻的疼真实存在,道也藏在每一次呼吸、每一步行走里,藏在淘米时水流过指缝的感觉里,从没想过要躲。
入秋的暴雨连下了三日,山下传来呼救声。云游子跟着樵夫下山,见李家庄的堤坝被冲开个大口子,浑浊的洪水卷着泥沙奔涌,村民们扛着门板堵缺口,却被激流冲得人仰马翻,已有两个后生被卷进水里。
“不能硬堵!” 云游子突然喊。他望着溪里的鹅卵石,那些圆石从不会和水流较劲,却总能稳稳站在水底。“快搬圆石来,顺着水流的方向堆!”
村民们半信半疑,有几个年轻的跟着他往缺口搬石头。云游子指挥大家按溪底礁石的模样垒砌,石头间特意留着缝隙,像给洪水让开的路。村长攥着湿胡须跺脚:“这能挡住洪水?怕不是要让村子全淹了!”
话音未落,狂暴的水流竟顺着石缝蜿蜒而去,像条被捋顺的龙,乖乖绕着村庄流。原本汹涌的缺口处,水流渐渐平缓,刚才还在哭嚎的村民们都看呆了。
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挤到前面,抚着胡须惊叹:“这正是老子说的’不敢为天下先’!水流如气,堵则溃,疏则顺,道就在这顺势里!” 他转向云游子,眼神里满是敬佩,“先生这是得了大道啊!”
云游子摇摇头,指着水里的芦苇。那些细茎被洪水冲得弯下腰,却没一根折断,水一过又挺直了腰。“不是我得了道,是水在教我们啊。”
村民要给他立 “得道高人” 碑,被他摆手拒了。“你看田埂上的新芽,” 他扛起锄头补种被冲毁的秧苗,泥土沾在裤腿上,“它们从不求夸赞,却能让田地返青。道就像这泥土,踩在脚下时从没想过要显灵,可少了它谁能活?”
脚掌踩在泥里的深浅,正合着土地呼吸的节奏。他想起刻碑时,刀与石的碰撞早藏着道的声息,只是那时的自己听不见,满脑子都是飞升的幻象。
冬至,山上来了穿锦袍的道士。貂皮领子衬得脸发白,身后跟着两个抬罗盘的童子。见云游子在茅庐前晒草药,道士撇着嘴笑:“这般俗务,也配谈道?”
云游子把艾草捆成束,清香混着泥土味散开:“道长可知,揉面时力道太猛会碎,太轻发不起来?” 他指着檐下的冰棱,“道就像这冰,遇热成水,遇冷成冰,从没有一定的模样,这才是老子说的’常道’啊。”
道士气得吹胡子,从袖里掏出本《飞升秘要》:“此乃太上亲传,你懂什么?” 可当夜里山风骤起,他却看见云游子把唯一的棉被让给避雪的乞丐。月光透过窗纸,照见两人依偎取暖的身影,竟比任何罗盘都更合 “阴阳相生” 的道理。
开春下山赶集,洛阳学士还在争论 “道” 的模样。有人说在北斗星象,有人说在炼丹炉中,吵得面红耳赤。云游子买串糖葫芦,看糖渣掉在青石板上,引得蚂蚁们扛着碎屑钻进砖缝 —— 它们从没想过要成谁,却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这不就是 “道法自然”?
谷雨那天,云游子又去擦道德经碑。指尖抚过 “道可道,非常道”,忽然觉得字活了过来。就像他刻过的无数石碑,真正的道从不在字里,而在刻字时刀与石的每一次相遇里,在他现在踩着泥土的脚下,在风中摇晃的草叶上。
山风掠过碑刻,发出清越的声响,像老子在说:世人总把道捧在云端,却不知它早顺着指尖的温度,融进了脚下的泥土,融进了每个认真生活的瞬间里。
夕阳把终南山染成琥珀色,云游子坐在道德经碑旁。松针上的露珠坠向地面,在草叶间碎成星光,像极了他这半生 —— 从执着在石头上刻 “道”,到在补篱、抗洪、晒药里读懂道的呼吸;从苦求 “超凡入圣”,到明白活好每个当下,便是最真的 “圣”。老子说的 “道”,从不是悬在云端的奥秘,而是藏在烟火里的寻常。就像山间的风从不在意谁在听,却吹绿了每一寸土地。这或许就是超凡入圣的真谛:不是要成为与众不同的存在,而是终于学会,与万物一同在时光里,自在生长,自在呼吸,这便是道的全部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