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二十年前,刚从站了一辈子的讲台上退下来,那滋味,像是被人从一条奔流不息的河里,猛地捞起,晾在了岸上。周遭的空气都变得陌生而寂静,连墙上那挂了几十年的钟,走秒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心里头空落落的,是一种被需要、被填满的日子陡然抽离后的失重。庄老师更是坐立不安,那些日子,他总在书房里摩挲着他的教案和那些磨圆了边角的粉笔,嘴里喃喃着,说哪个班的孩子该复习到第几章了,眼神里满是不甘与眷恋,仿佛一匹老马,依旧向往着熟悉的疆场。
寂寞的日子过了两年,我们便决定出去走走。仿佛是要将那失落的重量,分摊到广袤的山河里去。
我们去了欧洲,在那些古老石砌的街道上,让异国的风拂过面颊;我们去了宝岛台湾,在太平洋的风里,看海浪一遍遍拍打着礁石;我们也去了越南,去了新疆,去了内蒙古。在新疆辽阔的戈壁上,我感觉天地间只剩下无垠的蓝与苍茫的黄;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我们并排坐着,看云朵的影子慢悠悠地从身上滑过,那一刻,似乎连时间也放慢了脚步。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新奇填补空虚,那些年,行李箱轮子的咕噜声,成了我们生活里最欢快的乐章。
然而,岁月终究是不饶人的。不知从哪一天起,长途的跋涉开始让我们的筋骨发出疲惫的呻吟,曾经向往的远方,渐渐变成了地图册上一个个安静的名字。
大约从七十五岁那年起,我们远游的脚步便真的停歇了下来。世界变小了,小成了一个家,一方阳台。
这阳台,便成了我们新的疆域。起初只是随意摆弄几盆绿萝、仙人掌,后来却一发不可收拾。本来不喜欢花花草草的老头也开始戴着老花镜,不厌其烦地给花剪枝浇水。
日子,就在这侍弄中,变得缓慢而丰盈。我们的阳台,渐渐成了一个微缩的王国。有热烈奔放的三角梅,一开便是泼泼洒洒的一片紫红,仿佛要把积攒的所有生命力都宣泄出来;有娇羞的茉莉,总是在清晨吐出细小的、洁白的花苞,香气清幽得像是夜的私语;有吊兰,垂下一丛丛翠绿的瀑布,生机勃勃地向外探着头;还有那几盆月季,红的像火,白的像雪,粉的像少女的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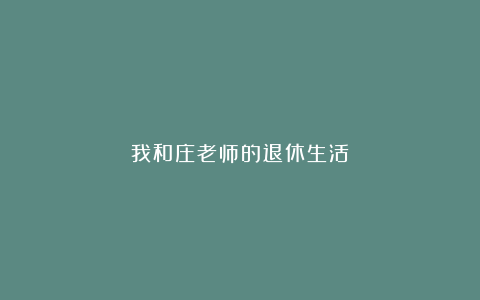
它们依着时令,次第开放,从不同断,将这小小的阳台,装点得四季如春。
我尤其爱在午后,搬一把藤椅,泡一杯清茶,坐在这花丛之间。阳光透过玻璃,变得温驯而暖和,静静地流淌在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上,勾勒出明暗交织的柔和轮廓。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着自己是个富足的人。
目光偶尔越过花枝的缝隙,望向楼下的中学校园,那些匆忙的身影,曾几何时,也是我们的模样。如今,我们却安然地退守在这一片芬芳里,像两株终于找到适宜土壤的老植物,不再向往迁徙,只安心于脚下的方寸之地,与阳光雨露为伴。
朋友来访,总会惊叹这一阳台的灿烂,说我们真会过日子,把晚年经营得如此漂亮。
这哪里仅仅是一盆盆花呢?这每一片新抽的嫩芽,都是我们对生命不息的期盼;每一朵绽放的花苞,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沉甸甸的欢愉。我们从喧嚣走向宁静,从广袤回归方寸,最终在这姹紫嫣红里,寻得了内心真正的平和与安宁。
窗外,或许仍有世界的喧嚣;但窗内,我们的花园正静默地盛开。
这,便是最好的时光了。
中学退休教师:吴老师
书于202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