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的水,在夏末的风里泛着碎银似的光。四十岁的专诸蹲在船头,手里攥着半块烤焦的鲥鱼,鱼鳞沾在他粗布短褐上,像撒了把细碎的金箔。妻子阿朱捧着陶碗过来,碗里是刚熬的藕粉羹:“阿专,阿爹说今日渔汛好,让你去湖心泊子试试新网。”
他抬头,额角的汗珠子落进羹里,荡开一圈涟漪。“晓得嘞。”他应着,把烤鱼往竹篓里一塞,起身时腰间的鱼篓撞在船板上,“咚”的一声闷响。
那时的专诸,不过是太湖边一个普通的渔户。臂力过人,能徒手搏虎,却因生得浓眉阔眼,总被邻人笑“像庙里金刚”。阿朱嫁给他五年,只见过他两次动怒:一次是村头王二家的崽子偷了他晒的鱼干,他追出二里地,把那孩子按在泥里,却没舍得打,只揪着耳朵骂“再敢偷,把你扔进湖喂鱼”;另一次是去年冬天,有个行脚商人摸黑进村,兜售说是“吴王祭天用的玄铁”,他摸了摸那铁块的棱角,突然红了眼——像极了当年他在刑场见过的,被砍头犯人脖颈处迸溅的血。
“阿专!”阿朱扯他的衣袖,“莫发呆,日头要落了。”
他应了一声,弯腰去提竹篓,却触到篓底一块硬邦邦的东西。掀开草席,是把锈迹斑斑的短刀,刀鞘上缠着褪色的红绸。这是三天前在芦苇荡捡的,当时刀刃半埋在泥里,他本想熔了打鱼叉,可指尖刚碰着刀身,就像被雷劈了似的——刀纹里竟渗出一丝暗红,像凝固的血。
“许是哪个渔户落的。”阿朱说,“明日拿到镇上去换两斤盐。”
专诸没说话,把刀重新裹好,塞进怀里。风从湖面掠来,带着股若有若无的铁锈味,像极了……像极了他十二岁那年,在刑场闻到的味道。那天他跟着爹去看斩头,犯人是个穿青衫的士人,被绑在木柱上,脖子上的血沫子溅到青石板上,像开了一地的小红花。监斩官喊“开斩”时,那士人突然笑了,说:“此剑名为鱼肠,本应藏于鱼腹,今日却要见天日了。”
“阿专!发什么呆?”
阿朱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抬头,看见夕阳把湖水染成了血色,像极了那柄短刀渗出的红。他突然觉得,这刀不该熔了打鱼叉——它该见天日,该沾血,该……
“阿朱,”他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我想去吴都。”
阿朱的手猛地一颤,陶碗“啪”地摔在地上,藕粉羹顺着船板流进湖里,像一滩凝固的血。“去吴都做什么?”她声音发颤,“你忘了你爹临终前怎么说?他说我们渔户要守着太湖,莫要沾那些贵人的是非。”
“可我昨日梦见我娘了。”专诸轻声说,“她穿着蓝布衫,站在门口喊我吃饭,可我走近了,发现她的脸是模糊的。”他喉结动了动,“我想去吴都挣点钱,等攒够了,接你去城里住大瓦房,让阿娘能看清我的脸。”
阿朱低头抹眼泪,眼泪砸在泥地上,洇出一个个小坑。“那你……那你早去早回。”
专诸没再说话。他弯腰捡起碎碗片,割破了手指,血珠滴在青石板上,像极了那柄短刀渗出的红。
三个月后,专诸站在了吴都的城门口。他换了身干净的粗布衫,腰间别着那柄短刀——刀鞘已经重新打磨过,红绸也换了新的,却仍遮不住刀身上若有若无的幽光。他怀里揣着伍子胥写的引荐信,信纸上墨迹未干,写着“专诸,勇士也,可近王僚”。
那是他在市集上替卖鱼的阿婆出头,被三个泼皮围殴时,那个穿玄色锦袍的男人救了他。男人拍着他的肩说:“你这身力气,该用在刀刃上。”然后递来这封信,说:“去见公子光,他会给你想要的。”
公子光的府邸在姑苏城最深处,朱漆大门上挂着青铜兽首衔环,门房见了引荐信,上下打量他一番,冷笑:“就你这副渔户打扮,也配见我家大人?”专诸没说话,解开腰间的鱼篓,取出两条刚烤好的鲥鱼——鱼身金黄酥脆,鳞片都泛着油光,香气顺着门缝钻进去,门房的嘴角立刻松了。
“等着。”门房甩下一句话,转身进了院子。
半个时辰后,门房出来,态度恭敬了许多:“大人请你进去。”
公子光坐在正厅,穿着月白锦袍,腰间挂着玉玦,见了专诸,起身相迎:“可是专诸兄弟?”他的声音清亮,不像一般贵族的矜持。
专诸抱拳:“小人专诸,见过大人。”
公子光指着案上的烤鱼:“听闻兄弟在太湖善炙鱼,可否让在下尝尝?”
专诸上前,用银箸夹起一块鱼,吹了吹,放在公子光面前的青瓷盘里。公子光咬了一口,眼睛一亮:“妙!外酥里嫩,连鱼刺都酥了。”他放下筷子,目光灼灼:“兄弟这手艺,在市井里埋没了。”
专诸低头:“小人只会烤鱼。”
“会烤鱼的人,就能靠近王僚。”公子光突然压低声音,“王僚爱吃鲥鱼,每餐必用太湖活鱼现烤。可他的护卫如狼似虎,连只苍蝇都飞不进他的宴席。”
专诸沉默片刻,问:“大人要小人做什么?”
公子光从袖中取出一方锦盒,打开,里面是柄短刀,刀身狭长如鱼肠,刃口泛着幽蓝的光。“这是鱼肠剑,欧冶子所铸,藏在鱼腹中可断金石。”他合上锦盒,“我要你带着这柄剑,以烤鱼为饵,刺杀王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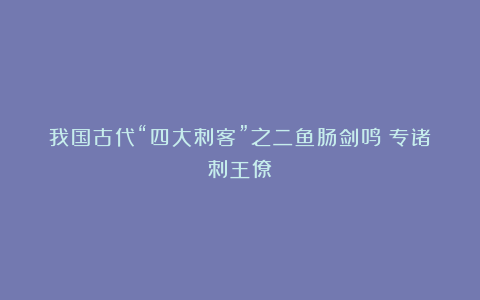
专诸的手按在腰间的旧刀上,指节发白。他想起十二岁那年的刑场,想起那个穿青衫的士人说的话,想起阿朱在湖边抹眼泪的脸。“为何选我?”
“因为你平凡。”公子光笑了,“王僚防的是剑客,是死士,却不会防一个浑身鱼腥味的渔户。”他从腰间摘下玉玦,递给专诸,“这是信物,明日卯时,我在南门码头等你。”
刺杀前七日,专诸搬去了公子光安排的住处。那是个带小院的瓦房,院里有口井,井边种着几株枇杷树。每日清晨,他去太湖边钓鱼,午后回来烤鱼,傍晚时分,公子光会派车夫送来酒肉,说是“补补力气”。
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局。车夫每次来,都会在他烤鱼时站在旁边,看似闲聊,实则在观察他的手法;丫鬟送来的布料,里子都缝着细针,针尖涂着麻药——他试过,扎一下,能让人昏睡半日。
真正的训练是在深夜。公子光亲自来了三次,第一次教他用筷子夹起滚烫的鱼,如何在递给王僚时,手腕轻轻一抖,让鱼腹的剑滑入手心;第二次教他辨认王僚的护卫站位,哪两个是左撇子,哪几个腿上有旧伤;第三次,他递给专诸一杯酒,说:“这是毒酒,喝了它,你死后,他们不会怀疑你是刺客。”
专诸没喝。他把酒泼在地上,说:“我只做该做的事。”
公子光盯着他看了许久,突然笑了:“好,像条汉子。”
刺杀前一日,专诸回了趟太湖。阿朱正在湖边补渔网,见了他的面,手一抖,梭子掉进湖里。“阿专?”她扑过来,又不敢碰他,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你不是说要挣够钱接我去城里?”
专诸摸出怀里的玉玦,塞到她手里:“替我收着。若我回不来……”
“胡说!”阿朱捂住他的嘴,“你定能回来的,定能!”
专诸把她搂进怀里,闻着她发间的芦花香气。他想起初见那天,她蹲在船头补网,阳光照在她脸上,像朵开在湖边的野菊。“阿朱,”他轻声说,“等我走了,你把我埋在太湖边,要面向东方——这样每天日出,我就能看见你了。”
阿朱哭出声来,眼泪打湿了他的衣襟。她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他:“这是我攒的鸡蛋钱,你路上用。”
专诸打开布包,里面是十二文铜钱,还带着阿朱的体温。他把布包贴在胸口,说:“等我回来,给你买十匹最好的锦缎。”
公元前515年四月丙子日,吴王僚的寿宴。
王僚穿着十二重锦衣,坐在主位上,身边围着十二名甲士,每人手持长戟,腰间挂着青铜剑。大殿外的庭院里,三百名卫士手持戈矛,目光如炬。连送菜的仆役都要脱光上衣,露出胸膛,让护卫检查有没有藏刀。
专诸穿着新做的青衫,腰间系着鱼篓,手捧烤得金黄的鲥鱼,跟在侍从后面走进大殿。他的心跳得厉害,像擂鼓,可脚步却稳得很——这七天,他每晚都在院子里练步伐,从井边到枇杷树,从枇杷树到院门口,每一步都要踩在砖缝的正中间,误差不能超过半寸。
“启禀大王,这是公子光进献的太湖鲥鱼。”侍从高声喊。
王僚放下酒爵,笑着说:“光弟有心了。”他伸手去接鱼,目光扫过专诸的脸——这张脸他在市井里见过,是个卖鱼的,倒也生得憨厚。
专诸弯腰,将鱼放在案上。就在王僚的手即将碰到鱼腹的瞬间,他突然挺直腰板,左手按住王僚的手腕,右手从鱼腹里抽出鱼肠剑。剑光一闪,如游龙穿雾,直刺王僚心口。
王僚的甲士反应极快,左边那个挥戟来挡,右边那个挺剑刺向专诸心口。专诸早有准备,侧身避开,反手一剑削断了左边甲士的戟杆,同时鱼肠剑已刺入王僚胸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王僚的十二重锦衣,像开了朵狰狞的花。
“抓刺客!”不知谁喊了一声。庭院里的卫士蜂拥而入,戈矛如林。专诸挥剑乱砍,剑刃虽利,到底是凡铁,砍了七八个卫士,剑刃卷了口。他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低头一看,一支弩箭穿透了甲叶,正往心脏里钻。
“阿朱……”他想喊,却发不出声。眼前渐渐模糊,他看见王僚倒在案几旁,案上的鲥鱼还在冒着热气,鱼腹里的剑闪着幽光。他笑了——这剑,到底见着天日了。
最后一个念头是:阿朱的鸡蛋钱,还没花呢。
专诸的尸体被扔在街头,曝尸三日。阿朱得到消息时,正蹲在湖边补网。她手里的梭子掉进湖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裙角。她踉跄着往城里跑,路过城门时,看见专诸的尸体被野狗啃食,心口还插着那柄鱼肠剑。
她扑过去,抱着专诸的头,哭得肝肠寸断。围观的百姓指指点点,有人说:“这刺客活该。”有人说:“可惜了那姑娘。”阿朱没听见,她只看见专诸嘴角的血沫,像极了那年刑场上的小红花。
三个月后,公子光派兵袭杀了王僚的儿子庆忌,自立为吴王阖闾。他在专诸的坟前立了块碑,上刻“忠士专诸之墓”,又把鱼肠剑封存在剑匣里,说:“此剑因忠义而鸣,不当再染血。”
后来,有人在太湖边发现了一座小渔村,村里有个白发老妇,每天蹲在湖边补网。她的竹篓里总放着两块烤焦的鲥鱼,说是等她男人回来吃。村里人都说,那老妇的丈夫是个勇士,曾用鱼腹藏剑,刺杀过吴王。
再后来,《史记》里多了段记载:“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如吴时,遇之于途。闻阖闾即位,乃进专诸于阖闾。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阖闾曰:’子待吾。’伍子胥乃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遂弑王僚。”
只是没人记得,那个叫专诸的渔户,在死前最后一刻,想的是阿朱的眼泪,和太湖边的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