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政智君 政智局 2025年11月29日 13:15 福建
许多年前,我是一名在顶级媒体报社工作的调查记者,有件事情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去广东,悄悄调查一位“出事”的正部级领导。
01
那时我还是家顶尖媒体的调查记者,刚混进来不久,名气没有,理想倒挺满。
领导把我叫进屋,开门见山:“文化部副部长(正部级)于幼军出了点事,你去他曾经工作的广州、深圳转一圈,看能不能挖出一篇像样的好稿子。”
当时于幼军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在南方报业当小记者时,他正是广东的宣传部长,广州媒体那几年风光到什么程度?全国媒体人,都盯着这座城看风向。
02
那会儿广东报业如日中天,三大报业集团又叫座又好卖。金融危机来临,城市土地卖不动,上面只好动员“现金流最好的单位”出手相助,媒体单位被点名去买地。
很多人心里是委屈的——谁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纸媒不行了,正是当年这些被迫买下的地块,成了养活一整家媒体的“救命钱”。时代转几圈,谁也算不准。
03
在不少广东媒体人口中,这位后来出事的正部级官员于幼军,有一件事一直被记着——在舆论风向最紧的时候,他硬是顶住中央的压力,把南方周末保了下来。
那时,南方周末锋芒太盛,在一些更保守的视角里非常“扎眼”,关停的声音时不时冒出来。关键时候,是于幼军和几位老同志扛住了:有人愿意担责,这家媒体才得以继续存在。
如今这家媒体还在,只是像很多人一样,从锋利变得圆润,从愤激变得更懂“顾全”。
04
后来,于幼军去深圳当市长。
那时,一位深漂呙中校写了一篇刷屏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言辞犀利,城市焦虑被摆上台面。
出乎很多人意料,于市长没有翻脸,而是请作者呙中校和几位民间代表坐下聊天,面对面听他们骂城市、挑政府的毛病。
那场“官民对话”,一度被视为深圳的公共事件样板。可几年后,市长调离,写文章的人因涉嫌违法被抓,各自命运转向,没人再提那次座谈。
于幼军左边是呙中校
05
按调查记者的套路,要摸清一个官员,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他工作过的地方,找那些跟他有过摩擦、被他“得罪”过的人聊聊。
于是,我在广州、深圳转了两个月,找了几十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老同事、旧下属、文艺圈、媒体圈……
结果却很尴尬——
几乎没人愿意说他坏话。
有人说他“不太像传统官场的人”;
有人说他“想事情快,有主见”;
还有几位广东鲁迅学会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到表示:要是有机会,真想去北京替他讲几句公道话。
对一个已经“出事”的正部来说,这种评价很反常。
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更麻烦——你不能在所有人都盼着看“猛料”的时候,突然写一篇“为落马高官叫好的报道”。
于幼军写给记者的几句话
06
追根溯源,他的出身说不上显赫。
早年只是工厂里的青工,下班后别人打牌,他啃鲁迅。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让他被上级注意,从普通政工干部一路走上省里主管意识形态的岗位。按坊间说法,他是“南下干部后代”,但接触过的人普遍觉得:他更多靠的是脑子和勤奋,而不是背景。
至于他后来为何出事,江湖上流传过一个版本:
有人托他办事,他在湖南工作再到山西工作那段期间,一路坚持不办,双方彻底翻脸,举报随之而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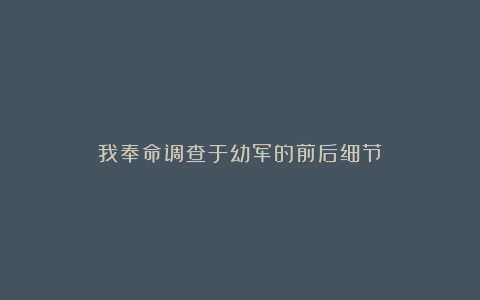
各种说法我听过,细节却都缺乏可公开核实的证据——
作为记者,这当然是不能写的。
07
反而让我更在意的,是他被闲置那几年怎么过的。
朋友说,他几乎每天定点去图书馆写作:
背个包,几瓶水几块面包,坐在固定的位置,一写就是一天。
坚持了三年。
其间,他和原《广州日报》主编黎元江合作,写出一部《社会主义五百年》,三大卷、数百万字。
黎元江也是狠人,在狱中硬是考下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
说到这儿,广东媒体圈有句半真半假的调侃:
广州办得最好的报纸,不是哪家都市报,而是一张内刊——《番禺监狱报》。
从传统党报“一哥”到市场化报业大将,不少人都在里面当过编辑,业余做的小报,在司法系统内评价一直很高。
命运有时,比任何文案都更讽刺。
08
与黎元江一同被提起的,还有喻华峰。他跟黎一样,出自人大新闻系,却一直做经营。南方都市报初创发不出工资时,他悄悄自掏近百万元,把团队扛了下来。
有人回忆,喻华峰快出狱前,猎头伪装成家属进去“探视”,想请他出山当总经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前阵子,一家全球知名投行,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来找过我了。”
出狱后,他选择自己创业,做出了“本来生活”这个生鲜电商品牌。有人说,他用自己的起伏,演了一遍中国媒体人从黄金年代到互联网风暴的全程。
2020年在深圳疗养的于幼军
09
回头再看那次广东之行,我最终没交成一篇稿子。
不是因为没故事,而是那些故事,要么缺乏证据链,要么无法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讲出来。
但这趟路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别轻易用“完人标准”去审判任何个体。
人非圣贤,要挑毛病,谁都有。
真正值得拿出来说的,往往只是那么几瞬间——
他有没有守住自己认定的底线?
他在体制起伏里,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哪怕付出代价,也要坚持一点点个人的判断。
如今,他已从聚光灯下退场,成了一名教书的“于老师”。
不再是新闻里的主角,只在偶尔被人提起的段落里,留下一句:
“他当年,其实是有点理想的人。”
愿他在讲台上、书桌前安然度过后半生,
也愿我们在看待每一个“被定性的人”时,
都能多一点节制,少一点简单粗暴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