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对着一本光绪年间的线装书发愁——书页发黄脆化,轻轻一翻就有碎屑飘落,活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在向我控诉时光的残忍。这是我上周在旧书市场’抢救’回来的’战利品’,此刻却让我陷入了’藏书容易护书难’的现代困境。
现代人收藏古籍的狂热,活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赎身’。我们这些穿着牛仔裤、用着智能手机的当代人,突然对几百年前的纸张产生了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某位藏书界前辈的名言在圈内广为流传:’买书不读谓之藏,藏书不护谓之戕。’第一次听到时我还不以为然,直到亲眼见证一本康熙年间的《唐诗鼓吹》因为保存不当,书页粘连得像块葱油饼,才恍然大悟,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古籍爱好者’,常常一不小心就从文化保护者变成了文物破坏者。
古籍修复这门手艺,堪称’与时间讨价还价’的艺术。记得初次尝试修补一页破损的《水经注》时,我紧张得像是要给蝴蝶做心脏手术。专业的修复师们有一套精密如外科手术的工具:pH值中性的糨糊、比发丝还细的修复用纸、特制的压书板…而我这个业余选手的’手术台’上,却摆着从厨房偷来的面粉(自制糨糊)、化妆用的细刷(替代毛笔),甚至把媳妇的丝绸围巾征用为压书布。结果可想而知,那页《水经注》被我’修复’后,活像打了块补丁的乞丐服,引得专业修复师朋友连连摇头:’您这哪是修复,简直是行为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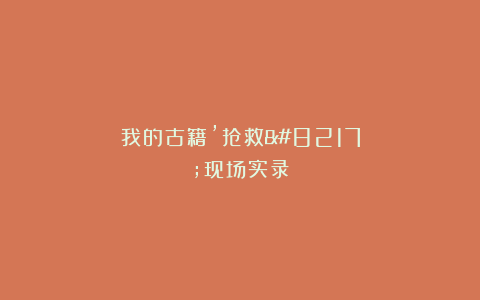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代科技在古籍保护中的’水土不服’。我曾在某论坛看到有人建议用微波炉给古书’杀菌’,结果可想而知——一本珍贵的明版书就这样变成了’爆米花’。还有人迷信电子防潮箱,把宋版书和普洱茶饼放在一起’养生’,最后书页吸足了茶香,倒是省了熏香的步骤。这些令人扶额的’创新’做法,活脱脱是现代科技遭遇传统文化时产生的’喜剧效果’。
但正是在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实践中,我渐渐领悟到藏书之道的真谛。某次拜访一位老收藏家,他的书房没有昂贵的恒温恒湿设备,却用最朴素的法子——在书柜里放置吸湿的竹炭、定期通风、用无酸纸做书套。他边抚摩着一部《昭明文选》边说:’护书如护心,太娇惯反而失了韧性。’这话让我醍醐灌顶。我们总想用高科技对抗时间,却忘了古人’纸寿千年’的智慧本就藏在那些看似简单的方法里。
如今我的书房里,那些历经沧桑的古籍与现代化设备达成了微妙的和解:温湿度计旁边放着传统的樟木防虫块,LED阅读灯下展开的是手工修补的宣纸衬页。每当夜深人静时翻阅这些幸存的文字,指尖传来的触感仿佛是跨越时空的握手。某次成功修复一页《东坡志林》的破损处后,我对着灯光欣赏自己的’杰作’,忽然哑然失笑——这修补的痕迹,不正是我们这代人接续文明香火的最好证明吗?
藏书与修书,说到底是一场与时间的谈判。我们这些现代’书痴’,既不能像古人那样纯粹,又无法像未来人那样超然,只能在笨拙的尝试中,小心翼翼地传递着文明的星火。那些被我们救下的残页断简,或许正是历史留给当代最意味深长的考卷——它考验的不是我们的技术,而是对待文明的诚意。
作者:孔网书友 地山古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