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敦煌】微刊 — 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办
以下文字 图片 视频为 CCTV 《文化十分》友情提供
导语
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把自己生命中50年的时光留在敦煌大漠戈壁,从清沙筑墙到修复洞窟,为敦煌保护打下坚牢的学术和管理基石,而他自己却付出了妻离子别、放弃专业的代价,弥留之际,他让女儿把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他说:“如有来生,我还做常书鸿,还要守护在莫高窟”。近日,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自己敦煌题材的艺术作品,回顾了与父亲在敦煌的艰苦岁月。
常沙娜,画家,前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年轻时是十足的文艺女青年,现在是文艺老太太,看到她你就知道什么是榜样。
“沙娜”这个名字是法国里昂的一条河“La Saone”的中文音译。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里昂,父亲常书鸿是赴法留学的年轻中国画家,才华横溢,后来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的工作室深造,其画作多次获法国国家级金质奖和银质奖。母亲陈芝秀是父亲的表妹,总打扮得摩登时尚,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
说到父亲,常沙娜看着父亲常书鸿在法国时画的一家三口的画像说:那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刻。
常沙娜忆常书鸿 时长:1′18″
与父亲的艰苦岁月:他只要认可,一定执着
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妻子陈芝秀也在法国学习雕塑,两人琴瑟和鸣。留学十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在巴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1935年秋天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
常书鸿(左一)夫妇与留法艺术家
“我父亲看了这个书很激动,他说:哎呀,我到法国来追求欧洲的文化艺术,文艺复兴的艺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这么精彩的石窟,我法国学完了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到祖国,我一定要想办法到甘肃敦煌看一看。”
在战火纷飞的1936年,常书鸿告别了妻女回到了祖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第二年,常沙娜跟随妈妈回到了国内,开始了逃难生活,最终到达重庆安顿下来。但常书鸿始终没有忘记敦煌,没有忘记莫高窟。1943年,常书鸿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我父亲下决心要把全家都迁移到那边。1945年我们就开始全家走了整整一个月,我妈妈很时尚穿旗袍什么的,从兰州到莫高窟更加苦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妈妈简直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穿一个老羊皮,穿靴子,我妈妈不穿,说难看得很。”
到了莫高窟,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常书鸿一家住在崖壁下面的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的,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在滴水成冰的屋里甚至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到了第一顿饭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顿饭,晚饭,又冷,一碗醋,一碗盐,然后一个面条,什么都没有。我还说爸爸有菜吗?爸爸说这就是,没有菜了,以后我们要种菜,今天晚上没有,我父亲面临着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很多矛盾,但是很乐观的去一个一个解决。”
常沙娜与父亲和弟弟在敦煌
常书鸿就这样在莫高窟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他放弃了个人的艺术创作,带领研究人员清沙筑墙、整理资料、修复石窟塑像、临摹历代壁画,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期间家庭的变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因为受不了艰苦的环境和寂寞的生活不辞而别。不久,他又收到国民政府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放弃还是坚守,是摆在常书鸿面前的难题。然而,一想到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便下决心留在敦煌。在自身经费无着落的逆境中,常书鸿靠为人画像、变卖自己的画作为莫高窟筹集资金。
常书鸿在莫高窟工作
像父亲一样对美好始终坚持
成年的常沙娜虽然很少有机会和父亲深谈,但父亲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他从没有说过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也从没有明确设计过我的未来,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948年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父亲对这个女儿是满意的,两人经常通信谈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观点,仿佛志同道合的朋友。
“杭州有句话叫”杭铁头”,爸爸经常这样说自己,想干的事情不管有多苦,非干到底不可。当年如果不是爸爸坚持去敦煌,恐怕那些壁画就很难留下来了。当地人求神拜佛,挖土烧香,人为与自然的因素使洞窟一天天被破坏。是爸爸带着研究所的同仁在艰苦的环境下尽力维护,在那里修围墙,做研究,一待就是几十年,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守护神”。而爸爸给她最重要的传承是”敦煌精神”,”就是对中国历史艺术的保护、研究,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
当年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常沙娜参加设计了很多送给外国首脑的景泰蓝礼品,设计灵感大都来源于敦煌壁画,礼品大受欢迎,被称为”代表了新中国的新礼物“。20世纪50年代末,常沙娜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建筑和装饰设计,其中,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的天花板设计,常沙娜采用的就是敦煌唐代装饰风格的图案,这一设计成为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建筑的典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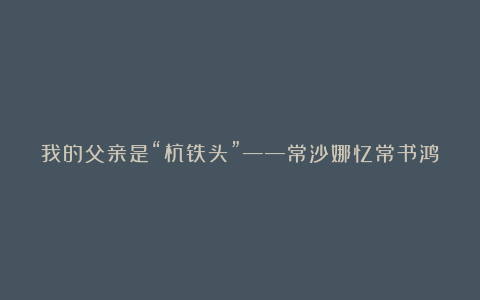
至今常沙娜还留着父亲1980年写给她的话:“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在中央工艺美院工作50年,常沙娜带着教师深入民间采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在敦煌莫高窟,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分类收集整理了历代壁画、彩塑人物服饰上的图案,当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给了他们很大支持。1986年,这一资料成书为《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常书鸿亲自题写书名并作序。
常沙娜从1983年起任副院长,整整15年,中央工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紫光阁、北京饭店、国际贸易中心等建筑的室内、陶瓷、染织和装饰设计都是他们的手笔。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一些学生说,常沙娜在他们的心中是一尊艺术女神。他们景仰她,因为她的作品,也因为她个人美丽而高贵的气质。
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常沙娜对世界的感受力最强的那部分永远是美,是艺术。即使被下放农村,她都为野地、菜园里不起眼的小花儿所感动,”这些花儿默默无闻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得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
她的艺术思想与父亲一脉相承,那就是对美好始终如一的坚持。
常书鸿:请将我埋葬在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常书鸿听了几十年,退休后在北京安度晚年的日子里,他在窗前挂一副铃铛,梦里依稀回到敦煌。
“他老说我在这里做客,这不是我的家,条件是好了,但是老惦记着敦煌,他后来病了以后他跟我说,他说沙娜我将来死了也要回敦煌。专程给他安葬在那里,给他安排的地方正好是面对九层楼,让他永久的可以瞭望着他所守护着一辈子的莫高窟。”
常书鸿被后人尊称为“敦煌守护神”,常沙娜提及父亲传承给她的不仅是艺术天赋,还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她说自己对敦煌的爱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就像沙漠中生长的花一样坚忍,践行着父亲交予的使命。这次画展,她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自己的24幅作品,期待让更多人了解敦煌,了解莫高窟。
常沙娜,马夫与马(初唐431窟),13x19cm
常沙娜,华盖图案,晚唐14窟,29x35cm,2000-2004,彩墨
常沙娜,佩饰29×44cm
记者 | 孟颖 张思齐 朱梓铭
编辑|李博丹
运营|邓 荣
部分图片来源互联网
– END –
···
/ 当 代 敦 煌 /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Dunhuang Culture and Art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