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一趟回来本想睡个懒觉,正做着红楼梦,狗就上床来把我舔醒了,腥骚的臭嘴一抵近,我便失去了秦可卿。此刻觉得世上最不懂事的就是狗了。往事不可追,只好爬起来。
哈欠还没扯圆就听楼下朱大厨惊吒吒地叫,说隔壁二楼的店子垮了。我吃了一惊,我管过这项目,房子垮了怕不是还要进去吃几天牢饭?一问说是鸡汤店子开垮了,才又把我从看守所扯了回来。中国人说话总是说半句,都不知怎么去说他们的了。却似乎事不关己,我也没改喜欢凑热闹的毛病,小时候隔壁生产队有户人家烧起了我也跑去看,毕竟烧的不是自家的房子,那火烧的好旺,真个好大火。
垮了这家店主我认识,平时都叫他老王,最近垮的王姓老板挺多,看来这姓氏太大,颇有些不吉的意思。老王肥头大耳,长得象个伙夫,油噜噜的脖子上总是套着根拇指粗的金项链。一喘气,那根粘着油有些乌暗的项链,就在敞开的胸口上滞滞地晃。
我走到他面前时,二楼的东西已搬了下来。锅碗瓢盆冰箱烧箕散落一地,老王站在面前吆喝,额上平时用以支撑脸面的几络头发,正有气无力地搭在一边。勉强整了个二八分,油油的粘在头上。眼白处起涎涎焦黄,于是他黄黄地看了我一眼。看来他的肝区遭的凶,恐怕拖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往硕大的肚皮象个泄了气的皮球,胡乱挂在腰间起伏。
我递了杆红塔山给他,烟雾起处,锁紧的川字纹才渐次舒展,换了以前,他可都是抽大重九的。今天十元一包的塔山他还是叭得啪啪啪的,我觉得自己挺有面子,人家老王没嫌我的孬烟。我蹲下来假装选物件,顺便与他讨价,原想安安他的心。好歹也买了口高压锅,一来减减他的压,也没还价。毕竟我自己也黄着眼睛,走路跌跌拌拌,头上更是一毛不拔。算是惺惺相惜吧!
老王平时喜欢叫嚣餐饮业要高质量发展,在市餐饮协会大会上,他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踌躇满志。当时我就觉得他桌子面前安个话筒纯属多余。现而今,这家名为’鸡汤爱上牛肉’的店子终于被年富力强的他干垮了,但那瘦下来的身材成了他最大的福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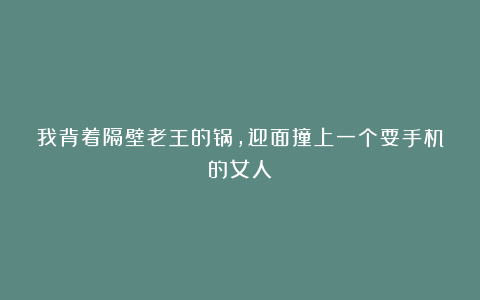
我觉得他遭就遭在卖鸡汤,现在谁还吃鸡汤?网络早就把鸡汤玩坏了,成了潘金莲同学端给武大的药药。还有他只慌着赶潮流却又不专一,真卖鸡汤还好,这鸡爱上牛是怎么回事,何况当下谁还相信有爱情这回事。我起身付了钱拍了拍他的肩膀,背着锅走了,回望,他仍怔怔地忤在那里,胸口处白茫茫一片,已找不见那一圈黄光。
一楼的香佰里火锅,也正懒心无力地忤在面前。就在我市,之前他们已倒了五家店。唯此一家还在摇摇晃晃地开着。门口的迎宾已由婷婷玉立的小甜甜换成了五大三粗的牛夫人,唯一不变是她们站在那里,看手机短视频时的专注,恰似她们高老板刚开店时的全心投入。
门口原来停满的进口轿车已被电池车替代。车牌是绿的,说是绿色新能源汽车。它们静静的呆在那里,绿油油一片,只是没有生气。人为涂绿的东西怎么比的过春天的绿?
两边,这如雨后春笋般倒下的店铺,让街面有一种被劫财劫色后衣衫不整的蓬头垢面。。。
背着的高压锅压得我喘不过气,若有所思得漫无目的。不想一个举着手机傻笑的女人波涛汹涌地向我袭来,尖尖的鞋跟刚好叉在我脚背上的太冲穴上,那里是肝经的位置。我们撞个满怀的时候,碰撞的欢愉掩盖了疼痛,我懵懂的脑壳头竟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油腻的诿琐有些狼狈,没想到福报这么快就来了,于是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她这才终于放下手机,一脸徘红,让脸上的几颗土印也显得好看。你学过中医?我弱弱地问,否则你的穴位怎么踩得这么准。一脚下去就疗愈了我的肝瘀,痛却舒展。她骂我神经病的时候我已走远,原来肝才治好又得了个神经病,这病可是在头上不在足上,下次哪里去找能踩这么高的高跟鞋啊。便宜没占着,也没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情。
落个灰头土脸才想起我原是个病人。该回去吃药了!为节省,我把熬过的药渣又拿来熬了一道,可以多吃一天了。病虽不见大好,我却为自己如此聪明如此会过日子竟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