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作品在2006年进入国内,那时他已经70多岁,暮年成名。
80岁时,他回国隐居在故乡乌镇,于2011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84岁。
为纪念木心,展示其毕生心血与美学遗产,乌镇修建了木心美术馆,并由他的得意门生,陈丹青担任馆长。
也正是得益于陈丹青的宣传,木心和他的作品才得以在国内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
如今,木心美术馆已是乌镇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
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与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感受木心那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木心曾说:“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没有这样早熟。三十岁时,我关在牢里。当时我笑,笑人生三十而坐,坐班房。但我有我的而立之年,叫作’六十而立’比孔子迟了三十年。”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而立”呢?
所谓“三十而立”是前人的智慧总结,而非人生阶段的刻板定义。
回顾木心的一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当五辈子来活”。
从江南富家子弟到监狱囚徒,从流亡海外到隐居故里,从暮年成名到蜚声中外,他一生的经历和遭遇,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其所受的苦难也非一般人能承受。
若要为他的人生剧本寻找注解,孟子的话恰如其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倘若要文艺精简些,那便是“民国故事,十有九悲”。
木心这一代人深受当年政治局势影响,以至于对现今的我们而言,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时代鸿沟。
时代之下,他是悲剧性的存在,或许可以说,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如此。
“十年浩劫”是国之殇。可这悲恸又恰如史铁生所言:“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诚然,你我皆非亲历者,不可妄议他者之痛,且后世史书也只能以“文革”二字警示后人。
不过总会有人能为我们一解心中所惑,一宽心中所郁。
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
一如木心第二次入狱,身陷囹圄那些年,他在监狱里写出了132页、近65万字的《狱中手稿》。
可这些文字不会发表更不会被看见,因为一经发现就是罪加一等。
但他依旧坚持写,只为自己写。
失去尊严、失去安全,甚至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靠着“我写我心”一个字又一个字地救自己于水火,直到出狱那天。
后来,无论身处何境地,他始终用文学与艺术抵御世事无常。
众所周知,木心一生曾三次含冤入狱,而每一次入狱都如同史铁生入院一样,次次都要失去点什么。
第一次入狱,他失去了母亲;第二次入狱,他几乎失去了一切;第三次入狱时,他已是失无可失。
重获自由那天,面对物是人非的景象以及朋友的问候,他浅笑淡然,拍了拍帽檐,一派绅士风度地说了一句,“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话语之间没有任何愤怒、不甘,有的只是对生命深刻的理解和无尽的慈悲。
当然,这份心智上的成熟是历经沧桑后的平静,或许也有他大大方方地从悲哀中走出的艺术家智慧。
鲁迅教会中国人什么是尊严,而木心用行动捍卫了尊严。
1989年,旅居纽约的木心,在学生陈丹青的建议下,为留美的艺术家开设了一门“世界文学史”的课。讲授内容横跨东西,贯穿古今,深受学子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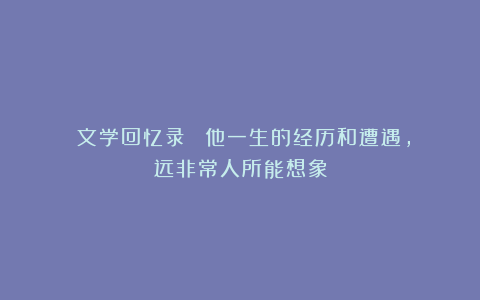
由于课堂是非正式的,氛围自由,学生们常围坐一起,聆听木心娓娓道来,一如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对众弟子传道授业般。
这一课程长达5年时间,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年轻学子们打开了一扇文学之窗。
内容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到印度史诗,从诗经赋比兴到唐诗宋词元曲直至现代文学,涵盖中西文化精髓。
他说有些书要反复咀嚼,譬如《老子》,而有些书则要浅尝辄止,如《楚辞》,并阐述了这么做的理由:前者需深悟其哲理,后者宜领略其辞藻之美。
相类似的见解在课堂上比比皆是,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2012年1月15日,在木心的追思会上,陈丹青应众多读者的请求,将木心5年间的授课笔记整理成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文学回忆录》。
为什么叫“文学回忆录”?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世界文学的历史梳理,更是木心个人心路历程的缩影,记录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思考。
诚如他在开课前所说:“我讲世界文学史,其实是我的文学回忆。”
在书中,木心如是说道:“这是我六十七岁讲的课,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看看,我敢于讲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在六十几岁时读,读了想,幸亏我听了木心的话。”
听了什么呢?世界文学史?
当然不止如此,是一位年逾花甲、历经风雨沧桑巨变的老人对生命、艺术与智慧的深刻洞见,也是他的优雅、干净、高贵与格调。
不可否认,知识固然重要,但融入个人经历中的智慧与感悟,往往更能触动人心,引发灵魂的共鸣。
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明确表达了对《文学回忆录》的赞赏。
他不仅称赞该书内容深邃且不失风趣,还惊叹于木心读书涉猎之广,并笃信如果能亲临现场聆听,必定会非常有趣。
同为节目嘉宾的许子东则以为,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制高点,使大家能够“一览众山小”。
复旦大学教授陈果在一次课堂中,也曾推崇这部书,时常觉得她的心里话都被木心说透了——物质的尽头屹立的是精神。
物质无能为力的终点,恰恰是思想有所作为的起点,物质所不能带来的人生幸福,恰恰只有在思想当中才能尘埃落定。
众多读者更是一致觉得《文学回忆录》是木心留给世人最真诚的礼物,但也有人认为该书观点过于主观,缺乏学术严谨性,抑或觉得其内容食之无肉、弃之无味。
事实究竟如何,想来是见仁见智的。
书和人一样,它也是活的、会说话的东西。既是如此,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木心笔下的文学世界。
或许,正是在这种主观与客观的交织中,木心的文字才显得如此鲜活有魅力,触动心魂。毕竟,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启迪心智,而非其他。
然而,这些都已成为后话。世人对该书的看法如何,又从书中看见了什么,那个头戴礼帽,穿着黑色大衣的老人大抵是不在乎的。他的情感与智慧早已融入字里行间,至于世人如何评说,这就不是他所在意的了。
木心曾说过:“即使到此为止,我与人类已是交浅言深。”
再者,没有人能经历完全相同的岁月,即便身处同一时代,每个人的境遇也各不相同,这是生命的独特之处。
我们之所以能从木心的文字中找到共鸣,是因为他以独特的笔触触动了那些藏于心底、共通的情感与思考,让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感受到了人性深处的相似与呼应。
时间会远去,历史会尘封,记忆会模糊,人似乎留不住什么,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
下周,我们将共读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在中国近代史上,溥仪是一个极具争议和复杂性的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经历了从皇帝到平民的巨大转变,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通过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历史面貌。
领读人 · 零露
专业撰稿人,人生如露,知白守黑。
主播 · 一宁
有声平台主播,用声音传递温暖。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