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贵州学政严修开设贵州官书局(资善堂书局),聘雷廷珍为董事并总理书局事务,首开贵州官府印行图书之例,成为贵州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首个场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修聘雷廷珍为贵阳学古书院山长,从全省招考了40名高才生开班教学,雷廷珍亲授经史。其间,他又在贵阳动议创办了“黔学会”,“约集同人以相讲肄,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雷到兴义笔山书院任山长,也造就了一大批经世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迭请雷廷珍赴武汉执掌两湖书院,次年成行,不幸于途中病故,归葬绥阳。
严修誉雷廷珍为“黔中大儒”“当代通儒”“贵州俊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和《中国书院辞典》《中华教育通史》等史书有传,民国著名藏书家凌惕安所著《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列48位清代贵州名贤画像和小传,雷廷珍“压轴出场”。
一、“贵州俊才”名之于世,必有可堪追溯之源
水有源而木有根,根深方能叶茂。雷廷珍能成为黔中大儒,可以天地人三才造化来说明。
一者“天道赋其异禀,勤奋立志奔大道”。雷廷珍“五六岁时受书家庭,寓目成诵”(《绥阳县志·列传·雷玉峰》),孟子的“立志”理念,于雷廷珍当是烂熟于心,“幼有异志,喜读书”(民国《贵州通史·人物志三·雷廷珍》),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并通过勤勉刻苦学习来实现其志向。同治三年(1864年),绥阳县令邵维新被吴元彪起义军杀死,雷廷珍写了两首《哭邑宰邵维新殉节》的诗,试举其一:“斜阳衰草吊忠贞,白骨抛荒有令名。我既不存何惜死,身虽残毁亦如生。迢遥望阙君知否?朝夕求援眼欲昏。一似睢阳当日惨,英雄今古总吞声。”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对邵维新等他心目中的忠贞之士的深切悼念,也通过对当时困境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身虽残毁亦如生”,对忠贞不渝的追求跃然纸上,而创作此诗时,雷廷珍年方十一,表现出的“天生我材必成大业”之志,已令人刮目相看。
二者“地脉传其灵气,故土文化深根脉”。绥阳人杰地灵,有洋川大坝、蒲场大坝、郑场大坝和旺草大坝相连,山川秀美,土地平阔,溪流众多,雨热同期,系“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在农耕时代最为肥沃富庶地之一。东汉尹珍在绥阳旺草大坝设馆讲学15年,开启文化先河,播下文学种子。明清以来,绥阳还出了108位举人和203位贡生,故绥阳之文化背景在贵州实属蔚为大观。这里是“中华诗词之乡”,雷廷珍浸润其中,诗意的丰富想象力中蕴含热情、激情甚至豪情,其“兴、观、群、怨”功能和“思无邪”的归旨显露无疑。可见雷廷珍在讲学时“敢于破格,敢于疑古”是有几分“诗人气质”的:我讲的是“学”,有何“不敢”?生于斯、长于斯,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饭,走得再远,飞得再高,总有这最初生长地烙印铸就的基因。
三者“家风塑其良才,家庭家教美德传”。家庭家教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雷廷珍的家当然是其“第一教育场所”,为其成长为大儒有着耳濡目染的引导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他的祖母张氏,说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家里房屋忽然变成一口巨井,巨井冒出无数古代竹简书,直至堆满后仍在源源不断地冒(详见《时学正衡》)。无独有偶,明代大儒王阳明出生前夜,其祖母岑氏曾梦见一位身着绯衣、佩玉的神人自云端而来,在鼓乐声中送下一名婴儿,岑氏惊醒后,恰逢王阳明降生(《阳明先生年谱》)。两个梦境虽行差路远,其意象却又异曲同工。雷廷珍的父亲雷锦帆在1864年、1865年时局动乱时,写下一首诗:“国计民生事事攒,水深火热赖谁安?闲来读罢龟山操,且把虞君仔细看。”其情志修为哲思毕现,诗中可见,其父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痛恨官场腐败,表露出有心治国奈无权势的心绪。雷廷珍母亲郑氏“德比孟母”,她艰难抚孤,不惜节衣缩食,购书以供其阅读,并送雷廷珍入书院学习深造。雷廷珍也是争气,坚持寒窗苦读,久久为功,到1888年,34岁的雷廷珍中举(光绪十四年举人)。绥阳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传为雷廷珍中举后自撰:“八石余斗多,到而今天仓满了;三载两年苦,比从前地位高些。”可见雷廷珍家时年并不宽裕,而母亲自任家事,“惟教廷珍以读书学好人”,多么不易。
二、“黔中大儒”躬身笃行,必有匡时济世之举
作为晚清贵州儒林典范,雷廷珍以其毕生实践诠释了儒家“三不朽”精神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为雷廷珍大展身手提供了平台,雷廷珍恰如鸟飞得高天,鱼游有阔海。雷廷珍与严修于1895年相逢相识相知,两人志同道合,联手合力大干一番事业,着力除弊士人皓首穷经只为科举虚名的虚浮作风。雷廷珍在拼搏前行中,对传统“三立”范畴有所创新突破,在时代裂变中重构道德境界、事功维度与学术体系,为贵州的近代化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文化路径,大力推行新学,推进新式人才培养,其成果显而易见。
其一,醇儒风骨,践行士人担当
雷廷珍以儒者自持,“修齐治平”自然是深入骨髓,他对自己要求高、标准严,尤其在德行修养上,时刻以自身的形象带动和示范于世,焕然中华文化道统,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雷廷珍严谨于治学之德。他天资聪颖、勤学苦读,恪守“通经致用”理念,拒斥空谈,严修称其“内探经史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凌惕安高度称赞其“天资之敏,近于陆象山;治学之严,类乎顾亭林”;他的学生董伯平(早年留学日本)评价其“章句追秦汉,学术探洙泗”。他的主张“学必求其有用,言必归于可行”,实为严谨通达之论。
雷廷珍和合于处世之德。他淡泊名利,中举后不改书生意气、学者之风,返黔专心文教,洋川书院、学古书院、笔山书院留下其忙碌的身影。厐思纯在其著作《明清贵州6000举人》称赞他是“洞悉时代弊病又极为爱国的士人”;凌惕安盛赞其“黔人讲学,其敢于破格,敢于疑古者,珍一人而已”。在担任官书局董事期间,他经营管理书局刻印、进货、门市销售一应事宜;担任山长(堂长)时,他摒除门户之见,秉持有教无类。
雷廷珍坚毅于济世之德。他关注民生,心忧天下,尤其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后,在爱国先贤纷纷寻求救亡图存真理之际,作为晚清孜孜不倦谋求以朴学精神矫正虚浮学风之代表,他锐意改革,主张教育界和学术界“通经为体,匡时为用”“合炉而冶,以求致用于现代”。躬耕讲台,并非只为寻章摘句;坐老洙泗,实则力求救国图存。其学生多受其进步思想影响,在清末民初贵州政治、军事、经济特别是教育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利于近代,泽被后世。
其二,兴学育才,奠基黔中教育
雷廷珍身处清末新政与西学东渐之际,时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和教育制度来增强国力,同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雷廷珍于此心领神会。他在推行教育革新的实践中,巧妙地将东方古老的智慧与西方先进的理念相融合,试图为处于困境的中国探寻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致力于以教育实践回应时代变局。
雷廷珍以图书的印制、刊发、广泛阅读为重要抓手,为革新之举储备和充实“子弹”,推动新学。1895年,参与创建贵州官书局,担任官书局董事后,与严修联合草拟了书局章程,汇编图书的目录,明确图书价格,并规定:“凡筹公款兴善举,由绅士经理者,应荐请地方官稽核实数,妥议章程。”为了建立遍及各府、厅、州、县的图书发行网络,书局将现存可销售的图书和即将刊刻的书目印刷出来,每州、县各寄一本,要求各地书院、学宫以公款或其他款项,结合本地需求,拟出订书单寄至书局,约定日期前来书局提书,书局没有的书可由书局向外省运购,代运费用由各地公款内开支。由于交通不便,运费昂贵,图书的实际售价已按原书定价增收了三成。为补贴寒士购书,书局规定,凡是各地读书人亲自到书局购书者,只照原价增收一成,其亏损以各州、县购书的盈余补贴。为发挥有限藏书的作用,书局规定,凡是到书院、学宫借阅图书的,把名字、借阅次数登记下来,以便考察士子和教官的勤绩。
该书局除翻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购进西方学术书籍。流通的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如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有人文科学类,如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览要》《时事新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等。凡书34种,为册9000有余。这些图书开阔了贵州士子的眼界,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将知识文化深入到贵州的各边远地区,对启迪民智和扩大士人的视野贡献甚大,并且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贵州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雷廷珍以改革旧式书院、创办学堂学会、倡导和推行新式教学为重要阵地,推动新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严修到贵州任学政,深感贵州书院既少,教学方法和内容又较为落后,其改革贵州旧式书院的设想日臻成熟。他首先倡议变通书院,然山长人选,久不能决。严修屡次劝说雷廷珍主持改革后的学古书院,但雷廷珍一再推辞。后来严修再次恳切劝说:“细数黔中人才,山长之职非先生莫属。”鉴于严修一片诚心,雷廷珍走马上任,为贵州新学展开序幕。
雷廷珍出任山长后,积极配合严修,拟以“辩志”“明师”“评文”“匡时”为主题策论。随即,他与严修等人草拟了招生文告和学堂章程,发往各府,在全省考核选拔,录取40人。经世学堂成了贵州历史破天荒之创举,比维新派在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和北京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分别早了半年和一年多,开了风气之先。为了加强管理,雷廷珍拟订了《学古书院肄业条约》,经严修反复修改后发布施行。雷廷珍除了主持书院工作外,还主讲经学,严修教数学课,书院时务、英文、格致、地理等课都聘著名学者任教。
经世学堂的创办,开创了贵州新学,培养了一批粗通代数、微积分、英文、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人才,畅通了西方科学文化在贵州的传播道路,培养了贵州一批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先行之士。同时,雷廷珍发起以引进西学、振兴贵州文化为宗旨的黔学会,倡导入会者研究传统经学、历史、文学和新近传入的数学、格致等新科学。学会订阅《时务报》《日知报》等新学杂志,集中贵州士子共同讨论天下大事,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与强学会、苏学会、南学会等遥相呼应,使贵州闭塞风气为之一变。桃李成蹊自无言,他担任山长期间,培养出姚华、刘显潜、周恭寿、华之鸿、任可澄、戴戡、周素园等上百位黔中名士,为贵州近代转型储备了治世人才。
黔西南声名显赫的刘官礼(云南候补道)为谋求家族更大发展,先是让子侄到贵阳经世学堂学习,后来重修兴义笔山书院。1899年,刘官礼诚请雷廷珍及其学生姚华、熊继先、徐天叙等名师到兴义执教,雷廷珍为首任山长。雷廷珍有一项工作是订购《时务报》供学生阅览,规定学生每月两次呈送笔记批改,发还时当堂讲评发奖,这一项扎实的举措,成效立显。
雷廷珍在笔山书院3年,成就突出,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气相求,邀其前往武汉执掌两湖书院,惜于途中病逝于重庆。后继有人,他的学生姚华、熊继先、徐天叙先后出任笔山书院山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原山长徐天叙带领魏正楷等13人投考贵州省公立通考中学,并且以前13名入选,名震全省教育界。后来,笔山书院培养了许多学生到日本留学,有进入日本中央大学的、早稻田大学的、明治大学的,有进师范专科学校的,也有进振武堂和士官学校的,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医学,何应钦、王伯群(师从姚华)、李儒清、刘若遗等军界、政界、教育界、商界知名人士,都是从笔山书院走出来的学生。民国《兴义县志》称,“留学生之多,声誉兴隆,甲于全省”。无疑,这与雷廷珍等一批名师的执教是分不开的。
其三,经世致用,熔铸黔学精魂
雷廷珍著述立足地域,贯通古今,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著有《时学正衡》《经义正衡》《文字旁通》《诗意旁通》《声韵旁通》等著作。其中“正衡”的意思是匡正、衡量、评判,“旁通”有广泛通晓之义。从这些著述可见,雷廷珍之学,广泛而深入,饱含疑古和创新的精神,其学术既接续乾嘉朴学传统,又暗含近代转型意识,堪称“黔学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里程碑”,雷廷珍有此根柢,实不愧为推动新学、培养新式人才的优秀学者。
雷廷珍对晚清学风作出深刻的评判,希望匡正时人只为走科举之路皓首穷经而不图实用于治国理政、不吸收西方学术为中国注入新鲜血液的落后学风。其著述《时学正衡》,开头的概说部分,分析时局和落后学风,提出“今人之为学必综天下之学术”,以及“志与道合,学与志合,业与学合,体与用合,用与道合”的学术观点;主体部分提出高等学校肄业的十项条例,即原学、端本、探源、辩体、考文、征事、数典、通义、炼才、游艺。最后总结:无论古今人才有何奇异,使国家富裕的都是农、工,而真正使国家富裕的又不是表面的农、工;使国家强大的是船、炮,而真正使国家强大的又不是表面见到的船、炮。综览五大洲农、工、船、炮的技艺之中,有一些奇异而能使危险局势或即将倾覆的国家转为稳定的人才,并不稀奇。无论时间怎么变,必须有学人坚定意志,集中精力,开启智慧,增长才识,不要在富贵、贫贱、屈伸、强弱之中醉生梦死,而不能自立,无所建树,而辱其所生。所以学习经术的人,就应该辅助处理时政,而不是仅仅提出指责和批评。
雷廷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是深入而深刻的,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和注解,体现出了其对儒家思想的独到见解,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他的著述《经义正衡叙录》,重点就是匡正经学。他将经学分为四个部分。他说《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如天空一样没有不能覆盖的地方,如大地一样没有不能承载的物体。参照天地运行规律,帮助天地展示出化育万物的力量,就是合乎时宜而无过与不及的圣学。《孝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荀子》,传导了五经的深刻内涵,可以定为贤学。《礼经》的《大戴记》《小戴记》和《周官》,《春秋》的《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与《易经》《尚书》《诗经》的今古传注,都是在解释经传章句的意思和思想,可以定义为士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及其形、声、义,用以解释经传的文字,可以定义为士学中的小学。这种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对后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具有积极作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晚清时期贵州推行“新学”,雷廷珍与严修合作,创办新式学堂、编写教材、推广新式教育理念,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努力提供了实践支持。其中,雷廷珍的生平事迹、工作实践和学术思想留下的优秀文化精神,可资我们借鉴。
雷廷珍以“三立”为标杆,践行儒家理想,在传统崩解之际坚守士人精神,树立了区域文化典范而立德;突破地理封闭,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文化转型而立功;构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使黔学跻身近代学术版图而立言。
雷廷珍所折射的光芒,同张锳、张之洞父子的“加油文化”一脉相承,是坚强的传承和接力,不愧为学者型教育改革实干家。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坚守兼容并蓄的文化根基,文脉才能传承,才能长出文人巨木、丰茂文学森林,支撑文化天地。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
「李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任岭,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
一
“加油文化”在孵化和传承中,姚华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姚华原名学礼,字重光,号一鄂,晚号茫父,别署莲花庵主,世称弗堂先生、秋草诗人,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祖籍江西抚州,五世祖入黔。父源清,贩商维持家计,尚能温饱。姚华五岁发蒙,从广顺学正姚荔香先生学。十岁时,父延师入室教馆,尝精习段玉裁先生的《说文解字注》,几能成诵,打下深厚的小学根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应童子试,竟以“三鸟群飞一鸥翔”夺魁,成秀才入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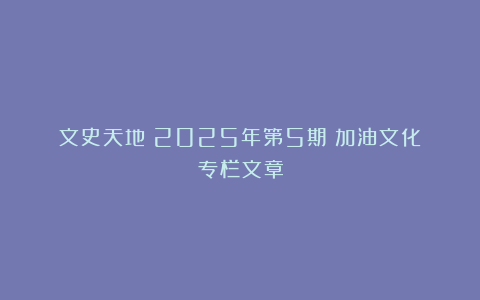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任贵州学政的津门严修锐意新学,遵张之洞在成都改革尊经书院制,对贵阳的学古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世称“经世学堂”),向全省公开招考生徒,首批择优录取了40名。其中一名高材,即是年贵州乡试的举人姚华。严修厘定《学古书院肄业条约》,姚华亲笔将其书碑镌刻,立于院中,以垂教训。
严修任贵州学政期间,秉承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积极开办书局,改革书院,革新考试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聘请“黔中大儒”雷廷珍(1854—1903年)担任贵州官书局董事并主持工作,同时担任学古书院的山长。二人合力推行以经史、数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地理、英文、格致等科目的新式教育(《文史天地》2024年1期《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
考入经世学堂(即学古书院)后,姚华精心从山长雷廷珍研习经学,更泛览并精研传统的经史子集、五典三坟,学业大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姚华入京会试,不幸报罢(落第)。回筑后,潜心汉学研究,旋著《说文三例表》《小学问答》二稿,在贵阳学界已初试牛刀、崭露头角。贵阳学子如陈筑山、文宗潞、熊继成、黄韵谷等,纷沓而来,拜伏门下。
雷廷珍在严修卸任贵州学政后,便离开贵阳经世学堂受邀到兴义县出任笔山书院山长,他把学古书院新式教育的模式、经验,全部搬到笔山书院。后雷廷珍受张之洞邀请去武汉执掌两湖书院。离开兴义前,雷廷珍推荐了自己的弟子姚华前往兴义,执掌笔山书院,1902年农历二月姚华受聘担任笔山书院山长(《文史天地》2024年1期《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
姚华以自己在经世学堂所学,并以自己深厚的学问功底、广博的知识、精湛的书画技艺,一丝不苟,认真执教。而且亲自编撰《笔山讲录》《佩文韵注》两书,以作教材。同时还指导学子阅读宣传新思想的《时务报》。
兴义地区的许多优秀学子,如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皆出其门下。
二
姚华长笔山书院教习仅一年,便辞职赴京赶癸卯(1903年)科春闱会试。真是时运不济,此次会试仍然名落孙山,因川资紧迫未能回筑,只得滞留京师。先是卖书画谋生,旋受聘为顺天工艺学堂印书科员兼国文教习。次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恩科,也就是中国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年历史的最后一科,姚华终于赶上了末班车,总算高中进士。时值庚子赔款之事,姚华更是感慨万端,才有“洗劫经庚子,春闱又甲辰”的诗句,抒发中进士的复杂心情感受。
姚华中进士后,即被分发工部任虞衡司主事。姚无心做官,旋由进士馆出资去日本留学,就学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攻读政治法律,一年后毕业转入银行讲习科学习。在学校,姚华结识了志同道合的范源濂、陈叔通、周大烈,另有乡友蹇季常等人。大家都抱着“志学能藏用,图艰欲济时”的理想,埋头苦学。多人都据其所学,或翻译,或编著,进行艰苦的著述。姚华写出了《银行论》《财政论》两书稿,陈叔通亦写出《政治学》《法学通论》两著作,后分别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为当时国人学习法政者之先导。姚华还时时以自己精湛的书法技艺为日本友人写字,深受日本各界喜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姚华在日学习期满,以优等成绩毕业归国。次年,先被任命为邮传部船政司主事,旋改任邮政司建核科科长。时邮传部的一些官员,多迷于戏曲,姚华根据多年对诗词曲的研究成果,对戏曲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有为的是,他从文字学、书法绘画艺术的角度,深入剧院现场访察,对京剧脸谱的芝术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引起了京剧界很大的震动。当时王瑶卿、梅兰芳等一代名伶,皆拜伏门下,以师礼事之,并结为“兰石”。不仅如此,姚华还在多所学校任教职。初到邮传部时,即在殖边学堂任教,继与范源濂、雷学兴、孟容生等发起“尚志学会”,并纳入陈叔通、邵仲威设立的法政学堂,姚华亲临学堂任教,对学子循循善诱、认真执教。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以“庚子赔款”退款为资金组建成立“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范源濂为第一任校长,即聘姚华为国学教习。姚华家住北京城南莲花寺,到西部“清华园”上课,道途有20余公里,光坐马车,来回也得五六个小时。每当授课日,真可谓鸡鸣即起,子夜方归,辛苦异常。
三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清帝退位,民国已降。
姚华的许多老友皆在文化教育部门任要职。范源濂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接着又返北京继任总长。就连画界老友陈师曾(衡恪)也供职教育部,主管全国美术事业。姚华初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然已无心政治,更厌弃官场,一心只想专门治学,埋头艺术,潜心学问,或教书以育青衿。先是黄远庸聘姚为《论衡》杂志“文苑”栏主笔,并编审稿件。姚华撰《艺林虎贲》在《论衡》连载。还为《庸言》撰写三部论著:文字学《书适》、文论《曲海一勺》、戏曲理论《菉猗室曲话》。民国二年(1913年),受教育部聘,姚华出任“全国语音统一委员会”委员,连续工作数年,撰述《翻切今纽六论》,阐明汉字的读音、命名、声母、四声等音韵学的知识,又为汉语注音字母厘定“一篆、一草、一正二体书式,注音字母采用正书体”。后“委员会”集专家于京师,公定字母以表国音,汇为一集曰《国音汇编》。姚华与鲁迅等二十余位语言文字学家,为中国开创汉语改革语音统一,均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民国初年,姚华除“清华园”的教职外,还任教于民国大学、中华大学(即原北京私立法政大学)、朝阳大学等多所院校,专门讲授国文和书法、绘画等艺术课程。此时又撰《中国文学要义》一书,以作讲稿。民国三年(1914年),教育部委任姚华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妇女解放和中国早期的女子师范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亲自讲授多门课程外,他还专门聘请名师为教,如聘请陈师曾教博物、聘请日本专家教家政,等等。最有趣的是,他亲自“以钢琴调子”,为学生谱写了六七首歌曲,让学校运动会和毕业典礼时都有歌可唱;为每一位毕业生书写墨盒一方,由琉璃厂篆刻高手镌刻,时人视为珍贵纪念,争相收藏。姚华在掌“女师”之时,除兢兢业业工作外,还要警防各方面“明枪暗箭”的伤害。当时任“女师”学监的杨荫榆,投靠北洋军阀,争权夺利,为所欲为,常制造事端,为校长姚华设置障碍,使姚华感到举事危艰。于是在民国五年(1916年)12月,姚华愤然辞去“女师”校长之职,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讲席。此事当今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专门作过研究,早已作了公允的述评。待到十年后杨荫榆主校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为之写下了千古绝唱《为了忘却的纪念》。是时曾任过该校校长的姚华,更是悲痛无比、义愤填膺,愤然作《二女士》,沉痛哀悼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爱国女学生。其诗云:
宣和不闻陈东死,南渡胡为死东市。
千年夷夏祸犹存,碧血又渍绿窗史。
呜呼!刘、杨二女士!
四
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名流大力倡导“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教育部决定在京创办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次年,学校建成,姚华辞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之职,与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师级艺术家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等,被聘为该校教授,专门从事美术教学。姚华、陈师曾两位大师,在校坚持中国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强调“功夫在画外”的主张,以此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美学艺术修养,且不断提高书画艺术技巧。两大师又联络来华访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大村西崖教授,三人意气相投,言必契合,对艺术的见解更为默契,竟合作《中国文人画研究》一书,由中华书局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版发行,是为中国绘画理论的重要文献。是时,北京画家组织有中囯画学研究会,姚华、陈师曾皆为该会骨干。该会又被认为是“绘画教育单位”。现代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已故教授启功先生,就曾为姚华题诗,其首句为“记得髫年拜弗堂”。说明启功先生早年曾在此拜姚华为师,向姚华学习书法。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在陈师曾谢世后仅8个月,姚华发起,约集在京的著名画家齐白石、陈半丁、王梦白、凌直支等以及画界同仁数百人,汇集作品千余件,在北京樱桃斜街老贵州会馆开画展大会。日本画家小石翠云等也到会交流。时值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来华到会参观,并发表了演说。后泰戈尔又专程到莲花寺访问姚华,作了真诚的交流。徐志摩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泰戈尔曾问梅兰芳“对绘画曾下过功夫?”梅告之:“那天出席的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师。”泰戈尔把姚华的画带回印度,陈列在他们美术馆。后来姚华也将泰戈尔散文诗名著《飞鸟集》,用五言古体改写成《五言飞鸟集》,堪为中国诗歌翻译之创举。《五言飞鸟集》后得出版,封面竟刊出“姚华演绎”。
正值这一年,北京国立美专的第一期学生毕业,该期毕业生是为美术师范专业。当时国内美术专门学校甚少,学生谋职相当困难。身为美专教授的姚华,为了安置这批得意门生,解决其“饭碗”问题,决定自立,另外创办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于是又约集美术界的众多名流,多方筹措资金,其子姚鋆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也积极参与学校的创办工作。学校旋即建成,取名“北京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时人以“京华美专”简称,公举姚华任校长。教务由原国立美专的毕业生邱石冥担任。姚华多年来结交的美术界许多名流,也多在京华美专任教。
姚华还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绘画艺术、词曲创作的理论技法如“颖拓”“别子为祖”等等,认真传授给学生。学校的教学质量之高,可见一斑,培养美术人才等成就,更是誉满京都,国人有口皆碑。原国立美专姚华的学生方伯务,毕业后,在京华美专任教,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1927年,与李大钊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成为革命烈士。姚华曾作诗,以示沉痛悼念。及后的20多年,学校一直办得红红火火,即使在校长姚华仙逝后,京华美专亦后继不乏,可谓人才辈出。
五
1952年,京华美专由姚华的学生高希舜主校,并入了国家公办的中央美术学院。姚华等先生创办的京华美专,从此在北京的图舆上消失了,至今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仍能找到一些记忆。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17日,姚华突发脑溢血,经京中德国医院抢救,虽免一死,然已半身不遂。后坚持锻炼,仍坚持创作,坚持教学,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8日西归道山,与世长辞。
综观姚华先生的一生,起自“荒服”,工诗文,通词曲,善书画,喜碑刻,创颖拓,在文学、文字学、教育、翻译领域皆有创获,被誉为“旧京都的一代通才”。成名京师,誉满华夏,名扬海外,著作等身,桃李遍布天下。
早在兴义“朝夕请业”的弟子王伯群,当年以交通部部长的身份,不仅亲到莲花寺拜望先生,并将姚华一生的诗、词、曲、赋、文等,组织编辑,共31卷,并亲作序,出资由中华书局刊行,名之曰《弗堂类稿》。后,弟子郑天挺教授刊行《莲华庵诗画集第一册》并作序。贵州《黔南丛书》辑其《庚午春词》和“散曲”合编印行。在20世纪50年代,陈叔通还编有《贵阳姚茫父颖拓》一书,名家题跋甚伙。后陈将其赠送贵州博物馆珍藏。
鲁迅评道:北京书画笺“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鲁迅书信·1933年10月2日致西谛》)
郭沫若题词评道:“规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规摹金石刻画者,能不谓之画乎?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叔老(陈叔通)特加珍护,匪唯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一九五七年元月。”(《贵阳姚茫父颖拓》)
郑振铎评道:“在民国初期的画坛上,北京的陈衡恪、肖愻、姚华等重要的画家们,都有大胆的、创造性的艺术劳动成果。”(《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发展》)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
「谭佛佑,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南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
版式:刘 丹 李 楠
责编:王封礼
审核:姚胜祥
总监:丁远红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