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听 图/刘洪听
一、唐诗中的“胡腾舞”
全唐诗中涉及到“胡腾舞”的诗作共有4首,诗人李端、刘言史、元稹和白居易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胡腾舞”进行了赋写: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李端《胡腾儿》)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设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元稹《西凉伎》)
客有东征者,夷门一落帆。二年方得到,五日未为淹。在浚旌重葺,游梁馆更添。心因好善乐,貌为礼贤谦。俗阜知敦劝,民安见察廉。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闾阎。文律操将柄,兵机钓得钤。碧幢油叶叶,红旆火襜襜.景象春加丽,威容晓助严。枪森赤豹尾,纛吒黑龙髯。门静尘初敛,城昏日半衔。选幽开后院,占胜坐前檐。平展丝头毯,高褰锦额帘。雷捶柘枝鼓,雪摆胡腾衫。发滑歌钗坠,妆光舞汗沾。回灯花簇簇,过酒玉纤纤。馔盛盘心殢,醅浓盏底黏。陆珍熊掌烂,海味蟹螯咸。福履千夫祝,形仪四座瞻。羊公长在岘,傅说莫归岩。眷爱人人遍,风情事事兼。犹嫌客不醉,同赋夜厌厌。(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韵》)
图1—1北齐“胡腾舞”银饰扁壶
(一)诗人眼中的胡腾舞姿
从这些诗作来看,刘诗“跳身转毂宝带鸣”句,与李诗“环行急蹴皆应节”句,均是对舞姿的动态描写,表明“胡腾舞”不但多有腾跳、旋转动作,而且脚部动作也较为繁复。“双靴柔软满灯前”与“弄脚缤纷锦靴软”句,两位诗人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锁定在舞者的脚部动作上,再次印证了舞者脚下动作很有吸引力,诗中舞者脚穿长靴,动作琐碎繁杂、小范儿灵活、刚柔相济、快慢交织,让人眼花缭乱,似乎让人产生了幻觉,难以分清哪里是灯,哪里是舞者的脚。此处诗人还指出了舞蹈的时间是在晚上,这可与白诗“回灯花簇簇”、刘诗“残月”相互印证,证明三位诗人皆是在晚宴中欣赏到的“胡腾舞”。李诗“扬眉动目踏花毡”句,是对舞者头部及面目神态的描模,舞者并非机械呆板的表演,而是“摇头撼目、或踊或跃、乍动还息”(杜佑著,颜品忠等校:《通典·乐典》,湖南:岳麓社社,1995年版。)面部表情丰富,以至于达到了眉目传情的艺术效果。而“摇头撼目”通常是舞者头部动作较多,身体动作较少,在头部和颈部晃动的同时,也伴随有眼睛和眉毛的动作,这在今天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舞蹈中依然十分常见,舞者利用眼神来传情达意,以使舞蹈更加精彩诱人,也让观者增加了参与感。
图1—2北齐“胡腾舞”银饰扁壶 (高斯琦手绘)
李诗所谓“环行急蹴皆应节”大概同张庆捷先生所言,舞者的舞蹈幅度有限于毯子的面积,但刘诗有“跳身转毂宝带鸣”句,这就意味着舞者是有旋转动作的,而且旋转速度如车轮般快速,就连腰带上的配饰都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从“蹲舞”、“跳身转毂”、“弄脚缤纷”“乱腾新毯”看,“胡腾舞”不仅给观者带来了速度和激情的快慰,还透露出舞者对低、中、高三层舞蹈空间的合理运用,以至于达到“皆瞠目”、“观者悲”的演出效果。其中“乱腾”一词是指舞蹈动作非常的激烈,是舞蹈的高潮部分,舞的也最快。此时的配乐也是快速的“遍头促”。向达先生认为:“环形急促”、“跳身转毂”是“胡腾舞” “大率动作甚为急剧,多取圆形”。(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页。)张庆捷先生进一步解释“多取圆形”的原因是:“从虞弘墓石堂图像中可以找到原因,是因舞者只限于在一小圆毯上舞蹈”。(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山西:山西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39页。)向、张二人就史料而言,各自述说皆能令人信服,但由于受到文献或图像资料的限制,其描述均略显单薄。向先生所谓“多取圆形”不无道理,张先生所云“舞者只限于一小圆毯上舞蹈”也未尝不可。关于舞者脚下所踏舞筵的具体形制下文有专门论述。而就上述二人解说笔者以为,“胡腾舞”不仅是受到圆毯的限制而“多取圆形”,而是舞蹈自身也有绕圆而舞的动作,况且也有很多在空地上舞蹈的“胡腾舞”形象。张先生认为虞弘墓中踏圆毯而舞的舞者,是诗句“乱腾新毯雪朱毛”、“扬眉动目踏花毡”的正解,笔者以为大致无误,但至于“新毯”与“花毡”具体是何种样式的毯子,因诗文语焉不详,尚且存疑。
图 2-1陕西西安出土唐代苏思勖墓胡腾乐舞图
李诗“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与刘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描述的是酒干舞罢、肴核既尽、残月高悬、东方既白的宴会结束时的场面,同时也可从两位诗人的诗句中看出,“胡腾舞”是整场宴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唐人在描绘曲终人散时,通常用“画角”一词来表示夜深人静,如章碣《陪浙西王侍郎夜宴》的末句“小儒末座频倾耳,只怕城头画角催”。李诗有“反手叉腰如却月”句,关于此处的舞蹈动态,笔者试作三种推测:一、如按照向达先生的猜想:“首足如弓形,反立毯上,复又腾起”。可以设想,此种舞姿的动态形象与今天的男子技术动作——小翻儿极为相像,亦或小翻后紧接双飞燕,并且还有可能是一次连续翻了两个以上,如此以来,舞者既能呈现“叉腰”之态,又能展现“却月”之姿;二、从舞蹈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纵然是男性舞者也很难保持以“却月之姿”来进行“环形急促”、“转身跳毂”等舞蹈过程,笔者推想这种舞姿可能是舞者将身体腾于半空后,以胯部为轴心,上半身与下半身在最大范围内相互对折、贴近,双手在空中相扣或相握,双腿交叉或相并,这样舞者的身体可在空中形成优美的弧线,也可呈现“却月之姿”与“反手之态”;三:诗人往往喜欢以夸张、想象的手法来描摹事物,“反手叉腰如却月”的舞姿形态既是诗人在观看了“胡腾儿”的表演后,将自己脑海中的舞蹈过程加以回想、连缀,故而形成“反手叉腰如却月”的舞蹈形态。因为笔者在观摩比对数十幅“胡腾舞”图像后,并未发现有任何一幅舞姿与诗人的描述完全吻合,没有发现用手(或反手状)叉腰同时又身如却月的造型。图像中有多处叉腰舞姿,如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胡腾舞”姿、宁夏灵武北齐彩绘扁壶上的胡腾舞形象、陕西礼县唐昭陵陵园出土的玉铊尾“胡腾舞”形像等。也有双手相扣于头顶,整个身体呈现却月一般的情态,如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玉板带“胡腾舞”、河南安阳北齐修定寺“胡腾舞”浮雕、西安丈八沟唐代窖藏出土伎乐纹白玉带铊尾“胡腾舞”形象,上述舞姿形象均是双手相连、身呈“却月”,但唯独不见诗人所谓“反手叉腰如却月”式的舞姿动态。
图2-2 唐代苏思勖墓“胡腾舞”(高斯琦手绘)
从刘、李二诗看,刘诗中所说的“蹲舞”可能是舞者蹲下来舞蹈的动态,这种舞姿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粟特石棺床上有所体现,在唐代众多的玉板带组合中也多有体现。所谓“急如鸟”,亦如前文所述,有蹲身则必有起身,此处可能是舞者快速的蹲起动作。刘诗“手中抛下葡萄盏”与李诗“醉却东倾又西倒”,都说明“胡腾儿”是在饮酒之后才开始起舞,这里与元稹所说的“胡腾醉舞筋骨柔”,白居易所说的“过酒玉纤纤”句不谋而合,均有在酒宴中观舞取乐、以舞助兴的意思,而且李端诗句中有表现“胡腾舞”醉酒后的步态,同时,元稹诗也为我们营造了一番舞者醉舞的景象,一幅舞者在醉意浓浓中起舞的画面复现在眼前。只见那筋骨柔软且富有弹性的粟特美少男在昏暗的灯光下激情舞动着,一会旋转,一会跳跃。而在已知的“胡腾舞”图像中,也有很多表现“胡腾舞”与酒的关系的,例如,在粟特扁壶上出现的众多胡腾乐舞的画面,而粟特扁壶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用来盛酒,还有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等众多墓葬均有宴饮乐舞场面。其中形象最为生动的就是唐代鎏金“胡腾舞”佣,舞佣身后背着一个酒葫芦,其右手正举着来通杯,做出一副正欲饮酒的模样。如果将李诗“东倾西倒”句、刘诗“葡萄盏”句、元诗“筋骨柔”句加以纵向连缀,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逐渐递进的、水到渠成的剧情展现,即舞者经历了从祝酒——小酌——初醺——豪饮——大醉——抛盏——狂舞,这样一个次第分明起舞过程,伴随着舞者个人情感升温,其演绎情境也经历了致语——拾襟搅袖——转身跳股——弄脚缤纷——环形急促——乱腾新毯——东倾西倒——反手叉腰——扬眉动目——红汗交流——酒阑舞罢——城头画角,这样的歌舞场景。
图3陕西礼县唐昭陵出土唐代“胡腾舞”玉板带
(二)诗人眼中的胡腾舞音乐与服饰
将刘诗“横笛琵琶”句与墓葬中的乐舞图像结合,再将史料与之互证可知。“胡腾舞”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横笛、琵琶、箜篌、铜钹、筚篥、排箫、筝、笙、拍板、洞箫、曲颈琵琶、腰鼓、方响、答腊鼓,还有击掌为节和现场唱和的情况。通过观察大量的图像资料,胡腾舞在演出时所使用的乐器或多或少,可根据具体需要自由组合,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横笛与琵琶。关于胡腾舞伴奏乐队具体使用的是何种乐曲,任半塘先生曾指出:“胡腾之乐曲,可能为凉州大曲,亦可能为醉胡子杂曲”。(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45页。“醉胡子杂曲”在《教坊记》中有所载述,在陈旸的《乐书》中也记载有童舞“醉胡”的舞服,该曲在今天的日本国尚有流传,日本伎乐团体将其称之为“醉胡”、“酒胡子”、“酒公子”、“胡饮酒”等,是取胡人醉酒之意,日本正仓院至今收藏有演奏“醉胡子曲”时的服饰——“醉胡袍”。任先生认为:“胡腾之舞则刚柔相济,胡腾之乐又胡汉交融”。(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页。)若依任先生之言,胡腾舞的伴奏乐器是胡汉皆有,这在已见的胡腾舞图像中也得到了颇多印证,在众多的胡腾舞演出场面中不仅有筚篥、箜篌等西域乐器,也有排箫等汉族乐器。
图4隋代虞弘墓后壁“胡腾舞”者(高斯琦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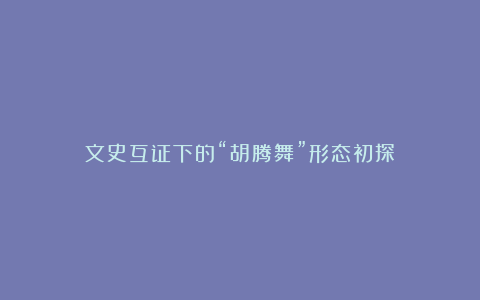
刘诗的“织成蕃帽虚顶尖,细㲲胡衫双袖小”句,与李诗的“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描写胡腾儿所穿服饰的。刘诗中的舞者头戴虚顶尖帽,身着窄袖翻领长袍。需要注意的是,两位诗人虽然都是描绘舞者服饰,但又不尽相同,刘诗所云“细㲲胡衫双袖小”说明舞者所穿为窄袖式舞服,唐代鎏金胡腾舞佣所着服饰即为“小袖”,其中,“㲲”指是中亚的木棉布;李诗“桐布轻衫前后卷”以及白居易诗“雪摆胡腾衫”,实则为“大袖”式舞服,其中的“桐布”则指的是白㲲,即白色的木棉布,唐代苏思勖墓、五代冯晖墓中的“胡腾舞”者都是“大袖”式的服装。这说明“胡腾舞”的服饰既有窄袖长袍,也有宽袖长袍。而就舞者帽饰而言,刘诗中舞者戴的是边缘饰有“织成”( 笔者注:“织成”,也叫“织绒”、“绒”,是古代一种以彩丝或金缕织出来的名贵织物,这种织物主要用于皇家贵族服装上的奢侈品,清人任大椿在《释缯》中解释:“不假他物为质,自然织就,故曰织成。”)的虚顶尖帽,李诗中舞者戴的是缀有珠饰图案的粟特式胡帽。舞者帽檐无论是以“织成”为饰还是点缀以珠,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舞动的效果,使舞蹈产生流光溢彩的艺术效果。此外,当时舞者腰间系带形象十分常见,而且大都束着带有葡萄叶图案的黑色长带,常端常常掖在腰间,如李瑞诗“葡萄长带一边垂”句。
图5唐代“胡腾舞”玉板带拓片(高斯琦手绘)
李诗中的“踏花毡”、“环形急促”句,刘诗中的“乱腾新毯”句,白诗中的“平展丝头毯”句。都是对舞者脚下所踏之毯的描绘,结合图像资料来看,“胡腾舞”多是在舞筵上起舞,而舞者脚下所踏之毯则不一而足,有圆毯,如冯晖墓、虞弘墓中的舞者以及大量的唐代玉板带上的舞者;有方毯,如唐代苏思勋墓中的舞者;有脚踏莲花台的舞者,如唐代鎏金“胡腾舞”佣;也有脚下无毯的舞者,如安伽墓中的舞者。李瑞诗“葡萄长带一边垂”句。舞者腰间系带形象十分常见,而且大都束着带有葡萄叶图案的黑色长带,带端常常掖在腰间。李诗“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句与白诗“高褰锦额帘”、“过酒玉纤纤”句。其中的“帐前”、“锦额帘”、“过酒”,均预示了舞者是在室内起舞。这在已出土的粟特贵族墓葬中,就有很多墓主人在帐篷里饮酒,舞者在帐篷前跳舞的场景。“本音语”大概系指舞者在起舞之前先一边略蹲,一边用粟特语致词问好,介绍所跳之舞,这很像是宋代队舞“竹竿子”在引队和遣队时的致语,也有类于如今节目主持人的报幕环节。舞者不仅腰间系有黑色长带,往往双肩有锦帛飘飞,“拾襟搅袖”说的是舞者所用绕肩锦帛以及手臂上的长袖随风飘摆,但不论是“搅袖”还是甩袖,都必须先“拾袖”,即先将长袖收回手中,才能甩出或进行搅动。
图6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鎏金“胡腾舞”纹银香宝子(高斯琦手绘)
从唐人诗词来看,“石国胡儿人少见”与“胡腾身是凉州儿”句所指胡腾儿应系故乡为中亚的石国人,前者应是寓居中原的粟特少年胡儿,后者当是长期流寓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粟特胡儿。向达先生用以诗证舞的方法,曾就刘、李二诗作解道:“就刘、李二诗观之,胡腾舞大约出于西域石国,舞此者多属于石国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李诗又云“肌肤如玉、红汗、腰如却月”,可知其所见舞伎是一位粟特美少年。若“石国胡儿”与“凉州胡儿”相比较,显然前者是更加地道的粟特胡儿。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有:“据李诗,此剧演于洛阳,演员用真胡儿”的推测,这一结论与向达“胡腾儿为印欧族之伊兰种人”的观点颇为相似。再从出土文物来看,在北周安伽墓、北周史君墓、隋代虞弘墓等大型粟特人墓葬中均发掘了大量的“胡腾舞”形象。故若论“胡腾舞”的源出之地,向达、任半塘二位先生所言所考所证皆令人信服。但综合史料与图像看,“胡腾舞”虽从粟特石国传入中原,但这并不能说“胡腾舞”仅就石国一邦所有。种种迹象表明,安国、史国、鱼国等粟特国家均有粟特舞蹈流行,也极有可能是“胡腾舞”的原产地,只不过是石国的“胡腾舞”流传最广,也最受欢迎。
图7北朝“胡腾舞”纹饰粟特石棺床(高斯琦手绘)
李诗末句“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此句似拮问舞者,实则是诗人暗自神伤。唐代宗时,河西、陇右二十余州被吐蕃占领,留寓该地的胡人再次飘无定所,以歌舞为生。诗句饱含作者对国土丢却的哀伤,这又与元微之的《西凉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刘诗所云“西顾忽思乡路远”与李诗“故乡路断知不知”,白诗“泣向狮子涕双流”、“哀吼一声观者悲”。所寄托的是同一种情愫,这其中既有对“胡腾儿”背井离乡现实的关照与同情,也有诗人痛失国土的忧愤情怀,诗句互为映衬,歌舞相互弥彰,此处的舞蹈和伴奏应都是抒情的慢板,以便表达舞者舒缓低沉的情绪,恰好可与快板的急速、热烈形成鲜明对比。
二、唐诗其他史料中的“胡腾舞”
除了上述诗人对胡腾舞有所赋写以外,通晓音律的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将“胡腾舞”划归为唐代“健舞”。其所撰《乐府杂录》是一部乐舞史料论著,该杂录成书于唐朝末年(894年),收录了唐代以前的乐舞情况,是研究唐代音舞、舞蹈、百戏的专门著作。段氏是唐代的显贵大族,其父曾为掌管礼乐的太常寺少卿,其祖父更是官职宰相,他本人也是国子监司业,诗人温庭筠的女婿,他自幼善通音律,颇知乐舞,故而能撰《乐府杂录》。其中,《乐府杂录》舞工条载:“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缀,舞延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如段氏所言,他把来自西域舞风雄浑健朗的胡腾、胡旋、阿连、柘枝等舞列入“健舞”,这与成书于盛唐时期的《教坊记》有很大不同,盛唐崔令钦编著的《教坊记》主要记述了唐代宫廷教坊的构成、流变及乐舞名目,还有乐舞伎人的生活状况及演出状况。其书载:“《垂手乐》、《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由是观之,二人所列“健舞”共有11种,“软舞”共有13种。但仅“柘枝”一舞,两人均将其列入“健舞”类。两书所列舞蹈名目相差甚远,这说明从崔令钦到段安节,从盛唐到唐末的百余年间唐代舞风发生了很大的流变,其舞蹈种类的归属也会伴随着舞蹈风格的流变、发展而不断更新。如中亚传来的柘枝舞在历经了百余年中原舞风的浸染后,由原来铿锵刚劲的健舞柘枝演变发展出了婉转柔美的软舞屈柘枝。其中,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拂林舞、大渭州、达摩支等均是来自西域的乐舞,这些西域乐舞占据了“健舞”总量的一半以上,名目众多的胡舞在中原的传播与盛行大大影响了唐人对舞蹈的分类。胡舞的奔放、狂野、厚重、直爽、坚实、铿锵、刚劲、雄健、朴实、古拙、洒脱、矫健等风格特点,深刻的影响到有唐一代的舞蹈审美趋向。
图8北朝史君墓“胡腾舞”形象(高斯琦手绘)
三、宋及宋以后史料中的胡腾舞
宋元之际学人马端临(1254~1323)所撰《文献通考》载:“健舞曲有大杆、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有凉州、苏合香、柘枝、团圆旋、甘州等。”同书又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䩞鞢,戴毡帽……”(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卷,第4403页。)马端临不仅将胡腾舞划为“健舞”,更将其列为宋代队舞小儿队当中。陈旸也在《乐书》中记载了舞“醉胡”时演员们所穿的服饰,其书“童舞”条载:“圣朝禁坊所传杂舞有舞童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卯童四人,作语一人,凡总七十一人,舞名有十焉……醉胡之舞衣红锦襦银䩞鞢毡帽”。((宋)陈旸:《乐书·俗部·童舞条》,卷一百八十四。)书中所谓的 “醉胡”实际上就是宋代的队舞——醉胡腾队。《宋史·乐志》的记载可以为之佐证,《宋史》“乐志十七”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䩞鞢,戴毡帽;……”(脱脱等著: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宋史》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
图9辽代“胡腾舞”拓片(高斯琦手绘)
马端临(1254—1323年)所修《文献通考》约成书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于泰定二年(1325年)付印。元人脱脱担纲编纂的《宋史·乐志》是从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开始修撰,故《文献通考》的成书时间显然早于《宋史·乐志》。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中关于唐代“健舞”与“软舞”的分类问题上,显然是参考了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一书。而《宋史·乐志》所载“醉胡腾队”则可能从马端临处做了借鉴。“队舞”至迟到唐代已经出现,唐代宫廷宴乐有《叹百年队》、《菩萨蛮队》,王建《宫词》中也有“春设殿前多队舞”句。宋代队舞是在唐代多段体歌舞套曲——大曲的基础上,加以诗歌、道白分成若干段落来表演的多场歌舞形式,具有一定的程式性和综合性。马端临等将胡腾舞纳入宋代队舞行列,名曰“醉胡腾队”,这一方面是因为该队舞是胡腾舞的续曲,另一方面,马氏依然以“醉”字为其命名,说明宋代“醉胡腾队”也与酒有很大关系。胡腾舞在中原地区历经魏晋隋唐的长期发展演变后,在表演程式上已经建立了明显的程式化规范与综合性套路。这一时期的胡腾舞已不再是单纯传情达意的舞蹈节目了,应是在胡腾舞的表演过程中添加了若干情节、歌曲、诗词等内容,并具有朗诵、对话、独白、歌与舞等多种表演角色的设置,所以,才会出现在“小儿队”中,由72人的庞大队伍来共同演绎。近人任半塘在其《唐戏弄》一书中详实的论述了胡腾舞与《西凉伎》二者互相穿插演绎的史实,任先生认为“胡腾歌舞戏系出《西凉伎》的前身”。(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明人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一书中载:“软舞曲垂手罗、兰陵王、回波乐、春莺啭、乌夜啼、半社渠、借席、凉州、屈柘枝、团乱旋、甘州、绿腰、苏合香;健舞曲拂林、黄章、柘枝、大渭州、达摩支、大杆阿连、阿辽、剑器、胡旋、胡腾儿出安西。珠帽、桐布衫、双靴,及手叉腰,应曲节舞。李端诗云:洛下词人抄曲与。知舞曲非一矣”。(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此处胡震亨也是誊传了前人关于胡腾舞的论述,又进一步指出胡腾舞的舞蹈与音乐并非出自一处。明末清初的孙永祚在其《雪屋文集》的第三卷中,记载了他在友人徐文虹家中观剧的情形。其诗《徐文虹斋观剧四章》其一言:
“十三小伶锁子骨,能行屏风靴踏壁。俳场一道不数尺,蹲蹲起舞应节拍。陡然险势疾飞翮,利刀短剑当头掷。一声扑地翻向空,座上寒毛如蝟磔。旋身未数胡腾儿,烛花暗飞红毯移。石国遗师至今在,不向君家那得知。”
由诗观之,自不必赘述“胡腾儿”与“石国” 所指何物,单就“十三小伶、靴踏壁、不数尺、应节拍、疾飞翮、翻向空、旋身未数”而言,生动活泼地“胡腾舞”形象便跃然纸上,可说是与李端、刘言史所描绘的“胡腾舞”同出一辙。尤其是“烛花暗飞红毯移”一句,与刘言史的“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句,更可看作是同一舞蹈场景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重演。“踏壁”、“行屏”、“飞翮”、“旋身”、“翻向空”也可看作是舞者多重空间的不断变换,而“陡然险势疾飞翮,利刀短剑当头掷”一句,这说明此时的“胡腾舞”中融入了大量的杂技成分。从全诗来看,此时“胡腾舞”技艺的精湛与高超程度绝不亚于唐代!但仍需注意的是,此时距离“胡腾舞”初传中原已逾1500多年,故笔者以为,关于此诗所描绘的“胡腾舞”真实性还有待作进一步考证。清人杨伦笺校注《杜诗镜铨》时,对“胡腾舞”做了些许载述,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一文中对“胡腾舞”有所旁涉,他引段安节《乐府杂录》将胡腾舞归之为“健舞”类。其文如下:“段安节《乐府杂录》: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82页。)巧合的是,清人仇占鳌和浦起龙也分别在《杜诗详注》与《杜诗心解》中,将胡腾舞列入“健舞”类。依此可鉴,在宋及宋以后的史料中,对于胡腾舞的记载多附旧说,少有新作。
结语
文献中有关胡腾舞的记载并不算多,但少量的史料依然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胡腾舞历史镜像。使我们能够透过静谧的文字来领略胡腾舞的千年余韵,那舞了千年的胡腾儿仿佛又在“跳身转毂”了。来自中亚石国的胡腾舞频频出现在豪门贵族的晚间宴会上,它非但舞风健朗,腾踏跳掷,而且还具有固定的表演结构与一定的情节性。其伴奏形式多以粟特乐队与粟特乐器为主,其间偶尔夹杂中原汉族乐器,亦有专人唱和与击掌为节的。胡腾儿通常头戴虚顶尖帽,脚踏长靴,腰系长带,身穿长袍,于舞筵之上起舞。而“小儿队”中的胡腾舞则不再是由一人独舞,而是由多名身着华丽的服饰的舞者共同在宫廷演绎。风靡一时的胡腾舞在给人带来视听之娱的同时,也以它那雄健洒脱的动律给中原舞风带来了改变。
本文载于《舞蹈》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刘洪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