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唯亭,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放得很慢,像在读一首旧诗——不必买一物,不必遇一人,只让卵弹石在脚下发出轻浅的回声,像是从前的人还在前头走,回头冲我笑一笑。巷口的红灯笼是旧年挂的,颜色褪了一半,却还在风里轻轻晃,像是要把年光晃回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圈,两圈,直至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仍舍不得离开。
老街的香味是极好的。那香味杂陈,有油炸糕饼的酥,有煮卤味的浓,有炒货的香,也有腌货的陈,甚至有谁家煤球炉上炖着的腌笃鲜,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汽,像是从瓦缝里钻出来的旧年魂灵。它们挤在一处,竟也不相冲,反倒融成一种独特的“年味”,像是谁家灶王爷调的一锅老汤,熬了百年,熬得连风都是软的。我每每行至此处,总要驻足深吸几口,像是要把那香味都吸进肚里去,藏进肺里,待日后在异乡的夜里,慢慢翻出来回味——像偷吃了一块母亲藏起来的糖,甜得不敢声张。
踱步的路线是固定的,像一条老狗认得的归家路。从东街起,经过乙未亭——那亭子早已没了匾额,只剩一个亭子和一块长碑记录着它的兴衰荣辱,像老人掉光牙后仍不肯闭的嘴,令人肃穆。走过状元桥,桥侧雕刻的“状元泾桥”四个字的笔画被数百年风雨打磨得光滑圆润,更有气韵。
路过粮管所,那扇铁门依旧半掩,像是从我小学那年就没再关严过。老照相馆的橱窗里,还摆着一张1987年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孩子如今也该四十出头了,不知他是否也回来看过。
不觉间就到了中街,中桥头就近在咫尺。我们有时会跨上中桥头,往下塘去玩。唯亭市镇以娄江为界,分南北两片。北片称“上塘”,住户聚集,有街市;南片称“下塘”,住户少,无街市,像是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那里最有名的是住着个刘少平的老中医,白眉白须,说话带着无锡口音。我七岁那年,脸上长了个疖子,母亲抱我去看他。他拿一把铰刀,在灯火上燎了燎,轻轻一划,再敷上自制的药膏,竟未留一丝疤。母亲连连称奇,他却只是摆摆手:“皮肉记得疼,就不记得丑了。”这句话我记到如今。
上塘的街市也称“唯亭老街”。中桥横跨娄江,把“上塘”、“下塘”联为一体,像一根磨得发亮的骨头,串起两截旧时光。街面全为侧铺卵弹石路,宽处四五米,窄处仅容两人擦肩。街分东、中、西三段,俗称“东横头”、“西横头”和“中街头”。中街头最热闹,年前尤为如此:卖春联的老先生把“福”字倒贴在摊前,像是要把一整年的好运都兜住;卖糖画的妇人手腕一抖,一条金龙便活过来,被孩子攥在手里,舍不得舔;还有卖气球的老头,气球是干瘪的,他一个一个吹起来,吹得腮帮子发红,像是要把最后的力气也吹进这年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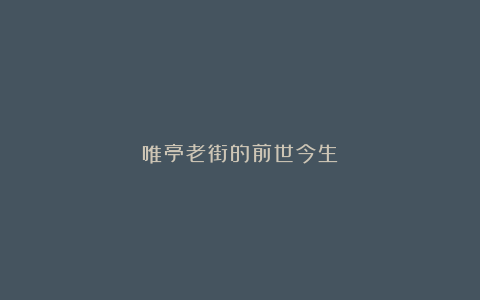
走过百货商店——那其实只是个两层小楼,楼下卖火柴、雪花膏、松紧带,楼上卖布匹,柜台后永远站着一个烫卷发的阿姨,指甲修得极好看——一直往西街走。穿过长长的廊棚,棚顶是旧瓦,漏光也漏雨,雨天走过,像走在一条水帘洞里。路过邮局,买一本当月的《少年文艺》,封面是水墨画,里头有篇《小船 小船》,我读了不下五遍。往金弄堂方向一路向北,过312国道汽车站、金埂岸——边上便是汪家坟,坟头早已平了,只剩几棵老柏,像几个不肯走的守墓人——再过小桥,便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是我幼时常嬉戏之处。偶有客运和运货列车慢吞吞驶过,汽笛长鸣,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叹息。我们便站在铁轨边,拼命挥手,仿佛那司机能看见我们,能把我们的呼唤带到远方。火车站北是泾上村,那里住着二姑家。二姑做的红糖糯米饭极好吃,上面撒一层金黄的桂花,甜得发腻。然而除了唯亭的外婆家,若无家长吩咐,我们是断不会擅自去亲戚家串门的。这规矩自我小时便立下了,至今犹存——像是某种古老的契约,不能破。
我们常踱到路灯初上。那灯是昏黄的,灯罩上积着一层油灰,像是谁家灶台搬上了天。光漏下来,把人影拉得老长,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另一个自己。巷子里飘来的菜香愈浓了,想是各家已在准备晚饭。那香味是极奇妙的,既有浓缩的调料气息——八角、桂皮、老抽、冰糖——又有食材本真的味道——鲫鱼、咸肉、春笋、雪菜——二者相安无事地融合在一处,竟不觉得冲突。记忆中的味道与我们农村的家常便饭是绝不一样的:老家的菜是“喂饱”,老街的菜是“款待”,连油花都开得比别处好看。
老街的声响亦是多样。有麻将牌相碰的零乱声,自某家窗户飘出,像是一阵急雨;有隐约的弹词开篇,自收音机中传来,女声婉转动听,唱的是《珍珠塔》,一句“方卿啊——”拖得老长,像是要把人的魂也勾走;间或还有半斤五加皮下肚后的高声谈笑,佐着一包花生米,那笑声是破的,却破得真诚,有点大小姐的脾气,穷瘪三的腔调,在这年节时分,竟也都显得可亲起来。连巷口那只总爱吠人的黄狗,今日也摇着尾巴,像是知道过年了,不便再凶。
踱上唯胜路,还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方能到家。然而父母从不因我们晚归而责骂——年节里,许是有些小出格也无妨的。母亲甚至会温一锅糯米酒,里头浮着几粒桂花,等我们回去喝。父亲则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头是暗红的,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他不说“回来了”,只说“冷不冷”,然后把棉袄往我身上一披,像披上一层旧年的月光。
此时常在傍晚,迷路的风裹挟着暧昧的光芒,再带着一点冬雨的湿漉。我心里飘满了满足感,像是一只盛满了热水的陶罐,一路晃,一路溢。慢慢地踱回家去,脚步轻得像猫,怕踩碎了这满地的年光。
唯亭老街不是景点,它是我童年的一块补丁,缝在心头最破的地方。年年回去,年年看它旧一点,也年年发现自己心里那块补丁,竟愈发结实了。然而有一天,唯亭老街搬迁的消息像一记闷棍,从《苏州日报》的角落砸进我眼眶:“唯亭老街整体征收,打造滨水智慧商业综合体,预计三年内完工。”我盯着那图,喉咙里泛起铁锈味,仿佛有人拿钝刀割我的补丁,线头一根根崩断,噗噗地,像极小时候过年时将小爆竹点燃后,扔在河里的炸声,呜咽而无助……
唯亭老街搬迁的消息铺天盖地,很快就进入了实施阶段,也拆掉了数代人的记忆。这里将崛起一条新的唯亭老街,给予新一代的唯亭人回想父辈曾经的生活……
万物生木公众号 25.9.11